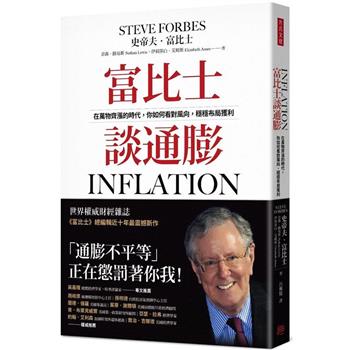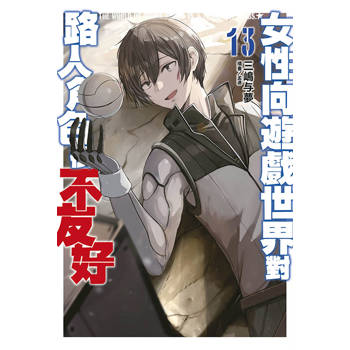我來重新建構中國神話的大廈完全是一種緣分。緣分始自童年。很小的時候,我便在奶奶的懷抱、
父母的膝頭聽神話了。盤古開天地、女媧補天、夸父追日以及後來因為政治因素而家喻戶曉的愚公移山等神話進入了我純真的感情天地,並以它那恆久的魅力滋養着我的身心靈魂。我後來拿起筆寫作與這些神話的哺育有着密切的關係。追憶我最早的寫作該是小學五年級時,在新年的爆竹聲裏,我伏在大炕上的窗台,在算術演抄本的背面寫下了一個劇本《神筆馬良》。當然,寫作的衝動是讀了洪汛濤先生的神話《神筆馬良》產生的。後來對我影響最大的該是《西遊記》了,雖然這部巨著現今被劃為四大古典長篇小說之列,但我一直固執地認為《西遊記》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它的神話色彩。也是在小學五年級我開始讀《西遊記》,孫悟空成了我心靈世界的第一巨人,僅《石猴出世》的美感就足以陶冶我一輩子。當然,兒時對神話的介入是不自覺的,有些甚至是被動的。自覺的、主動的進入神話領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了。那時我兼任了文物旅遊局長,這個角色的任務
很大,但當時選我赴任的首要工作是修復被大火焚燒後的堯廟。我所在的臨汾是堯都,堯都少不了有祭祀帝堯的廟宇。堯廟進入我的記憶就是一種破敗景象,到我上任前夕仍然是這般模樣。中間雖然曾經修復過快要倒塌的主殿,可惜這一舉措沒有持續下去。而且,那年一把大火燒毀的恰是修復過的這座主殿。主殿的焚毀讓不少人都在歎息:堯廟從此消失了!我所以組建這個局並出任局長,就是要讓眾人的失望變為希望。希望在一年的時間裏就實現了。堯廟修復了,重新巍然於世。這似乎是我年屆知天命時最大的收獲。其實,最大的收獲不是堯廟的重建,而是為了探求帝堯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給其做出恰如其分的定論,我一次又一次走進古籍史料, 當然也沒有忽略神話傳說,就這樣,我自覺進入了神話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我不僅感知帝堯,而且感知天地的誕生、演進,感知天地在誕生、演進中建立勛勞的那些創世英雄。經過一年多的閱讀、感悟、梳理, 這一切在我頭腦中形成了一個清晰的歷史文化鏈條,無疑,帝堯在其中所處的位置和對他的評價就一目了然了。似乎我的主動進入是為了帝堯,然而,我的收獲卻遠不止於帝堯,當我在《山海經》、《搜神記》等眾多的典籍中遨遊時,神話的豐姿又一次向我展示了它那迷人的風景。也就是在這個探求過程中, 我發現神話也需要成長。產生這個想法是基於兩點認識:一是古典神話由於其時傳播手法的局限都很瘦韌。雖然這種瘦韌沒有影響其風骨,但是卻影響在更大讀者範圍中傳播;二是對於
這些古典神話白話化的作品和民間流傳的神話,由於缺少文學家的傾心構製, 多數都龐雜臃腫。當然, 也不可否認中國現代作家在神話天地中尋寶擷珠的不少,魯迅、茅盾都曾涉獵, 而且魯迅還以神話素材寫過小說《故事新編》。只是,那已經成了個人情緒化了的小說,有別於神話的初衷。由於這兩點認識,我以為神話仍然停留在很久前定位的一個平台上,說句時尚話就是亟待與時俱進。因此,我在為神話感動時,也為神話惋惜。不過,此時卻還沒有試筆補天的妄想。如今,經過幾個月的勞作,我就要擱筆了,當然,還有很大的修改任務,但比之一稿寫作是要輕省多了。回首寫過的文字, 我不敢說將瘦韌的豐滿了, 將龐雜的凝煉了,但至少說我是奔這個目標來的。由於時間短暫,由於是給少年兒童寫作,語言也就盡量淺白明曉。這樣的目的是否達到,則需要讀者和偶或讀到此書的專家、學者批評指教了。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中國經典系列叢書:中國神話的圖書 |
 |
中國經典系列叢書:中國神話 作者:喬忠延 編 出版日期:2023-11-3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41 |
中文書 |
$ 441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490 |
中國古典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經典系列叢書:中國神話
《中國經典系列叢書:中國神話》共有30多個神話主題,源於尚書、國語、山海經、楚辭、列子、太平廣記等歷代典籍,與各地府志縣志或口耳相傳的民間傳說,題材多元。每篇故事皆有作者手記解釋故事來源,亦包括聞一多等著名神話學者研究成果,有助掌握神話出處。
作者簡介:
編者簡介
喬忠延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已出版散文集等專著二十多部,曾獲得趙樹理文學獎、冰心兒童圖書獎與冰心散文優秀獎。
作者序
我來重新建構中國神話的大廈完全是一種緣分。緣分始自童年。很小的時候,我便在奶奶的懷抱、
父母的膝頭聽神話了。盤古開天地、女媧補天、夸父追日以及後來因為政治因素而家喻戶曉的愚公移山等神話進入了我純真的感情天地,並以它那恆久的魅力滋養着我的身心靈魂。我後來拿起筆寫作與這些神話的哺育有着密切的關係。追憶我最早的寫作該是小學五年級時,在新年的爆竹聲裏,我伏在大炕上的窗台,在算術演抄本的背面寫下了一個劇本《神筆馬良》。當然,寫作的衝動是讀了洪汛濤先生的神話《神筆馬良》產生的。後來對我影響最大的該是《西遊記》了...
父母的膝頭聽神話了。盤古開天地、女媧補天、夸父追日以及後來因為政治因素而家喻戶曉的愚公移山等神話進入了我純真的感情天地,並以它那恆久的魅力滋養着我的身心靈魂。我後來拿起筆寫作與這些神話的哺育有着密切的關係。追憶我最早的寫作該是小學五年級時,在新年的爆竹聲裏,我伏在大炕上的窗台,在算術演抄本的背面寫下了一個劇本《神筆馬良》。當然,寫作的衝動是讀了洪汛濤先生的神話《神筆馬良》產生的。後來對我影響最大的該是《西遊記》了...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盤古開天闢地 004
女媧造人畜 011
女媧補天 016
神奇的布洛陀 022
伏羲教民捕魚 032
九天神女下凡塵 038
神農嚐百草 059
風後生捨身救民 065
倉頡造字 070
黃帝平定天下 076
堯天舜日 101
射日英雄后羿 132
大禹治水 149
布伯鬥雷王 167
山民娶神女 175
精衞填東海 187
神女瑤姬 191
李冰斬蛟治水 198
少年郎築城牆 203
給帝王養龍的人 207
周穆王奇遇 215
狼煙烽火看笑顏 223
懂鳥語的公冶長 229
楚王鑄劍 234
孟姜女哭倒長城 242
相思樹 250
柳毅傳書結良緣 255
小長工和大財主 262
虎斑花仙 268
粉嘟嘟的白蓮花 273
翠微娘子 279
幸運的...
女媧造人畜 011
女媧補天 016
神奇的布洛陀 022
伏羲教民捕魚 032
九天神女下凡塵 038
神農嚐百草 059
風後生捨身救民 065
倉頡造字 070
黃帝平定天下 076
堯天舜日 101
射日英雄后羿 132
大禹治水 149
布伯鬥雷王 167
山民娶神女 175
精衞填東海 187
神女瑤姬 191
李冰斬蛟治水 198
少年郎築城牆 203
給帝王養龍的人 207
周穆王奇遇 215
狼煙烽火看笑顏 223
懂鳥語的公冶長 229
楚王鑄劍 234
孟姜女哭倒長城 242
相思樹 250
柳毅傳書結良緣 255
小長工和大財主 262
虎斑花仙 268
粉嘟嘟的白蓮花 273
翠微娘子 279
幸運的...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