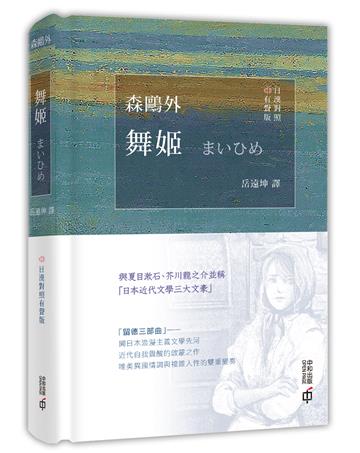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森鷗外是與夏目漱石並肩的文學家,兩人並稱為明治文學的「雙峰」。他的文學創作開啟了日本近代浪漫主義文學的先河,而他對歐洲浪漫主義文學作品的翻譯與文藝思潮的介紹,則對整個日本近現代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森鷗外原名森林太郎,生於江戶時代末期(1862年)的藩醫世家,是森家招了幾代入贅女婿後誕下的長子。在深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封建家庭裡,森鷗外作為長子自幼被寄予了繼承家業的厚望。他自幼熟讀四書五經,五歲開始讀《論語》和《孟子》,七歲進入藩校系統地學習漢學和國學,八歲開始跟父親學習荷蘭語,十歲時到東京學習德語,十一歲進入醫學校預科(東京大學醫學部的前身)學習,十五歲考入東京大學醫學部,十九歲即從東京大學醫學部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其後作為軍醫任職於陸軍省,三年後夙願以償,奉官命前往德國學習西洋醫學並考察西方的衞生制度,此後在柏林度過了將近四年的時光。他根據這段時間在柏林學習和生活的親身經歷或所見所聞,回國後業餘創作並發表了《舞姬》《泡沫記》和《信使》這三部具有濃厚浪漫主義傾向的作品。這三部作品在日本文學史上被稱為森鷗外文學的「留德三部曲」(又被稱為「浪漫三部曲」)。
《舞姬》以第一人稱的方式講述了「我」(太田豐太郎)奉官命遠赴德國留學,在柏林的陋巷遇到出身貧賤的芭蕾舞者愛麗絲,與之相愛最後卻將其拋棄的悲劇愛情故事。在對豐太郎的描寫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詞,那就是「好友」相澤謙吉所說的「軟弱」。但必須注意的是,「我」在說到自己的時候,也常常使用「軟弱」這個詞。然而,稍微注意便不難發現,相澤謙吉站在外部所說的「軟弱」,與敘述者「我」說起自己時所說的「軟弱」,其內涵從根本上是不同的。相澤所說的軟弱,指的是男主人公內心不夠強大,不足以抵抗外在的誘惑(慾望);而男主人公口中的「軟弱」或「怯懦」,則是無法忠實於內心的「情」,不敢抵抗道德共同體的約束。而這樣的敘述,可以說是源自中國朱子學與陽明學對於「情」與「理」態度的不同,也是明末以降才子佳人類型小說及受中國晚明主情主義文學思潮影響的日本近世小說的一種敘事傳統。
另外,從結構上來說,《舞姬》的創作也受到中國傳奇小說的影響,尤其是由於《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與《舞姬》在故事情節上的相似性,引起了中日兩國學者的關注,成為中日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熱門個案。而從細節上來說,自幼熟讀漢文的森鷗外在《舞姬》的創作中充分發揮了他的漢學功底,散見於細節處的大量漢文典故是解讀《舞姬》時不可忽略的重要線索。
《舞姬》是作者根據自身的經歷創作的,向來被認為是一部具有自傳性質的短篇小說。而在現實中,森鷗外從德國回國後,正如文中的愛麗絲所說,「和母親一起去,倒也簡單」,的確有一位與愛麗絲同名的德國女性曾帶着母親一起去找森鷗外,然而以森鷗外的母親為代表的家族如臨大敵。他們火速為森鷗外安排了一樁門當戶對的親事,森鷗外因此迎來了他第一次短暫的婚姻。有一種說法認為,在「留德三部曲」中,森鷗外最先執筆創作的是《泡沫記》,但他卻選擇了首先發表《舞姬》,是對母親的一種宣戰。這種說法是否屬實暫且不論,但就作品本身來說,豐太郎拋棄愛麗絲發生在母親去世之後,當時已經沒有母親的阻撓。雖然也有學者認為作品中的母親是出於悲憤而「自殺」,而那封讓主人公淚眼凝噎的信乃是以死相逼的勸諫信。若是如此,「我」在當時就應該選擇與愛麗絲分手,但實際上「我」卻並沒有因為母親的死而馬上疏遠愛麗絲。「我們」的關係在那之前,「比外人想像的都要清白」,而在此之後才變得「難捨難分」。「母親去世」這個情節的設定可以說是有意設置了母親這個角色的缺位。在母親和家族的羈絆並不存在的情況下,豐太郎選擇了回歸仕途,拋棄愛麗絲,表明他的選擇並非完全迫於儒家倫理的約束和封建的體制。作者是通過這樣的書寫,揭露了更深層的人性自私與懦弱。豐太郎在彷徨與猶豫中選擇了自己認為更光明更有利於自己未來的道路,正如小說中所說:「若不抓住這次機會,我將失去故國,斷了挽回名譽的途徑,葬身於歐洲大都市的茫茫人海之中。」
因此,《舞姬》最重要的一個主題與其說是對封建制度與儒家道德提出的挑戰和反叛,是近代自我的覺醒,不如說是對複雜人性本身的深刻剖析。正因如此,小說開頭的那句話對於解讀這篇小說又顯得格外重要,即「領悟到人心的叵測,別人自不必說,就是我和我的心,也是變幻無常」。在作品中雖然有對同鄉的抨擊,但這並非作者着墨的重點和批判的主要對象,大部分篇幅實際上是在敘述「我」內心的「變幻無常」與「難測」。這種對自我的內面剖析與書寫,才是《舞姬》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里程碑意義之所在。
與《舞姬》相比,《泡沫記》具有更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作者巧妙地利用了德國歷史上的千古謎團「路德維希二世之死」,加上作者出色的想像力,虛實交錯,講述了日本畫家巨勢和「賣花姑娘」瑪麗的愛情故事。雖然結局令人扼腕歎息,但對拋卻一切世俗羈絆的男女主人公浪漫激情的書寫卻讓人讀了感覺酣暢淋漓。這部作品之所以具有更加濃厚的浪漫主義傾向,在於其塑造了不拘一格的「狂女」形象。可以說「狂」是理解這篇小說的關鍵詞,也是歷來論及這篇小說的重要切入點。小說中有關「狂」的這些思想,當然是來自於當時西歐文藝思潮的影響,另一方面,譯者認為與中國晚明的陽明學思想也有着相通之處。如在陽明學及其左派的思想中,「狂」被認為是理想人格的體現,是通往「聖」的必經之路。或說「聖狂一體」,與小說中瑪麗的神(巴伐利亞女神)、人(賣花姑娘)、妖(羅蕾萊)三面一體的形象塑造,以及瑪麗口中的對「狂」的議論,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信使》是三部作品中故事情節較弱而敘事技巧卻最為巧妙的一篇。青年軍官小林作為故事的旁觀者,向在場的日本貴族講述了自己在德國參加軍事演習時的所見所聞,塑造了一個清新脫俗的女性形象(伊妲公主)和一個追求她的「兔唇」癡情男孩(牧羊人)。其中無論是伊妲的「黑衣」、夢中體現的獅面人身,還是牧羊人的「兔唇」,都是一種「畸」的表現。在中國晚明和日本近世,很多人動輒自稱「畸人」,這裡的「畸」與「狂」一樣,被視為理想人格的體現,象徵着自我的發現與人性的解放。另一方面,作者也通過伊妲公主對軍官小林的長段自白,揭露了近代歐洲具有明顯階層性質的個人解放和所謂「自由」的虛偽本質。
「留德三部曲」是森鷗外文學的起點,同時也可以說是對其自身青春時代的謳歌與祭奠。《舞姬》通過告白體的書寫,將遠去的青春客體化,為自己的青春畫上了一個終止符;《泡沫記》盡情謳歌了男女主人公放蕩不羈的青春與愛情;《信使》則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對青春遠逝的哀悼,尤其是最後一段的描寫,加入宮差隊伍中的公主在敘述者的視線中漸行漸遠,以至於最後「偶爾在人們的肩膀之間瞥見她那身淺藍色的漂亮禮服」,盡顯青春落幕的哀傷與惆悵,同時象徵着作為個體的人淹沒於歷史的長河中。
此後十幾年,送別了青春激情的森鷗外開始專注於軍醫的公務,幾乎中斷了文學創作,而當他再次執筆正式開始創作時,又以一種全新的創作方式開啟了新的創作巔峰。這一時期的作品中書寫的不是青春的浪漫、激情或哀傷,而更多的是對歷史的深邃思考。《高瀨舟》《山椒大夫》和《阿部一族》都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代表作。此乃後話,不再贅述。
作為日本第一批接觸西方社會的知識分子,森鷗外不僅具有深厚的漢文功底,而且精通德國文學。以留德經歷為素材創作的這三部小說,正如他給幾個孩子取的名字(如長子「於菟」的名字)那樣,綜合運用了日本、中國和西方的各種元素。只有在深入理解中日古典文學和德國文學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作品的深度與廣度。
以上是對森鷗外及其三部短篇作品的簡單介紹,更為細節的部分則以腳註的形式體現在譯文的頁面下方,僅供參考。其中無論是解讀還是註釋,《舞姬》都較為詳細,而另外兩篇則稍顯簡略,但願這些簡單的介紹能對年輕讀者的理解有所幫助和啟發,乃至產生一些共鳴。
岳遠坤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舞姬 (日漢對照有聲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48 |
日本文學 |
$ 348 |
日本文學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日本古典 |
$ 396 |
日本文學 |
$ 396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舞姬 (日漢對照有聲版)
與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並稱 「日本近代文學三大文豪」
「留德三部曲」⸺ 開日本浪漫主義文學先河 近代自我覺醒的啟蒙之作 唯美異國情調與複雜人性的雙重變奏
「雖仍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可我卻體會了浮世的艱辛,領悟到人心的叵測,別人自不必說,就是我和我的心,也是變幻無常的……」
日本近代文學巨匠森鷗外最負盛名的「留德三部曲」⸺《舞姬》《泡沫記》《信使》,以留學德國經歷為素材傾情創作。充滿激情與哀傷的異國愛情故事之下,是對人性內面的深度剖析,和對西渡青春時代的不捨告別。細膩抒情的文筆,揭示置身異域的敏感而矛盾的內心,自我意識覺醒與現實挫折的交鋒中,他將選擇反抗還是妥協?
書中日文部分全文標註假名,日漢對照,附贈日文全文朗讀音頻,有助日語學習,豐富閱讀體驗。
作者簡介:
森鷗外(もり, おうがい)
1862—1922,日本醫生、藥劑師、小說家、評論家、翻譯家,是日本浪漫主義文學的開創者,與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齊名,被譽為日本近代文學三大文豪,與夏目漱石並稱為日本近代文學上的「雙璧」。本名森林太郎,自幼受武士道德教育,通習漢學經典。1881年畢業於東京大學醫學部,成為陸軍軍醫。奉命留德,專攻衛生學。四年的留學生活,對他的思想影響極大。歸國後開始從事外國文學翻譯、小說創作等文學活動,成為日本近代歷史變遷文化轉型重要時期的一個啟蒙主義者。代表作有《舞姬》《泡沫記》《信使》《雁》《阿部一家》《高瀨舟》等。
譯者簡介:
岳遠坤
北京大學日語系助理教授,碩士生導師,曾獲「第十八屆野間文藝翻譯獎」。譯有《德川家康》《起風了》《怒》《田園的憂鬱》等日本文學作品20餘部。
章節試閱
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森鷗外是與夏目漱石並肩的文學家,兩人並稱為明治文學的「雙峰」。他的文學創作開啟了日本近代浪漫主義文學的先河,而他對歐洲浪漫主義文學作品的翻譯與文藝思潮的介紹,則對整個日本近現代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森鷗外原名森林太郎,生於江戶時代末期(1862年)的藩醫世家,是森家招了幾代入贅女婿後誕下的長子。在深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封建家庭裡,森鷗外作為長子自幼被寄予了繼承家業的厚望。他自幼熟讀四書五經,五歲開始讀《論語》和《孟子》,七歲進入藩校系統地學習漢學和國學,八歲開始跟父親學習荷蘭語...
森鷗外原名森林太郎,生於江戶時代末期(1862年)的藩醫世家,是森家招了幾代入贅女婿後誕下的長子。在深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封建家庭裡,森鷗外作為長子自幼被寄予了繼承家業的厚望。他自幼熟讀四書五經,五歲開始讀《論語》和《孟子》,七歲進入藩校系統地學習漢學和國學,八歲開始跟父親學習荷蘭語...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舞姫 002
舞姬 003
うたかたの記 072
泡沫記 073
文づかひ 138
信使 139
舞姬 003
うたかたの記 072
泡沫記 073
文づかひ 138
信使 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