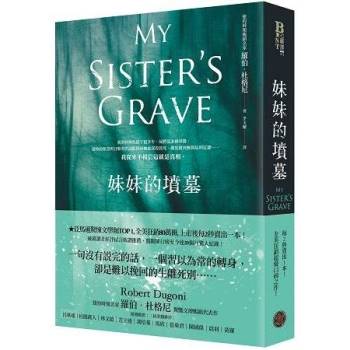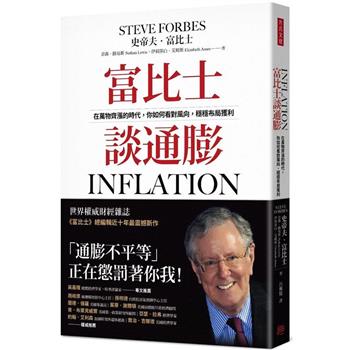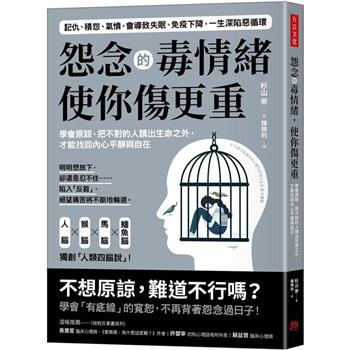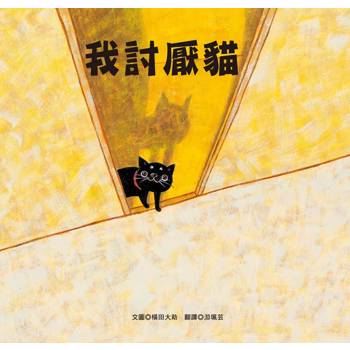前言(節錄)
本書可以視作一部另類的蕭紅傳記。不同於以生平為中心的常規結撰方式,本書採用了一種相當「冒險」的寫法:對蕭紅作品的分析被放置在中心位置,構成了串連本書的核心線索。
這是因為蕭紅的生平經歷早已為公眾所熟知。據不完全統計,從駱賓基《蕭紅小傳》(1947)算起,蕭紅傳記已有上百部。可一提起這位作家,人們往往談及的是她作為「文學洛神」的不幸遭遇,抑或是幾段不盡如人意的感情生活。這些苦難故事與花邊文學,早已衍生成為無數版本,而且飽含爭議。事件的當事人各執一詞,早逝的蕭紅處在風暴眼,是沉默的中心。
蕭紅成長與生活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時代。倘以常情揣度她的生平經歷,大概只能獲得一個簡單的刻板印象:「文學洛神」、早逝的天才、無助的女人、被時代耽誤了的作家;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是圍繞在蕭紅身邊的三個男人,感情裏的負心人。類似話語不斷沉澱,造就了今日蕭紅形象的單純。2014年,由李薔編劇,許鞍華導演的電影《黃金時代》採用擬紀錄片手法,有意突破,可形式的複雜仍未改變全片敘事邏輯的簡單。在這部影片中,蕭紅仍為感情所定義,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三人又被蕭紅所定義,他們精彩的生命經驗在既定的敘事模式下收縮成為一則女性向時代的柔弱控訴,至於「女性」與「時代」的具體意涵,則是被抽空了的。
一方面無限逼近作家個體,甚至是私生活的海量細節,一方面卻是驚人簡單的形象與認知,蕭紅的傳記似乎最為顯豁地呈現出「傳記」文體的不可信性—─一個人的生命經驗是可以再現的嗎?我們能夠依賴生命碎片去定義人的一生嗎?更具體而言,如果說「傳記」的預設是依賴細節紡織出作家生命作品的「整體」,那這個任務是有可能達成的嗎?
而在蕭紅這裏,更耐人尋味的是:傳記作者們所仰賴的「細節」,不是出自同時代人的回憶文字,就是源於蕭紅自己的作品。這與蕭紅創作的「自傳性」高度相關,如果沒有這些文學作品,今日的傳記作者甚至無法獲得如此詳盡的生平材料。可傳記作者們又似乎把這些作品想像為太過透明的文本,這種對文本的處理方式未免有些「粗暴」。轟毀形式的圍欄,我們終於在歷史的縫隙裏找尋到了蕭紅,卻是與「文
學」無關的。
我想這可能是因為我們都忽略了「文學」的緣故。蕭紅幼年喪母,青年逃婚,孕中被棄,意外獲救後走上文學道路。她先後流徙在哈爾濱、青島、上海、武漢、重慶與香港,經歷國恨家難,飽受病痛折磨,在短短十年時間裏,留下了近百萬字的作品。這些創作大都具有自傳性,寫作與她的生命經驗纏繞交織。從哈爾濱、上海到香港,她的視野一步步擴大,蕭紅憑藉寫作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憑藉寫作面對並回應着愈來愈為廣大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寫作構成了她消化個人創傷,梳理自身與時代關係,回應社會問題的手段。這些作品忠實地記錄了她的思想痕跡,也是最為一手的精神史材料。拋開作品,蕭紅的一生也變得乏善可陳。
本書提出「寫作者蕭紅」這一概念,就是希望重新喚回「寫作」行為的第一性。「蕭紅」首先是一個文學存在,寫作者的生活只能經由寫作來證明。因此,本書有意採取一種相當冒險的寫法,希望回歸形式批評,以文本細讀為中心,由此寫出一部「文學」的傳記。筆者相信,相較於外部材料,只有從文學作品的形式中破獲那些凝結在歷史中的慾望與願望。打開形式,才能抵達最為內在的真實。文學研究者蔣暉曾精闢指出:「形式是以藝術手段表現出來的內容,是使一部作品得以自我確立的精神實體。一件作品的形式說到底就是這件作品和世界的根本關係。作品通過形式言說世界,人的意識對存在整體的把握通過形式而凝固下來」。形式「關係着作家以甚麼樣的方式進入和理解世界,他的藝術的政治性、倫理性都根基於此」。尊重文學的形式自律性,重新回到文學,或許很多問題在蕭紅那裏早就有了答案,不過是以文學的名義保存。
從一無所有的逃婚女人成為文壇著名的青年作家,寫作改變了蕭紅的一生。文字對蕭紅來說,不僅僅是記錄,更是創造,是思索,是激發。魯迅曾高度評價蕭紅有「越軌的筆致」,這從她初入文壇伊始就有淋漓盡致的展現。蕭紅始終是一位有着濃郁個人風格的作家。今日為研究者津津樂道的「兒童視角」、性別化敘事與日常生活敘事,都是蕭紅看待世界的眼光。追蹤它們在文本中緩慢的生長過程,有助於我們把握蕭紅生命經驗中的變與不變。而作為一位願意反覆書寫記憶的作家,記憶對於蕭紅而言有着相當特殊的意義。對記憶的重複書寫,意味着蕭紅在變動不居的世界裏找尋自己存世的依據。在這個意義上,蕭紅的創作相當「耐讀」,因為她真正做到了用文學思考,又保有了對文字的忠實。她在文學中保留了她的痛苦、不安與對種種情緒的克服,將她的作品串連在一起,彷彿可以形成一條療癒自我、回應時代的思想軌轍。而由粗糙到精良,從借助理論的腳手架到鍛造出個人的意義尺度,這或許正是「寫作者蕭紅」的核心含義,也是蕭紅留給今日寫作者的財富:不斷寫下去,迎着時代的風。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跋涉:蕭紅的哈滬港行記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跋涉:蕭紅的哈滬港行記
本書可以視作一部另類的蕭紅傳記,重新從文本細讀出發,審視蕭紅的文學身份。坊間論調
常把焦點放在她的感情關係,把作品視作窺探私生活的材料,忽略她在寫作上的自主性和時代背景,包括與左翼理論的聯繫。全書集中以蕭紅在哈爾濱與上海的創作經歷為線,揭示她以文學尋求自我的歷程,探研背後回應的時代脈動。
閱讀蕭紅:一部另類蕭紅傳記
文本細讀:重文本細讀,回歸文學身份
兩地經歷:重哈爾濱與上海文學經歷
作者簡介: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方向博士,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聯合培養博士生(2022-2023),獲北京大學中文系學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左翼文學研究、東北文學與文化研究,關注中國新詩史與當代詩歌批評,也從事胡適海外佚信的蒐集與整理工作。博士論文為《跨域流動中的文學與政治—重繪「東北作家群」的認知地圖(1931-1948)》,獲北京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2023)。
作者序
前言(節錄)
本書可以視作一部另類的蕭紅傳記。不同於以生平為中心的常規結撰方式,本書採用了一種相當「冒險」的寫法:對蕭紅作品的分析被放置在中心位置,構成了串連本書的核心線索。
這是因為蕭紅的生平經歷早已為公眾所熟知。據不完全統計,從駱賓基《蕭紅小傳》(1947)算起,蕭紅傳記已有上百部。可一提起這位作家,人們往往談及的是她作為「文學洛神」的不幸遭遇,抑或是幾段不盡如人意的感情生活。這些苦難故事與花邊文學,早已衍生成為無數版本,而且飽含爭議。事件的當事人各執一詞,早逝的蕭紅處在風暴眼,是沉默的中心。
蕭紅...
本書可以視作一部另類的蕭紅傳記。不同於以生平為中心的常規結撰方式,本書採用了一種相當「冒險」的寫法:對蕭紅作品的分析被放置在中心位置,構成了串連本書的核心線索。
這是因為蕭紅的生平經歷早已為公眾所熟知。據不完全統計,從駱賓基《蕭紅小傳》(1947)算起,蕭紅傳記已有上百部。可一提起這位作家,人們往往談及的是她作為「文學洛神」的不幸遭遇,抑或是幾段不盡如人意的感情生活。這些苦難故事與花邊文學,早已衍生成為無數版本,而且飽含爭議。事件的當事人各執一詞,早逝的蕭紅處在風暴眼,是沉默的中心。
蕭紅...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創系十週年叢書總序
前言
第一章 哈爾濱
「春天到了」
記憶的形體
套盒裏的「瘡疤」
「學說」的意義
生存在「人林」
草垛旁的「瘋」女人
第二章
上海
匯聚上海
「九.一八」的年盤
上海的「義軍」
「牛車上」的女孩
重述商市街
「黃金時代」的夜
餘論
前言
第一章 哈爾濱
「春天到了」
記憶的形體
套盒裏的「瘡疤」
「學說」的意義
生存在「人林」
草垛旁的「瘋」女人
第二章
上海
匯聚上海
「九.一八」的年盤
上海的「義軍」
「牛車上」的女孩
重述商市街
「黃金時代」的夜
餘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