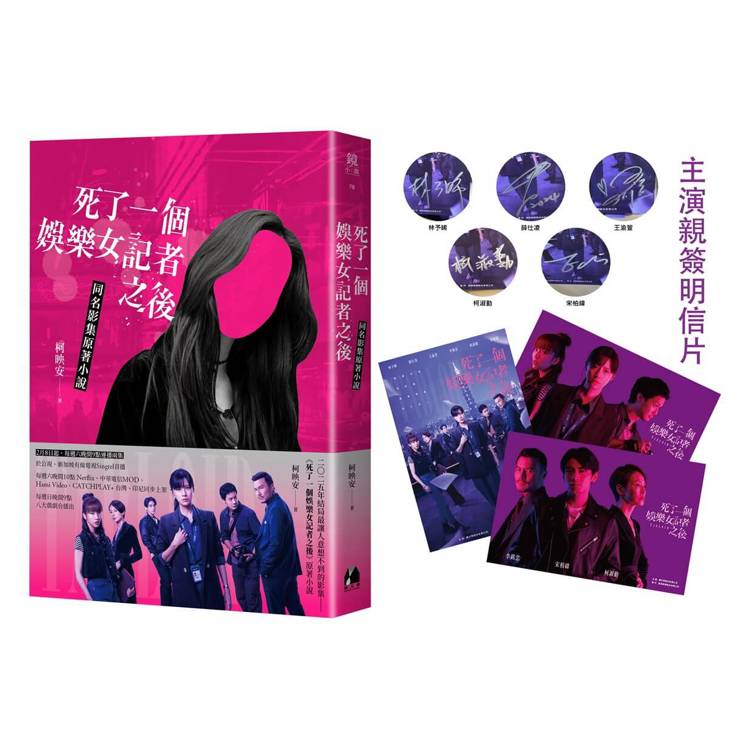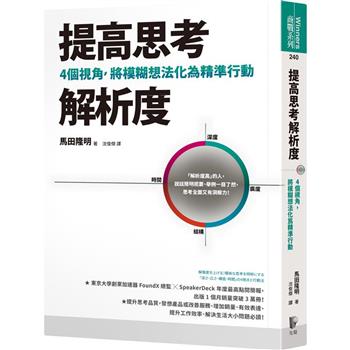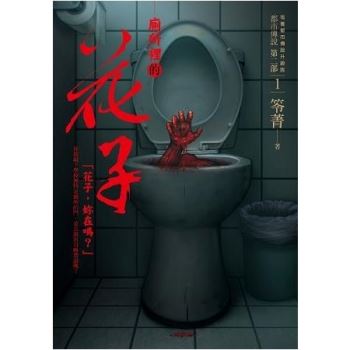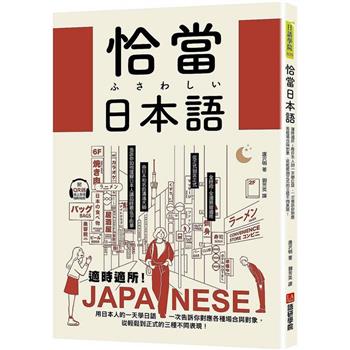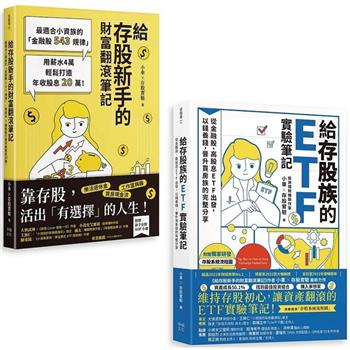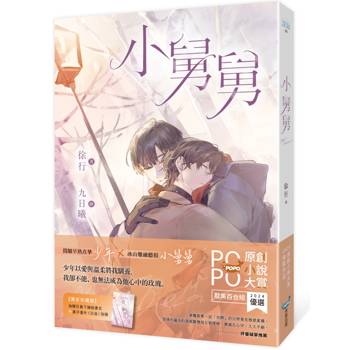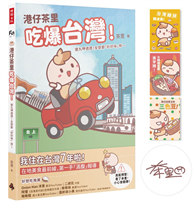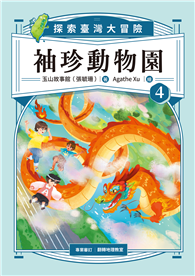★2025年最具懸疑感的同名影集原著小說,2月8日起每週六晚間9點連播兩集,於公視、新加坡有線電視Singtel首播;每週六晚間10點,Netflix、中華電信MOD、Hami Video、CATCHPLAY+ 台灣、印尼同步上架;每週日晚間9點,八大戲劇台播出。
★鏡文學傾力開發,打造臺版娛樂新聞圈的《紙牌屋》」!
★勇於碰觸「娛樂圈潛規則」與「新聞白手套」的禁忌話題!翻開本書,會勾起你不由自主找人對號入座的衝動!
★本款贈送《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同名影集明星酷卡明信片一組三張,其中主視覺酷卡由五位主演林予晞、薛仕凌、王渝萱、柯淑勤、宋柏緯隨機一位簽名!
看到「美女記者賣淫慘死毒趴」頭條,
你好奇的,是什麼版本的真相?
人人都愛桃色八卦,
虛華的表象只為掩蓋真實的腐臭!
娛樂圈潛規則:每個女孩都有身價。
但當事不關己,又有誰真的在意?
新聞若是項利器,該用來防衛自保?交換利益?
或是奮不顧身地贖罪?
八卦週刊娛樂女記者劉知君,因工作過度陷入昏睡,
錯過了同事林姵亭命喪酒店性愛毒趴前,最後傳來的求救訊息。
大家說,姵亭是用身體交換新聞、甚至金錢的虛榮妖女,
但她不信。知君想贖罪,想追蹤真相。
同事、恩師、上司,有誰能幫她一把?誰又能夠信任?
而她自己的懺悔心與正義感,又摻著多少野心?
大家都笑娛樂新聞難登大雅之堂。
知君偏不死心,想挑戰那條不可見的界線:新聞豈有高尚、低俗之分?
當她毅然起步,才發現贖罪之途竟是姵亭的舊路──假賣淫、真臥底。
正義女神與落難天使,哪一個才是她的身分?
她能否追尋到自己想要的真相?或者真相,不過是真與假的無解迷思?
專文推薦►
馬欣 作家
李桐豪 退役娛樂記者
娛樂重磅推薦►
隋棠 知名演員
謝盈萱 金馬演員
海裕芬 主持人/演員/製作人
膝關節 臺灣影評人協會理事長
關韶文 娛樂記者/節目主持人
徐佑德 娛樂重擊副總編輯
馬欣|作家
「被這娛樂場子內化了的人,極盡所能想把這圈子的妖怪現形,哪知在她們追新聞時,也對映出了自己心頭的那些鬼火。」
李桐豪|退役娛樂記者
「我們都愛娛樂新聞,為了生計,也為了心中某個情感的核心。…… 一張張娛樂新聞報紙是華美的壁紙糊在蒼白空洞的人生版面上。」
膝關節|臺灣影評人協會理事長
「相當具有寫實度的媒體描繪(至少我也在報社七、八年,對影劇新聞運作有一定熟悉度),帶領一般觀眾理解媒體水深火熱的悲慘截稿輪迴。如此聳動的書名標題,呈現茶餘飯後的影劇新聞也可以變成奪人性命的社會新聞。」
海裕芬|主持人/演員/製作人
「『記者』,多有使命感的身分啊!為了別人的難題奮不顧身、為了別人的愛情喜不自禁、為了別人的家庭夜不成眠。『記者』,多有責任感的身分啊!以為讀者都想知道就揭露、以為社會都有興趣就曝光、以為群眾都可公評就定論。『記者』,多有正義感的身分啊!不符合普世的標準就點名、不容於世俗的眼光就標記、不正視媒體的報導就負評!『記者』!真是彰顯了公義?!還是被勢力左右了輿論風向?生活周遭充斥著監視器,卻不代表眼見為憑!非得《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才發現原來根本摸不透遊戲規則,能被撰寫出來的永遠不可能是全部的真相。這本書,有多少是為求娛樂而杜撰、有多少是為求公理而真實、有多少是為求避嫌而改編,身為讀者,反正我是信了!」
#女星花名冊/豔照門事件
#影視圈潛規則/名氣都是睡出來的
#當代仇女百態:蕩婦/淫女/母豬
#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妓者快來抄
→標籤永遠不嫌多!未審先判就是大家的正義?
作者簡介:
柯映安
柯映安,創作內容包括影視劇本、漫畫劇本、小說。 創作內容涵蓋愛情、喜劇、奇幻等,編劇作品獲得數項獎補助,包含:拍臺北劇本首獎、電影優良劇本獎優等。分別以劇集《動物園》、電影《旺的Girl》入選金馬創投會議。近期影劇作品有《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彈一場完美戀愛》 ,並著有同名小說《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和《權力製造》。
鏡文學作者專頁|https://www.mirrorfiction.com/zh-Hant/writer/80807
章節試閱
楔子
身為一個娛樂記者,習慣躲在文字身後的劉知君沒有想過,有一天,她也會捲入風暴中心,受萬千視線所監視,動輒得咎,一步一步越走越錯,終至無法自拔。
所有事情的開端,抑或說是「禍端」,應回溯到許多個日子以前,那一個殺機暗伏的寒冬說起。
第一章
林姵亭死前最後一個往外發送的求救訊息,安安靜靜地躺在劉知君的手機內。
那是一個年節過後的夜晚。
在八卦週刊擔任娛樂記者的劉知君,硬生生扛了兩期的封面題目之後,總算能夠在午夜以前回家,並且好好睡超過五個小時。這並非能者多勞,純粹是被趁機揩油,讓其他人能輕鬆過年而已,但她並不在乎,反正舉凡大小節日,只要打著團圓的名號,她都非常反感。
這天晚上,她踩著虛浮的步伐,走過臺北雨後潮濕昏暗的小巷,再舉步維艱地踏上狹窄逼仄的老公寓樓梯,一路直上頂樓加蓋的六樓套房。
大學以後,劉知君從中部某個偏僻的西部沿岸漁村來到臺北生活,日子在大學破敗漏水的宿舍、房東違建隔起的雅房中度過。當年,剛剛出社會的她,背負著學貸跟母親龐大的債務,領著初入社會微薄的薪水,住在一個潮濕的地下室雅房當中,唯一的對外窗是鑲嵌在牆壁上緣的氣窗,那氣窗甚至沒有比一個餅乾盒子大多少。
那段時間,每天下班後,她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躺在床上,表情麻木地盯著那扇隱隱透出街燈的氣窗看。記者這工作必須時刻與人群打交道,導致回家之後,只剩下自己一個人時,心裡有了極大的寂寞反差。
氣窗外照進來的街光、或是行車經過時,捲上牆壁的影子及走動聲,這些對一個獨自在外打拚、毫無家庭後援的女孩子來說,全是微不足道但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
那時,她依靠隔音差勁的隔房動靜、氣窗外偶爾經過的各種噪音維生。唯有這些聲音還在,她才有辦法入睡。現在的她,經濟狀況比較寬裕了,於是搬到這間頂樓加蓋的套房,隔音依然相當差勁,但隔壁的人聲依然是促使她入睡的催眠良曲。
出社會後那個在地下室的小房間,是她在疲倦工作、毫無朋友,沒有任何依靠時唯一對外溝通的管道。事實上,表面堅強的她不只怕黑還怕鬼,那個小氣窗傳來的任何消息,都是一點點與人有所連繫的證明。她非常喜歡。
工作數年後,拚命三郎的她,從那個住著體育大學男學生、父親與啟智兒子、一個把房間堆積了無數垃圾的老女人的地下室,輾轉一路搬到了現在這個位於六樓的頂樓加蓋套房,即使隔音差勁,能清楚聽見室友電話聲、洗衣機運轉嘎拉嘎拉的聲音,但五坪大的空間、溫暖的木質地板、一些好看的家具,已經與過往是地獄天堂的差別。其中她最喜歡的就是那面對外的大窗戶。往後的日子裡無論她流轉何處,她總是有這樣的需求:一面對外的窗戶,早晨灑進的陽光,一目了然晴朗與否的天空。
那天回到套房,一如既往地,她先推開了窗戶,窗外透入涼風,她刻意添購的白色蕾絲窗簾隨著涼風擺盪。彷彿完成了今日最後一道手續,睡意侵襲,指頭方離開窗沿,她便感到一股難以抗拒的睡意。她真的太久沒有好好睡上一覺了,今天是個絕佳的時機。以往她總要職業病地反覆確認幾個屬於記者、公司的群組,確認一切無事,才能夠安然入睡。事實上她確實想這麼做,但倒在床鋪上,方才打開通訊軟體,她眼皮便逐漸沉下,眼前的文字消融成一團,變成沒有意義、進不了腦袋的符號。
她側躺在床鋪上,仍亮著螢幕的手機從她手心緩緩滑落,倒在床鋪上。
她的睫毛眨動幾下,最後完全閉上,呼息緩慢而規律。
與此同時,半滑落在手心與床鋪之間的手機螢幕重新亮起,來訊者的名字,叫做林姵亭。
*
一片漆黑的房內,月光灑了半邊床舖。
白色月光沿著劉知君的手肘,描上指尖,來到她手心上的手機螢幕。
手機又亮又暗、又暗又亮。
來自林姵亭的訊息寫著:
「知君,救我」
「他們想殺了我⋯⋯」
「救救我」
「救命」
「他們要殺 」
螢幕反覆亮了數次,終於暗去。
而劉知君沒有及時醒來。
*
一名女記者在高級酒店內遭餵毒身亡,為年節過後的臺灣社會投下一枚震撼彈。
根據媒體初步披露的消息,指出這是一個富商們的狂歡派對,邀請不少小模同歡,現場有使用毒品的痕跡,而在這場派對中身亡的女記者林姵亭,擁有足以匹敵小模的姣好容貌、E奶身材,這些都化身為某種符號,現身在各大新聞畫面的聳動標題當中。
畫面中的林姵亭臉部被打上薄薄一層馬賽克,仍然可見其靈動的大眼,巧笑倩兮的可人樣貌。新聞畫面被五顏六色的跑馬燈佔據,畫面一轉,主播指著身後秀出的一張手機通訊軟體截圖,顯示在林姵亭死亡前半小時內,曾經傳訊息給閨蜜求救。換一個新聞臺觀看,會發現這個「閨蜜」在幾經釐清之後,確定了身分,是林姵亭在八卦週刊內的同事劉姓女記者。
據知情人士指出,劉女與林姵亭同期進到八卦週刊工作,兩人年紀相近、私交甚篤,劉女也許對林姵亭為何會出現在狂歡派對內、以及她交友狀況都略有所知。
劉女作為最後收到林姵亭消息的證人,一早就被帶到警局內。
意外被捲入風暴中心的知君此時坐在警察局內部的小房間,暫時躲避了警局外早已繞了好幾道人牆的記者們。
今天一大早,天尚未亮,原本預期能一路睡到中午的劉知君就被響到快要沒電的手機給叫醒,一睜開眼,就看見幾十通的未接來電,以及採訪主任黃慈方的來電通知。即使腦袋一片糨糊,劉知君仍反射性地接起電話,多虧幾年的記者生涯,她練就了一身醒來就進入工作狀態的好功夫。知君應答的聲音充滿精神,一點都不像剛剛睡醒,只是她萬萬沒想到,這通突破重圍、總算找到她本人的電話,竟是敲響林姵亭死亡喪鐘的訃聞。
接下來的一小時內,從整裝出門、踏上計程車,到進了警局,知君都覺得自己在雲裡霧裡,做著這些制式化動作的人似乎不是自己,而是某個假扮成她的機器人。在前往警局的路上,劉知君總算是掌握了在她睡著的這幾個小時內,世界發生了什麼翻天覆地的事情。
根據報導內容,以及劉知君手上收到的消息拼湊,林姵亭在昨天晚上十二點左右,進到高級飯店內,參與狂歡派對。實際與會人士目前還不清楚,大致知道是一些有權有勢的男性,以及面貌姣好的模特兒、酒店小姐們。這類的聚會平常大多辦在私人招待所內,並不算是什麼稀奇的事情,喝酒、吸毒,也是常態。但到底為什麼身為一個記者,林姵亭會進到那個聚會裡,才是令所有人想破頭也不明白的事情。
身為新聞臺所說的「閨蜜」劉知君本人,更是全然不清楚狀況。
一年多前,劉知君跟林姵亭一同錄取八卦週刊《立週刊》的記者招考,成為新進員工。
猶記得剛到公司報到那天,劉知君胃痛得吃不下早餐,但為了抑制胃酸翻騰,只能坐在公司樓下的超商,硬逼自己吞下一些麵包,神情之痛苦,不知情的人還以為她吃了什麼可怕的東西。
就在劉知君勉強吃了幾口麵包,又吞下胃藥時,身邊坐下一個女孩子。不同於知君慎重地穿著套裝,女孩一身率性,落落大方地朝她笑著說:「嗨,妳也是新來的吧?我叫林姵亭。」
劉知君記得第一次見到這個女孩子的震撼。她彷彿看見年輕時的母親。自信、張揚,黑白分明的大眼裡永遠閃爍著慧黠的光。被她盯著看的時候,會覺得這個女孩子古靈精怪、不懷好意,與母親不同的地方,大約是她總是彎眼笑著的面容,以及嘴邊的梨渦,這讓她看起來不若知君的母親那樣冷淡疏離。
姵亭問她:「都已經錄取了,幹嘛還這麼緊張?」
劉知君面色慘白,自己也覺得很丟臉。「我也不知道,就是習慣性的緊張。」
姵亭歪了歪頭,「妳不是那個一畢業就到大報社工作的劉知君嗎?」
知君還想著她怎麼會記得這麼清楚自己是誰,林姵亭又自顧自地說:「沒想到像你這樣的模範生也會怕喔。」
知君不知道是否該反駁,只覺得丟臉。
「沒關係啦。」姵亭豁然開朗地說。她朝知君擠眉弄眼,突然從包包裡掏出一瓶礦泉水,逕自打開知君的水瓶,滴了兩滴在裡面。姵亭神祕兮兮、好像對待珍寶那樣地收起自己的水,然後催促知君:「這是法水,妳喝喝看。」
知君半信半疑看著她,姵亭又催促她:「其實我昨天也很緊張,特別去廟裡求的,妳喝喝看。」
劉知君是有點太不會拒絕人了,真的就順著她的意思喝了兩口。
姵亭一臉期待地看她。「怎麼樣?是不是不緊張了?」
知君摸著胸口,感覺了一下,不太確定是不是起了什麼變化,但越想越覺得心情好像變得比較平靜。於是她點點頭,有點訝異地說:「好像是。」
林姵亭撐著臉,笑得心滿意足。
「知道高材生也這麼好騙,我安心很多哦。」
她對姵亭當下那張狡詐又非常可愛的笑臉始終記憶猶新。未來的日子裡,知君知道,她很需要姵亭那種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都能雲淡風輕地告訴她「別怕,先怕是傻瓜」的態度。
如果要形容林姵亭是個什麼樣的人,只需要舉一個例子,便可以清楚了解她不按常理出牌的程度。
大學並非正統傳播科系出身的姵亭,也沒有亮眼的文憑,畢業後在新聞行業的求職路程上比起其他人要來得辛苦一些。她輾轉幾個小報社,心裡卻很清楚,這些都不是她想要的。她要的,是當一個「真正的記者」。何謂真正的記者?林姵亭心裡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標準。
那年初春,跟現在一樣的天氣,姵亭意外得知《立週刊》可能在七月舉辦大型招考。招考這件事對週刊來說是相當罕見的。得知消息的那天,姵亭就以身體不適為由,向老舊擁擠的小報社請了假,搭著搖搖晃晃的公車,從臺北東側的老舊社區,一路到了西邊辦公大樓林立的新開發地段。她的腳步緩慢悠閒,在春天燦爛的太陽底下歪著頭審視這間嶄新的辦公大樓,窗明几淨,大公司的做派。
她看了看,腳步輕盈穩健地踏進了辦公大樓,也不曉得她怎麼做到,竟然可以理直氣壯、如入無人之境地避開警衛視線,上到週刊辦公室所在的八樓,隨意跟櫃檯接待講了個理由,就走進了週刊寬闊明亮的辦公室內,在來來往往的記者之中,再自然不過地在辦公室內晃了一圈。她特別喜歡面向整面落地窗的茶水間,也有點小女孩的心情,喜歡那些五顏六色的小椅子,她挑了粉紅色的那只坐下,對著窗外看了一會。大約是這時候,有個人走進來,看到她,面帶困惑又親切地問:「妳是新同事嗎?」
劉知君是在姵亭進來工作的數個月後,才聽姵亭說了這段經歷。她幾乎可以想像姵亭當時的表情,肯定是泰然自若地,用那種親切又不過於親近的笑容,宛如進入演員般的狀態,回答:「是呀。」
那個下午後,這個號稱自己是新員工的林姵亭就消失了,來無影去無蹤,沒有人知道她是誰,就如同那個過度曝光的春日午後,澈底消失在過白的陽光當中,直到晚幾個月那場大型招考過後,她的名字正式被填上週刊的記者名單當中。
沒有學歷、背景,更稱不上有資歷的她,為了在眾多有亮眼履歷的高材生之間脫穎而出,果斷辭掉了原本的工作,用三個月的時間進酒店臥底,意外打聽到了某位受封「國民老公」藝人的外遇醜聞,在這件事之後更爆出一連串醜聞,各式腥羶八卦全浮上臺面,震盪演藝圈一時。外界沒人知道這新聞正是這個沒背景、沒資歷的小記者一手打造的作品,但在週刊內部,倒是引起了一陣譁然。就因為這條新聞,林姵亭以二十四歲的年紀進到週刊內擔任娛樂組記者,打破了週刊內的紀錄。
與姵亭不同。從小個性就嚴謹到近乎一板一眼的知君,無論在課業還是工作上,一直都跟拚命三郎畫上等號。沒有家庭的後援,靠著自己的努力考上知名大學新聞系,在學期間,不要命一樣的工作、累積相關資歷,讓她一畢業就進到知名報社擔任記者。
初出社會,沒有人脈的她,靠著土法煉鋼蹲點、搏感情,成功地累積起一則又一則的獨家。能力出色的知君在同事關係上卻不見討好,剛出社會那幾年,所有人都對於一個小記者竟然可以接二連三拿到獨家一事感到不可思議,甚至私底下臆測她的新聞是「睡出來」的。劉知君雖然氣憤,但流言澄清不完。她只能埋頭不斷工作,直到有一天驀然回頭,她已經走了很遠很遠。
直到認識了林姵亭。
但林姵亭卻死了。
劉知君覺得內心某個部分正在崩解,但沒有人聽見。
許多問題盤繞在知君心中,纏繞成一圈又一圈,她試圖梳理,卻一再打結。
林姵亭到底為什麼出現在那裡?她平常認識這些人嗎?
她跟那些人是什麼關係?為什麼他們要殺了她?
又或者責備自己,為什麼在姵亭向她求救時,她沒有醒?
在她死前最後的半小時內,她在想什麼?
想著手機內姵亭最後傳來的訊息,心裡面滿滿都是後悔。
要是昨天沒有睡著的話、要是她及時醒來的話⋯⋯
一連串的「要是」全擠在腦袋裡面。死亡、消失、再也不會出現。想起來一點真實感都沒有,但身處警局,都再再提醒她:林姵亭確實已經死了。
房門打開,一名看起來年約五十歲的警官走進來,神情疲憊。警方為了這件事,從半夜到現在都不得入睡,來來往往經過的警察,都神色蒼白。
「劉小姐妳好,敝姓王。」王警官在拉開椅子入座前,將手機遞還給知君。手機微微發燙,螢幕上滿滿都是訊息未讀通知。「妳的手機我們已經看過了,可以先還給妳。」
知君有些出神地收下了手機,甚至沒有心情看這段時間裡到底又收到了哪些訊息,就只是捧著這隻發燙的、收藏著姵亭死前訊息的機器,自顧自地出神發呆。
她看著王警官低頭翻看手上的資料,五十歲左右的壯年低沉嗓音,彷彿隔了一層水,聲音忽遠忽近。
「妳跟被害人的私交很好是嗎?」
「我們是好朋友。」知君說。
「也是,不然她最後怎麼會傳訊息給妳?」王警官手上資料翻了一頁,知君看見上頭寫著自己的資料。「妳對於被害人交友情況的了解有多少?」
知君搖頭。「我不是很清楚。」
王警官看她一眼,抽出資料夾裡的幾張照片,一張張擺在知君面前。
「這幾個人,你見過嗎?」
上頭是幾張男人的照片,知君點出其中兩張人臉。「我是記者,認得出他們是誰。但我們互相不認識。」這兩張面孔分別是房地產公司的二代,以及某間大型食品公司的公子。
「那被害人與這兩人的關係呢?」
「⋯⋯我不知道。」
「好吧。」王警官在簿子上簡單記下方才詢問的內容。「劉小姐,能請妳跟我闡述最近這陣子被害人的狀況好嗎?什麼事都可以,工作狀況、你們相處的情況,或是妳覺得可疑的事情⋯⋯」
知君沒有立刻回答。她有些焦慮地輕捏指間,下意識地深呼吸,回想最近幾天,甚至幾個月來的情形。
王警官沒有搭話,靜待她的回答。
知君的視線停在桌上的姵亭照片,站在陽光下笑得自信十足。
這就是林姵亭的個人標誌。
*
在招考上表現出色的林姵亭,破例錄取到《立週刊》工作。雖然在招考上表現亮眼,但沒有足夠的資歷,仍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八卦週刊記者與一般記者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一般報社的娛樂記者,其報導來源,多來自記者會、通稿,這些記者大多與娛樂圈建立良好的利益共生關係,一旦記者累積了一定的人脈,有時新聞甚至會自己找上門來。但八卦週刊的記者不一樣,藝人很難在檯面上與記者們交好,更多時候通常交惡。因此,八卦週刊的記者就更要能夠自己開闢出一條生路。他們的新聞來源,大多仰賴在其它報社工作時期累積來的人脈、線民,如此一來,即使來到八卦週刊,他們也能夠自給自足,自行挖掘出許多題目來;另一個八卦週刊的記者壓力更大的原因,在於八卦週刊的競爭性,能不能夠寫出具爆炸性的獨家,成了記者的第一要務,人人肩膀上都扛著沉重的業績壓力,一週兩次的編採會議就需要各提出三條以上的新聞題目。
這種狀態下,八卦週刊的記者固然擁有比較好的薪資待遇,但若沒有超乎尋常的抗壓力,也鮮能扛起這份工作。而沒有人脈、也沒有資歷的林姵亭,縱然有外向勇敢的拓荒型人格特質,在每週需要大量產出題目的高壓工作狀態裡,也時常一籌莫展。每週六道新聞題,她時常是零零落落、東湊西湊,工作備受挫折,開會時,更是常遭奚落。
反之,知君的狀況就完全不一樣。當初《立週刊》辦招考,設定的求才目標,就是像知君這樣的年輕人:擁有完整的新聞產業背景、工作上擁有一點小資歷,表現出色。簡單來說,就是穩定且有潛力的新人。劉知君從來不讓人失望,她簡直就像是一面鏡子,擅長照出別人喜歡什麼、想要什麼,然後她就按照別人的希望做出高分的模仿,獲得別人的認同,或是獲得別人的愛。
從小到大,她都擅於扮演「好孩子」這個角色。
跟姵亭大起大落的工作狀態不一樣,她的表現是有目共睹、且持續進步的。
但姵亭就不同了。她沒有足夠的人脈資源可以供她寫新聞,過去她所做的大新聞,就是那則臥底酒店三個月的紀實報導。雖然聽起來很偉大動人,但換個角度看,這代表別人可以一句話要到的新聞,換算成林姵亭的時間,卻需要三個月的肉身拚搏。個性外向大方的林姵亭,在同事、長官間討喜,雖然自身資源不足,卻不乏同事們大大小小的幫助。其中,知君本人更是不斷不小心「多做了」很多題目,與姵亭分享。
幾個月前,知君靠自己的線人追蹤到某藝人在高級地段經營私人賭場的消息,很幸運地一獲得消息時,就已經掌握到幾張關鍵性的照片,這使得知君在編採會議上,順利地確定了題目,甚至被定調為下一期封面新聞。這不是知君第一次扛封面新聞,但這次做的報導,比起之前的題目,更有機會引起高度關注。知君很清楚,自己這樣認真工作的人,就是需要幾件像這樣的大新聞,來加速升遷的機會。
那天的編採會議上,知君特別被副總羅彩涵稱讚。羅彩涵這個人,生下來就像講話只有尖酸刻薄這個選擇,就算是讚美,聽著也像是挖苦。
羅彩涵近半年才來到《立週刊》,一來就空降佔走了黃慈方原本有望的副總之位。黃慈方進公司的時間比羅彩涵早,資歷也比她深。當初前副總的位置空缺下來,所有人都以為黃慈方即將高升,怎知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羅彩涵自其他報社被挖角過來,公司需要給她一個位置,娛樂組副總的空缺,就這麼拱手讓人了。
黃慈方一向行事溫和,對這件所有人都抱不平的事,她卻是一副不鹹不淡,毫不在意的模樣。她越是不在意,就越成為羅彩涵的心魔,日後無論大事小事,只要是能拿出來當談資的,她全要繞到黃慈方身上去說一圈。
個性謹慎靠譜的劉知君,路線自然與黃慈方是走得比較近的,羅彩涵對這票的「慈方黨」通常沒什麼好臉色看,但那天開會時,知君報完題目,羅彩涵卻反常地沉默幾秒,沒有立即開砲開酸。會議室內一陣安靜,大家都等著她是不是又要發飆。孰料她安靜一會後,卻是說:「不錯,做下一期封面吧。」講完嫌不夠似的,又加一句:「妳很適合當記者。」
到底什麼叫很適合當記者,又是為什麼羅彩涵從那篇新聞裡歸結出這結論,到底幾分真心還是有哪些計較,劉知君不去細想了。她承認,當下她真的是飄飄然,有點了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滋味。後來輪到其他人報題,羅彩涵又恢復了原先開砲的氣勢,霹哩啪拉把所有人都罵了一頓,尤其對那天遲到的林姵亭罵得更狠,簡直要將她胸口轟出個大洞。
「學一年了能力還是這樣,妳報的這是新聞嗎?要不要妳現在從窗戶跳下去,自己變成新聞啊?」
林姵亭喜怒不驚,被罵還嬉皮笑臉。「那不是白白便宜社會組了嗎?」
羅彩涵對林姵亭這種油條的態度最是反感,散了會之後,還單獨把姵亭叫去罵了好一會兒。開完會後,記者多要出去跑新聞了,劉知君坐在咖啡廳裡一邊整理資料,一邊等著林姵亭。因為姵亭沒什麼跑新聞的經驗,一星期內有一兩天讓知君帶著她跑,已經成了一年多來共事的默契。姵亭來了以後,唏哩花啦地抱怨了羅彩涵有多煩人,知君注意力在電腦螢幕上頭,偶爾應兩聲。
「妳也要小心,」姵亭講到一半,突然蹦出這一句。「羅彩涵今天突然這樣誇妳,八成是要拉攏妳。」
知君敲擊鍵盤的手指突然一停,幾秒的停頓,很快地又繼續方才未完成的工作。她語氣不見起伏。「說不定是真的想稱讚我啊?」
林姵亭嗤之以鼻。「拜託,妳寫那個男明星什麼咖啊,還開賭場咧,開妓院都沒人在意!這種題目居然做封面,羅彩涵是瘋了吧。」
知君嘴角拉了拉,這是她平復情緒的習慣動作。視線的焦距從螢幕上的文字,聚焦到投映在螢幕上自己的表情。她沒有接話,但內心充滿難消的躁動。身邊林姵亭也拿出筆電來,完全沒注意到知君的情緒,自顧自地工作起來。知君仍在與憤怒做抵抗,工作的事一行都進不了腦袋。身邊姵亭的動靜,在這種情境下,變成無與倫比的噪音。她聽見林姵亭在雜亂的包包中海底撈針一樣翻找事物,最終掏出一張皺皺的名片、打電話、手指撩過長髮、漂亮的臉微側,一邊打字一邊接聽電話⋯⋯「嗨,Henry,我姵亭啦⋯⋯」Henry是某大牌女星的經紀人。是幾個月前,知君牽線給他們認識的。
理智線突然就斷了。知君闔上電腦,也不管姵亭還在講電話,側過身就對著她說。「雖然那個男明星不是什麼咖,但我很想好好寫。」姵亭看她突然發作,還在跟Henry討價還價要新聞的她一陣錯愕,來不及反應,知君又急又快地繼續說:「做封面壓力很大,妳可能太久沒做忘記了。接下來報稿時,沒辦法再送妳題目,妳自己要好好加油,不要又東缺西缺到處找人幫忙。工作成這樣真的很難看。」
她一口氣講完,深怕自己後悔一樣。話一說完,她就收拾包包走人,畏懼於接觸到姵亭的表情,也畏懼於看到自己現在的模樣。
那天後,姵亭傳了一封訊息跟她道歉,說自己說錯話了,希望兩人還是朋友。知君其實知道姵亭的性格,要是不在乎的人,林姵亭根本鳥都不鳥。她知道姵亭是真心把她當朋友。收到那訊息,劉知君也自我厭惡,覺得自己小氣、想裝好人還裝不澈底。年輕的友誼唏哩呼嚕也就和好了,但對女孩子來說,有些裂痕即使微乎其微,仍然不是真正的完好無缺。
稍一觸碰,又會現出醜陋的原型。
*
楔子
身為一個娛樂記者,習慣躲在文字身後的劉知君沒有想過,有一天,她也會捲入風暴中心,受萬千視線所監視,動輒得咎,一步一步越走越錯,終至無法自拔。
所有事情的開端,抑或說是「禍端」,應回溯到許多個日子以前,那一個殺機暗伏的寒冬說起。
第一章
林姵亭死前最後一個往外發送的求救訊息,安安靜靜地躺在劉知君的手機內。
那是一個年節過後的夜晚。
在八卦週刊擔任娛樂記者的劉知君,硬生生扛了兩期的封面題目之後,總算能夠在午夜以前回家,並且好好睡超過五個小時。這並非能者多勞,純粹是被趁機揩油,讓其他人能輕鬆...
推薦序
追尋他人鬼火前,娛樂記者如何先制伏自身心魔?
文|馬欣(作家)
看完《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心想這樣的魍魎之境一點都不陌生,愈靠近名利之處,如同有熊熊火焰燃燒,愈明亮的舞臺,四周的黑暗就更深邃,這是自古皆然。
於是讀完後,曾與本書的故事原型與素材提供者分享心得,書中的幾位娛樂女記者,每日真槍實彈地接觸第一線新聞,雖然女主角自認熱血,但要在這樣的名利場裡揪出知名人物的慾望鬼火,她是否又能制伏自己的心頭鬼?
我在當影劇線編輯時,臺灣影劇業正是風光大好之時,日日是熱鬧的記者會,大排場的慶功宴更是開不完,娛樂記者像置身大觀園一樣,一路花紅柳綠,彷彿有開不完的宴席。
如此繁盛的產業,也把人的慾望養得跟池中的錦鯉一樣活跳跳地爭食,無論幕前或幕後的人得利,周邊的娛記也如大觀園的丫頭與姥姥們爭著排名,爭的不僅是八卦與獨家,爭的更多的是權力的展示。
九○年代整個熱錢燒起來,記者收禮的風氣開始浮濫、唱片與經紀公司不斷製造假新聞、透露別家公司藝人的八卦來換取自家的版面、大牌記者搶著為主打歌作詞的高報酬等等。影劇線在社會眼光看來或許風花雪月,但在當時是個肥缺,因此辛苦是必然的,對內總有人要搶這肥水多的線,幾個記者在社內大戰時有所聞,對外每家大媒體記者自己的面子與排場更要做足。
說穿了,這是一個不僅明星要作態,幕後與記者都要擺出排場的圈子。固然有不少認真跑線的記者,但浮誇氣氛已成,九○年代末,唱片與戲劇品質開始下滑,各種作態與擺譜足以混淆視聽。遠看簡直是本《紅樓夢》,預見遲早得樓起樓落,內在崩壞地迎來二十一世紀時臺灣影劇業的蕭條。
這樣彼此歌功頌德、做新聞如做假球的時代,迎來香港八卦雜誌的攻城略地,以夠腥更狠辣的方式,掀開了之前臺灣九○年代唱片圈的醬缸文化,如此造就了這本書中的自命要追求真相的記者劉知君與林姵亭,還有兩位女主管,這樣緊咬不放的記者特質,看似追求真相(是也追到了一些真新聞),不想像以前許多記者那般粉飾太平,他們是追出的飯局價、吸毒趴、耍大牌、潛規則等新聞頭條,久了也知道那只是咬出冰山的一角,咬出了空虛的本身,這類新聞開始無限循環,如吃不完的流水席,八卦隔週只有廚餘的溫度。因為周刊本身用字是鹹膩過火的,字這東西寫得過重會吃掉一切核心。
這一行只有作品能論功夫真假,其他就是造夢,連明星當事人與幕後推手都難分真假圈子,觀眾目光追逐的是他們一早就預約的一哄而散,與古時候鄉鎮戲臺子一搭無異,人們湊近,半日的熱鬧就是圖個以假亂真。
因為眾人的不當回事,影劇記者很像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無論裡面如何廝殺,搶到了什麼頭條,或是如愛高調收集多少明星朋友當作「江湖地位」的虛榮,都是自己的黃粱一夢,他人只當閒事一樁。如同被關在大紅燈籠裡,誰也不踏實地在這五光十色中,彼此看似熱絡卻從不真切。
這本小說裡的四位女記者,主管或嗜血,或收賄,或是臥底追獨家而犧牲了生命,或主角鍥而不捨追蹤到某大經紀強迫旗下藝人性招待的真相,故事中呈現出的記者的焦慮生活,的確寫實。寫出我這十多年來看到的娛樂記者的眾生相:犧牲生活、為流量產出大量文字,在這樣異常的節奏中,有人開始上癮,即使偶爾感到搶即時新聞的空虛,偶爾感到交淺言深才是這行的本質,但如滾輪上的老鼠也回不去。
這樣的狀況發生在經紀、企宣人員、記者都是如此,我們被紅燈籠的皮影戲所吸引著,以至於自己同樣在演也都不自覺。但隨時散場的落寞,卻是我在影劇圈邊緣遊走時最大的心得發現,包括藝人都無法承受這隨時散場的落寞,我們都緊接著要去找另一場大戲,即使那紅豔豔的世界裡有亮光但也到處都是鬼影,如同小說中所呈現出的黑幕。但與其說我們是為了多有使命感而追新聞,更接近的是一群怕寂寞的人在追尋光源,即使懷疑這一切是幻象,人們也吃不完這一切的空泛,且永不飽足,不僅書中的四個女記者被這幻象吞食進去,裡面受害的援交網紅也是,我們空吃著那些霓虹光,幾年下來餵大了我們更多的黑暗。
這大概是我在月刊當採訪的原因,因為離一步觀看前方的修羅場太吸引人了,我每每看得入神。無論是誰的慾望之鬼吞食了對手的名聲;還是誰出賣了敵手的致命八卦,或是哪個記者長期被唱片公司餵養八卦以致受制於人,抑或是當年哪位大牌記者搬家,會指定唱片公司送他各式名牌電器,也是想挨近藝人求歡的褓姆緋聞,這哪有什麼稀奇呢?我看著人們的心頭鬼跳上跳下,誰可以幸運地看到這樣如同陰陽師安倍晴明眼下的妖魅世界?
關於這本小說最有趣的,不是那兩位年輕記者如何臥底抓新聞,而更像是被這娛樂場子內化了的人,極盡所能想把這圈子的妖怪現形,哪知在她們追新聞時,也對映出了自己心頭的那些鬼火。所以我曾思索為何這書名要註明是「女」記者,的確,這行是陰性的,在看似開放實則封閉的工作生態裡,女記者的歇斯底里時有所聞,多數因為自己的不被重視而前帳後算,或是要裝出一個甄嬛的威儀,壓制其他的女性同業。這「女」字,顯影了我們的宮鬥劇基因到現在還沒去除,那種守住腹地的陰狠是這行爭鬥常有的特質。
於是女記者居多的影劇圈對於權力的抓取仍是舊宮闈的思維與手段,也一如書中所寫,記者圈女性彼此的厭女昭然若揭,對無形的權力順服更是女主角劉知君的特質,她對體制的乖引出了她的狠,因為只有一個視角的盲目而毀了另一個女明星,劉知君的自命正義,何嘗不是渾然不知的平庸之惡?
這圈子太有趣,我曾經歷過,看到這一切現形,一路是有很多值得敬佩的從業者,但慾望這景幕把多數人給抓住,不是沒好人,但正常人不多。這多年下來讓我這雙眼看盡張愛玲說的那襲華麗袍子下的蚤子,你要看嗎?都在這書裡,主角們都是蚤子。
追尋他人鬼火前,娛樂記者如何先制伏自身心魔?
文|馬欣(作家)
看完《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心想這樣的魍魎之境一點都不陌生,愈靠近名利之處,如同有熊熊火焰燃燒,愈明亮的舞臺,四周的黑暗就更深邃,這是自古皆然。
於是讀完後,曾與本書的故事原型與素材提供者分享心得,書中的幾位娛樂女記者,每日真槍實彈地接觸第一線新聞,雖然女主角自認熱血,但要在這樣的名利場裡揪出知名人物的慾望鬼火,她是否又能制伏自己的心頭鬼?
我在當影劇線編輯時,臺灣影劇業正是風光大好之時,日日是熱鬧的記者會,大排場的慶功宴...
作者序
後記
收到改版的消息,編輯邀請我新寫一篇後記,雖然很開心,但想了幾天實在不知道該怎麼下筆。若是回到二○一八年底,將這份任務交給剛寫完這本書的自己,大概是能寫下一篇血淚交織的創作心得,只是這本書從完稿至今畢竟也六年了,要是那時有哪個國中生不湊巧在圖書館讀到這本書,現在甚至已經是個大學生。
因此,要調動記憶找回寫作時的心境是有點難度,只大約記得從寫第一個字到完結,我都是戰戰兢兢,害怕寫得不好,反覆修改,折磨死編輯(每交一版就告訴編輯,我前面又改了,拜託你再看看,編輯叫我別改了,趕緊先寫後面的劇情,我回:做不到)。在寫《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之前,已經好久沒有寫小說了,茫然不知道該怎麼做但已經跟編輯誇下海口寫得完,約都簽了開始膽戰心驚,安慰自己,沒事沒事,又不是要寫什麼曠世鉅作,既然寫的是娛樂記者,那標準就是要足夠娛樂。從此,寫完每一場戲,就問自己,這樣好看嗎?回頭想想那應該是自己創作的最初衷,寫故事沒什麼願望,主要是讓別人看得開心,沒有技巧,全是感情。
在那個(虛構的)國中生考上大學的時間,知君的故事並沒有隨全文完告終,六年裡,也一直在往前走。書出版之後不久,就拍板定案成了鏡文學的自製劇,我也加入了編劇團隊。將這個故事交到團隊手中,它就是個集體創作了,無論是知君、姵亭、大海,在劇本中都是經過團隊日以繼夜地討論重新鍊成。一版又一版的劇本,光是會議紀錄列印出來大概就比小說還厚,定版劇本完成大約花費了三年。在這個故事裡,所有人都投入了誠意真心,這實在是當初寫小說時想不到的福氣。寫小說時,大多數時候是自己苦惱,但轉譯成劇本的過程,跟一群才華洋溢的人一起沒辦法睡覺,想想就高興。
這劇本寫了三年,團隊都努力地想要做到更好,回想起來都不記得寫過多少個版本,知君已經不僅僅是我個人創作的角色,她當然變得跟書裡有點不一樣,但有另一份靈活深刻,無論是哪一個劉知君我都很喜歡。因為知君,我有了很特殊的三年,與一群傑出的夥伴一起工作,也不斷不斷地重新打磨創作技巧,反覆琢磨人物心境,直到他們也都成了我心中另一種形式的朋友。雖然過程中也不免希望這些朋友活過來,自己的劇本自己寫,別再折磨我,但幸好編劇團隊足夠堅強,就算我倒下了後面還有隊友扛著。最後我們都因為這個劇本胖了不少。
接著進入製作階段,我的任務功成身退,期間偶爾像是參加小學同學會那樣,問一下最近過怎樣,基本上就沒再為孩子操過心。去過讀劇一次,第一次看到林予晞,I人嚇死,瑟瑟發抖,只能偷看她的美貌,不敢說話。予晞好像有想跟我說點什麼(抱歉也可能是我的記憶美化),但那場合我渾身上下充滿了現在就得逃走的大I人本能,沒什麼發揮。接著去探班一次,看的是劇裡招待所那個場景,景是搭的,有夠華麗,我在裡頭興奮地晃來晃去,跟遊客沒有區別。
那時候,距離寫這本書已經好多年了,我其實沒什麼原作者的感覺,更覺得是故事長出了自己的生命,有了屬於知君自己的命運。後來,跟夥伴們一起看了初剪、聽說了補拍、直到定檔,團隊即使到最後階段都是用盡全力。能有這麼多人一磚一瓦地創作出這部劇集,首先要靠故事中劉知君的堅定,走完整趟英雄旅程,接著這份信念又在不同的時間階段裡,不斷交棒,直到劇集完成並上架的那一刻,交到觀眾手上。
在創作的過程中,我們反覆地在問,知君想為姵亭翻案的動機是什麼?我們希望可以在影像化的過程中,把這個重要環節更具體地展現出來。三年間你來我往的討論,要為這題目另外寫本書都沒問題,不過時至今日為了後記又重新看了看小說,知君的想法其實始終如一的純粹,姵亭是她窒悶的生命中,那道透光的裂縫。她嘴上縱有千萬種理由,但內心想向陽而去。
我曾經思考過,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創作者,走過這幾年再反思,其實與當初想的差不多,只是更確定。創作要善良,然後逗很多人開心。
最後,請讓我好好地感謝一路走來的夥伴們。最要感謝的是子薇姐,從小說的第一個字她就是最忠實的讀者與最可靠的顧問,子薇姐手把手替我梳理娛樂記者的細節,即使是半夜都不辭萬難為我解惑。那時的我比現在更資淺,面對一個需重頭學習的職人故事,遇到子薇姐是我最大的幸運,我也很慶幸,直到劇本完成的最後一刻,都有她陪伴在故事身邊。姐教給我的不只是怎麼寫娛樂記者,更是一個人可以善良寬厚如斯。此外,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推動《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影集版的製作人兼編劇統籌Lily,在三年劇本鍊金術裡讓我看見自己缺乏的勇氣跟毅力,Lily不僅是前輩,更是我心裡面很喜歡的姐姐。還有同在一條友誼小船上載浮載沉的小夥伴編劇志濤跟執行製作范軒,工作還能交到朋友,想不到吧。
最後感謝在成書過程中,為這本書的行銷努力奔走的小夏,以及我的精神依靠編輯老王、毓瑜、佩璇,沒有你們這些優秀又有毅力(講了幾次毅力就知道我多沒毅力)的編輯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我還只能是個小寶寶。走過漫長幾年,《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的影集終於跟大家見面,最感謝的是出版後收到無數讀者的鼓勵,因為你們,讓我開始長點信心能寫小說,也希望今後還有更多讓你們讀了開開心心的小說面世。不太確定什麼時候,如果想念我,也能去看看我寫的劇,開頭忘了說,我的正職其實是編劇。
柯映安 2024/12/16
後記
收到改版的消息,編輯邀請我新寫一篇後記,雖然很開心,但想了幾天實在不知道該怎麼下筆。若是回到二○一八年底,將這份任務交給剛寫完這本書的自己,大概是能寫下一篇血淚交織的創作心得,只是這本書從完稿至今畢竟也六年了,要是那時有哪個國中生不湊巧在圖書館讀到這本書,現在甚至已經是個大學生。
因此,要調動記憶找回寫作時的心境是有點難度,只大約記得從寫第一個字到完結,我都是戰戰兢兢,害怕寫得不好,反覆修改,折磨死編輯(每交一版就告訴編輯,我前面又改了,拜託你再看看,編輯叫我別改了,趕緊先寫後面的劇情...
目錄
專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最終章
後記
專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最終章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