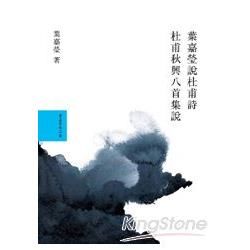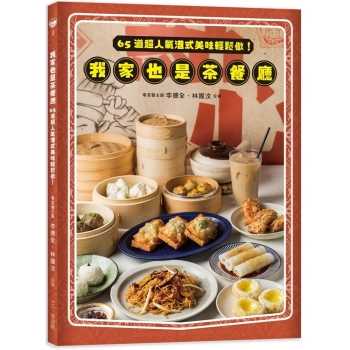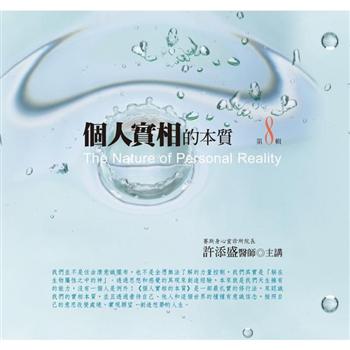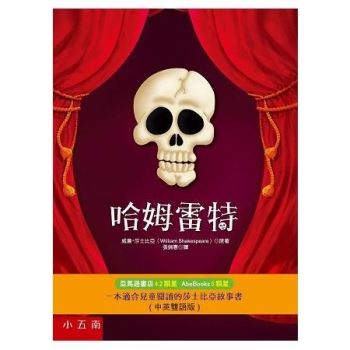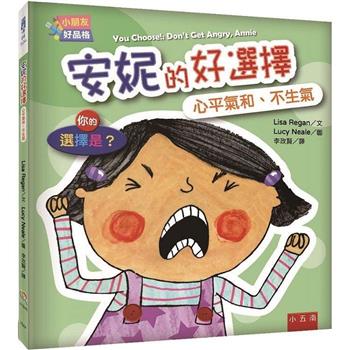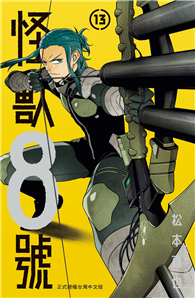葉嘉瑩說杜甫詩
從中唐以來,像元稹以及後來的秦觀等人都這樣讚美過杜甫,為什麼有很多人讚美杜甫,說他是一個「集大成」的詩人呢?
在中國的詩人裡邊,不同的人有各種不同的成就。有些人七言詩寫得好,有些人五言詩寫得好,有些人古體詩寫得好,有些人近體詩寫得好。李白的詩我們也講過了,像他那些長篇的七言歌行和短小的五言絕句寫得就很好,可是我們沒有講李白的七言律詩,因為他的七言律詩沒有太好的作品。這是以體裁而言,如果再以內容而言,有些人善於寫大自然,比如王維的詩,我說他那些寫自然景物的五言詩能夠給人一種感動和觸發,這是王維的好處,可是王維別的作品不能夠完全達到這樣一個最好的水準。有些人善於寫邊塞,像高適、岑參的邊塞詩就很不錯。總之,有的人某種體裁能寫好,有的人某方面的內容能寫好,但是很難做到全面。而大家讚美杜甫是一位集大成的詩人,就是因為杜甫的各種體裁、各種內容的詩都能寫好。
我們說,杜甫以集大成的胸襟生在一個可以集大成的時代。所謂集大成的胸襟,就是說你要能夠接受、容納各方面的好處,而不是故步自封,自己先畫個圈把自己封起來,把其他的排除出去。就胸襟而言,杜甫不像很多人那樣,只認為自己對,一定要把對方打倒。每個人都有長處,每個人也都有短處。有些人心存成見,認為律詩都不好,自從建安以來的詩都不好,可杜甫不這樣說,每個時代每個作者都有他的長處。杜甫之所以有這樣的胸襟,我認為這可能與他的家世有關係,因為他的祖父就是寫近體詩的,所以他不鄙薄近體詩。他後來在律詩的寫作上取得這麼高的成就,與他從小所受的影響有很大關係。
可是,如果杜甫生在建安的時代,他能夠寫出〈秋興八首〉這樣的律詩嗎?不能夠,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律詩的體裁。律詩是在唐朝形成的,杜甫能夠把五言七言、古體近體都寫得好,也是因為他生在一個可以集大成的時代,他可以集各種形式的大成。
不僅如此,唐朝上接隋朝,但隋的年代很短,沒有出現偉大的詩人。隋以前呢?以前是南北朝,是晉代的五胡亂華,中國北方被很多少數民族佔領,所以那個時候,詩歌中就滲透了一些新的質素,有很多外來的、新鮮的文化滲透到我們的文化中來了。那時我國北方都是少數民族,他們騎馬射箭,雄健豪放,其文學體式和風格也具有這樣的特點;而當時南朝的宋、齊、梁、陳,偏安在南京附近,文士們每天沉溺在歌舞享樂之中,其文學作品的風格也偏於綺麗柔靡的一面。陳子昂、李白等人認為綺麗柔靡不好,可北朝的雄健豪放他們也沒有完全繼承,他們繼承的完全是古代,是建安以前的文學遺產,那麼建安以後的近代的文學遺產呢?無論是北朝的雄健豪放還是南朝的綺麗柔靡,都被他們抹殺了。
杜甫不然,他能夠吸收古今南北的各方面的風格,接受各方面的好處,完成他集大成的成就。一方面,他生在唐朝這樣一個可以集大成的時代;另一方面,他也有接受各方面質素的容量和胸襟。而在杜甫之前,像李白這樣絕頂的天才都否定了近體詩的成就,所以不能在律詩的領域裡開拓出一片更廣闊的天地。我們曾做過這樣一個比喻,如果以詩歌之平仄對偶的格律為鳥籠,李白這個飛揚的天才就像被關在籠中的大鵬鳥,翅膀都張不開,施展不開怎麼能寫好呢?所以他破壞了籠子。杜甫也是一個天才,他將籠子研究了一番之後,摸透了籠子的原理,然後對其進行了改造,使改造後的籠子可以容納他在裡面變化飛騰了!
我們說杜甫是一位集大成的詩人,可是,造成這種集大成的結果必有某種原因。他為什麼會有這種集大成的成就?我實在要說,因為他能夠深入生活,面對生活。李白是了不起的一位天才,但他的詩多半是從自己出發的;杜甫不是這樣,他真的是深入生活,關心大眾。像他的「三吏」、「三別」等很多詩,所反映的都是人民大眾的生活,他能夠體驗各方面、各階層的人的生活,而且能夠把它寫好,這是造成杜甫詩歌之集大成的一個原因。
杜甫之所以能夠如此,既有環境的關係,又有性格的關係。杜甫在其所生長的環境中接受的是儒家用世的教育,儒家常常說「士、農、工、商」,憑什麼資格就把「士」放在那些辛辛苦苦勞動的「農」、「工」之上?儒家之所以把「士」放在「農」、「工」、「商」之上的緣故,是因為「士」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你將天下的治亂安危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當作自己的責任,可謂任重而道遠,理應受到尊重。杜甫所繼承的真是儒家傳統中最正確、最高最好的理想,所以他能夠深入生活,面對生活,關心人民大眾。至於性格情感的一方面,每個人天生下來的資質不同,後天的因素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我們常常說詩人要表現一種感發的生命,一般說來,作為一個詩人,只要你的感情真摯,有一種真摯的感動,就可以寫出好詩來。
杜甫秋興八首集說
最後,還有一點我願在此一提的,就是二十年前當我撰寫此一冊《杜甫秋興八首集說》時,原意本是想要將杜甫此八詩中的一些超越變化的妙用之理,提供給當日台灣之寫作現代詩的年輕人,作為參考之用。如今事隔二十年以後,台灣的現代詩風已早趨沒落,而另由質樸簡淨的新詩風所取代。可是近年大陸興起來的朦朧詩,其文法之突破傳統及意象之超越現實的作風,卻似乎形成了一種風尚。然則此一冊《集說》在今日之大陸增輯再版,對於大陸寫詩的年輕人,便或者也仍可以有一些用資參考之價值。不過,舊體詩之寫作與新體詩之寫作,在寫作藝術方面雖然也有相似之處,然而卻也有很多相異之點。
一般而言,如詩歌中所講求的音聲之效果、句法之結構及意象之安排等,這些基本的原則自然是無論寫作新舊體詩都應該重視的。至於其相異之點,則除去文言與白話之差別及古今語法和語彙之不同以外,另外一點極顯著的差別,則是舊體詩特別是像《秋興八首》一類近體律詩,都具有極整齊的聲律格式,而新體詩的形式則是完全自由的。對於不熟悉舊詩聲律的人而言,那種嚴格的格律自然是一種死板的約束,可是對於習慣於這種聲律格式的作者而言,則這種嚴格的聲律,卻不僅不是死板的約束,而且還可以成為一種呼喚起感發之力量的媒介。所以舊傳統的詩人一般都注重吟誦。就以杜甫而言,他的詩中就有不少提及作詩時常與吟詠相結合的例證。即如其《解悶十二首》之七中的「新詩改罷自長吟」、《題鄭十八著作丈故居》中的「詩罷能吟不復聽」、《至後》中的「詩成吟詠轉淒涼」諸句,就都表現了杜甫寫詩時是注重吟誦的。而這種吟誦的習慣對於寫作聲律嚴格的近體詩,實在極為重要。因為寫作舊體詩的詩人,他們一般並不是逐字逐句去核對平仄和聲韻來寫詩的,他們的詩句是在形成時就已經與聲律之感發結合在一起了。然後在修改時,也不是檢查著字書、韻書去修改,而是在邊寫邊吟的情況中,同樣伴隨著吟誦的聲律去修改的。無論在詩句的形成中,或在詩句的修改中,聲律所呼喚起的一種感發,在舊體詩的寫作中,都是極值得重視的。而我以為這也就正是中國詩歌傳統一向都以感發為其主要質素的許多原因之一。前文所引高、梅二教授對杜甫此八詩的「語音之模式」之分析,正可以作為杜甫寫詩時,其音聲之感發與情意之感發密切結合的最好證明。我們後人說詩,可以自其形成後之結果作出細密的理論之分析。但杜甫當日寫詩時,卻並沒有理論的思索,而是僅憑吟誦時之聲律所呼喚起的一種直覺而寫成的。至於就新體詩而言,則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新體詩歌雖然也重視音聲之效果,可是卻並沒有一定的格式可以依循,在這種情形下,新體詩之寫作,一方面雖在形式上獲得了極大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卻也同時失去了經由聲律而呼喚起感發,和經由聲律而加強字句之鍛煉的一種輔助的條件。因此資質和才能優秀的詩人,雖可以在自己對形式的自由安排設計中,創作出內容與形式密切結合的精美的作品,而資質才能有所不足的詩人,則在此絕對的自由中,便不免會或者故求艱澀或者掉以輕心,而寫出一些迷亂粗糙的失敗的作品了。要想避免此種流弊,則對於中國古典詩歌中的一些典範作品,如杜甫《秋興》八詩一類工力深醇藝術精美的詩篇,若能加以仔細的研讀和體會,則對於寫新體詩的年輕人要想養成更精切的掌握和運用中國文字的能力,也定能有所助益。
這是我二十年前編寫此書時,對台灣年輕詩人的期望,也是我今日重新增輯此書再次出版時,對大陸年輕詩人的期望。而在前面所曾提出的東方與西方理論之結合、文學研究與科學技術之結合、台灣與大陸學術之結合以外,如能再加以古典與現代之結合,則我們的學術研究與詩歌創作,都必將收到更為豐美的果實,和開拓出更為廣闊的道路。在此增輯版出版的前夕,謹拉雜書寫與此一冊《集說》有關的情事和想法如上,希望能得到廣大讀者的批評和指正。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葉嘉瑩說杜甫詩套書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葉嘉瑩說杜甫詩套書
葉嘉瑩說杜甫詩
在唐朝詩歌的歷史演進中,杜甫是一位集大成的人物,
他的詩作中,有相當一部分反映的是他現實中的生活,所以被稱為「詩史」。
葉嘉瑩先生結合杜甫的生平,融入自己對於詩歌感發生命的理解,
深入講解杜甫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尤其對〈秋興八首〉作了詳細的解讀。
杜甫秋興八首集說
葉嘉瑩先生在本書中以〈秋興八首〉為例,
展現了杜甫詩歌之集大成的成就,可以作為現代詩人之借鑒。
並先後選輯了自宋迄清的杜詩注本53家,不同之版本70種,
考訂異同,在仔細研讀和體會中將古典與現代結合,
希望對新詩創作和學術研究都能有所助益。
作者簡介:
葉嘉瑩 1924年生。1945年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國文系。自1945年開始,任教生涯長達六十五年以上。曾在台灣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任教十五年之久,1969年赴加拿大,被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聘為終身教授,並曾先後被美國、馬來西亞、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多所大學以及大陸數十所大學聘為客座教授及訪問教授。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是加拿大皇家學會有史以來唯一的中國古典文學院士。此外,還受聘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名譽研究員及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並獲得香港嶺南大學榮譽博士、臺灣輔仁大學傑出校友獎與斐陶斐傑出成就獎。2012年被中國中央文史館聘為終身館員。
1993年葉嘉瑩教授在天津南開大學創辦了「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並捐獻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萬美金)設立了「駝庵獎學金」和「永言學術基金」,用以吸引和培養優秀人才,從事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普及和研究工作。
著作有: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中國詞學的現代觀》、《唐宋詞十七講》等多種著作。
TOP
章節試閱
葉嘉瑩說杜甫詩
從中唐以來,像元稹以及後來的秦觀等人都這樣讚美過杜甫,為什麼有很多人讚美杜甫,說他是一個「集大成」的詩人呢?
在中國的詩人裡邊,不同的人有各種不同的成就。有些人七言詩寫得好,有些人五言詩寫得好,有些人古體詩寫得好,有些人近體詩寫得好。李白的詩我們也講過了,像他那些長篇的七言歌行和短小的五言絕句寫得就很好,可是我們沒有講李白的七言律詩,因為他的七言律詩沒有太好的作品。這是以體裁而言,如果再以內容而言,有些人善於寫大自然,比如王維的詩,我說他那些寫自然景物的五言詩能夠給人一種感動和觸...
從中唐以來,像元稹以及後來的秦觀等人都這樣讚美過杜甫,為什麼有很多人讚美杜甫,說他是一個「集大成」的詩人呢?
在中國的詩人裡邊,不同的人有各種不同的成就。有些人七言詩寫得好,有些人五言詩寫得好,有些人古體詩寫得好,有些人近體詩寫得好。李白的詩我們也講過了,像他那些長篇的七言歌行和短小的五言絕句寫得就很好,可是我們沒有講李白的七言律詩,因為他的七言律詩沒有太好的作品。這是以體裁而言,如果再以內容而言,有些人善於寫大自然,比如王維的詩,我說他那些寫自然景物的五言詩能夠給人一種感動和觸...
»看全部
TOP
目錄
葉嘉瑩說杜甫詩
葉嘉瑩作品集序言
導言
早期生活及詩作
房兵曹胡馬
望嶽
在長安求仕時期之生活及詩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官定後戲贈
安史之亂將起時的一篇名作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身陷長安時的作品
哀江頭
對雪
悲陳陶
脫身至行在後的作品
喜達行在所
述懷
羌村三首
長安收復後官拾遺時的作品
曲江二首
春宿左省
晚出左掖
題省中院壁
自左拾遺移官華州又離華州經秦州輾轉至同谷時期的詩作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居蜀及離蜀後飄泊西南之作
聞宮軍收河南河北
登岳陽樓
...
葉嘉瑩作品集序言
導言
早期生活及詩作
房兵曹胡馬
望嶽
在長安求仕時期之生活及詩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官定後戲贈
安史之亂將起時的一篇名作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身陷長安時的作品
哀江頭
對雪
悲陳陶
脫身至行在後的作品
喜達行在所
述懷
羌村三首
長安收復後官拾遺時的作品
曲江二首
春宿左省
晚出左掖
題省中院壁
自左拾遺移官華州又離華州經秦州輾轉至同谷時期的詩作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居蜀及離蜀後飄泊西南之作
聞宮軍收河南河北
登岳陽樓
...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葉嘉瑩
- 出版社: 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出版日期:2012-12-0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805頁
- 商品尺寸:長:230mm \ 寬:170m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中國古典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