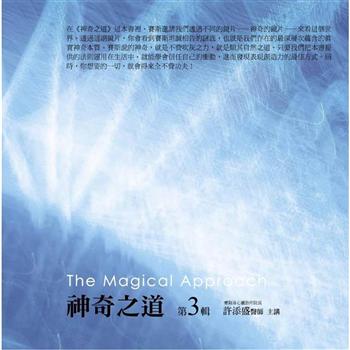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俗女養成記(電視劇書衣版)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8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05 |
華人文學 |
$ 205 |
電影 / 電視原著 |
$ 205 |
社會學 |
$ 205 |
Psychological & Relationships |
$ 205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21 |
社會人文 |
$ 229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圖書名稱:俗女養成記(電視劇書衣版)
和台灣十大建設差不多時間出生,和台灣經濟一起長出來的六年級女孩啊,
蹣跚跨步之初,生命藍圖臨摹著淑女形象,
不料潮流與時代正在改寫「好家教」的定義,
六年級女人繼承的輪廓正在式微,
於是,她們聰明伶俐,卻聽從爸媽和老師說的話;
照顧好自己的功課,又主動幫忙家務;
待人溫文可親,自己則堅毅果敢;
長大後擁有一份穩當的工作,同時經營著一個齊備的婚姻;
最好玲瓏剔透但又福厚德潤;
懂得追趕新時代的先進也能體貼舊觀念的徬徨。
作者簡介
江鵝
六年級生,輔仁大學德文系畢業,是住在淡水的台南鄉下人。人生第一專長是在快門瞬間眨眼,第二專長是打包行李,其餘普通。養貓,做肥皂,目前處於「停下來想一想」的人生階段。著有《高跟鞋與蘑菇頭》,與另一個OL小芳閒聊上班心情,其餘的生活瑣碎寫在臉書粉絲頁「可對人言的二三事」www.facebook.com/things.to.be.talked.about/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 |||
| |||
| |||
| |||
|
|


 2019/08/03
2019/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