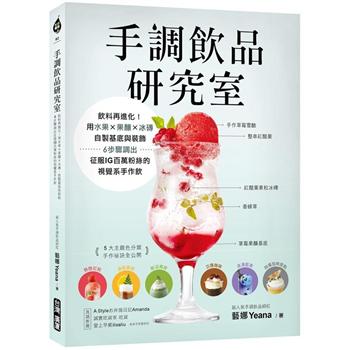【試閱1】生態學是什麼?(部份節錄)
▌那個吃什麼?
「那個吃什麼?」好幾年前,我的三歲兒子愛把這句話掛在嘴邊,他對四周的各種生物深深著迷。凡是恰好進入他視線的動物,都會令他產生這個疑問。身為父親的我,一心希望稚子培養更豐富的創意,對於他一再重複的提問感到氣餒,然而這個簡單的疑問不啻為生態學的核心重點。生態學主要在探討生物如何彼此互動,以及如何與環境互動。這包括牠們吃什麼,還有什麼東西會吃牠們。掠食者、獵物、植物、寄生蟲、病原體──都運用不同的食物封存策略來獲取能量,努力生存以及繁殖。不同的策略使大自然出現了一些樣態(pattern,見圖1)。究其根本,生態學其實就是力圖了解自然界中,是什麼樣的生物過程塑造出這些樣態。
當然,生態學不僅止於討論吃與被吃之間的關係所形成的樣態而已。生物會競爭稀少的資源,也會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牠們會改變周遭環境、創造交互作用的機制,並且在自然界中表現出新的樣態。牠們受限於周遭既複雜、又會隨時空變化的環境。人類也會藉由改變環境以及生物豐度(abundance,生物個體的數量),而左右生態樣態與過程。
我的孩子還小時,我們常去一座小池塘玩,夏天裡,那座池塘滿是蜻蜓和豆娘。「蜻蜓池塘」吸引了我兒子的注意力,他們認出許多從水面輕點而過的昆蟲,不需要任何課本,他們已對生物多樣性的概念略知一二。確定這些生物吃什麼以後,他們下一個問題必然就是:「那一個叫什麼?」知名物理學家理查.費曼(Richard Feynman)堅信「知識不是由名稱堆砌出來的」。就知識的嚴格定義來說,這句話或許沒錯,但我的孩子可不這麼認為。對動植物名稱的好奇心,促使他們發掘物種間的差異,而這些差異又讓他們確定,牠們確實是需要不同名稱的相異物種。更多疑問接踵而來:「那一個會做什麼?」「為什麼這一個總是待在樹林裡,另外那個卻在草地上?」他們開始察覺自然界有秩序與樣態了。生態學就是從這樣的樣態開始的。樣態使得「牠吃什麼?」這類問題含有生態學的趣味。以描述、鑑定及分類生物為內容的分類學(taxonomy)提供了一個基礎架構,藉由這個架構,我們能夠識別及理解生態學的樣態和交互作用。名稱開啟了觀察與探詢的新前景。費曼是極為優秀的物理學家,不過大概會是蹩腳的生態學家。
我在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工作,其西爾伍德園(Silwood Park)校區有大片草坪,夏天常看得到野兔。我兒子超愛追野兔,儘管根本追不上。不過,只要他們發現有狐狸鬼鬼祟祟地躲在樹林邊緣,就會馬上煞住腳步。他們鮮少看到狐狸,看到時會有些不安。他們知道狐狸吃野兔,但他們很疑惑:既然野兔這麼多,我們怎麼沒看到更多狐狸呢?向他們解釋一隻狐狸需要靠很多隻野兔才足以養活整個家庭,也就等於帶出生態學一項基本定律:隨著我們在食物鏈往上移動,由植物到吃植物的植食動物,到吃植食動物的肉食動物,可用的生物量(biomass,也就是活體生物的質量)會逐級遞減。消費者(consumer)建構生物量的能力受限於牠們取得食物的能力,也受限於牠們將食物能量轉換成生物量的能力。因此,狐狸的數量遠比野兔少。
並不是每年夏天都有那麼多野兔。有某幾年,很明顯地野兔零零稀稀。我兒子開始注意到,田鼠、橡實和山毛櫸果實也有類似的因年份而異的數量波動。某些年,西爾伍德園裡的小蘋果園結實纍纍;某些年,產量少到孩子們為了確保分到足夠的量,還要趕在住校的研究生之前採果。現在,我兒子開始提出資源波動(resource fluctuations)和族群動態(population dynamics)的問題了。或該說他們問的是:蜜蜂為什麼要飛去停在蘋果花上?蚯蚓在做什麼?刺蝟為什麼只在晚上才出來?岩槭的種子為什麼會旋轉?蘋果樹為什麼會長出蘋果?這些都是生態學的問題。
▌什麼是生態學?
生態學是科學,也是一門學科。它也是強調與環境連結的世界觀,廣義上可算是「環保主義」的同義詞。從科學及文化這兩種角度來詮釋生態學,會讓人困惑兩者之間如何有所關聯,不過也能藉著社會討論將一些生態學觸發的想法擴散出去。最後的結果就是,生態學成為社會政治及文化敘事中普及度相當高的科學。生態學思維遍及浪漫主義、唯心論、文學和政治領域,它已成為現代生活選擇以及政治方針的驅動力。
生態學作為學科時,關注的是生物之間,以及生物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生態學致力於描述這些樣態,並了解其形成機制。描述自然界的樣態往往很容易,譬如說,眾所皆知當我們從極地往熱帶移動,物種的數量會增加。至於理解樣態背後的原因則比較困難。有些理論探討物種豐富度(species richness,物種的數量)與非生物環境(abiotic environment,環境中沒有生命的成分,例如水、土壤、岩石、礦物、氣候等)、能量可及性、氣溫或降水量之間的關係;有些理論強調促進物種共存的生物交互作用。較普遍的物種可能承受疾病或掠食者高得不成比例的攻擊,而稀有物種也可能發展出特殊生存策略,有助於牠們在擁擠且競爭激烈的環境中長久續存。無論如何,對稀有物種有利的過程往往能支持更多的物種。
生態學與演化的整合架構密切相關,而演化基本上可說是生態交互作用的結果。古生物學家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的論文集《達爾文大震撼──課本學不到的生命史》(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探究了生態與演化的交互作用。古爾德本人對生態學無感,或許是因為他是古生物學家,唯有自然系統的歷史發展才能激起他的好奇心,而他在生態過程中看不出什麼具歷史意義的解釋。儘管古爾德興趣缺缺,其實生態學仍然有其歷史性觀點,十九世紀的地質學家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就看出來了。萊爾的地質學很明確地奠基於歷史觀點上,以可觀察到的地形抬升與侵蝕等自然過程為研究基礎。萊爾將此歷史觀點應用在生物世界,反駁靜態且缺乏歷史觀點的「自然平衡」論述,更偏向支持在播遷、掠食、競爭等生態過程中,而形塑的連續擾動(disruption)與變化。這為大自然開了一扇更有活力的詮釋之門,激發達爾文(Charles Darwin)、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等人以生態學的洞見發展出演化論。
以演化論的觀點為基礎,生態學才真的有意義。就本質上而言,生態結果就是演化過程的即時狀態。某物種的個體要與其他生物以及與環境交互作用,其中一項功能在於使該物種能長久續存。套用一句老套的戲劇比喻:環境就像舞台,所有互動都在其上演。在「演化」這齣戲裡,天擇是導演,而生態學就是戲碼。
【試閱2】族群(部分節錄)
▌旅鼠大爆發
據說旅鼠是會集體自殺的動物。這種生活在極地凍原的小型齧齒動物,每隔兩三年數量就會暴增,卻又往往在幾個月內就直線下墜(見圖5)。當生活條件對牠們有利時,旅鼠不到兩個月大就能達到性成熟,而且多數雌鼠能在夏季生育好幾次,每一次最多可生下六隻幼鼠。這種非凡的繁殖力,難怪能造就一飛沖天的數量成長。此時,包括鼬、雪鴞和北極狐等掠食者也會快速增加,但沒快到足以遏制旅鼠的數量。最終使旅鼠數量陡降的原因不是遭到獵食,而是食物耗竭。缺乏食物時,往往會使旅鼠大規模遷徙,去尋找更理想的草生地,而遷徙過程中死亡率很高,使牠們獲得自殺的名聲。然而,與其說是自殺,不如說旅鼠是缺乏遠見。
族群量會大起大落循環的並不只有旅鼠而已。所有熟悉園藝工作的人,必定都注意到了蚜蟲和田鼠會突然出現,讓你數個月的心血毀於一旦。非洲沙漠飛蝗大軍突然席捲而來,是《聖經》中有名的故事(見專欄1),並且可能對經濟和人類造成嚴重危害。與此類似,亞洲的鼠患每年造成的稻作損失,換算起來可以供養約兩億人。
///
【專欄1:蝗災】
沙漠飛蝗分布於茅利塔尼亞至印度,通常數量很少。然而若是遇上豐沛的降雨及隨後長出的新鮮植物,牠們就會快速增加。在兩到三個月內,就會形成一大群年輕無翅的若蟲和有翅的成蟲,占據的範圍經常可達五千平方公里左右。如果持續降雨,蝗蟲會移入鄰近有新鮮植物的區域,以倍數連續繁殖好幾代。這樣龐大數量成長所形成的群體,會吞噬掉整片區域。在天時地利之下,蝗災就發生了。蝗災時,每平方公里可能多達一億五千萬隻蝗蟲,而一平方公里的蝗災在一天之內就能吃掉三萬五千人份的糧食。
儘管蝗蟲數量激增是常有的事,其實很少會猛烈成長,達到蝗災程度又更稀少。容許這種極端數量成長的條件,是在廣大區域內可持續獲得新鮮食物,而這必須仰賴充沛的雨水。東非二○一九年末的豪雨導致二○二○年一月出現一大群蝗蟲,摧毀了索馬利亞、衣索比亞和肯亞的農作物。我於二○二○年一月底寫下這些文字的此刻,有些人正憂慮三月份的季節性降雨會使該區域大部分地區又長出新的植物。這可能使得繁殖速度飛快的蝗蟲,在六月較乾燥的天氣抑制牠們擴散之前,增加五百倍之多。在二○二○年之前,前一場大型蝗災發生在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後來二○○三年至二○○五年還有一次蝗蟲數量暴增,影響了整個薩赫爾地區(Sahel),從塞內加爾和茅利塔尼亞一直到紅海。
///
天氣和食物都是族群量爆發的原因。充沛的降雨會驅使植物生長和生產種子,旅鼠、蝗蟲或小型鼠類的數量都會因此而增加。溫和的冬天以及暖和的春天也幫了一把,因為冬季的死亡率會下降,讓族群量從繁殖季就居高不下。在加州、夏威夷、澳洲等不同地點,小型鼠類的數量爆發都是相同原因所致。溫和的冬天也造成大量小蠹蟲爆發,牠們目前正破壞遼闊的北美森林。
數量爆發的物種有個特徵,即牠們的「固有成長率」(intrinsic growth rate﹝r﹞)非常高;固有成長率指的是某物種有潛力達到的自然增加速率。這類物種典型的特徵包括:很早繁殖、繁殖頻率高、每次能產下的子代多。實際的數量成長率往往比固有成長率要低得多,因為大部分的年輕個體在性成熟前就夭折了。但如果環境條件有利,偶爾也確實如此,那麼許多子代就能存活下來並繁殖。接下來就是數量快速成長,形成族群大發生。很快讓資源供不應求,倏忽之間,那些個體又死光了。所以我們並沒有被旅鼠淹沒。
▌掠食者控制
另一種小型極地齧齒動物田鼠,其數量循環的特徵是緩緩上升,達到高峰後維持很久,下降時也比旅鼠來得逐步遞減(見圖5-b)。在高峰期的時候,雌田鼠的性成熟速度較慢,繁殖率也下降。田鼠吃的是快速生長的禾草,食物比較不虞匱乏。旅鼠的悲劇是將食物來源耗盡,田鼠則因為繁殖率較低,而能將數量高峰期延續到好幾年之久。最終是掠食者數量增加導致田鼠數量減少。奧爾多.李奧帕德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沙郡年紀》(A Sand County Almanac)中,生動地形容,若是將地景上的狼全都消滅,就像是交給「上帝嶄新的園藝剪,然後不准祂做別的事」。他的論點是,狼群消失後,鹿的數量會增加到某個程度,所有灌木和幼苗被吃到「先是半死不活,然後是無一倖免」。野生動物管理員運用這個論點來捍衛狼、猞猁、山獅和其他大型肉食動物的必要性,以控制植食動物的數量,對生態系帶來更廣泛的惠益(見專欄2)。
///
【專欄2:恐懼的地景】
對我們這些習慣安全祥和環境的人而言,與野生的狼或熊來個不期而遇,肯定會激發一股原始的恐懼。於是接下來我們在野外行動會更為謹慎,時時都全神貫注留意著周遭的狀況。獵物時常都懷著不安,與掠食者共處在相同空間,牠們的心情大概就像上面所述。在掠食者環伺之下,植食動物會更警戒和緊張。掠食者的足跡、氣味、吼叫和偶爾被瞥見的身影,都為獵物創造出不斷的警戒狀態。獵物腦中形成一幅「恐懼的地景」,以風險和安全的相對程度區分棲地和位置。
這幅恐懼的地景,僅僅因可能有掠食者存在就能創造出來。就生態學而言,可能比直接的獵食行為更具意義。絕跡六十年後,一九九五年美國黃石國家公園重新引入狼群,定居該地的紅鹿數量便直線下滑。下滑的程度遠超出獵食這單一因素的極限。原來紅鹿花了更多時間移動,覓食時間相對減少,只能養育三分之一的後代。在那之後,黃石國家公園內的柳樹和楊樹就變多了,因為能免於紅鹿的啃食,而這些起死回生的樹也是河狸愛吃的食物,所以河狸數量也跟著增加。
關於黃石國家公園生態系的變化,多大程度能歸因於狼群回歸,都未有定論。在加拿大卑詩省海灣群島(Gulf Islands)的岩石海岸上,實施的恐懼地景研究成果則較為明確。研究人員運用擴音設備,讓浣熊身處於犬吠聲(狗會獵殺浣熊)或是海豹叫聲(海豹不會獵殺浣熊)之中。聽到狗叫聲時,浣熊變得較為警戒,減少沿著海岸覓食的時間。於是海岸處潮池內的魚類、蠕蟲和螃蟹等生物量便顯著增加。
///
不過,要判定是掠食者在控制獵物數量,抑或受到其他因素控制的獵物數量,反過來調節著掠食者數量,其實相當困難。從哈德遜灣公司提供的毛皮紀錄,整理出的代表性資料集,展現出雪鞋兔和掠食者加拿大猞猁之間週期性的變動關係(見圖6)。多年來,學者都認為野兔受到猞猁獵食,能抑制其過多的數量,而這又會反過來減少猞猁的數量。猞猁變少後,野兔遭到獵食的壓力減輕了,因此又能繁殖興旺。再進一步使猞猁的數量增加,於是啟動新循環。然而,在一些沒有猞猁的島上,雪鞋兔的數量仍然會依循類似的十年週期循環。目前看起來,更大的可能是,大量野兔將食用的植物消耗殆盡,週期性的數量崩潰就會發生。在數量直線下跌後,植物慢慢長回來,於是野兔又增加。猞猁的數量可能只是跟著野兔數量變動而已。
▌競爭性調控
多數物種與旅鼠、田鼠和野兔不同,牠們會維持相對穩定的族群,儘管本質上擁有倍數成長的能力也不例外。一九五四年,英國生態學家及演化生物學家大衛.拉克(David Lack)如此描述:「大部分野生動物的數量都在一定範圍內不規律地波動,與牠們實際上最高的成長率相比,那個範圍極度狹窄。」沒有幾個物種的固有成長率能像旅鼠和田鼠那樣高,因此任何數量變化都會逐漸變化。掠食者也會發揮控制族群量的功能,不過更普遍的控制機制是「競爭」。
當必要的資源無法滿足族群中所有個體時,競爭就會發生。隨著族群成長,個體密度也會增加。個體密度低的時候,資源很豐富,個體的繁殖率和存活率都很高。理論上,族群成長率可以達到每個個體成長率的最大值,即固有成長率。然而密度增加後,每個個體能獲得的平均資源減少,於是個體為了有限的資源互相競爭。敗下陣來的生物將留下較少的子代,或是很早死去,這會減緩族群成長的速度。到最後,可得的資源可能極為稀少,以致於整個族群的死亡率高於出生率,因此族群量開始下降。每個個體能取得的資源,透過密度依變(density-dependent)的競爭,成為調節族群量的實際因素。
互相競爭的個體並不需要直接接觸。某一個體取用了有限資源,便會剝奪其他個體取得的機會,即使這些生物素未謀面也是如此。與此類似,某株植物可能耗盡土壤中的養分,而對鄰近的植物造成傷害。話雖如此,生物仍經常在競爭場地中直接廝殺。有些動物會捍衛專屬領域,積極地趕走競爭者,不讓其靠近資源。很多鳥類、哺乳類動物、魚類,甚至是昆蟲,都會捍衛領域,確保只有自己能靠近窩巢、獵食區或配偶。捍衛領域有時要付出高昂代價,必須時時消耗能量保持警戒,還可能受傷或死亡。因此動物只在資源極度稀缺時,才會占領及捍衛領域,因為,保護隨處可得的資源根本就沒有意義。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Jaboury的圖書 |
 |
$ 277 ~ 405 | 【牛津通識課27】生態學:理解我們的世界如何運作 (電子書)
作者:傑布里.哈蘇(Jaboury Ghazoul) / 譯者:聞若婷 出版社:日出出版 出版日期:2024-10-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初版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牛津通識課27】生態學:理解我們的世界如何運作
為什麼地球上有那麼多物種?
為什麼大型猛獸很罕見?
為什麼我們該關心生物多樣性的議題?
打開牛津大學出版社最受歡迎通識讀本,
用最簡明的方式認識生態、環境保護與我們的關係。
了解我們的生活環境如何運作,
本質上也就是對生態系統的研究。
生態學是研究生物如何交互作用及其與環境的關係,
以及這些交互作用如何創造自我組織的群落和生態系統的科學。
這門科學與我們息息相關。
我們吃的食物、喝的水、使用的自然資源、
身心健康以及我們的文化遺產,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生物與環境之間生態交互作用的產物。
本書作者探討了生態學如何由自然史快速演進為一門鑑往知來的學科,
不但有助於解釋自然界的運作方式,也能作為環保政策與管理決策的指引。
他援引各種實例,具體說明生態學能如何應用於管理和保育,
包括理論對做法發揮了什麼程度的影響。
生態學亦改變了人類施加於環境的社會和文化觀點,
而這會影響環境的政治學。
在本書的結尾,作者並探討了面臨當前與未來的環境挑戰,生態學將何去何從。
【你是知識控嗎?關於牛津通識課】
用最簡明直白的方式,了解現代人最需要知道的大問題。
牛津通識課(Very Short Introductions,簡稱VSI)是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的系列叢書,秉持「為所有讀者提供一個可讀性強且包羅萬千的工具書圖書館」的信念,於1995年首次推出,多年來已出版近700本讀物,內容涉及歷史、神學、藝術、哲學、文學、醫學、自然科學、政治等數十多種領域。每一本書對應一個主題,由該領域公認的專家撰寫,篇幅簡潔精煉,並提供進一步深度閱讀的建議,確保讀者讀完後能建立該主題的專業級知識框架。
作者簡介:
傑布里.哈蘇(Jaboury Ghazoul)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 Zurich)生態系統管理教授,及愛丁堡大學永續森林和地景中心(Centre for Sustainable Forests and Landscapes)主任。傑布里身為熱帶森林生態學家,曾於東南亞、印度、哥斯大黎加以及哥倫比亞工作。他已出版數本關於熱帶生態學和熱帶森林的著作,包括包括《森林:短篇導讀》(Forest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PU,2015)。
譯者簡介:
聞若婷
自由譯者,曾任職出版社編輯,喜歡動物。
譯作包括《我們為何成為貓奴》、《唐拔博士的狗狗訓練完全指南》、《孤獨世紀》、《獨帆之聲》。
【審訂者簡介】
林大利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副研究員、澳洲昆士蘭大學生物科學系博士。由於家裡經營漫畫店,從小學就在漫畫堆中長大。出門總是帶著書、會對著地圖發呆、算清楚自己看過幾種小鳥。是個龜毛的讀者,認為龜毛是探索世界的美德。
章節試閱
【試閱1】生態學是什麼?(部份節錄)
▌那個吃什麼?
「那個吃什麼?」好幾年前,我的三歲兒子愛把這句話掛在嘴邊,他對四周的各種生物深深著迷。凡是恰好進入他視線的動物,都會令他產生這個疑問。身為父親的我,一心希望稚子培養更豐富的創意,對於他一再重複的提問感到氣餒,然而這個簡單的疑問不啻為生態學的核心重點。生態學主要在探討生物如何彼此互動,以及如何與環境互動。這包括牠們吃什麼,還有什麼東西會吃牠們。掠食者、獵物、植物、寄生蟲、病原體──都運用不同的食物封存策略來獲取能量,努力生存以及繁殖。不同的策...
▌那個吃什麼?
「那個吃什麼?」好幾年前,我的三歲兒子愛把這句話掛在嘴邊,他對四周的各種生物深深著迷。凡是恰好進入他視線的動物,都會令他產生這個疑問。身為父親的我,一心希望稚子培養更豐富的創意,對於他一再重複的提問感到氣餒,然而這個簡單的疑問不啻為生態學的核心重點。生態學主要在探討生物如何彼此互動,以及如何與環境互動。這包括牠們吃什麼,還有什麼東西會吃牠們。掠食者、獵物、植物、寄生蟲、病原體──都運用不同的食物封存策略來獲取能量,努力生存以及繁殖。不同的策...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生態學是什麼?
那個吃什麼?/什麼是生態學/物理嫉妒/
生態學理論/生態學的世界觀
第二章 生態學的開端
古典生態學/系統生態學/洪堡德的自然分布圖/
生態群落/系統性思考/動物生態學與艾爾頓的生態棲位/
競爭與共存/自然的平衡?
第三章 族群
旅鼠大爆發/掠食者控制/競爭性調控/r和K策略/
決定性混沌/生活史取捨/功能性狀/播遷/
關聯族群/管理族群
第四章 群落
合作/不簡單的關係/忠實與不忠/層階/演替/
競爭與拓殖之間的取捨/那動物呢?/生態系/
營養結構/生物地球...
第一章 生態學是什麼?
那個吃什麼?/什麼是生態學/物理嫉妒/
生態學理論/生態學的世界觀
第二章 生態學的開端
古典生態學/系統生態學/洪堡德的自然分布圖/
生態群落/系統性思考/動物生態學與艾爾頓的生態棲位/
競爭與共存/自然的平衡?
第三章 族群
旅鼠大爆發/掠食者控制/競爭性調控/r和K策略/
決定性混沌/生活史取捨/功能性狀/播遷/
關聯族群/管理族群
第四章 群落
合作/不簡單的關係/忠實與不忠/層階/演替/
競爭與拓殖之間的取捨/那動物呢?/生態系/
營養結構/生物地球...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