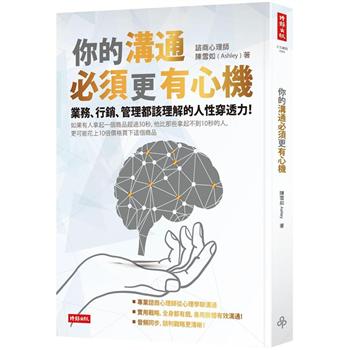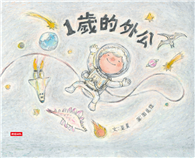【真愛挑日子】電影原著小說
◎ 英國暢銷書排行榜冠軍、《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 改編電影【真愛挑日子】由安.海瑟薇主演,2011年8月全臺上映
亞馬遜超過兩百位讀者近五顆星好評、理查與茱迪讀書俱樂部選書
《ELLE雜誌》2010年夏日十大好書選、英國衛報2009年度風雲書
《男人與男孩》作者東尼.帕森斯(Tony Parsons)、《謎宮(Labyrinth)》作者凱特.摩斯(Kate Mosse)、泰晤士報、鏡報、衛報、獨立報、《ESQUIRE君子雜誌》等媒體強力推薦
可能,你活了一生都還不曉得,
原來自己追尋的就在眼前……
「我可以想像你四十歲的樣子,」她用調侃的語氣說。「我現在就可以想像。」
他閉著雙眼,微笑著說,「繼續說。」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五日,艾瑪.摩利和達斯.麥修在他們畢業的前一夜相識,而第二天他們就要各奔前程了。
一年之後的這一天,他們會在哪裡?兩年後呢?之後的每一年呢?
二十年,同樣的兩個人,同樣的一天,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初識彼此時,他們僅一起度過一天,而在那之後,他們無法停止對彼此的想念。
這個故事歷時二十年,描述兩人每一年七月十五日那一天的生活。二十年裡,艾瑪和達斯當然有口角也有爭吵,生活中有希望,也曾錯失機會,有歡笑也有淚水。而對他們而言,這重要的一天所代表的意義,他們必須藉此了解愛和人生的本質……
作者簡介:
大衛.尼克斯 David Nicholls
大衛.尼克斯出生於一九六六年,來自英國漢普郡伊斯特列,曾就讀湯恩比綜合中學、巴頓裴佛利學院,一九八八年自布里斯托大學畢業,取得英國文學及戲劇學位。
大學畢業後大衛懷著演員的夢想,取得獎學金於紐約美國音樂影藝學院深造。一九九一年返回到倫敦,先後曾在幾家餐廳和酒吧工作,最後終於取得英國演員協會會員的身分。大衛現在與伴侶漢娜住在北倫敦,育有兩名子女。
大衛在開始寫作前是一名男演員,曾演出《猶豫不決(Cold Feet)》第三季、《火線救援(Rescue Me)》、《遇見你(I Saw You)》等片。他的第一部小說《戀愛學分(Starter for Ten)》,名列2004年「理查與茱迪讀書俱樂部」選書第一名,2006年拍成了電影。他還寫過多部受歡迎的電視劇本,曾經兩度被提名英國金像獎。
大衛的個人網站: www.davidnichollswriter.com
譯者簡介:
賴婷婷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職翻譯公司與新聞局國際輿情小組編譯。興趣是用文字演戲,信仰是翻譯。譯有《我只是骨架大》、《結婚友沒友》、《幸福來不來》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如果你容易為年輕時期的憂愁往事、白日夢或是獨特的回憶而傷感,那你一定要讀大衛.尼克斯的最新作品……讀的時候請千萬記得自己讀到哪了,相信你也會像其他人一樣,極欲知道這故事的答案。」──《紐約時報》
「耀眼無比的一本書,講述的是關於過去與現在的自己,那令人傷心的間隔……自《時空旅人之妻》之後最獨特的愛情佳作。」──東尼.帕森斯(Tony Parsons,《男人與男孩》作者)
「肯定是當代經典……在所有讀過的小說中,它絕對是最有趣、最觸動人心的愛情故事。」──《時人雜誌》
「大衛.尼克斯在描述時代精神,以及表現同理情感上有其天分,獨樹一格……他寫出了輕淡的描述卻呈現了令人感受深刻的愛情小說,徹底滿足讀者的心。」──《娛樂週刊》
「如果你夠幸運,你會遇見真正感動人心的故事。如果你夠幸運,你會遇見對你傾訴的角色。而在《One Day》這個故事裡,我同時找到了兩者。」——安.海瑟薇
名人推薦:「如果你容易為年輕時期的憂愁往事、白日夢或是獨特的回憶而傷感,那你一定要讀大衛.尼克斯的最新作品……讀的時候請千萬記得自己讀到哪了,相信你也會像其他人一樣,極欲知道這故事的答案。」──《紐約時報》
「耀眼無比的一本書,講述的是關於過去與現在的自己,那令人傷心的間隔……自《時空旅人之妻》之後最獨特的愛情佳作。」──東尼.帕森斯(Tony Parsons,《男人與男孩》作者)
「肯定是當代經典……在所有讀過的小說中,它絕對是最有趣、最觸動人心的愛情故事。」──《時人雜誌》
「大衛.尼克斯在描述時代精神...
章節試閱
第一章
關於未來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五日,星期五
愛丁堡,蘭開勒街
「我想重點是要有所改變,」她說。「你知道的,就是具體去改變些什麼。」
「什麼?妳是說類似『改變世界』嗎?」
「不是整個世界,只要改變自己周遭,一點點就夠了。」
暗夜裡,他們倆蜷在單人床上,靜靜躺著一會兒,然後開始笑著。黎明前,他們的聲音聽起來特別低啞。「天啊,你相信我剛剛說什麼嗎?」她不可置信地說。「我聽起來好八股,對吧?」
「有一點。」
「但我是在啟發你耶!我想提升你可悲的內在。畢竟不久後,我們就要面對人生的冒險。」她轉過身面對著他。「但我想你也不用人提醒,你應該早就規劃好了吧?搞不好連流程圖都畫好了呢!」
「怎麼可能。」
「好吧。那你想做什麼?未來有什麼打算?」
「我爸媽會先幫我把東西搬到他們那借放,接著到他們倫敦的公寓住幾天,和朋友們見面,然後去法國——」
「非常好——」
「再來可能會去中國,看看那裡究竟在幹嘛,還可能會去印度旅行——」
「旅行,」她嘆了口氣說。「好老套。」
「旅行有什麼不對嗎?」
「是逃避現實吧。」
「我認為大家過份高估現實的重要性了,」他暗自希望這番話聽起來高深莫測又迷人。
她哼了聲。「也許吧,反正負擔得起就好,但你怎麼不說『我要去放假兩年』?說穿了不就是這樣?」
「旅行可以開拓心胸,」他邊說邊抬起手肘,然後親吻她。
「喔,這樣的話,我想你的心胸未免太開放了,」她把臉別過去,一會兒後他們又再次靠在枕頭上。「總之,我不是問你下個月要做什麼。我是說未來,你以後想做什麼?就是,我也不知道……」她頓了下,接著好似想到什麼超新奇的點子(像五度空間之類的),她接著說:「……四十歲!你希望自己四十歲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四十?」他看起來很難接受這想法。「不知道。可以回答『很有錢』嗎?」
「那好……好膚淺。」
「好吧,那『很有名』。」他的鼻子輕輕碰著她的脖子,「聽起來很討人厭嗎?」
「不是很討人厭,是很……新鮮刺激呢。」
「『新鮮刺激呢!』」他模仿她輕柔的約克郡(譯注:Yorkshire,英格蘭東北部的一個歷史郡。)口音,把她學得像個笨蛋。這種情況她見慣了,那些時髦的男孩子就喜歡這樣,好像這腔調有多稀奇古怪,突然間,討厭他的感覺令她顫抖一下,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她聳個肩轉過身去,背部貼著冰涼的牆壁。
「是啊,刺激,人生在世就是要活得有挑戰,不是嗎?為了所有的可能而奮鬥。副校長也曾經說過:『機會的大門會為你而敞開……』」
「『有朝一日,你可能會名留青史……』」
「不太可能。」
「所以,為什麼會新鮮刺激?」
「喔,不,我在胡言亂語。」
「我也是。天啊……」他突然轉過身去,伸手在床邊地板上找菸,彷彿想穩定自己緊張的心情。「什麼四十歲,他媽的四十歲。」
她對著焦慮的他微笑,決定說得更絕,「所以,你四十歲究竟會是什麼樣子呢?」
他邊點煙邊沉思。「嗯,是這樣的,小艾——」
「『小艾』是哪位?」
「大家都這樣叫啊,我聽見他們這麼叫小艾。」
「沒錯,我朋友確實叫我小艾。」
「那我可以叫妳小艾嗎?」
「好,你繼續說吧。」
「總之,關於『變老』這件事,我決定要維持像現在這樣。」
這就是達斯.麥修。她抬起頭,視線穿過瀏海看著他,他的身體靠在廉價的塑膠床頭上,即使沒戴眼鏡,她也很明白為何他想「維持像現在這樣」。他的雙眼緊閉,嘴裡漫不經心地刁著菸,側臉映著透過紅色簾幕的溫暖曙光,一副隨時準備拍照的模樣。看著這幕,艾瑪.摩利只想到「好看」兩個字,很蠢很老套,但卻沒有更貼切的字眼了,「帥氣」或許也可以。他輪廓深刻,皮膚下的線條讓人無法忽視,彷彿就算只剩骷髏也還充滿魅力。精緻的鼻樑泛著亮光,眼睛下膚色深沉,看起來有點像瘀青,但那是抽菸、熬夜以及和比戴爾女郎們玩脫衣撲克(他還故意輸)的結果。他的樣子有點像貓:眉毛細緻,豐厚而深色的雙唇刻意微微噘起,但現在有點乾裂而且染上了保加利亞葡萄酒的色澤。幸好他留著一頭亂髮,後面和側邊削得很短,因為現在沒上髮膠,前面的捲髮看起來蓬鬆的像頂笨拙的帽子。
他閉著雙眼,鼻子呼出一口氣,他知道有雙眼睛正注視著他,所以將手夾在腋下,用力顯出胸肌和二頭肌。那結實肌肉究竟是哪來的?顯然不是因為運動(除非裸泳、玩水也算運動),那應該是家族遺傳,這種東西就像可以繼承的股票、股份以及高級家具。帥氣也好,好看也罷,大學四年的最後一天,他睡在她狹小的外宿房間裡那張單人床上,他身上的多色渦紋四角褲拉到髖骨邊。「帥氣」,妳以為妳是誰?十九世紀的簡愛嗎?成熟點,理性點!別再胡思亂想了。
她拿走從他嘴上的菸。「我可以想像你四十歲的樣子,」她不懷好意地說。「我現在就可以想像。」
他閉著雙眼,微笑著說,「繼續說。」
「好——」她從床上坐起,把羽絨被塞到腋下。「你會開著敞篷跑車行經肯辛頓或雀兒喜區,最棒的是這輛跑車一點噪音都沒有,因為所有的車到了,我不確定,大概二○○六年吧,都會沒有噪音。」
他皺著雙眼在心裡默算,然後說:「是二○○四年——」
「你駕著跑車,離地十五公分向前狂飆,朝著國王路駛去,小肥肚頂著方向盤的皮革,手就像放在枕頭上;你頭髮稀疏,胖得不見下巴;你身形臃腫,擠在一輛小車裡;你曬得像隻油亮的烤火雞——」
「我們可以換個話題嗎?」
「你身旁坐著個戴太陽眼鏡的女人,她是你第三任,不,第四任老婆,大約二十三歲,是位非常漂亮的模特兒,不,那是她過去的工作。你們在尼斯或是哪裡的車展上相遇,當時她正躺在引擎蓋上做裝飾,臉蛋美麗的令人驚嘆,妝厚得跟鬼一樣——」
「謝謝妳,聽起來真不錯。我有孩子嗎?」
「你沒有孩子,你就離過三次婚。喔,然後那天是七月的某個週五,你們正驅車前往鄉間的度假小屋,小小的後車箱裝著你們的網球拍、槌球拍、一大籃美酒、小鵪鶉肉以及蘆筍。風吹過窗戶頂,你很滿意那樣的生活。第三還是第四任老婆對你微笑,秀出一口閃亮兩百倍的白晰貝齒,你也對她微笑,並試著忽略你們倆無話可說的窘境。」
艾瑪突然停住,心想:拜託別這樣,妳聽起來簡直像個瘋子。「當然啦,可能不到四十歲,我們就死於核武大戰,可能根本活不到那個時候!」她的口氣瞬間開朗明亮,但是他依舊皺著眉頭。
「也許我該離開了,如果我真像妳說的如此膚淺墮落——」
「不,別走,」她很快地說。「現在是凌晨四點。」
他翻了個身對著她的臉。「我不知道妳對我的這些想法是哪來的,妳根本就不懂我。」
「我知道你這種人。」
「我這種人?」
「我看過你,四處閒晃,對別人大聲說話,把整個正式的晚餐派對給搞砸——」
「我連個黑色領帶都沒有,哪能參加什麼正式晚餐派對,而且我肯定也沒有大聲說話——」
「如果我這麼糟糕——」現在他的手放在她的唇上。
「——你是。」
「——那妳為什麼要跟我上床?他的手放在她溫暖的大腿內側。」
「嚴格上來說,我沒有跟你上床,我有嗎?」
「這得看,」他俯身親吻她。「妳對這兩個字的定義是什麼。」他的手放在她背脊的下方,雙腿滑進她的雙腿之間。
「還有,」她喃喃地說,然後雙唇緊壓著他的唇。
「什麼?」他感覺她的雙腿像條蛇攀著他,把他繫得更近。
「你得刷個牙。」
「妳沒刷我不在意啊。」
「這太可怕了,」她笑著說。「你聞起來就像葡萄酒和菸草。」
「這沒關係吧,妳聞起來也是這個味道啊。」
她迅速撇過頭,中斷這個吻。「有嗎?」
「我不在意啊。我喜歡葡萄酒和菸草。」
「我一秒鐘都受不了。」她把羽絨被丟回給他,爬過他身上。
「妳要去哪?」他把手放在她赤裸的背上。
「廁所,」她從床邊書堆拿起一副國民保健指定眼鏡,標準的黑色大粗框。
她站起來,隻手抱胸,背對他說:「不要走開,」然後步出房間。她用兩隻手指勾住底褲邊,拉到大腿上,邊走邊對著他說,「我出去時,不要亂動房間。」
他用鼻子呼口氣,翻身坐起,瞄了眼這破破爛爛的小房間。裡面充滿各種藝術明信片與舞臺劇複印海報(不滿社會現況的舞臺劇),他確定裡面絕對有曼德拉的照片,搞不好那還是她的理想男友。這四年來他在這城市裡看過許多這樣的房間,每間都像是犯罪現場,而且肯定有妮娜.西蒙的專輯。雖然他很少拜訪同個房間兩次以上,但這一切都太熟悉了——燒盡的夜燈、枯萎的盆栽、尺寸不合且瀰漫洗衣粉味的廉價被單。她大概是那種著迷於蒙太奇裝飾而且附庸風雅的女孩子,她會拿大學同學和家人的隨意照,混搭夏卡爾、維梅爾、康丁斯基、切.格拉瓦、伍迪.愛倫以及塞繆爾.貝克特等人的畫作及照片。這房間裡的一切都無法中立存在,所有東西都呈現她的忠誠或觀點,並且帶著宣示的意味。達斯嘆了嘆,他覺得她就是那種會濫用「中產階級」這四個字的女孩。他可以理解為什麼「法西斯主義者」帶有貶義,但是他很喜歡「中產階級」這四個字以及其中的意涵——穩定、旅行、美食、禮儀、野心。難道他要為這些感到抱歉嗎?
他看著煙從嘴邊捲起,想找煙灰缸,便在床舖旁發現一本書,書名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譯注: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於一九八四年所撰寫之小說,背景設於布拉格,內容涉及相當多的哲學觀念。),書脊上染了性愛過後的痕跡。像這種極度崇尚個人主義的女孩最大的問題是——其實她們根本都一樣。他又看到另一本書:《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譯注: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為美國神經學家奧利佛.薩克斯的首部神經病學案例書,於一九八五年出版。),他心想:還真是個又笨又可憐的男人,他有自信絕對不會犯這種錯誤。
達斯.麥修現年二十三歲,他對未來的想法並不比艾瑪.摩利來得清楚。他希望自己能功成名就,讓雙親感到驕傲且同時和不同的女人上床,但如何才能魚與熊掌兼得呢?他想替雜誌撰文,希望有天能出版回顧作品集,雖然他對這份工作一點概念也沒有。他想竭盡所能地活著,卻不想過一團混亂又複雜的生活。他的希望是,如果攝影師要拍攝他的生活,隨時隨地都能拍出一張很酷的照片。他希望自己的生活要正確到位,要充滿樂趣,甚至只有樂趣,至於悲傷,如果不必要,最好不要有。
這其實不算計畫,而且光是今晚就已經出錯了。今晚原本應該是個惆悵的夜晚,要充滿淚水,要怯懦地通話告別,要回顧過去的錯誤。或許他應該盡早離開,他看了眼散落在地上的衣服,準備逃跑。這時浴室傳來一陣咯咯的警告聲,老舊的馬桶水箱發出砰!的一聲,他迅速把書本放回去,同時在床下找到一個黃色的柯曼芥末醬鐵罐,打開蓋子,果然不出所料,裡面裝著保險套,還有一點大麻煙的灰色殘渣,像老鼠大便一樣。黃色鐵罐裡的性愛和毒品證據,讓他的心裡又燃起一絲希望,決定至少再留久一點。
浴室裡,艾瑪.摩利把牙膏擠在牙刷上,刷洗嘴角,心裡想著,這會不會是個錯誤的決定。過去四年,她的感情世界極度荒涼,而現在她終於能和自己喜歡的人同床共枕了。一九八四年她第一次在派對上見到這個男孩,當時就喜歡上他了,然而再過幾個小時,他又要離開了,而且可能是永遠地離開,他當然也不可能問她要不要一起去中國(更何況她打算以行動抵制中國)。達斯.麥修這個人還算不錯,不是嗎?其實她懷疑這男人並沒有那麼聰明,而且可能過度自滿,但他既受歡迎又風趣,而且毫無疑問地——他非常帥氣。所以為什麼她的態度要這麼難搞,口氣又這麼的酸呢?為什麼她不能就表現出自己自信風趣的那面?就像那些常和他約會、活潑又亮麗的女孩們。她從這間小浴室的窗戶看見黎明微光,這裡有的盡是嚴肅冷靜的氛圍。她用指尖抓了抓那頭亂髮,抬起頭來,拉下老舊馬桶水箱的沖水閥,然後往房間走去。
達斯從床上看見她出現在門邊,她穿著長袍,戴著為畢業典禮租借的學士帽,把腳勾起來靠在門框邊,非常性感的樣子,轉了轉手中那捲畢業證書,她把學士帽拉低,視線穿過鏡片,問他說:「你覺得怎麼樣?」
「很適合妳,帽子的角度很漂亮,快脫下帽子回到床上吧!」
「不要!這可花了我三十英鎊呢!可得好好利用。」她穿著長袍服轉來轉去,看起來像吸血鬼穿的斗篷,達斯抓住袍服邊,她立刻用畢業證書把他的手拍掉,然後她坐在床邊,收起眼鏡,脫下袍服。他瞥了眼她赤裸的背部與雙峰曲線,然後她的雙峰就消失在一件訴求單邊核武軍裁的T恤之下。算了吧,他心想,黑色的政治意味T恤絕對是世界上最滅人性致的東西,其次是崔西查普曼的專輯。
他放棄了,於是他撿起地上的畢業證書,把橡皮套拆下來,大聲唸著:「英國文學與歷史學雙修,全班第一名。」
「看了很想哭吧,二級二等學位畢業的男孩。」說完她把卷軸拿回來。「呃,小心一點。」
「妳會拿去裱框吧?」
「我媽和我爸打算把它當壁紙。」她把畢業證書捲得更緊,把邊邊黏緊。「或是拿來墊東西,我媽甚至還想把它刻在背上。」
「所以,他們現在住哪?」
「喔,他們就住隔壁啊。」
他突然一陣退縮。「天啊。真的嗎?」
她笑了。「假的啦。他們開車回里茲(譯注:Leeds,英格蘭西約克郡最大的城市。)了,我爸覺得飯店是給花花公子們住的地方。」她把畢業證書捲軸藏在床舖下。「你往上面移一下,」她將他輕輕往床墊較涼的那側推,他讓她進來,他的手臂繞著她的肩膀,有點害羞的感覺,並試探性地親吻著她的頸子。她轉頭看著他,下巴縮進被窩裡。
「達斯?」
「嗯。」
「我們抱抱就好了,好不好?」
「當然啊,如果妳這麼想的話,」他紳士地說,雖然事實上他根本不懂抱抱的意義何在,抱抱不是對阿姨或是泰迪熊才會做的事嗎?想到抱抱就令他腳抽筋,他覺得自己最好現在就放棄,越早回家越好,但她枕在他的肩上,佔有地把他當枕頭,他們就這樣躺了一會兒,姿勢僵硬且意識清醒,然後她說:「真不敢相信我竟然用了『抱抱』這兩個字,也太噁了——『抱抱』,實在很抱歉。」
他微笑著。「沒關係,還好妳沒用『親親』這兩個字。」
「『親親』是真的滿糟糕的。」
「或是『親熱』。」
「『親熱』真的是糟透了。我們要答應彼此,永遠,絕不會用『親熱』這兩個字,」說完她又後悔了。這表示他們還會在一起嗎?但機會看起來似乎是微乎其微。他們倆又再次陷入沉默。過去八個小時裡,他們說話、親吻,所以到了接近黎明時,兩人都只剩疲憊的身軀而已。這時,外面雜草叢生的花園裡傳來了黑鳥唱歌的聲音。
「我好愛這個聲音,」他對著她的頭髮低聲呢喃。「黎明時的黑鳥。」
「我討厭這聲音,讓我想到自己是否做了什麼會後悔的事情。」
「這就是我喜歡它的原因,」他的話語針對著她的看法,這麼說是為了塑造出個性黑暗、迷人的印象。一會兒過後,他又說:「為什麼這麼說?妳做過嗎?」
「什麼?」
「妳做過讓自己後悔的事嗎?」
「什麼意思?你是說這樣嗎?」她捏了下他的手。「喔,我還以為你指得是現在這樣。我也不知道,我有嗎?為什麼一大早問我這個問題?那你有嗎?」
他的嘴唇覆在她的頭上,「當然沒有啊,」他說,並心想:絕對、絕對不能再發生。
她很滿意這個答案,並蜷起身體更靠近他。「我們應該睡一下。」
「為什麼?明天沒事啊,不用交報告,不用工作……」
「明天開始眼前就完全是我們自己的生活了,」她愛睏地說。她吸一口氣,聞到他身上那股美好溫暖而混濁的氣味。「獨立社會人士生活」這幾個字突然掠過她腦中,肩上不禁地泛起一陣焦慮的漣漪。她不認為自己已經是成熟社會人士,她還沒準備好,這就像是深夜裡,火警突然響起,她只能匆忙逃跑,手裡拿著一堆衣服站在大街上。如果不用上課,那她又該做什麼?如何才能填滿每天的生活?她完全不知道。
最弔詭的是,即便如此她還是告訴自己要勇敢大膽地改變,不是改變這世界,而是改變自己的生活。她心想:自己應該帶著那雙重一級榮譽學位(譯注:Double-first,英國大學生畢業時會按照成績優劣授予學位,一級榮譽學位最優秀,其次為二級一等學位、二級二等學位、三級學位,或是不及格等。雙重一級榮譽學位是相當優秀罕見的。)、熱情,以及新買的電動打字機見見學校之外的世面,在某個行業裡努力奮鬥……。她應該藉藝術來改變生活,寫很棒的文章,珍惜朋友,堅持自我的原則,熱情努力地使生活更加圓滿,真真切切地體驗新的事物,如果可以的話努力地愛人與被愛,有意識地飲食,諸如此類的。
這不是什麼人生哲學,也不是那種可以與他人分享的大道理(至少她無法和眼前的男人分享),這是她的信仰。目前為止,她的獨立的社會人士生活已經開始幾個小時了,感覺一切都還可以。也許到了早上,喝杯茶吞顆阿斯匹靈後,她會鼓起勇氣叫他回到床上,但那時他們倆就清醒了,這樣一切就更難了,但或許她會樂在其中吧。她曾經和幾個男孩子上過床,結果不是咯咯的笑聲就是難過的哭聲,或許介於高興與難過之間的感覺也不錯吧。她心想,不知道那芥末醬的鐵罐裡是否還有保險套,照理說應該是有的,上次看的時候還有,那是一九八七年二月,對方是個背部毛髮濃密的男人,名字叫做文斯,是個化學工程師,他還在她的枕頭套上擤鼻子。美好的時光,真是美好的時光啊……
外面天色開始變亮。達斯看見外面光線滲過厚重的冬季窗簾,照進這外宿的小房間,那是新一天的粉色光線。他小心翼翼地移動以免驚醒她,伸出手臂把菸蒂丟進裝著葡萄酒的馬克杯裡,抬頭看著天花板,現在沒什麼機會睡覺了,他想就這麼盯著灰色的天花板看吧,直到她完全入睡,他會偷偷溜出去,不會吵醒她。
他心想現在離開意味著,大概永遠不會見到她,不知她是否會在意,假設會在意(一般人都會在意),那他又會在意嗎?過去四年,他一個人也過得很好。直到昨晚在派對上見到她,以為她叫安娜,他的視線就無法從她身上移開,為什麼他到現在才注意到這女孩?他仔細端詳她的睡臉。
她很漂亮,但她自己似乎覺得漂亮很麻煩。她有一頭酒紅色的髮,但髮型很糟糕,大概是自己對著鏡子剪出來的,或是她的室友提莉(誰管她叫什麼名字),那個粗手粗腳的大隻女幫她剪得。艾瑪的膚色蒼白,有點浮腫,說明她可能花太多時間在圖書館或是在酒吧裡喝太多酒,眼鏡讓她看起來嚴肅又拘謹,下巴有點柔軟圓潤,不過也可能是因為嬰兒肥(或許不能說「圓潤」也不能說「嬰兒肥」,就像你絕不能說她胸部很大,就算是真的,她還是會覺得有點被冒犯)。
無論如何,重點回到她臉上。她小巧白淨的鼻尖上泛了點光亮,前額上灑落許多小紅斑,除此之外,這確實張美麗的臉。看著她緊閉的雙眼,他無法想起那雙眼究竟是什麼顏色,只記得那雙眼的慧黠與幽默,就像她的大嘴旁邊的那兩條紋路,微笑時會更加深刻,正好她也常笑。她的雙頰平滑,透著粉嫩的紅,散著細碎的斑點,柔軟的像枕頭,肯定是很溫暖的觸感。她沒有擦口紅,微笑時,那柔潤的苺色雙唇也緊閉著,彷彿是不想露出那比例有點過大、缺了點的牙齒,所以總給人有所保留的感覺,感覺特意保留了笑意或聰明的評論,或是一個很棒的私密笑話。
如果現在離開,大概永遠都見不到這張臉了,除非這十年間舉辦了什麼可怕的聚會。她可能會變成一個胖女人,失望地抱怨著他偷偷溜走,連聲再見都沒說。想到這,他還是覺得默默離開,不要辦什麼聚會比較好。向前邁進,看著未來的路,外面還有很多美麗的臉呢。
但當他這麼決定時,她的嘴唇漾出一抹寬闊的微笑,閉著眼睛說:
「所以,達斯,你覺得怎麼樣?」
「小艾,妳指得是什麼?」
「我和你。你覺得這是愛情嗎?」她低聲笑了笑,但雙唇還是緊閉著。
「睡覺吧,好嗎?」
「那你就別再盯著我的鼻子瞧。」她睜開眼睛,一邊藍色,一邊綠色,眼神明亮又機靈的感覺。「明天是星期幾?」她喃喃地說。
「妳是說今天吧?」
「今天。就是在我們眼前的這全新的一天。」
「是星期五,整天都是星期五,也是聖瑞信日。」
「所以呢?」
「依據傳統的說法,如果今天下雨,那未來四十天都會下雨,或是整個夏天會下雨,諸如此類的。」
她皺著眉。「這聽起來不合理。」
「這不需要合理,這是迷信。」
「是指哪裡下雨?每天總有某個地方在下雨。」
「聖瑞信之墓,他被葬在溫徹斯特大教堂外面。」
「你怎麼會知道這些?」
「我以前的學校在那。」
「嗯,啦——滴——答,」她對著枕頭咕噥著。
「若聖瑞信日真下雨/彷彿又有大事將至。」
「這真是一首很棒的詩。」
「我在改述這首詩。」
她又笑了笑,然後疲倦地抬起頭說:「但是,達斯,」
「怎樣,小艾?」
「如果今天沒下雨呢?」
「嗯——嗯。」
「那你晚點要做什麼?」
告訴她你很忙。
「沒什麼事,」他說。
「所以我們該找些事做嗎?我是說,我和你。」
等到她睡著,就趕緊溜走。
「嗯,好啊,」他說。「找些事做吧。」
她再次把頭靠在枕頭上。
「這是全新的一天呢,」她低聲道。
「是全新的一天啊。」
第一章
關於未來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五日,星期五
愛丁堡,蘭開勒街
「我想重點是要有所改變,」她說。「你知道的,就是具體去改變些什麼。」
「什麼?妳是說類似『改變世界』嗎?」
「不是整個世界,只要改變自己周遭,一點點就夠了。」
暗夜裡,他們倆蜷在單人床上,靜靜躺著一會兒,然後開始笑著。黎明前,他們的聲音聽起來特別低啞。「天啊,你相信我剛剛說什麼嗎?」她不可置信地說。「我聽起來好八股,對吧?」
「有一點。」
「但我是在啟發你耶!我想提升你可悲的內在。畢竟不久後,我們就要面對人生的冒險。」她轉過身面...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