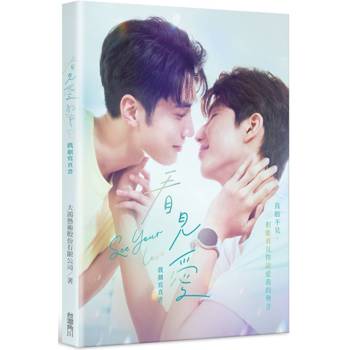如果十號孤兒院是個煉獄,
凡亞必定是開在油鍋上的一朵蓮花,
任何路過的人,都忍不住想要把它捧起救走……
【內容簡介】
在莫斯科,他們把身體有缺陷的孩子,集中收容到孤兒院。在十號孤兒院,所有孩子都厭厭一息。照顧他們的人,從不正眼看他們,也不付出情感。何必呢?反正他們這樣的小孩,最終會因為缺乏互動,獲判失智送去精神病院,而送去精神病院的孩子,多半沒幾年就死了。
然而,莎拉第一次在十號孤兒院看見凡亞的時候,事情有了轉變。那時,她在探視一個盲眼病童,就在要離開的那一刻,聽到背後傳來一個小男孩說:「請妳下次再來。」莎拉轉頭,看見凡亞,凡亞綻放著笑容,眼睛都瞇了起來。莎拉詫異,這孩子身處地獄一般的地方,為何能笑得這麼燦爛?
不只是莎拉,薇卡也在偶然機會見到凡亞,大受他特殊魅力的吸引。從此,兩個互不相識的女人,分別奮不顧身踏上援救凡亞之路,這一路長達5年。甚至不止她倆,其間還有人權律師辜利葛利,寄養媽媽桑雅,英國女人琳達等等,都分別用自己的方式為他拼命!
是什麼樣的特質,讓凡亞異於其他院童,激發每個見過他的人,都像失心瘋一樣,心繫於他?
十號孤兒院上演的這段故事,讓人看見,有悲慘境遇的人,不一定就註定走向悲劇的人生,當年才四歲的凡亞,就已經用他的態度,決定了自己的人生。而人都有奮不顧身的時候,激發他們這麼做的,絕不僅僅只是憐憫而已,他們說,那叫做「凡亞效應」!
英國媒體評論,凡亞的故事,就像狄更斯的小說,在看似悲慘的境遇中,讓人讀到溫暖的生命力;而凡亞一路尋求生存的掙扎,絕不是個悲劇,更像一齣高潮迭起的冒險故事。
作者簡介:
亞倫‧菲爾普斯(Alan Philps)
牛津大學畢業,主修阿拉伯文及波斯語文。投身新聞界逾20年,主跑政治及戰事,先後擔任路透社和英國《電訊日報》駐莫斯科及中東等地的特派記者。派駐莫斯科期間,他報導了一則俄國孤兒院不當對待院童的新聞,並進而投身長達多年協助援救這個孤兒的行動。目前他和他太太莎拉住在倫敦。
約翰‧拉哈斯基(John Lahutsky)
原名凡亞.帕斯圖霍夫,一九九○年出生於莫斯科,因早產雙腳有缺陷,被迫進入孤兒院,經歷非人道待遇的童年。經過幾個熱心人士多年的努力,終於讓他得以透過跨國收養,脫離差點毀滅他的國家與生活環境。接受收養之後,與美國養母寶拉‧拉哈斯基
同住在賓州伯利恆市,改名約翰‧拉哈斯基。他目前是高中生。
譯者簡介:
林淑娟
自由譯者,譯作包括《包法利夫人》、《把托斯卡尼帶回家》、《姊姊的守護者》、《萬世師表》、《劃破地毯的少年》及《我的孤兒寶貝》等。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這是本如此重要、迷人又感動人心的書,值得更多人來閱讀,我高度推薦!
—凡諾拉.班尼特(Vanora Bennett)/英國知名作家
這個重要的故事,讓人看見人性中強勁,有韌性的那一面。它也是一個艱困的旅程,旅程中有苦痛,更有無限的愛。
—Bookreporter.com
這個身體殘的但意志過人的小孩,透過好心地人帶離苦痛的故事,透露著狄更斯式的感人、奮發向上的力量。
—英國每日郵報
作者以敏銳的筆調描寫凡亞的故事,這個令人心酸的傳記故事,述說後蘇聯時代的兒童照護系統,充滿忽視、虐待孩童的事實。
—英國週日泰晤士報
這是個奇蹟般的故事,書末卻警醒世人,還有五千的孩童仍在受苦。
—愛爾蘭時報
這如果是部小說,一定是狄更斯寫的。作者述說悲慘的故事,卻不採用另人沮喪的筆調,反而像是個積極正面的冒險故事
—The Sullivan County Democrat
媒體推薦:這是本如此重要、迷人又感動人心的書,值得更多人來閱讀,我高度推薦!
—凡諾拉.班尼特(Vanora Bennett)/英國知名作家
這個重要的故事,讓人看見人性中強勁,有韌性的那一面。它也是一個艱困的旅程,旅程中有苦痛,更有無限的愛。
—Bookreporter.com
這個身體殘的但意志過人的小孩,透過好心地人帶離苦痛的故事,透露著狄更斯式的感人、奮發向上的力量。
—英國每日郵報
作者以敏銳的筆調描寫凡亞的故事,這個令人心酸的傳記故事,述說後蘇聯時代的兒童照護系統,充滿忽視、虐待孩童的事實。
—英國週日泰晤士報
...
章節試閱
半開的門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月
「我可以要一個玩具嗎?拜託。」
凡亞的請求掛在空中沒人回應。房間裡滿是小孩,可是除了看護娜絲雅正安靜地用濕布擦拭東西之外,沒有人動。凡亞的目光跟隨她的每一個動作,極為渴望她有所反應。可是她依然背對著他,拖著腳步走到壁架前。瓦莉瑞婭在那裡的一張嬰兒搖椅裡躺著不動,她從來沒有自己搖過搖椅。瓦莉瑞婭在凝視,可是她沒有在看什麼,看護和孩子之間毫無交集—沒有碰觸,沒有話語,沒有瞥視—娜絲雅在瓦莉瑞婭周圍擦拭,彷彿當她是架子上其中一個木製玩具。抹布接近瓦莉瑞婭的腳時,小女娃畏縮,臉上顯現害怕的神情。
凡亞希望娜絲雅擦乾淨壁架後會轉過身來,那樣他能接觸到她的目光。可是沒有,她移向遊戲床,眼盲的托芽正在裡面摸索著,想找並不存在的玩具。當娜絲雅發現遊戲床的欄杆被小孩咬過了,她發出不耐煩的嘖嘖聲。
娜絲雅彎下身去擦幼兒學步車前面的淺盤,伊果整天坐在學步車裡,但是他無法移動,因為學步車用打了死結的破布與遊戲床拴在一起。伊果拱起背,開始用頭去撞他後面遊戲床的橫桿,凡亞看得出伊果企圖吸引娜絲雅的注意。可是她不理他。
凡亞不敢第二次請求娜絲雅給他玩具。他擔心她可能會做出什麼嚇人的事。她在上班的時間剛開始時,會陰陽怪氣地安靜工作,可是等到她的休息時間結束後,她會不耐煩地對小朋友吼叫,或是做更可怕的事。她有一次把伊果從換尿布台丟進遊戲床裡。後來凡亞注意到伊果的頭上出現一大片淤青。
凡亞焦慮地看他的朋友安德烈臉上茫然的表情,他坐在他們的小桌子對面。更令他焦慮的是,安德烈像個在坐學步車的孩子那樣身體前後搖晃著。他會這樣一整天搖個不停,可是凡亞需要一個能講話的朋友,而安德烈是房間裡另一個會講話的小孩。凡亞必須做些什麼。他無法再等更久,他無法等到娜絲雅轉身。她在房間對面的角落裡摺衣服。「娜絲雅,可以拜託妳給我們玩具嗎?」他對她的背說。
她以沉默來回應他的問題。凡亞做好她可能會大發雷霆的心理準備。當他看到她從一堆衣服前慢慢轉過身來,他屏住呼吸。她拖著腳步向一個高架走了幾步,拿下一個陳舊的俄羅斯娃娃,那是由一個套一個的空心木娃娃組成的套娃。她拿著玩具娃娃走向他時,凡亞幾乎壓抑不了他興奮的情緒。
「這個給你。和安德烈一起玩。」她把木製玩具娃娃砰一聲放到兩個男孩之間的桌上。安德烈停止搖晃,可是他的表情依舊茫然。
凡亞很快就發現那組套娃裡有一部份娃娃不見了或破了。但有玩具總比沒有好,即使是破的也無妨。他慢慢把所有的娃娃依序排好,擺在安德烈面前讓他看它們的大小。然後他把它們分開,一個套進另一個裡。他重複如此做,可是安德烈還是沒有反應。
「來吧,安德烈。現在輪到你了。」他用耳語催促。
安德烈繼續凝望前方。凡亞不肯放棄。
「我要把一個娃娃滾過去給你,你要接住。」那個娃娃搖搖晃晃地滾過桌子,撞到安德烈的胸部,然後掉到亞麻地板上。安德烈無意接住它。
凡亞焦急地看娜絲雅是否聽到娃娃摔到地上的聲音。她沒聽到,還忙著在摺幾件內衣。
「安德烈,你連試都沒試。這次你真的該試試看。」
凡亞把娃娃舉高到他朋友的面前。安德烈稍微轉動頭,用呆滯的眼神凝望著娃娃。「這還差不多。現在我要再一次把娃娃滾給你接。」
安德烈再次一動也不動地任由娃娃滾下桌。這次娜絲雅聽到聲音。
「你把玩具丟到地上?我告訴過他們不該讓你玩玩具。」她生氣的把其餘的娃娃都收走,凡亞震驚地呆望著她把娃娃放回高架上。她坐到她的桌子前填表格。
凡亞瞪視桌面,現在它和房間裡其他地方一樣無趣了。他看向安德烈,安德烈拒絕迎視
他的目光又開始搖晃了。伊果更殘暴地使勁用他的頭去撞擊遊戲床的橫條。在他一次又一次的撞擊之間,凡亞可以聽到小瓦莉瑞婭在壁架那裡嗚咪輕叫的聲音。他的目光落到窗下的暖氣。看著它矮胖的形狀,想到它金屬粗糙的表面和它會散發令人舒服的溫暖,他不禁微笑。他渴望滑下椅子,爬過去碰觸它,可是只有他最喜歡的看護—他叫她薇稜緹娜阿姨—會讓他在房間裡到處逛。娜絲雅如果看到他在地上爬會咆哮尖叫。
他記得有一個美好的早晨,當門打開來,一個男人帶個一個大箱子走進門。他宣布他要來修理暖氣。凡亞設法吸引那個男人的注意,問他是誰,男人允許他坐在旁邊看。男人對凡亞說他是個鉛管工人,他打開箱子,裡面是形狀大小不一的各式工具。
那時候的凡亞活到四歲還沒看過那麼多迷人的東西。鉛管工人注意到小傢伙很感興趣的樣子,他讓小男孩握著一把扳手。然後他拿另一支扳手開始將暖氣的螺絲轉開。凡亞注視他的每一個動作,詢問每一把工具的名字,重複說那個名詞好讓自己記得。鉛管工人微笑,他用完一支扳手後就給凡亞接過去握著。運氣很好,那天是薇稜緹娜當班,她沒有把凡亞拉開。凡亞想起那個令人非常興奮的時刻忍不住對自己微笑。水從鉛管裡流出來,地上有一灘水。薇稜緹娜去拿抹布。然後鉛管工人向他要回扳手,因為他急需使用它。
凡亞閉上眼睛,在腦子裡一再重播這一幕:他是鉛管工人,安德烈是他的助手,負責把扳手遞給他。他說,「安德烈,快點。把扳手遞給我。漏水了!」然後安德烈把扳手交給他,他用所有的力氣把螺帽轉緊。水不再滴了,薇稜緹娜把地上擦乾淨。他把工具收拾進閃亮的金屬箱子裡,然後離開去修理其他漏水的暖氣。那有多好啊!
娜絲雅的椅子往後轉,她突然站起來。凡亞已經觀察過她許多次了,詳知她的每一個動作,他知道她突然有目標感,那意味著她要去休息。她走到她掛在牆上勾子的袋子前,拿出一包香煙。她在外套口袋裡搜索打火機。她沒有看鏡子,不像另一位看護譚雅要出去之前都會抹口紅。
當凡亞看著她的時候,他的心跳得很快。因為他注意到與隔壁房間相連接的門半開著。它通常都關著。多麼意想不到的幸運—娜絲雅出去了,她沒有注意到那扇門開著。突然間他所有的感官都因為有個冒險的機會而活躍起來。娜絲雅不會礙事了,他可以爬到門那裡,偷窺看護稱作第一班的隔壁房間。他知道那裡有其他小孩。說不定會有個像他這樣的小孩,他可以跟他講話。他看向安德烈,他又一副茫然的表情。即使那裡沒有別的小孩,也可能有個他以前沒見過的友善看護。她可能親切地和他講話,他可以把這段交談記下來,留待稍後在長時間的午睡時間回味。
娜絲雅手裡拿著香菸,在離開之前遲疑地用目光掃瞄一下房間。凡亞垂下眼簾,屏住呼吸,擔心她會看出他的想法猜中他的計畫。她在幹嘛?怎麼還不走?現在她走向與隔壁房間相連接的門。凡亞緊張得心臟彷彿就要跳出嘴巴。她要是注意到那扇門是開的,順手把它關上,他就沒機會冒險了。幸好他看到娜絲雅是走去掛勾那裡拿她的袋子。奇蹟似地,她沒注意到相連接的門開著。凡亞的目光跟隨著她,她踏上走廊,他聽到鑰匙在鑰匙孔裡轉動的聲音。
現在小朋友得獨立照顧自己了。凡亞一點也沒浪費時間,他溜下椅子,抵達地上時發出砰一聲。他們不准他爬行,他們告訴他地板很髒,他在地上爬會生病。他不讓自己去想萬一被娜絲雅逮到他可能挨打。他用盡手臂的力量,把自己拖過閃亮的地板。在爬行到門那邊的半路上,他聽到美妙的聲音從半敞著的門的方向傳出來。有人在唱歌。他加快速度爬。
他抵達門口,把門推開一點,往裡頭看。中午的陽光穿透網狀的簾子令他眼花,在強光中他只看得到一個高大的身影。他瞇起眼睛。那個身影彎下腰來,看清了原來是個年輕的女人正輕輕把一個嬰兒放回搖籃裡。她對嬰兒多麼溫柔啊,可見她多麼關心那個幸運的小寶寶,她還一直邊低聲哼唱著歌曲。她抱起另一個嬰兒,凡亞注意到她的穿著與孤兒院裡其他女人都不一樣。她沒有穿白色的外袍,長腿上穿著的是牛仔褲,她的頭髮鬆散著,沒有綁到背後。
凡亞難得說不出話來。他沉默地注視著這個景象,不願打破這令他著迷的一刻。他要記住每一個細節,好讓他下午躺在小床上睡不著時仔細回想。
年輕的女人在房間裡到處走動,抱起嬰兒搖一搖,哄哄他們,再把他們放進搖籃裡。突然間,她的目光與他相遇。她沒有中斷她的輕聲吟唱,而反射性地對他微笑。凡亞以為她會對他吼叫,命令他回他的房間,可是她一句話都沒說。他鼓起勇氣往嬰兒的房間爬進一吋。他希望他能住在這一班。他懷疑,這是個夢嗎?這裡的氣氛如此令人嚮往。一個刺耳的聲音忽然在他背後響起。「凡亞,你給我回來。不准過去那裡。」凡亞認出娜絲雅的聲音,她休息過後回來了。他意興闌珊地爬回第二班。娜絲雅把相連接的門關上,抓著他的腋下,將他拖過地板,再把他整個人丟回椅子。
「不准再來一次。」她對著他的臉咆哮,強迫凡亞吸進她嘴巴發出令人作嘔的味道。
該是中午餵食的時候了。在廚房工作的女人推來兩個鋁製大鍋,和一個高高堆疊著碗與許多裝滿棕色湯汁的奶瓶的托盤,她們把這些東西放在靠近門的桌子上。凡亞仔細看托盤上是否有特別要給他吃的東西—一片麵包。其他小孩都沒有麵包,但是在他最喜歡的看護薇稜緹娜阿姨輪班的時候,她總是會給他一大塊麵包。今天輪到娜絲雅的班,她從來不給他麵包。可是或許廚娘記得他會吃麵包,特地在奶瓶之中塞一片麵包要給他。
娜絲雅把稀薄的馬鈴薯濃湯和蔬菜湯大約分十等分舀進一排碗裡。凡亞和安德烈永遠都是先拿到湯的人,他們預期隨時會拿到他們的碗。安德烈甚至不搖了。可是娜絲雅轉向凡亞,厲聲說,「因為你今天早上丟臉的行為,你最後才能拿到湯。你的朋友也要跟著你等。」
凡亞沮喪地看娜絲雅拿一個碗,蹲到伊果的學步車旁,把碗推抵著他的下巴,強迫他的頭往後仰,用一根大湯匙灌他喝湯。在吞進第一口湯後,伊果發出叫聲。凡亞知道那是因為熱湯燙到他的嘴巴。可是娜絲雅一言不發地繼續灌他喝湯,傾斜大湯匙,把馬鈴薯湯往他的喉嚨裡倒。伊果扭動,想把頭轉開。「你今天不餓,嗄?」娜絲雅說。她站起來,把碗拿回桌上。
然後她把托芽從遊戲床裡抓起來,扔進一張椅子裡,再拿另外一只碗。凡亞注視著企圖想搞清楚新環境的盲男童。當他的手指摸索著椅子,娜絲雅把他的頭往後推,開始把湯往他嘴巴裡倒。凡亞看到托芽根本來不及吞嚥,一匙又一匙的湯加快速度餵他。每當他要轉頭讓他自己有時間吞下口裡的湯,娜絲雅就把他的頭拉回去,繼續把食物鏟進他嘴巴裡。湯自托芽的嘴巴裡湧出來,幾乎像娜絲雅把湯推進去那麼快,湯流到他的下巴,再流到圍兜兜上。碗很快就空了,她轉向下一個小孩。
接著她拿一個裝著棕色湯汁的奶瓶,拖著腳步走到瓦莉瑞婭躺著的壁架那裡。她把奶嘴塞進小女孩的嘴裡,然後將奶瓶倒立。瓦莉瑞婭太虛弱了,凡亞幾乎聽不到她吮吸的聲音。「快一點。」娜絲雅催道,她轉身去環視房間。瓦莉瑞婭吮吸的韻律慢了下來,停了下來,奶瓶幾乎還是全滿的。娜絲雅不耐煩地把奶瓶拿走,移向下一個小孩。
凡亞看著娜絲雅匆忙餵小朋友吃午餐的例行步驟,感覺他愈來愈餓。他今天真的需要一塊麵包。或許如果他禮貌地請求⋯⋯不,今天不是他提出請求的日子。沒錯,她在兩個男孩面前的桌子重重放下兩個碗和兩根湯匙,沒有麵包。「不要吃得髒兮兮。」她警告。凡亞和安德烈在沉默中用湯匙把冷掉的湯舀進他們口中,一點都沒有能夠咀嚼東西的滿足感。
兩個男孩還在喝湯的時候,娜絲雅把小孩子一個個抱到換尿布台上,她的目光根本沒有和他們接觸,也沒有說話,直接脫掉他們的濕內褲和髒尿布,換上乾淨的。然後她走經凡亞和安德烈,把孩子一個個分別安置到隔壁臥房的小床裡。這意味著要開始午睡了。
凡亞最討厭長長的下午被限制在他的小床上。快輪到他的時候,他絞盡腦汁想辦法拖延不可避免的午睡。在薇稜緹娜阿姨當班的時候,等她把其他小孩放到床上睡覺後,她會讓他陪她坐一會兒。她會教他唱一首歌或唸一首詩。可是今天是娜絲雅當班。她已經叫安德烈躺下去睡了。凡亞假裝還沒吃完午餐,他用湯匙刮著碗蒐集最後一點點濃湯,想到開始跟她講話的方法。當她彎身要抱起他時,他問,「妳買地毯了嗎?」
娜絲雅顯得嚇了一跳。「你怎麼知道我的地毯的事?」「我上次聽到妳跟醫生講的。妳說妳在市場裡看到一條地毯,等妳下班後要去買。」
「是的,我去市場買了。」
「那條地毯很漂亮嗎?」
「是的,很漂亮。」她抱起他。
「娜絲雅,市場是什麼?」
「市場是你可以去買東西的地方。現在是你的午睡時間。」
「可是我不想睡覺。」娜絲雅沒有回答。她匆忙將他放進他的小床。等到她出去關上門,凡亞從他小床的圍欄之間凝視著牆上的裂縫。他用手指描繪油漆的線條。他的目光越過圍欄的鋼條,跟隨每一道裂縫到小床的床尾。他感覺自己被眼前擴展開來的浩瀚時間壓毀。他知道在他得救之前會有一段黑暗的時光。其他小孩煩躁地在他們沿著四面牆擺放的嬰兒床裡呻吟。
他關上耳朵不想聽其他孩子不快樂的聲音,專心在心裡重溫早上娜絲雅離開房間時他溜下椅子去做的大冒險。他想起長髮的年輕女人溫柔地抱著嬰兒唱歌的模樣。他記得她對他微笑,他想像她現在在對他唱歌。他再次問自己,她是誰?她的穿著為什麼和其他看護不同?她為什麼沒有對他吼叫,也沒有因為他離開他的班而打他?他翻來覆去想那些問題,但仍然和第一次想的時候一樣困惑。
他在腦中重播了幾次早上那段冒險過程後,尋找別的東西來想。他腦中浮現那組俄羅斯套娃的映像。他再次玩它們,不過這次它們沒有破裂,沒有缺一塊。他在想像中把它們一一排在桌上,從最小的娃娃,像他的手指那麼小的,排到最大的,像瓦莉瑞婭坐在她的搖椅裡那麼大。有好多好多套娃,桌面幾乎不夠放。它們在他的桌子末端形成一道大牆,他躲在娃娃牆後面不讓安德烈看到,那逗得安德烈哈哈笑。
然後他開始把娃娃滾下桌。這次安德烈的表情不再茫然。他為了抓住娃娃而撲向左邊或右邊—所有的娃娃,從輕盈的小娃娃迅速掠過桌面,到超大娃娃搖晃著慢慢從一邊滾到另一邊。安德烈接住每一個娃娃,把它們放回桌上。凡亞讓它們自桌緣掉落製造驚險,然後在它們摔落到地上之前抓住它們。娜絲雅完全沒聽到!
今天娜絲雅不可能再給他俄羅斯套娃了。明天呢?明天是譚雅值班的日子。他不知道譚雅會不會給他玩具,不過他會開口要求她。後天就輪到薇稜緹娜阿姨來照顧他們。她一定會讓他玩娃娃。他總算有些事情可以期待。
兩天後,凡亞坐在他的小桌子前,渴望地等待他最喜歡的看護來上班。譚雅已經脫掉白色外袍,看著她的手錶,等待下班的時間來到。門打開來,凡亞最愛的薇稜緹娜穿著舊外套走進來,她帶著一把雨傘,手裡提著一個鼓起的塑膠袋。凡亞看薇稜緹娜把外套掛起來後,手伸進塑膠袋裡翻找東西。她拿出一個紙包放到他面前。充滿了期待的凡亞用顫抖的手指撥開不吸油的紙,裡頭是一片厚厚的義大利蒜味香腸。
她對他耳語,「晚一點我會給你一根香蕉。」他的臉亮了起來。
「薇稜緹娜阿姨,妳知道的,妳是我最喜歡的看護。」他邊說話,滿口都是肉。
「別瞎說了,凡亞。」她說著走進臥室。然後她回來,抱著老是待在幼兒搖椅上的男童基里爾。她把他抱在她腿上,慢慢的給他穿衣服,先穿運動衫和內褲,然後穿長褲和毛線衣。她的表情全神貫注。
「薇稜緹娜阿姨,妳今天為什麼悲傷?」凡亞問。
「基里爾要離開我們了。他要去精神病院。」
凡亞聽過那個名詞,可是他不懂那是什麼意思。「精神病院是什麼?」他問。薇稜緹娜沒有回答。就在這個時候門打開來,絲瓦特拉娜匆匆走進來,她總是拿文件來。薇稜緹娜給基里爾穿上外出的外套,溫柔地親吻他的頭頂,在把他交給絲瓦特拉娜之前,她們簡短的交談了一下。等到門又關上,基里爾不見了。
凡亞記得這種事以前發生過。絲瓦特拉娜領走過一個小孩,她不曾把他帶回來。下次她或許會來帶走安德烈,那麼他就會連一個朋友都沒有。他把那個想法推出腦海。他四下看看,想請薇稜緹娜告訴她精神病院是什麼。可是她忙著幫別的小孩換衣服,而且她的表情在說:別問我那個問題。
幾分鐘後,與嬰兒室連接的門打開來,副院長抱一個金髮的小女孩進來。「妳現在有張空的小床了。這個給妳。」她看著一張棕色的紙對薇稜緹娜說,「她叫柯德蕥伊瓦。早產兒。她媽媽在她出生時就棄養她。她現在十五個月大,沒有人扶還不會坐。顯然很遲緩。絕對是該由妳照顧。」
薇稜緹娜把女孩放進拴在凡亞那邊的遊戲床旁邊的一台學步車裡,然後去簽文件。
「妳好。我是凡亞。妳叫什麼名字?」
女孩用聰明的眼神看著他,嘟嘟噥噥地說話,但是說出來的全都是嗯嗯啊啊的聲音。凡亞看得出她很想跟與她同桌的他和安德烈講話。
「這位是安德烈。」凡亞說。「薇稜緹娜阿姨每天會給我一個玩具。」
他開始展示他的玩具—一個有一半破掉的塑膠電話。凡亞這邊有電話的底座,安德烈握著聽筒,電話線已經不見了。凡亞用手指轉動撥號盤,女孩顯得很興奮,發出嘖嘖的聲音。她的表情在說:讓我玩。凡亞得到觀眾的注意,樂意示範如何撥電話,給她看玩具的正面。他太專心了,沒有注意到一個人站到他們面前。
「喔,瑪莎,妳喜歡那個,是嗎?」一個陌生的聲音說。一隻手伸過來,把那電話從凡亞手裡抓走給女孩。凡亞詫異地張著嘴巴。那個人現在背對著他蹲下來在關愛新來的女孩。「瑪莎,我們必須讓妳練習講話。說媽媽。媽—媽。」瑪莎服從地重複說,媽—媽。
凡亞被此刻的情景迷住。他的目光跟隨著站起來的年輕女人,她走向薇稜緹娜。「請恕我冒昧。我叫薇卡,我是個義工。我常來幫助我在嬰兒室工作的朋友。我因此跟瑪莎相當親近。現在她轉到第二班了,我可以來看她嗎?我也可以幫妳的忙。」
「好啊,我這裡永遠需要幫手。妳看得出來,我自己一個人要照顧一打小孩,餵他們吃東西幫他們換衣服,值班的時間長達二十四個小時。而我已經不像妳那麼年輕了。」薇稜緹娜笑著說。「妳願意的話可以留下來幫我給他們吃午餐。」
她們在交談的當兒,凡亞明白這位就是他曾經冒險進入相連接的門時,盯著她看的對嬰兒唱歌的年輕女人—從上次見到她後,他沒有一天不想到她。現在她就在他的房間裡,他幾乎無法壓抑興奮感。他注視她笨拙地用湯匙餵食瑪莎,有一半的湯灑到地上,不過她能在附近他就很高興了。他暗自練習說她的名字—薇卡、薇卡。
「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義工。」薇稜緹娜在她們分別餵食孩子們時說。「外面的人通常不能進來這裡。」
「我不確定別人是否接受我的善意。事實上,有些工作人員認為我會礙事。」
薇稜緹娜友善的微笑。「親愛的,妳當然不會礙事。」凡亞注視著年輕女人和薇稜緹娜阿姨,全神貫注傾聽她們一邊工作一邊聊天。他被忽略了,所有的注意力都投注到新來的女孩瑪莎身上,可是他不介意。他決心要使得薇卡成為他的朋友。
第二天凡亞醒來,他花了一會兒才想到他為什麼會感覺快樂。不是因為薇稜緹娜阿姨要來值班。昨天才是她值班的日子。然後他想起薇卡。她不像穿白袍的看護會定期來,他記得她們輪班的模式。薇卡隨時都可能出現。他第一次看到她是在娜絲雅值班的時候,然後她在薇稜緹娜值班時再次出現,所以他以為他躺在小床裡,她今天可能就會出現。一整天每次門打開來他就抬頭看,希望能看到她甜美的笑容,可是他每次都失望,直到天色黑了,他確定她今天不會來。
第二天她也沒來。他以對自己低語她的名字來尋求安慰。然後他看到她的頭自門邊探出來,「薇卡,薇卡。」他突然聽到自己在叫。「妳要來看瑪莎嗎?」
「你記得我的名字。你記得我,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凡亞。」
「喔,對。你給瑪莎看玩具電話。你說對了,我來看瑪莎。」她大步走進房間,低下身去,把瑪莎從學步車裡抱出來擁在懷裡。瑪莎平時顯得憂傷的臉漾出笑容。
「妳是誰?誰允許妳來這裡?」娜絲雅的聲音從臥室冒出來,凡亞的心跳漏了一拍。他太興奮了,忘了今天是娜絲雅值班。薇卡轉身去面對看護,懷裡還抱著小女孩。
「抱歉,我應該自我介紹。我來看瑪莎。」
「妳在這裡工作嗎?」
「沒,沒有。」
「那麼妳不該來。」
「可是我以前在第一班幫忙照顧嬰兒。我已經來了好幾個月。」
娜絲雅咄咄逼人的態度因為發現到她有偷懶的機會而軟化。「嗯,我需要休息一下。妳可以照顧孩子十分鐘。」
門關上,凡亞欣喜的看到薇卡在他桌旁的小椅子坐下來,她把瑪莎放在她腿上。她把小女孩轉過來面對她,看進她的眼睛,開始發出媽—媽的聲音。「來,瑪莎,妳可以學著說。」瑪莎沉默不語。薇卡用嘴唇親吻小女孩的臉頰,重複教她發音。但她還是不說。
「瑪莎,說啊,妳在嬰兒室時說得很好啊。」瑪莎繼續愉快的看著她,可是不發出聲音。
薇卡嘆氣。她脫掉瑪莎的襪子,把她光腳放到地上,雙手放到桌上,輕托著她腋下。「妳必須讓妳的雙腳強壯有力。」她說。可是女孩的身體往下沉。
薇卡看起來有些氣餒。當她的目光搜尋房間找可以激勵瑪莎的東西,她看到凡亞臉上流露出與她相似的表情。她的目光落到一個前面有馬頭和左右手把的嬰兒椅上。她把它從角落拖到凡亞的桌子前,把瑪莎放到椅座上,拉她的手去握手把。她那麼坐可以讓她自己坐直。「聰明的女孩!妳在騎馬了。」瑪莎的眼睛亮了起來。第一次,她看起來靈活地握緊手把。
薇卡發出在騎馬的聲音。她鼓勵凡亞加入。然後她開始拍手,咋舌發出卡嗒聲。凡亞好久以來不曾玩得這麼歡暢過。
「怎麼這麼吵啊?妳鼓動他們興奮起來。我今天下午別想讓他們乖乖睡覺了。」娜絲雅休息過後回來,忿忿地終止派對。「妳為什麼把她的襪子脫掉?」她厲聲問。「那樣她會感冒。」
「妳看她多高興。這把馬頭椅子可以幫助她活動。或許妳該常常讓她坐⋯⋯」
「我得幫他們更衣、清洗、餵食,妳以為我的事情還不夠多嗎?」
娜絲雅說著把瑪莎從馬頭椅抓起來,放回她指定的拴著的學步車裡。瑪莎發出一聲可怕的怒吼。
「總之,妳何必把時間浪費在她身上。」娜絲雅用手指敲她自己的頭兩次,那是表示瑪莎是智障的殘忍手勢。
薇卡明白娜絲雅可能不容許她再來看瑪莎,她最後企圖和看護交換條件。「妳允許的話,我願意幫妳餵他們吃午餐。」她提議。
「不。我可以自己來。妳不是該走了嗎?不要再來了!」
薇卡輕吻瑪莎的頭頂,拿起她的袋子,對凡亞輕揮一下手,然後走掉。凡亞再一次被沉默包圍。
整個下午凡亞在他的小床上清醒地躺著想薇卡。娜絲雅叫她別再來。他永遠再也見不到她了。失落感像個非常重的東西壓在他的胸膛上,令他難以呼吸。然後他想像自己溜出小床,大步走進休息室,站到娜絲雅面前叫嚷,「妳不是該走了嗎?不要再來了!」然後薇稜緹娜阿姨會在娜絲雅值班的日子來。那該有多好。
當娜絲雅過來要將他抱離小床,他渾身緊繃。在她幫他換尿布時,他一直閉著眼睛。等到他坐回他的桌子旁,在她轉身背對他時,他以恨意凝視著她。他太難過了,當門打開來,他不像平常那樣立即做出反應,等到他轉頭去看是誰來,太遲了,他自眼角看到某個穿著牛仔褲和毛衣的人經過。他以為那個人一定是薇卡,他的心跳得好高。他轉動椅子,但是失望的看到兩個不是穿白袍的女人,她們兩個都不是薇卡。一個像薇卡那樣留著長髮,然而是金髮;另一個用可笑的怪腔調講話。
她們和一個凡亞以前在第二班只看過兩次的看護一起進來,他記得她叫姌娜。她似乎不安,他感覺她想要訪客離開。可是短髮那個女人一直在問問題。姌娜終於領兩個女人走向門口,說孩子要吃晚餐了。凡亞相當驚訝,因為要等到娜絲雅下午的休息時間過後才會吃晚餐,而她的休息時間還沒結束。當她們接近門口的時候,凡亞把握住機會。
「請妳下次再來。」他對短髮的女人說。
他欣喜地看到她轉身走向他。她給他一輛玩具車,他問她是否也能給安德烈一輛車,她伸手進她的袋子裡拿出另一輛車。凡亞從來沒有玩過玩具車,安德烈也沒有。他們兩個相視微笑著移動玩具車繞著桌面玩。他們太專心玩車子,他差點忘了問女人的名字。她叫莎拉,她答應會再來。她說她會。
在開始吃晚餐之前,娜絲雅把玩具車收走,放到高高的架子上。第二天早上凡亞醒來,他第一個想到的是他的玩具車。他坐起來,伸出手,想像他沿著小床的欄杆移動玩具車。然後他想像玩具車沿著牆轉個弧形的大彎。
「娜絲雅,我現在可以玩我的車嗎?」他在她走進房間時問。
「車?什麼車?」
凡亞開始感覺不安。他抓著圍欄,把他自己拉高。「妳知道的,莎拉給我的玩具車。」
「莎拉?我不認識誰叫莎拉。」
凡亞開始恐慌。「妳知道的,那個口音怪怪的女人給我一輛玩具車。她也給安德烈一
輛。」
娜絲雅彎腰抱起一個孩子。「我不記得什麼玩具車。」她若無其事地說。「你一定是夢
到的。」
半開的門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月
「我可以要一個玩具嗎?拜託。」
凡亞的請求掛在空中沒人回應。房間裡滿是小孩,可是除了看護娜絲雅正安靜地用濕布擦拭東西之外,沒有人動。凡亞的目光跟隨她的每一個動作,極為渴望她有所反應。可是她依然背對著他,拖著腳步走到壁架前。瓦莉瑞婭在那裡的一張嬰兒搖椅裡躺著不動,她從來沒有自己搖過搖椅。瓦莉瑞婭在凝視,可是她沒有在看什麼,看護和孩子之間毫無交集—沒有碰觸,沒有話語,沒有瞥視—娜絲雅在瓦莉瑞婭周圍擦拭,彷彿當她是架子上其中一個木製玩具。抹布接近瓦莉瑞婭的腳時,小女...
作者序
【作者序】
我命令自己繼續爬。我的雙腿雖然無力,但我的手臂很強壯,可能和我那些童子軍伙伴一樣強壯。在我下方的男人和男孩們叫著:「約翰,加油!你辦得到。」我伸出左手臂抓緊繩子,把自己拉上去。我告訴自己:是的,我辦得到。
我看得出其他男孩沒人料想得到我會嘗試爬繩索網。我剛才看他們一個接一個奮力爬向頂端,並不輕鬆地前後搖晃,像水手在強風中爬上船桅。我擔心我的雙腿可能會被繩索纏住,到時候勢必得麻煩教練出馬救我。我說不定會跌下來被安全帶吊在半空中出糗。其他男孩都爬上去了,教練看著我說,「約翰,你想試試看嗎?」我明白我如果說不要,他不會在意。我看著他的眼睛說,「我想努力拼拼看。」
教練幫我繫安全帶,在我的腰部和肩膀處拉緊帶子紮牢。然後他把安全帽戴到我頭上,調整帽帶。我舉高手,抓住粗糙的網繩,把自己拉上去。我的腳一離開地面,整個身體就搖晃著往後傾斜,但我死命用力抓緊繩索,一手抓牢再換另一手抓更高的網繩,逐漸把我自己往上拉。我汗流浹背,呼吸開始沉重。我聽到下面有人在叫喊,「約翰,繼續爬!」
我操縱我的右手去抓下一條繩索,一個印象閃進我腦海—一個赤裸的小男孩,安靜地待在上鎖房間的鋼條圍欄後面。那個小男孩也企圖要爬。他想爬過小床的鋼條圍欄,可是圍欄太高了。他一次又一次嘗試,直到他累壞了,精疲力盡,倒在空無一物的塑膠床墊上。
我停下來喘氣,聽到下面的叫聲,「不要停。你辦得到的。」那個聲音彷彿在鼓勵我腦中的小男孩。我想:是的,我辦得到。我抓緊繩索,咬著牙,用盡全力把自己往上拉。為了那個孤單無助的小男孩我要奮力一搏。
那個男孩就是我,六歲時的我,當時我在另一個國家,說另一種語言,有另一個名字,簡稱艾文或凡亞。
我抵達繩網的最上頭,我的童子軍伙伴爆出如雷的掌聲。我轉身對他們微笑。爬繩網的確很困難,不過跟六歲時的我所克服的困難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
我的童子軍團友不知道我的過去。他們如果知道會怎麼說?
接下來要說的是我的故事。聽說我可能是唯一一個能在俄羅斯堪稱兒童集中營那種十分恐怖的收容機構存活下來,而且能到美國展開正常生活的孩子。那些機構是在史達林獨裁時代設立的,他們直到現在還在折磨孩童。因此我覺得我應該說出我的故事公諸於世。
就像我媽媽說的,只要能從我經歷過的地獄多救出一個孩子就值得了。
我,像其他數千個俄羅斯孩童一樣,在五歲時被歸類為「無法教育」,被所謂的專家宣判必須「終生在床上生活」—等於是個只能躺在什麼都沒有的小床上的活死人。我希望我在美國就讀高中的成功經驗—儘管直到將近十歲之前我沒有受過教育—能夠證明那些俄羅斯專家把像我這樣的孩子視為「智障」錯得多離譜。
知道我俄羅斯遭遇的朋友常常問我,很多像我這樣的小孩不到七歲就死了,我為什麼能活下來?我無法回答那個問題。
這本書醞釀了很久。我來到美國後,許多年來我媽媽都會向一對英國夫妻,亞倫和莎拉,報告我的進展。我還在莫斯科的十號孤兒院時就認識他們。我們寄照片給他們,例如:我第一次去迪士尼樂園,米老鼠歡迎我;在我成為美國公民的慶祝派對裡,我戴一頂有星條旗的高頂禮帽,我媽媽在照片背後寫:「完全成了美國人的約翰」;我穿著晚禮服扮演我的英雄○○七情報員詹姆斯.龐德;後來還有我穿著童子軍制服的照片。
二○○六年媽媽寄給他們不一樣的東西—我們本地報紙上的文章,記者訪問我和我媽媽,問我們如何結緣、我們現在的生活,和我幼年時期在俄羅斯的遭遇。亞倫寄回電子郵件說,從那篇報導看起來,顯然我對自己奇特的故事只曉得片段。第二年,亞倫和莎拉到美國來住在我們家,我們分享彼此在莫斯科時的記憶,當時亞倫是報社的駐外記者,莎拉是他的「拖油瓶配偶」,陪著他遷徙到派駐地,而我被安置在機構裡由國家養育。我有許多疑問:我的原生家庭怎麼了?我為什麼會被送進十號孤兒院?我六歲的時候為什麼會從孤兒院轉去成人精神病院?為什麼花那麼久的時間才把我救出來?
我聽到的事情越多,越渴望全盤了解。我要知道為什麼俄羅斯的醫生將智障和身障混為一談,他們怎麼可以宣判輕微身障的小孩必須發落到活地獄受煎熬。當我們坐談往事,亞倫說我的故事可以寫成一本很棒的書。那個主意令我怦然心動。我對他說,你一定要寫下來。在我的故事裡你和莎拉、薇卡和其他所有的人,應該全都說出你們所參與過的那部分。這個故事應該讓世界知道。
自從我來到美國,我學到許多關於俄羅斯的事。我最近才在歷史課上針對沙皇垮台,列寧崛起,繼而由史達林接管這些事做過簡報。做這報告讓我深入去了解那些企圖毀掉我的制度。
故事從我還只是個四歲的孩子說起。我對幼兒時期的記憶和大部分人一樣很模糊。我被鎖在孤兒院的房間裡,渾然不知有時候我是那些努力營救我的人颳起的旋風的暴風眼,風暴在我媽媽回應我的哭求時達到高潮。
為了寫這本書,亞倫回到莫斯科採訪在那段時間和我接觸過的大部分人,他也採集日記、照片、錄影帶和官方的文件等資料。我對自己人生的記憶在六歲以後變得比較清楚,自此才對本書稍有貢獻。
那些被監禁的地方發生的事,我透過自己的雙眼見證。其他故事則多半由兩個與我非常親密的恩人述說:年輕的俄羅斯女人薇卡,她奉獻她人生中的許多個月企圖營救我;還有莎拉,如果她沒有突破殘忍的制度為我找出路,我無法順利脫身。
—約翰.拉哈斯基
二○○八年九月於賓州伯利恆市
【後記】
住在伯利恆市的男孩
二○○九年九月
我來到美國已經十年了。我只消看看亞倫一九九六年在精神病院的草地上為我拍的照片,便看得出我改變了多少。那時候他把一頂棒球帽戴到我頭上,藏起我剃光的頭,可是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樣的恥辱。那是一頂紅襪隊的帽子。美國有那麼多職棒隊,為什麼我戴的剛好是紅襪隊的帽子?我是洋基隊的球迷。我有時候支持費城人隊,因為我住在費城所在的賓州,可是我從來不為紅襪隊加油。我希望新英格蘭區的人能原諒我。
我現在是賓州伯利恆市自由高中的學生,我最喜歡的科目是歷史。我每天早上五點四十五分起床趕搭校車,那一點都不好玩,不騙你。不過,不管多累,我從來不睡午覺。我在俄羅斯的人生浪費太多時間在床上,現在我總覺得我要做好多事情來補足。
我媽媽帶我到美國時我九歲半,可是才開始上一年級。我不會講英文,必須趕快學英文。好在我很幸運,因為我在日間照護班結交了一位朋友,他叫做丹尼。他和我同年,可是他已經唸四年級。丹尼教我,就好像我在俄羅斯時教安德烈。安德烈跟我學講俄語,我跟丹尼學講英語。在兩年的日間照護班裡我們每天交談,不管是上學前或後。他是第一個邀請我去參加生日派對、邀請我去他家過夜的人。在許多年後,丹尼依舊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媽媽告訴我,早年當我在學英文的時候,我最喜歡講的一個詞是「我們的」。我從來不曾擁有任何東西,我卻喜歡說「我們的車」和「我們的房子」。我會說,「每一樣東西都是我們的」,那是我向自己保證這一切不會轉眼成空的方式。
關於我剛來的那幾個月發生的各種事情,我媽媽可以談上幾個小時。例如,她給我一個工具箱,那變成我最寶貝的東西。現在她了解,我在俄羅斯的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刻是,當我玩槌子和釘子的時候。她回憶說,我喜歡在雪地上玩,弄得又濕又髒,因為我以前從來不准那樣。我到美國沒多久後,她帶我去野生公園。我看到關在籠子裡和柵欄後的動物會感到不安。我一直問,「那隻動物為什麼關在那裡?」不是每一樣東西都會嚇到我,或讓我想起在俄羅斯不堪的時刻。媽媽常談起在迪士尼世界遊樂園發生的事。穿著卡通人物跳跳虎服裝的工作人員暫時脫離他的角色︵那在迪士尼世界裡是嚴格禁止的︶,對我媽媽耳語,「願上帝祝福他。」我想上帝聽到了跳跳虎的祈禱。
三年級時有一天,發生一件我知道能夠擴展我眼界的事。學校有個集會鼓勵男孩參加幼童軍。我並不清楚參加幼童軍要幹嘛,但是聽起來好像會有刺激的活動,例如露營。那天放學後,我告訴媽媽這件事,問她我是否可以參加幼童軍。她懷疑幼童軍能否照顧殘障的我,她似乎勉強同意讓我參加。我對她說,「媽媽,給我一個機會。」︵那時候我的英文還有一點俄羅斯腔。︶她聽了後無法拒絕我。
等我當完幼童軍,我這個小隊的每個男孩都必須決定要參加鄰近幾個童子軍團中的哪個團。我們至少去看過四個團。其中有一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大部分男孩決定要一起參加一個特別的童軍團,然而我做出不一樣的決定。對我來說,我的選擇一定是三六二團。就我的判斷,它是到目前為止我所見到最好的團。我看得出它是個組織完善的童軍團,可以讓我獲益良多。
媽媽擔心我的選擇。她認為我單獨去參加那個團會不舒服。「你不想跟你的朋友們在一起嗎?」她問。
我堅持己見。「媽媽,妳可別想企圖說服我改變心意。」
那是五年前的事。媽媽常對我說,「約翰,我必須承認,當時你選擇三六二團是對的。」我在那個童軍團裡交到很好的朋友,我們到戶外探索、學會求生的重要技能。我最喜歡的是:他們從不認為我殘障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成為童子軍的團員使得我在過去五年裡成熟多了,也學到一些實用的領導技巧。
二○○六年,我如果想進階到童子軍的榮譽社團—聖箭盟—必須經歷所謂「嚴酷的考驗」。我必須通過的考驗是自己一個人在森林裡度過一夜。我不能帶手機或手電筒。即使我需要像助行器或柺杖來幫助我走路,我還是要接受和每個人一樣的平等待遇。我只能帶一個睡袋和防水布來保持我的身體溫暖乾燥。他們也給我一個柳橙和一個蛋讓我做早餐吃。我花了很久的時間才說服媽媽,幸好我終於讓她點頭同意我參加這個試煉,我和其他童子軍興沖沖地去體會我們的考驗之夜。我們抵達的時候大約晚上十一點,下著雨,天色很黑。一個年紀較大的童子軍讓我下車,接著我獨自一人在漆黑的森林深處。沒有一處乾的地方可以睡覺,防水布根本無法擋雨。到了早上,我的衣服濕透了,一整夜我的眼睛幾乎沒有閉一下。我媽媽發誓她也是眼睛幾乎沒有閉一下,一整夜都在為我擔心。當太陽升起,我吃著蛋和柳橙,等待某個人開車來接我。我活過嚴酷的考驗,通過測試,有資格做聖箭盟的一份子。從那個時候起我成為聖箭盟的會員兄弟,而且引以為榮。
我和媽媽在賓州的爾昧爾斯聖保羅東正教教堂做禮拜。這間教堂是我與我的過去最明顯的連結之一。我的俄文洗禮證書是由每個禮拜二到十號孤兒院的牧師簽的,那是我從俄羅斯帶到美國的少數幾樣東西中唯一派得上用場的。我上該教堂的主日學校,以前曾是彌撒中協助牧師的輔祭。那是個小教堂,可是教友都是很好的人。事實上,我每年為童子軍募款時,一向都可以仰賴他們向我買爆米花。
除了教堂、學校和童子軍,來到美國讓我有機會看許多我在俄羅斯從來沒看過的東西,並發展其他種種興趣,包括我喜歡的歷史悠久的電視秀和老電影。我看過每一齣詹姆斯.龐德的電影,二○○三年有一天我參加學校的化妝舞會,我選擇穿自製的燕尾服,打扮成○○七情報員。我喜歡J.K. 羅琳的整個哈利波特系列,我喜歡看運動賽事—費城老鷹橄欖球隊、賓州州立大學橄欖球隊、棒球和高爾夫球。我是老虎伍茲的頭號粉絲。
我的家族深受上帝的眷顧。當媽媽帶我到美國,我變成和樂大家族的一份子,家族成員大多住在賓州附近,也有遠及德州和加州的親戚。這個「家族」也包括一群我媽媽的朋友,他們都愛我,對我非常好。我還必須說,我在美國的大家族如果少了我的狗詹寶就不完整,我會給牠取這個名字是因為,我在去參加童軍大會前一天得到牠。不過,我的家族不僅限於美國的國界。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我躺在浴缸裡,媽媽在門外喊叫說,亞倫找到我姊姊歐嘉。我從一歲以後就沒看過她,那時候她六歲,我們分別被送進不同的國家機構。當我終於聽到她的聲音,我哭了。感覺好像是許多塊拼圖終於把我的家庭拼湊起來。
我人生中最大的神蹟當然是我媽媽,沒有她就沒有今天的我。當我在俄羅斯的時候,我所說的和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呼喊:給我一個機會。我媽媽給我一個機會。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母子關係。她愛我、支持我、鼓勵我、引導我。她愛不完美的我,以我為榮。我遇到問題時會去找她幫忙。我無法想像如果沒有她,我的人生會怎樣。她告訴我,如果沒有我,她無法想像她的人生會怎樣。我們知道是上帝帶領我們成為家人,我們每天因此感謝祂。
我很幸運。我有美好的人生,可是我無法忘記我的過去。我怎麼忘得了?我萬分感激當我在俄羅斯的時候所有幫忙拯救我的人。有些人書裡沒有提到。我們如果要把他們全都寫進去,那這本書可能要分好幾集。我希望他們都有力量和勇氣繼續他們的救援工作,好讓別的孩子不必再忍受如我所遭遇過的痛苦。
我希望並祈禱,這本書能夠終結把孩子鎖在高牆之內遭受不人道對待的邪惡制度。我的夢想是,有一天這些機構都關閉。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家庭裡生活。我要他們全都有個機會。
【作者序】
我命令自己繼續爬。我的雙腿雖然無力,但我的手臂很強壯,可能和我那些童子軍伙伴一樣強壯。在我下方的男人和男孩們叫著:「約翰,加油!你辦得到。」我伸出左手臂抓緊繩子,把自己拉上去。我告訴自己:是的,我辦得到。
我看得出其他男孩沒人料想得到我會嘗試爬繩索網。我剛才看他們一個接一個奮力爬向頂端,並不輕鬆地前後搖晃,像水手在強風中爬上船桅。我擔心我的雙腿可能會被繩索纏住,到時候勢必得麻煩教練出馬救我。我說不定會跌下來被安全帶吊在半空中出糗。其他男孩都爬上去了,教練看著我說,「約翰,你想試試看嗎...
目錄
序言
1. 半開的門
2. 沉默中的聲音
3. 鳳梨和孔雀
4. 天使也沒輒
5. 超人事蹟
6. 沒人關心
7. 媽媽的故事
8. 老鼠
9. 來自古拉格集中營的訊息
10. 酸葡萄
11. 僥倖脫逃
12. 林中的小孩
13. 白蘭地和巧克力
14. 土撥鼠日
15. 責備遊戲
16. 再次僥倖脫逃
17. 帝國反擊
18. 七月的聖誕布丁
19. 籠中鳥
20. 我們其中之一
21. 燭光
22. 潛在的佳音
23. 去聖塔芭芭拉的票
24. 邪惡的詭計
25. 高加索的犯人
26. 無傷大雅的謊言
27. 不可原諒
28. 重聚
29. 偵察探訪
30. 姊姊的故事
31. 凡亞效應
後記:住在伯利恆市的男孩
為什麼會寫這本書
序言
1. 半開的門
2. 沉默中的聲音
3. 鳳梨和孔雀
4. 天使也沒輒
5. 超人事蹟
6. 沒人關心
7. 媽媽的故事
8. 老鼠
9. 來自古拉格集中營的訊息
10. 酸葡萄
11. 僥倖脫逃
12. 林中的小孩
13. 白蘭地和巧克力
14. 土撥鼠日
15. 責備遊戲
16. 再次僥倖脫逃
17. 帝國反擊
18. 七月的聖誕布丁
19. 籠中鳥
20. 我們其中之一
21. 燭光
22. 潛在的佳音
23. 去聖塔芭芭拉的票
24. 邪惡的詭計
25. 高加索的犯人
26. 無傷大雅的謊言
27. 不可原諒
28. 重聚
29. 偵察探訪
30. 姊姊的故事
31. 凡亞效應
後記:住在伯利...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