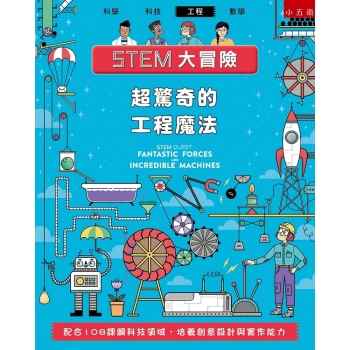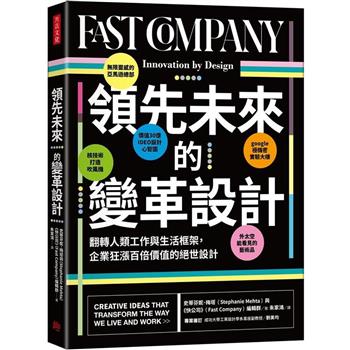五四一百週年,杜威訪華一百週年回顧
杜威如何親身經歷五四,留下對東亞巨變的第一手觀察?
一個意外邀約,杜威夫婦結束在日本的旅程後去了中國,親身經歷五四運動,目擊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巨變。他們的家書有思想家的深刻觀察,也有旅人體驗的溫馨趣味。
一九一九年,哲學家約翰‧杜威與妻子愛麗絲‧C‧杜威到訪日本和中國,他們將一路所見所聞記下,寄回美國與遠方的兒女分享。《一九一九,日本與中國》收錄了其中六十四封書信。
杜威夫婦原是要到日本度假散心。在日本與中國的朋友、學生,聽聞夫婦倆來訪亞洲的消息,便積極邀請他們在兩國演講、授課。單純的遠東觀光之旅,於是變成東亞講學之行。
他們在日本停留兩個多月,抵達中國時正好遇上五四學運。向來被西方人認為古老停滯的國度化身民主舞臺,民意對抗強權的歷史大戲就在眼前展開。兩人一邊講演,提倡著民主、教育與平權,一邊回想經歷的日本、審視當下的中國,研究著一戰後兩個亞洲古國和全球的政治局勢、社會變革與風土民情,一待就是兩年餘。
這六十四封家書,是杜威夫婦的異國行旅札記,是深刻全面的人文觀察,也是他們理清思路、建構往後思想的筆記;為讀者帶來旅遊逸趣外,更引領我們凝視變動的亞洲,跟隨兩人思索世界的過去與未來。
在五四中國這個舞臺上,杜威既是觀眾,也是演員,他盡量扮演好兩種角色,而杜威和夫人留下來的這些遠東家書,也讓我們有機會觀賞這齣難得的歷史劇碼。
──王清思(本書導讀人)
作者簡介:
約翰.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美國哲學家、教育家、心理學家。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引領進步主義教育運動,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美國的教育思維,中國五四時期的胡適等人也備受啟發。
杜威 1884 年取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執教於密西根大學,開始關注教育課題。1894 年至芝加哥大學任教。彼時,一派以經驗為基礎的知識理論——實用主義——方興未艾,杜威為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學說撼動,原先的唯心思想遂而轉向實用關懷。這段時期杜威開始嘗試落實教改理念,他創立實驗學校,實施從活動中學習的教學法。
1904 年杜威到了哥倫比亞大學,最後近四十年的學術生涯大都在此度過。杜威於此多元思想激盪的環境裡,不僅在知識論及形上學的題目上著述頗豐,也延續對於教育理論與實踐的興趣,陸續完成《我們如何思考》(1910)及《民主與教育》(1916)。
杜威同時也投身公眾議題、平權運動,是重要的社會評論家,1919-1921 年於中國講學,期間所發表的演講多達兩百餘場,提出合乎實用主義的哲學思潮和教育思想,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啟發甚巨、影響深遠。
愛麗絲・C・杜威 Alice C. Dewey,1858-1927
全名Harriet Alice Chipman Dewey,美國教育家、女性主義運動支持者。1896 年與丈夫約翰・杜威創辦實驗學校,後為該校校長暨英語、文學部門負責人。與丈夫赴中國期間,亦曾四處演講,致力推動中國女性受教權。
譯者簡介:
林紋沛(序至 4 月 22 日信件)
臺大外文系學士、歷史所碩士。喜歡看書、看戲、旅行、吃甜點。譯有《論友誼》(亞歷山大・內哈瑪斯著,網路與書出版)、《從彼山到此山》(大塊文化出版)。
黃逸涵(4 月 28 日至 8 月 4 日信件)
外語系、翻譯研究所畢業,靠著強調「譯者隱形」的本地化產業餬口,認為名字能印在出版物上就算美夢成真了。
章節試閱
〈東京,二月〉
我們來到這裡了,上陸後一星期,來到山坡上種植樹木的美麗庭園,樹木枝椏上已經含苞待放。梅花不久就會綻開,三月山茶花開,山茶花長在相當高大的樹上。遠方可以眺望壯麗的富士山,眼前則是這一帶的其他山丘,更遠一點是城市的平原。一條運河緊臨我們的山腳下,沿著河邊有條櫻花小徑,原本頗負盛名,但幾年前一場暴風雨摧折了大部分的櫻花樹。
有一棟漂亮的寓所歸我們使用,牆上滿滿裝了窗,這棟屋子裝的是玻璃窗。臥室非常寬敞,有間小小的更衣室,還有一間書房,我現在就坐在書房裡,陽光從四面的窗戶灑落。我們需要陽光——儘管火爐(炭火箱)妙用多多,可以暖腳、烘乾頭髮,像我現在就正在用。我們被探討日本的成堆書籍包圍,全是現代研究的產物,因此我們一刻也閒不下來。房子非常寬敞,屋子一間連著一間,布滿整個山頂,彼此之間由長廊相連,長廊在每間房的兩側暫歇,整體連綿一線。我真該試著拍張照。房子的最末端是X先生的圖書室,由數間房間構成,圖書室的最外側是茶室,舉行茶會之地。我們的主人不是新貴階層,不會為了舉辦茶會而砸下百萬重金購買整套茶具。他對這種做法不以為然。不過,茶室裡有張金漆茶几,彷彿凝結的陽光,也有其他古董家具,現在件件都是無價之寶,在家族裡代代相傳。看看我們怎麼吃早餐,你們應該會覺得很好玩,早餐由阿悌(阿悌是派給我們的侍女)在陽光室侍候我們用餐。一開始先吃水果。兩張小小的漆面茶几可以隨意擺在我們想坐的地方。這棟屋子裡的碗盤和服務方式合我們的習慣。餐具有精緻的古董中國廣彩青花瓷盤,其他則是日式風格餐具。吃完水果之後,她用火爐裡的炭火烤吐司,兩根細長的鐵棒叉進麵包裡,把麵包固定住。她把吐司就這樣叉著遞給我們。她同時一邊教我們日文,我們教她英文,我們教的她早就都會了,我們每次說話,她都會輕聲地笑。喔,我們把吐司放在盤子上,阿悌就不見人影了。咖啡壺放在邊桌上,我們努力要找到杯子來用,又有點擔心破壞了規矩。沒有杯子,阿悌忘了。過了一會,她拿著杯子再度現身,我們喝到咖啡,然後她又下去,用精緻的古董青花瓷盤端來炒蛋。阿悌又是一陣輕笑,然後用我們前所未聞的輕柔嗓音開口說話,一邊把叉在鐵叉上熱呼呼的美味吐司遞給我們;我告訴她吐司掉到地上也沒關係的,地板太乾淨了,因此她樂呵呵地輕笑起來,然後走出房間,到大臥室把咖啡從瓦斯暖爐那拿過來。一切就像美妙的演出,完全不受關於效率、省時省力機器的任何一絲念頭侵擾。接著,兩位侍女來為我們整理床鋪,然後清掃地板,一人斜斜抬起沙發,另一人掃除底下的灰塵,她們微笑、鞠躬,對我們的一舉一動關心不已,彷彿我們是她們的摯友。
現在管家登場,她不停鞠躬,緩——慢——無——比——地聲明她希望能陪我在城裡逛逛,向我導覽說明,這樣可以跟我學習英文。我問她她要上教會嗎,她說她不是基督徒。想想這聽起來多好笑。她是X先生的祕書,也是新成立的基督教大學(由X先生擔任校長)的學生。現在她進來侍候我們吃早餐,她待在旁邊,重複我們說的英語。她懂的英文很多,但太過文謅謅了,因此我要把她說話的方式變得像日常對話那樣,非常好玩。我花最多力氣的地方,是讓她張開嘴巴,打破禮貌的日式輕聲細語(這是日本女士說話的方式)。昨天我們參觀了女子大學,從這棟房子步行就能抵達。校長成瀨先生因癌症而生命垂危。他臥病在床,但還能相當自然地談話。他向學生發表了告別演說,在演講中向教員道別,指定學監(學監現在正代理他的職務)成為他的繼任者。女子大學教授花道、劍道、日式禮儀,總舍監是位出色的女性。她歡迎我隨時過來,看看這些不一樣的東西。
下午我們又有訪客,其中有兩位女士。女性訪客很稀有。其中一位是R醫師,她是整骨醫生,已在此地執業十五年,是我們主人的老朋友。另一位T小姐剛從我們的故鄉歸國,結束七年的旅美生涯。又我在史丹佛常常聽說她的事蹟,也帶了信給她。她在女子大學有一席教職,負責教授社會學,但她說長官恐怕現在還不適合讓她開始教社會學,因此她會從英文教起,在課堂上灌輸社會學,藉此慢慢教授社會學。她是個很有意思的人。她被派來拜訪我,說因為你們的爸爸不在,我可能會很孤單,所以她要來帶我去看戲,我若想帶其他朋友也歡迎。我們已經去過帝國劇場,還坐在男爵的包廂裡,因此這次終於要安排我去看歌舞伎了,我們會席地而坐,欣賞真正古老的日式表演,我非常渴望能一睹風采。我知道演出早上十一點開始,一直演到晚上十點。
〈東京,四月二日〉
我們今天也度過了美好的一天。今天早上很早起,動筆寫信,但儘管匆匆寫完卻沒有寄出,因為我們斷定慢船太慢,相較之下,等晚一點出發的快船會更快。所以你們應該會一次收到很多封信。今天天氣晴朗,陽光燦爛,但一點也不悶熱,非常適合四處走走。我們去了藝術品店,拿昨天挑好的幾幅版畫,然後去拜訪一位政治經濟學教授,他也是國會議員,立場激進、頭腦非常清醒,也很有趣,就其活力、好奇心、興趣而言,很像美國人。我們四處走走,獲益良多,然後教授帶我們去岳母家用午餐。他們的房子是美輪美奐的日式建築,外加一間洋房,就跟許多有錢人家的房屋一樣;日式房屋和洋房毫無相似之處,後者遠遠不及前者之美。地毯、桌布、掛毯皆向德國人取經,日本人在這方面毫無品味,但是在他們的本行上還是非常講究。這間屋子潔淨無比。每寸地板都像鏡面一樣閃亮,現在纖塵不染,也從不曾惹上塵埃。讓我試試自己能不能精確描述我們受到的招待。我們搭上三輛人力車,越過山丘上櫻樹林立的狹窄街道,從街上可以看到有錢人家的美麗庭園從大門閃現、從竹籬上方現出蹤影,竹籬由又長又直、高約六呎的竹竿築成,用繩子綁在一起。竹籬翠綠動人。我們抵達宅邸之後,U先生帶我們到西式客廳,整體非常有維多利亞中期和德式風格。裡頭有漂亮的漆櫃,體積龐大,壓過房間裡的每件東西。家裡的幾位女主人走進房間,向我們鞠躬,她們非常平易近人,聽到我們感謝她們的殷勤好客,向我們報以微笑。首先是小姨子,十六歲的年輕女孩,想去美國,接著是祖母,完全是祖母應該有的樣子,負責發號施令。圍繞她們的孩子個個都跟我們的孩子一樣。幾位女主人親自為我們端上茶,漂亮的青花茶杯,配上小小的漆面茶托和杯蓋。糖果隨茶送上,茶是綠茶。我忘了提到,和U先生共度的那一小時當中,我們已經喝了三次茶,而且是三種不同的茶,加上隨茶附上的小茶點。過了一會,我們被叫去用午餐。矮几上設了三個位子,擺上漂亮的藍色緞面坐墊。兩位年紀較小的女士已跪坐就位,準備招待我們用餐。她們為我們倒葡萄酒、苦艾酒,我們選擇後者。我們每個人面前都有漆碗,蓋著蓋子,盛著普通的魚湯,裡頭有小塊魚肉和切成碎末的綠色食物。我們喝下湯,用筷子把小塊食物送入口中。祖母原本覺得應該要準備西洋料理,但是十六歲的機靈少女為家常菜發聲,於是我們謝謝她們為我們準備家常菜,因為我們少有機會吃到真正道地的日式餐點。除了女兒節上的人偶食物之外,這是我們第一次有這樣的機會,而且是由家裡的各位女主人招待。這似乎是我們獲得的至高殊榮,因為唯有在他們要求外國人席地而坐、由家裡的女主人招待用餐時,日本家庭才真正對外國人敞開。她們跪在矮几附近,侍女端來菜餚、遞給兩位女主人,接著女主人再將菜餚端給客人。真是賞心悅目。我已經漸漸習慣跪坐,可以跪坐一頓飯的時間,但起身時相當笨拙,因為腳一直到膝蓋頭都是麻的。我們喝了湯,吃了冷炸龍蝦和冷炸蝦,蘸旁邊的醬一起吃;接下來是裝在另一只碗裡的冷蔬菜,然後吃了熱炸魚;接著是一些小醬菜,然後是米飯(日本人吃好幾碗飯)、甜點,甜點從頭到尾都擺在旁邊,是冷煎蛋捲,非常美味,最後他們為你送上茶,臺灣烏龍茶。我們也吃了吐司,但那是西式餐點。之後我們離開餐桌,被帶到樓上的房間,房裡有許多漆器、銅器、木器,然後我們又下樓,茶水和一盤水果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但我們沒有什麼時間享用,因為他們要開車送我們去御苑。不過,最後一種茶一定要送上,於是茶端上之際,我們正在門口穿鞋。送上的是濃烏龍茶,裡頭加了牛奶,還有兩塊糖由你自己加進茶裡。於是我們在三小時內喝了六次茶。
御苑很難以筆墨形容。讀讀旅遊書,你們就會明白確實如此。上萬株蘭花是美景的開端。我們看到萵苣、四季豆、番茄、馬鈴薯、茄子、哈密瓜,全都種在溫室裡,供天皇食用。前所未見的完美萵苣,整顆萵苣都長在大小、排列一模一樣的框架裡,彷彿是人工製品,其他蔬果也都很美。為什麼馬鈴薯要種在溫室裡?就別考我了。葡萄種在盆栽裡,看起來在溫室裡種葡萄似乎是初期培育階段,但或許並非如此,我不夠了解這些細小的藤蔓植物,不知道它們是否禁得起風雨。框架裡的花朵完美無瑕。大片的木犀草、雛菊,還有其他我不知其名的鮮豔花朵皆準備就緒,要放到為園遊會準備的花床上。我們十七號不能參加。他們正在搭建一個大亭子,覆上瓦片屋頂,供天皇和皇后在園遊會中落座,園遊會隔天亭子就會拆除,或者該說隔週,因為拆除要花一天以上。如果下雨,園遊會就不會舉行。看起來今天晚上雨好像會把花朵打壞。但白天天氣很好。以前讀了那麼多日式庭園的書,親眼看到這座名園,讓人有點詫異。園裡有大片寬闊的草地,沒有任何花卉,而且這裡的草不像我們那裡的那麼快轉綠,現在草地一片棕色,不過大片水仙花美麗絕倫。水仙花在櫻花樹下,陽光斜斜地灑落其上,構成永生難忘的景致。湖、河、瀑布、橋、小島、山丘皆巧奪天工,還有大型水鳥行走優游於其間,光是這些就值得一訪日本。樹木林立,優美無比,延伸如此廣闊,看上去就像一幅幅接連的圖畫。園區佔地一百六十五英畝,沒有任何建築。起初庭園位於城市的一側,毫無問題,但現在園子位在交通繁忙的軌道上,雖然仍舊屬於城市的外圍郊區。
我們星期一安排好再次到帝國劇場看戲。今天則是看偉大的演員鴈治郎在小劇場登臺演出。據說鴈治郎因為東京演員和經紀人的嫉妒而受到阻撓,來東京時得不到公平的機會。T先生(之前在芝加哥大學)剛剛來訪,打算為我們在臨行前安排一頓晚餐,餐會將在餐廳舉行,所有的老學生都會來。餐廳向來很有意思,我們當然欣然同意。這可能會讓我們在東京多待一天,不過事情尚未定案。剩下的時間裡,我們要盡可能彌補不足的拜訪,還要坐車四處賞櫻,我也希望可以見識大名鼎鼎的茶館。目前為止我們連一間茶館都沒見到,而且除了新潮的百貨公司之外,這座城市連一間適合女士的下午茶館都沒有,百貨公司代表的意義在此地和在我們那裡別無二致。這顯示了東京真正的淑女多不常邁出家門。
隅田川是一條大河,匯聚流自群山這側的條條小溪。河上滿是中式帆船和各種船隻,隅田川是許多歷史的中心,對東京這座城市如此,對整個國家亦然。
〈上海,五月三日〉
在船上時,有人告訴我們,日本人極度重視他人的觀感,中國人則是什麼都不在乎。比較這件事雖然危險,卻是種大家最喜歡的「室內運動」。中國人有點吵(還說不上喧鬧惱人)、親切熱情、有點邋遢——大體而言頗有人情味。他們比日本人高大得多,而且無論用什麼審美觀來評斷,通常都算是相當俊美。最驚人的是,許多勞動者看起來都非常聰明機靈,甚至有書卷氣,比如飯店侍者和接待人員便是如此。招呼我們的侍者帶了點陰柔的氣質,舉止極其優雅,可能是個詩人。我還注意到今天跟我講過話的教師之中,好幾個都散發著巴黎拉丁區那種藝術家的氣息。我逐漸能夠保持距離來看待日本人,顯然那些使他們人見人愛的特質,也正是令人反感的特質。他們將多山小島上的所有資源,運用得淋漓盡致,堪稱一大奇蹟,但是他們的性格整體來說就矯情做作了點,似乎一切事物都有規矩,外人在崇拜其文化中種種唯美效果的同時,也可以看出藝術創作(art)與工藝矯飾(artificial)之間的界線有多麼模糊。所以,能夠再度與隨和的人相處,真是一件輕鬆的事。只不過,他們的慵懶終究會跟日本人「永」保周到一樣,令人覺得煩躁。最後,借用中國友人的話,總歸一句:「東方人充分利用空間,西方人充分利用時間。」這比眾多雋永名句精闢得太多了。
〈上海,五月十二日,星期一〉
北京的動盪似乎暫時平息,校長仍堅守崗位為學生奔走,學生們獲釋。有拿了官府錢的媒體表示,這有部分是因為日方要求各界以寬容態度面對學生的惡作劇。報紙則報導抵制日貨的行動持續擴散,但我們見到的這些人都懷疑大家可能堅持不下去。目前,這裡的人拒收日本貨幣。
東方世界體現了男權文化可能會是什麼樣子、造成什麼狀況。我認為有一點是個大問題,就是眾人的討論一直侷限在女性的屈服順從,好像這件事只影響到了女性。我堅信,中國整個內政與教育的落後,乃至人民生理條件的日益退化、隨處可見的政治貪腐,以及缺乏公益精神,在在使得中國成了容易對付的目標,這些全都是因為女性的處境。日本也同樣有貪腐的現象,只不過狀況在掌控之中而已;在兩個資本集團和兩個大政「黨」之間,似乎有種聯盟關係存在。其中有股非常強烈的公益精神,不過偏向國族主義,而不是社會情感;換句話說,那是愛國主義,而不是我們所謂的公益精神。因此儘管目前日本強盛、中國衰敗,但因為女性的屈從,還是有著相對應的弱點,到時這個隱性的弱點將會使日本瓦解。再來說說兩件中國的事。有位傳教士告訴中國基督徒要如何運用星期天,主要強調那是個適合全家團圓、閱讀、談天之類的好機會。有個人就說,如果必須花一整天陪著太太,一定無聊得要死。後來我們聽說,富有人家的女人(她們理所當然不像貧困階級的女人能夠拋頭露面,行動更不自由)只好聚在一起打牌賭博。大家都認為,要讓成群妻妾過上鋪張奢侈的生活,成了政治貪腐的一大主要源頭。另一方面,在北京一場政治抗爭會議中,指派了十二人組成委員會,負責面見官員,而其中四位是女性。日本嚴禁女性參與任何談論政治的會議,並嚴格執行這項法律。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女性比日本女性還多,有部分可能是因為中國缺乏女子高等教育機構,但也是因為她們不必在接受教育時就放棄原有的婚姻——事實上,我們還聽說,留過學的女性在同樣學成歸國的男性市場中相當受歡迎,富有人家也對她們特別有興趣。想當然耳,對於女性處境的問題,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思想也比日本人進步多了。
「很難說」是中國人常用的口頭禪。八日傍晚,大學校長在內閣逼迫下辭職了,他其實是在暗殺的威脅下這麼做的。在此同時,軍警(也可以說是土匪)入城了,北京大學被包圍起來,所以他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希望拯救學校才毅然出走。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裡。學生獲釋的消息是透過電報傳出來的,但他們拒絕大肆宣傳這件事。這位校長似乎比我所認知的更具自由派高級知識分子的領袖風範,政府都對他有所敬畏。他才擔任校長兩年,在那之前,從來沒有學生為了政治上街遊行,可是如今,他們個個都是這波新興運動的領袖。當然了,政府會提出反動保守的言論,到時學生就會離開,正直的教師也會全數辭職。說不定全中國各地的學生都會走上街頭。但這真的很難說。
〈東京,二月〉
我們來到這裡了,上陸後一星期,來到山坡上種植樹木的美麗庭園,樹木枝椏上已經含苞待放。梅花不久就會綻開,三月山茶花開,山茶花長在相當高大的樹上。遠方可以眺望壯麗的富士山,眼前則是這一帶的其他山丘,更遠一點是城市的平原。一條運河緊臨我們的山腳下,沿著河邊有條櫻花小徑,原本頗負盛名,但幾年前一場暴風雨摧折了大部分的櫻花樹。
有一棟漂亮的寓所歸我們使用,牆上滿滿裝了窗,這棟屋子裝的是玻璃窗。臥室非常寬敞,有間小小的更衣室,還有一間書房,我現在就坐在書房裡,陽光從四面的窗戶灑落。我們需要陽光...
推薦序
【導讀】〈誌杜威:紀念一位哲人的文化行旅〉 / 王清思(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二十世紀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嶄露頭角的時期,在眾多哲學家中,約翰.杜威(John Dewey)可說是獨樹一格;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不僅限於哲學界本身,也遍及了教育界和一般的社會界。他一生的足跡廣及歐洲的土耳其、南美洲的墨西哥、遠東的日本和中國,以及蘇俄。杜威脫離了一般哲人深奧冷峻的印象,給人一種親民樸質之感,因為他所重視的是一種應用哲學,他所關切的是人的問題。杜威認為哲學應從事文化的批評,哲學家應自詡為文化的醫生,勇於診斷我們的文化哪裡生病了,真正的藥方又在哪裡。
敏銳的讀者在閱讀《一九一九,日本與中國:杜威夫婦的遠東家書》時,可以試著去感受杜威在字裡行間所流露的淑世關懷,也可以試著去拼湊出他所看到的各種病兆。評論家曾形容杜威本人和他的作品皆透露出他過人的持平能力,指的是他可以在正反兩面中看出各自端倪,既不失偏頗,又能如實探究。正如在這些書信中,杜威對中日文化的見地,各有褒貶,或者說,褒中有貶,貶中亦有褒,讀者可以細心留意。還有,杜威對於人事物的見解會隨著事實與經驗的改變不斷調整,大至他對五四運動的評價,小至他對中國民族性的看法。我相信藉由杜威的哲學高度,讀者所看到的世界應該會比一般的旅遊札記更多出了一份知性的饗宴。
對今日的讀者而言,一百年的時空轉換,意味著我們能讀出更多內涵,我們可以套入自己的旅遊經驗與文化體驗,與杜威和杜威夫人做一番比較。姑且不論有所一致或不一致,我們可以想想,這一百多年來改變了什麼?什麼沒有改變?其實,我發現,杜威和杜威夫人也是一直忙著比較,比較他們的歐洲經驗和遠東經驗,比較美國家鄉和遠東文化的差異,比較日本和中國民族性的不同。相信這種多重比較的視野,能為閱讀帶來更豐富的意義和樂趣。以下先談談我自己作為此書讀者的經驗。
◎
距離上次閱讀杜威夫婦的遠東家書《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已將是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時我正好開始著手準備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是杜威中國行的經歷和影響。我很想了解杜威在中國講學兩年經歷了什麼、反思了什麼?對他的意義和影響又是什麼?有趣的是,當時有人好心提醒我這個題目很難研究,建議我改題目,否則會畢不了業。還好,閱讀這些書信,給了我初步的信心繼續深究,也才有後來的研究成果,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我的英文專書《John Dewey in China: To Teach and to Learn》(美國紐約大學出版社SUNY,二○○七)。
如同我的專書書名所揭示,杜威在中國有兩個角色,一是教學者,二是學習者。書中兩個角色都有所著墨,但是,對於一個喜愛杜威的人而言,了解他如何在異地適應生活,如何與人互動,如何洞察周遭,如何詮釋所見,在在都讓我更認識杜威這個人,更貼近他的價值與理想,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經驗。如今再讀,彷彿遇到了老友,讀來格外親切。
十五年前閱讀這些書信時,我是站在研究者的角度,戰戰兢兢地探尋與主題有關的線索,生怕錯過任何重要的訊息。但這一次,我將自己設定成一般讀者,抱持著自然輕鬆的態度,隨著杜威夫婦細膩的文字,進入他們筆下所描繪的異國旅程,彷彿隨著他們的步伐,一起走進了當時的日本劇院、餐館、民宅,體驗了一百年前的日本和中國各階層的人們是如何地生活;隨著他們時而逗趣幽默、時而嚴肅反諷的口吻,一起反思社會百態與文化差異。有了這次不一樣的閱讀經驗,我更加能明白當年這本書─也就是一九二○年由杜威女兒編撰,由紐約的達頓出版社(E.P. DUTTON)出版的《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誕生的緣由。想想杜威和夫人每隔一段時間就捎回家鄉的家書,在親戚、家人和朋友之間如何地流傳、如何地受歡迎,就可以了解為何杜威女兒當時決定要出版這些本來沒有打算要公開的私人信件。信函中所描述的東方世界既深入又有趣,與更多人分享也不失為美事一件,畢竟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
現在再讓大家認識這段歷史:關於杜威夫婦的遠東行,一場意外的豐收之旅。
一九一八年秋天,杜威從哥倫比亞大學那裡獲得休假,動身前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授課。他和妻子愛麗絲心想,這樣可以在地理上更靠近亞洲,因此打算來年春天藉此去日本旅行。杜威也希望這樣的旅行對妻子有幫助,可以療治她先前因兒子在義大利旅程中意外夭折而帶來的長期抑鬱。杜威夫婦的日本朋友知道了杜威打算造訪日本的消息之後,就開始為他們做了一些參訪規畫,包括在當時東京帝國大學的哲學系列講座。杜威夫婦於一九一九年二月間抵達了日本,逗留了約兩個月之久,之後他便受邀前往中國。
杜威在日本雖然備受禮遇,出席了各種重要場合,並和許多知名人士會面,但他的學說並沒有引起特別大的回響,反之,他在中國卻受到了空前的歡迎。如果說日本行是杜威夫婦早先規畫好的遠東旅程,那麼後來追加的中國行卻成了意外而美麗的插曲,由於插曲太過精彩,太過撼動人心,轉而變成遠東行的主調。
事情的來由是這樣的:當年胡適等人輾轉得知杜威夫婦在日本旅遊的消息時,便嘗試與他取得聯繫,並邀請他到中國訪學一年。收到邀請時,杜威頗為驚喜。他覺得利用返美前的夏天造訪中國是個不錯的安排,只是他也不確定自己能待多久,畢竟哥倫比亞大學或許不會同意他請假一年。然而,這對杜威而言,是很有吸引力的一趟旅程,因為他想要多認識東方社會和文化。不過,儘管杜威在前往中國前夕得知哥大的請假申請已經獲准,他在抵達前仍然沒有正式答應要在中國待上一年。他需要多一點評估,以便做出明智的決定。
這當然不是一個輕鬆的決定。對於中國,杜威畢竟了解得很少,不知道這樣的決定是否要承擔一些風險。在經濟上,杜威也有顧慮,他的生活一點也不寬裕。事實上,若不是因為一位富人好友巴恩斯(Albert Coombs Barnes)的贊助,杜威無法支付去日本的旅程。巴恩斯答應支付杜威一個月的薪水,條件是要他撰寫一份報告,主題是日本在大戰後的國際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經濟方面的不放心,杜威也不知道他的中國弟子們會給他安排一些什麼樣的活動。儘管杜威對他的中國行有著種種複雜的感受,最後他想去探險的心還是大過擔憂。
然而,這份擔憂卻隨著他踏入中國時煙消雲散,因為迎接他的除了是久違的學生,還有那震撼人心的五四運動。杜威和夫人初抵華不久即遇上了五四學生示威運動。杜威心想,中國這個帶有神祕色彩的古老文明,不是一向被西方人視為被動而停滯不前嗎?為何在北京街頭抗議的學生,竟然可以如此公開激烈地反對政府當局將山東割讓給日本的決策,甚至還能成功地說服商人們一起加入他們的行列抵制日貨?杜威一直關注著學生運動的變化與後續發展,他甚至希望這個運動能喚起人民的決心,透過和平的方式重新建立一個真正有民意基礎的新政體。畢竟,杜威一直以來都相信:真正的民意所匯集而成的一種思想與道德的力量,絕對勝過任何軍事強權的武力威嚇。
說真的,五四運動宛如是好客的中國人送給杜威的見面禮。如果不是五四運動激起的社會浪潮和求變的社會氛圍引發杜威探究的興趣,若不是因為杜威正好在這精彩的歷史交會點上抵達中國,他或許待了兩、三個月遊山玩水一番之後,就決定打道回府,也不會答應在中國講學一年,甚至還願意再留第二年。杜威曾這麼說:「對一個外出漫遊、四處搜尋浪漫生動景致的人來說,中國看上去好似一幅令人掃興的圖畫。然而,要是用心靈的眼睛去觀察,那麼,它處處顯示出現在正上演著一部極富吸引力的大戲。」的確,「五四中國」充滿著各種問題,但也意味著無限可能,的確是一齣相當引人入勝的劇碼。在五四中國這個舞臺上,杜威既是觀眾,也是演員,他盡量扮演好兩種角色,而杜威和夫人留下來的這些遠東家書,也讓我們有機會觀賞這齣難得的歷史劇碼。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齣五四大戲中,還有另一名重要的外國觀眾和演員,那就是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羅素於一九二○年受邀至中國講學,停留了九個月(其中幾個禮拜,因大病一場,必須停止所有活動),與杜威在中國打過照面,最後離開中國的時間點也和杜威夫婦相去不遠。羅素回到英國之後,儼然成了中國專家,隔年(一九二二年)就出版了《中國的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其實,杜威也一樣有資格寫這樣一本書,他停留的時間更久,接觸的層面也很廣,他也接到了美國出版社的寫書邀請,但最後沒有答應。我想,這不是因為杜威沒有能力寫,而是因為他深知中國人的問題不是由一個外國人三兩下就可以講清楚、道明白的;杜威也曾表示過,他希望中國人的現況和問題,可以由中國人,以中國人的角度來寫。杜威看了羅素的《中國的問題》一書之後,提出了這樣的評論:他誇讚羅素寫得很清楚,但他認為這樣的清晰度,對於一直動盪不安的中國而言,不免格格不入。講到這裡,不知讀者們是否也跟我一樣,覺得這齣五四大戲實在太精彩,不看可惜!
◎
在閱讀「遠東家書」時,讀者應該能察覺到,在日本的杜威和在中國的杜威,給人不同的感覺,在日本的他,比較像是旅者,讚嘆著日本人如此周到的禮貌,如此精緻的美食文化,如此乾淨的街道和如此一塵不染的地板,但也詫異著他們的英文是如此的有限。雖然偶爾也會看到杜威陷入哲思,例如流露出對自由主義者的同情,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對於男性沙文主義的嘲諷,以及對於美國民主理想的擔憂,但整體而言,閱讀杜威和夫人的日本書信會令人放鬆心情,尤其看到杜威揭露自己一開始不熟悉跪坐,大剌剌地拿著椅子坐,到後來他們又寫到自己入境隨俗,願意跪坐兩小時,接受他人盛情款待吃飯,到起身時的笨拙和雙腳麻痺的樣子,實在令人莞爾。
反觀,在中國的杜威不只是個旅者,他更是個哲學家,因五四所拋出來的巨大難題,鎮日思索;他時而興奮,時而沮喪,時而又燃起希望,他毫無保留地將自己涉入其中,他投入的程度有多少,他的學習和成長就有多少。這些書信只記錄了杜威成長的一小部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杜威當時在中國為《新共和》(New Republic)和《亞細亞》(Asia)兩本雜誌所寫的四十多篇報導(有收錄在杜威作品全集中),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知名的政治評論人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還稱讚杜威的這些遠東報導是這一文類的最佳典範。
《一九一九,日本與中國》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其中有部分的信函是由杜威夫人愛麗絲所執筆的。當時很少女性,特別是在日本,能擁有像愛麗絲這樣的機會,出席大都只有男性才能參與的場所,看見多數男性看不到的角落風景,例如日本藝妓眼中獨特的悲傷。愛麗絲的眼光所關注的事物,應該與男性有所不同,這點對於現代讀者而言,也是彌足珍貴的,應該能引發高度興趣和共鳴。希望本書的讀者,不管是對歷史或對杜威有興趣,都能跟我一樣,從中發現許多樂趣和意義。
【導讀】〈誌杜威:紀念一位哲人的文化行旅〉 / 王清思(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二十世紀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嶄露頭角的時期,在眾多哲學家中,約翰.杜威(John Dewey)可說是獨樹一格;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不僅限於哲學界本身,也遍及了教育界和一般的社會界。他一生的足跡廣及歐洲的土耳其、南美洲的墨西哥、遠東的日本和中國,以及蘇俄。杜威脫離了一般哲人深奧冷峻的印象,給人一種親民樸質之感,因為他所重視的是一種應用哲學,他所關切的是人的問題。杜威認為哲學應從事文化的批評,哲學家應自詡為文化的醫生,勇於診斷我們的文...
作者序
【序】
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教授約翰.杜威(John Dewey)和夫人愛麗絲.C.杜威(Alice C. Dewey)於一九一九年初離開美國,前往日本旅行;本書出版的信件即是出自杜威夫婦筆下。杜威夫婦迫不及待地踏上旅程,因為他們多年來一直渴望至少能看一眼東半球的景色。這趟旅行原本純屬休閒性質,但就在他們從舊金山出發前夕,杜威教授受邀(邀請以電報發出)到東京帝國大學講課,之後也受邀到日本帝國各地演講。杜威夫婦三、四個月來在日本各地旅行參訪,度過非常愉快的時光,又因意外備受禮遇而倍感開心,於是到了五月,他們決定繼續旅程前往中國,在回美國以前,至少在中國待上幾週。
中國正身陷困局,掙扎成為統一獨立的民主政體,杜威夫婦對此深感興趣,因此改變了原本在一九一九年夏天返美的計畫。杜威教授向哥倫比亞大學申請一年休假,請假獲准,他和杜威夫人現在仍然留在中國。夫婦兩人皆四處演講、交流,致力將西方民主的幾分內涵帶給這個古老帝國,同時,兩人也十分享受這段經歷,一如信中所言,珍視這些時光,認為這趟旅程豐富了他們的人生。這些信件原是寫給他們身在美國的孩子,杜威夫婦從未想到家書有一天會付梓。
伊芙琳.杜威*
一九二〇年一月五日寫於紐約
*伊芙琳.杜威(Evelyn Dewey,一八八九─一九六五)是杜威夫婦的長女,本身也是美國教育家,社會運動者。她將父母一九一九年間所寫家書編輯整理出版(即為此書),也曾與父親合著《明日學校》(Schools of Tomorrow)。她與妹妹露西(Lucy)曾先後參與父母的遠東行,兩人也在中國演講、授課。
【序】
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教授約翰.杜威(John Dewey)和夫人愛麗絲.C.杜威(Alice C. Dewey)於一九一九年初離開美國,前往日本旅行;本書出版的信件即是出自杜威夫婦筆下。杜威夫婦迫不及待地踏上旅程,因為他們多年來一直渴望至少能看一眼東半球的景色。這趟旅行原本純屬休閒性質,但就在他們從舊金山出發前夕,杜威教授受邀(邀請以電報發出)到東京帝國大學講課,之後也受邀到日本帝國各地演講。杜威夫婦三、四個月來在日本各地旅行參訪,度過非常愉快的時光,又因意外備受禮遇而倍感開心,於是到了五月,他們決定繼續旅程前往中...
目錄
【導讀】誌杜威:紀念一位哲人的文化行旅 (王清思)
序 (伊芙琳・杜威)
*日本篇(一九一九年二月至四月二十八日)
東京,二月,星期一
二月十一日,星期二(東京)
東京,二月十三日,星期四
東京,二月
二月二十二日
東京,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三月二日,星期日早上
東京,三月四日,星期二
東京,三月四日,星期二
三月五日
東京,三月十日,星期一
東京,三月十四日,星期四
東京,三月十四日
東京,三月二十日,星期四
鎌倉,三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東京,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東京,四月一日,星期二
東京,四月一日
東京,四月二日
東京,四月四日
東京,四月八日
奈良,四月十二日
京都,四月十五日
京都,四月十五日
京都,四月十九日
京都,四月二十二日
四月二十八日,熊野丸船上,航向中國
*中國篇(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至八月四日)
上海,五月一日
上海,五月二日
上海,五月三日
上海,五月四日
上海,五月十二日,星期一
星期二早晨
上海,五月十三日
南京,五月十八日
南京,五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南京,五月二十三日
南京,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北京,六月一日,星期天
北京,六月一日
北京,六月二日
六月五日
北京,六月五日
六月七日
北京,六月十日
六月十六日
北京,六月二十日
北京,六月二十日
北京,六月二十三日
北京,六月二十五日
北京,六月二十七日
北京,七月二日
北京,七月二日,星期三
北京,七月四日
七月七日,星期天
北京,七月八日
北京,七月八日
北京,七月十一日
北京基督教青年會,七月十七日
北京,七月十七日
北京,七月十九日
北京,七月二十四日
七月二十七日,時間稍晚
北京,八月四日
*杜威夫婦寫信時日期略有誤植,本書謹遵照原書日期與排序。
【導讀】誌杜威:紀念一位哲人的文化行旅 (王清思)
序 (伊芙琳・杜威)
*日本篇(一九一九年二月至四月二十八日)
東京,二月,星期一
二月十一日,星期二(東京)
東京,二月十三日,星期四
東京,二月
二月二十二日
東京,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三月二日,星期日早上
東京,三月四日,星期二
東京,三月四日,星期二
三月五日
東京,三月十日,星期一
東京,三月十四日,星期四
東京,三月十四日
東京,三月二十日,星期四
鎌倉,三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東京,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東京,四月一日,星期二
東京,四月一日
東京...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