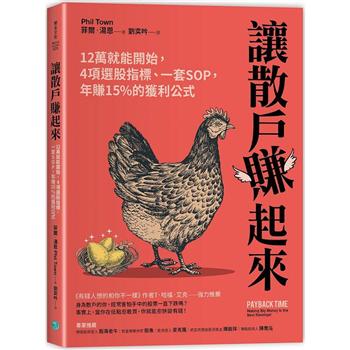這就像把望遠鏡倒過來,你只能看到那些大塊的東西:我是怎樣生活的?我愛過誰?我得到什麼?我錯過什麼?我還能做些什麼?
生與死本是自然遞嬗的過程,然而在今日社會,死亡和死亡的過程脫離日常生活,變得隱密而不可言說。人們對死亡的認識變得模糊,因而心懷恐懼。然而,這個把我們帶往未知世界的過程,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臨終關懷醫院是瀕死者度過生命最後時光的地方。
住進院裡的人,知道自己沒有機會回家,知道自己沒有多少時間,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
他們只有短暫的一段時間,可以為自己的生命做個總結,與自己和他人和解,面對死亡這個課題以及處理死後的問題。
本書作者和攝影者走訪德國數所臨終關懷醫院,和院中的病人、家屬及醫護人員深談,寫成細膩的文字紀錄。攝影者則分別為每個病人拍攝兩張臉部特寫;一張是即將畫上句點的生命,另一張則是死亡的容顏。從這兩張並列對比的照片,看到面對生命終點的倉皇、滿足或哀傷,也看到死亡的平靜。
斯特萊太太在死前一個月,仍抱著堅定的求生意志。
51歲的芭芭拉,從小在孤兒院長大,渴望母親的愛。她在最後幾個月常常夢到自己是個孩子。
當死亡站在曹太太的門前,她變得更誠實。能夠談論自己的內心,對她是一種解脫。
談普林太太打定主意,直到最後一刻都帶著清醒的理智,精心安排剩下的時間。
好幾個瀕死病人沒有機會和最親密的人開誠布公地談「死」這件事,他們來不及向對方說出愛。
這些瀕死者最後的願望是什麼?希望多活一些時候,希望死亡來得乾脆而溫柔一些,希望死亡不是一切的結束……
在臨終關懷醫院,這些願望並非完全不可能實現。
在死亡來臨前「真正的生活」,不但是瀕死者的願望,也是以為死亡很遙遠的每個人,珍惜生命最好的方式。
作者簡介:
Beate Lakotta(貝雅特.拉蔻塔)
生於1965年,現擔任德國《明鏡》週刊(Spiegel)科學編輯。攝影師華特.謝爾斯(Walter Schels)生於1936年,以人物和動物的性格特質研究而聞名。他們在2003年於《明鏡》週刊所發表的〈死前再活一次〉專題,因報導深入而獲頒漢薩–米特獎(Hansel-Mieth-Preis),以及聯邦志工福利工作會所頒發的德國社會獎(Deutsche Sozialpreis)。華特.謝爾斯的攝影作品並榮獲2004年世界新聞攝影大賽二獎。
章節試閱
18.對不起,我得了癌症
亞尼克•伯菲德(Jannik Boehmfeld)
6歲,生於1997年7月23日
第一張照片拍攝於2004年1月10日 2004年1月11日,病逝於德國漢堡市艾本多夫大學醫院
絲珂•伯菲德(Silke Boehmfeld)
30歲,生於1973年4月12日
第一張照片拍攝於2004年1月10日 2004年2月5日,病逝於德國漢堡市威廉斯堡區社區醫院
我們沒有機會為絲珂•伯菲德拍攝最後一張照片
在所有成員都還活著的最後一天,醫生說,這個家庭——包括絲珂•伯菲德、她的丈夫耶斯•巴瑙,以及他們的兩個兒子亞尼克和尼古拉斯——竟然還能積極地生活,讓人難以置信。但是伯菲德一家長久以來都很明白,對於他們來說,他們只能用克制來面對災難,不讓自己墜入無底深淵。唯有如此,活下來的兩人才不會停滯不前。
當醫生在亞尼克•伯菲德的小腦袋裡發現一個罕見的腫瘤時,他才四歲。某個基因細胞在大腦胚胎發育階段沒有正常地分離出來,而是不受控制地長成腫瘤。四個月後,亞尼克的母親絲珂•伯菲德被診斷出罹患乳腺癌,而且癌細胞已經開始擴散。絲珂的母親和姨媽都死於乳腺癌。她沒聽說哪個人患了這種病能夠活下來。對這對母子來說,治癒的希望從一開始就很渺茫。
這兩種癌症之間並沒有什麼關聯。但為什麼會是亞尼克和絲珂?為什麼兩個人同時患病?這意味著什麼?每一次當夫婦倆問自己這些問題時,就會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他們並沒有為即將失去幾個人共同的未來而悲哀。他們展開行動:手術、化療、複檢。不左顧右盼,只能不斷向前。他們期望,媽媽能死在後面;她覺得自己虧欠亞尼克,還有小兒子尼古拉斯。尼古拉斯還不到兩歲,他有權利要媽媽和哥哥留在身邊嗎?
進行腦部手術後,亞尼克的運動機能受到影響。七歲的孩子在地上爬,重新學習走路和說話。他是個小鬥士,父母很疼愛他這一點。他從不放任自己,難受的時候也不抱怨。有時候在遊樂場上,別的孩子會辱罵亞尼克:你怎麼這麼慢?我們聽不懂你說什麼。說清楚一點!這時亞尼克會說:
「對不起,我得了癌症。」
與此同時,絲珂也處於第一次手術後的恢復期,隨後的化療讓她的頭髮都掉光了,但是也讓她充滿希望。「都習慣了,」她說話的語氣好像在講一種讓人討厭的花粉過敏症:「癌症現在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其實,人們也可以反過來說:這個家庭的命運現在是癌症的一部分。它不放過他們。
每一天是好是壞,取決於癌症的各項指標和白血球數。耶斯負責安排病人看醫生,安排住院,接受治療。他是和醫生討論病情的那個人。有些事絲珂根本不想知道。她把對自己和對亞尼克的責任都放在丈夫手上。耶斯•巴瑙原本在一家飼料公司工作,但他常常沒法去上班。絲珂需要他的幫助,她必須讓自己先強壯起來。亞尼克也一樣需要他,尼古拉斯就更別說了。他還太小,不能理解家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至少得讓他不受傷害。
有一段時間,整體狀況還算不錯。這都要感謝漢堡大學醫院兒童腫瘤科的醫生和護士,他們讓亞尼克能過一種接近正常的生活。在醫院裡,伯菲德一家認識了其他癌症兒童家庭。有時候,一個孩子死了,所有人會一起悲傷悼念。在這個互相安慰的團體,伯菲德一家得到了很好的照顧。和醫院的心理醫師定期談話對他們很有幫助。絲珂不斷將自己的病大事化小。她總是說,一切正常。她不想聽任何反面意見。
但是到了夏天,幾乎是在同一時間,癌症在兩個人身上分別占領了更多的領地。絲珂的胸部長出腫塊,她必須馬上住院。三天後,醫生在亞尼克的頭部發現贅生物。短短幾個星期,贅生物已經擴散到整個頭部。兒童腫瘤科的醫生謹慎地說,理論上,有可能撐五年,但也有可能只剩幾個星期。
可以肯定的是:亞尼克會死。藉著化療,醫生們只能將腫瘤和轉移的癌細胞盡可能控制住,讓孩子在盡可能拉長的時間裡能走、能說話、能玩耍。當耶斯把這個消息告訴妻子時,他感覺到她的生命意志在那一刻崩潰。如果兒子好不起來,她怎麼會好呢?耶斯的腦海裡回響著另一個妻子不知道的診斷。醫生說,絲珂可能不會活過耶誕節。絲珂既不向醫生,也不向丈夫打聽自己的病情。她只是說:不管發生什麼,我絕不能死在亞尼克之前。
耶斯覺得,在他的妻子和兒子之間開始了一場荒誕的競賽,絲珂的生命力看來先衰弱下去。雖然照理說,亞尼克應該已經沒什麼體力了,但他卻能自己穿衣服,還能爬起來到處活動;與此相反,絲珂卻幾乎沒辦法從沙發起身。不管做什麼她都需要別人幫助。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她的腦部和肝臟。她的意識已經不怎麼清楚。她看上去好像試圖在跟孩子們保持距離,特別是對尼古拉斯。她不願把他抱在懷裡。她把他推開,不讓他在自己身邊,不讓他親吻自己。她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唯一的念頭上:只要亞尼克還活著,她就得活下去。
耶誕節時四個人一起慶祝,但是到了一月,比賽結果明朗化:亞尼克跟弟弟吵架時,突然嘔吐,然後昏了過去。緊急送到醫院,醫生發現,亞尼克的腫瘤又長大了,沿著腦幹蔓延,而且脊柱上也有轉移。亞尼克情況很糟,他口齒不清,對任何刺激幾乎都沒有反應。利用手術減輕對大腦的壓迫,對於這個孩子來說會是一種折磨。在兒童腫瘤科,所有人都知道,他們現在能做的只是陪伴他到死亡。
醫生可以給他接上監視器,好觀察孩子的生命徵象。但是當孩子即將離開人世,醫生會避免這麼做。他們想讓父母直接接觸處於彌留之際的孩子,而不是通過一臺機器。醫護人員試著尋找一種既能減輕亞尼克的痛苦,又不使他的意識完全喪失的方式。大約有十種藥物可能發揮作用,但必須一一嘗試。德雷舍醫師嘗試用一種抑制痙攣的藥物,輔以大量可的松抑制積水,以及小劑量嗎啡抑制疼痛。幸運的是,通過對心跳和血壓的監控,證明這種搭配是有效的。
耶斯在這段時間把尼古拉斯送到姨媽那裡,然後把妻子從家裡接到醫院。醫護人員在亞尼克的房裡給絲珂加了一張床。亞尼克已經幾乎不能動,也不能說話了,但是他還能認出自己的父親和一些醫護人員。過去的幾年,他在這裡度過很多時光。 父親從床頭櫃上拿起眼藥水。亞尼克的左眼無法閉上,這是神經系統的問題。父親給亞尼克眼裡滴了幾滴藥水,又幫他潤了潤嘴唇。他親了親自己的孩子,撫摸著他,輕聲對他說話。「你是個天生的戰士,」他說:「我知道,你從來沒有低過頭。甚至現在你也沒有放棄。你還在戰鬥。但是親愛的上帝說,不應該這樣。」護士克莉絲汀站在門口,問能否幫上什麼忙。不過巴瑙先生已經在給孩子擦洗了,他做得很好。「我已經做了兩年了。」父親看起來很疲勞,六個月前他請了病假,「當這一切都過去,我不知道自己會怎麼樣。」
這段時間以來,沒有人知道絲珂•伯菲德的感受如何。她並不想親近自己的孩子。耶斯請求她:「握著他的手,和他說話。」她做不到。耶斯知道,他不能責怪她。她愛孩子,但自從腫瘤轉移到她的大腦,她的意識和感覺有了很大的變化。雖然她說過她不想回家,要在亞尼克的房間一直待到他離開人世;但這段時間以來,她表現得好像不記得兒子生病一樣。亞尼克在家裡昏倒,等待救護車到來的時候,她無論如何一定要給半昏迷狀態的孩子餵點吃的。她罵丈夫說:「如果你不想吃,你不回答我,那我看你就是不餓。」
現在,絲珂在自己床上,看著丈夫怎樣撫摸亞尼克的小手。看起來,她這種遠遠的觀望裡混雜著一種恐懼,也許還有憤怒。幾個月來,不在亞尼克之前死去的想法給了她力量。現在,如果孩子滿足了她這個願望,她會怎樣呢?
兒童腫瘤科的醫生知道絲珂•伯菲德的情況很不好。「我們不知道亞尼克要走的旅程還有多遠,」德雷舍醫師說。最好伯菲德太太現在能跟孩子道別。但是她應該在那裡待到最後一刻嗎?「剩下的時間有可能是幾個小時,幾天,甚至是幾週。」但絲珂自己所剩的時間可能也不多了。
那天夜裡亞尼克突然痙攣發作,第二天上午又有一次。醫生和這一家人知道,死亡在幾個小時內就會來臨。孩子呼吸急促,表示他已經進入彌留狀態。絲珂問孩子:「你要喝杯熱巧克力嗎?」孩子早就不能給她任何回答。護士克莉絲汀又一次吸出孩子肺部的分泌物。她今晚會和伯菲德一家在一起。從亞尼克生病以來,她就認識了這一家人。失去這個孩子對於兒童腫瘤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件難過的事。但是現在沒有任何人會嘗試去延長他的生命。「你不用再折磨自己了,」耶斯在兒子耳邊悄悄地說:「你夠拚了,小人兒。你可以走了。請你走吧。」
後來,耶斯說,一直到孩子生命的最後幾分鐘,他的妻子才突然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兩人抱頭痛哭。絲珂說:「我看到自己躺在那裡。」
亞尼克葬禮後的那天夜裡,絲珂很長時間以來第一次睡得很好。耶斯在墓地上試圖不去看兒子敞開的墓穴,絲珂卻坐在輪椅上一直盯著看,她還仔細看了人們送來的花圈。花圈很多。她以前的同事們也來參加葬禮,讓她很意外。在極短的一瞬間,她突然有種感覺,覺得耶斯推著她的輪椅到墳墓邊緣的力量,足夠把她推到墳墓裡面去。神父張開手臂,開始禱告。墓穴已經覆蓋,讓亞尼克一個人待在底下。
一個星期後,絲珂開始接受新的化療,她看起來幾乎可以說是興高采烈。她說,她的癌症跟亞尼克性質不同。現在一切狀況都不錯。而且她現在更有活下去的勇氣,為了尼古拉斯,她的小兒子。
不管怎樣我們得挺過去,她丈夫說。 絲珂•伯菲德比她兒子亞尼克多活了二十五天。
當飛機投下的炸彈把華特•謝爾斯家和鄰居們的房子變成火海中的廢墟時,他只有九歲。這個戰爭中長大的孩子出生於一九三六年。沒多久,他置身廢墟中,藉著圍裙的花色辨認出一位鄰居,又挖出一隻炸斷的胳膊。這些經驗使他對屍體、骨骸和葬禮產生深沉而長久的恐懼。他曾經為總統、歌劇女伶、諾貝爾獎得主和新生兒拍攝肖像。對於在臨終關懷醫院中工作,他的感受不僅僅是敬畏。
我出生於一九六五年,還沒有親眼見到死人的經驗。初次接觸死者難免心懷忐忑。我最早的對死者肖像的記憶來自漫畫或電視:也許是漢莎航空公司被劫持的那架飛機死去的機長,或是被「紅軍組織」謀殺的施萊亞藏在汽車後車箱裡蜷縮的屍體*。總之不是我認識的人。最近的記憶則是我在報紙頭版看到的一張照片,照片的主角是個公車司機,在臺拉維夫一次恐怖襲擊中遇難,上半身趴在方向盤上。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他的臉。
每天我們都能看到慘遭殺害者的照片,看到在戰爭和自然災害中遇難者的照片,讀到對他們的痛苦和死亡的精確報導,並不覺得有什麼不自然。但是對於每天都在發生的日常自然死亡,我們卻很少看到報導或照片。也許這是因為,看到這些會讓我們更容易聯想到自己未來的終結?我們用所謂虔敬來避開這種不安。有人認為:展示死者的肖像是侵犯死者尊嚴。那麼,若是我們掉過頭,不去看剛剛去世者的面容,難道更能表示對死者的尊重?
當我們意識到,這麼做並沒有觸犯遠古的禁忌時,我們有了更多勇氣。這種對人的自然離世和正常死亡的避諱,實際上是新時代的產物。西方文化裡的基督教藝術家就曾充滿激情地描繪過苦痛的各種形態。所有的教堂充斥著這樣的作品:我們能想到的有那些被折磨至死的聖者,那些被雕成石像或是繪成油畫的瀕死富人或是戰功卓著的領袖。而其中代表則是聖母憐子圖;聖母瑪利亞哀痛地看著躺在她懷裡的兒子——被折磨得渾身血污,額上汗跡斑斑,兩頰和嘴唇變成藍紫色的耶穌基督。這一幕預示著最終的解脫。而引人注意的是,肉體的痛苦——即人性的表現——是如何精確地被描繪出來。
18.對不起,我得了癌症 亞尼克•伯菲德(Jannik Boehmfeld) 6歲,生於1997年7月23日 第一張照片拍攝於2004年1月10日 2004年1月11日,病逝於德國漢堡市艾本多夫大學醫院 絲珂•伯菲德(Silke Boehmfeld) 30歲,生於1973年4月12日 第一張照片拍攝於2004年1月10日 2004年2月5日,病逝於德國漢堡市威廉斯堡區社區醫院 我們沒有機會為絲珂•伯菲德拍攝最後一張照片 在所有成員都還活著的最後一天,醫生說,這個家庭——包括絲珂•伯菲德、她的丈夫耶斯•巴瑙,以及他們的兩個兒子亞尼克和尼古拉斯——竟然還...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