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律碰上道德,三個生死抉擇的狀況,你的選擇會是什麼?
理性判斷vs.良心煎熬;一場場猶如心理劇場的法律裁判
輔大法律學系教授 吳豪人
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謝世民
台大法律學院教授 顏厥安 專文推薦
------------------------------------------------------------
案例一︰輪船翻覆,一艘只能搭載24人的救生艇擠進40人,要拯救最多人命,必須將16人拋入海。誰該被犧牲?
案例二︰5名洞穴探險者受困山洞,水盡糧絕。他們決定抽籤選定1人供其他4人分食以求最多人活命。但有人反悔退出,怎麼辦?
案例三︰20個印第安人的命運掌握在1名外來者手中,他要嘛手刃其中一人而讓其他19人獲釋,要嘛拒絕執行而由槍手將20人全斃了。他該如何選擇?
要針對以上每一個案例提出明確的解決辦法是極其困難的,它們的核心問題都在於︰「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人應該做什麼?為什麼?」這樣的問題帶我們進一步思考,解決法律爭議是否需要道德理論?法律爭議可否被化約為道德問題,並以道德推理的方式加以解決嗎?
本書的原型是雨果.亞當.貝鐸教授於一九九五年春天在杜夫特大學開設的一系列講座。貝鐸教授在講座中選了三個著名的案例,包括真實發生的「美國訴霍姆斯案」,也有經典的虛構案例「洞穴奇案」和「吉姆的困境」,旨在讓讀者思考:當遭遇特殊情形,無論怎樣選擇都會導致有人喪生,我們該如何面對這樣的道德兩難?藉由理性的邏輯推演和真真切切的良心煎熬,貝多教授展示了「道德決疑法」這種已有千年歷史的倫理分析方法在當代依然具有影響力。目的除了探索道德理論在司法過程中的角色,也為法律人與一般大眾增加哲學內涵,讓我們更加認識自己信仰的原則。
作者簡介:
雨果.亞當.貝鐸Hugo Adam Bedau
美國哲學家,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Austin B.Fletcher榮譽哲學教授,致力於死刑的研究。一九六一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達特茅斯(Dartmouth College)、普林斯頓等知名學府。一生呼籲廢除死刑,作品涵蓋政治哲學與刑罰領域,包括︰The Death Penalty in America (1st edition, 1964; 4th edition, 1997), The Courts, the Constitution, and Capital Punishment (1977), Death is Different (1987), Killing as Punishment (2004);共同著作有《雖然他們是無辜的》In Spite of Innocence (1992)。
譯者簡介:
麥慧芬
東海大學外文系學士、奧勒崗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譯作包括《單騎伴我走天涯》、《查理與我》、《錫卡的鳳凰木》、《狗史》、《暗星薩筏旅》、《在遙遠那方的太陽鳥》、《明日世界的律師》等二十多本書。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水手赫姆斯與「威廉布朗號」沉船事件
大副對著船員吼道︰「兄弟們,你們必須動手,不然我們全都會完蛋。」
然後船員動手了……最後有十四名男性乘客加上兩名女性乘客」被拋出救生挺,迎向必然溺斃的命運。
一、案件事實
被法院判刑的那個人不是船長,也不是大副,只是一名小船員。
一八四一年四月十九日夜裡大約十點,天氣又冷又濕。距離加拿大紐芬蘭省雷斯角(Cape Race)東南方約兩百五十哩的北大西洋中,駛往目的地美國費城的槳帆船「威廉布朗號」(William Brown)撞上了冰山。船上六十五名蘇格蘭與愛爾蘭移民,以及包括三名船副在內的十七位船員,面臨到了迫在眼前的生死威脅。「威廉布朗號」上只有了兩艘救生艇,其中一艘是雜用艇,安全承載量是十人;另外一艘大艇可以容納約二十四個人。船長、二副、六名船員以及兩位乘客(一名婦女與一個小男孩)很快就讓小救生艇滿載。大副、八名船員以及三十二位乘客爬進了較大的救生艇,人數遠遠超過救生艇的安全承載範圍。其他留在船上的三十一名乘客毫無存活希望,與冰山相撞後一個半小時,「威廉布朗號」沉入海中,三十一人全數罹難。
破曉時分,精疲力盡、驚惶失措的倖存者們擠在兩艘滿載的救生艇上,隨著浪潮兩船逐漸拉開了距離。這時候船長命令大艇上的船員要聽命於大副,由大副接替船長的職務。大副向船長報告,根據他的判斷,大艇已經「難以操控」(unmanageable,後來法庭紀錄的用詞),船身受損,海水從不同的洞口滲入,舷緣也快要接近海面。如果要讓救生艇繼續浮在海面上,「必須減輕承載量,把一些人丟下海。」(同樣引述自法庭紀錄。)船長隔著海面回話(如後來在法庭上所說的證詞)︰「我知道你必須要做什麼……現在先別說這些。那是最後萬不得已的做法。」說完之後,兩條救生艇漂往各自的生路。
那一天氣候惡劣,雨下個不停,大艇上的乘客拚命把海水往外舀,船員也使盡力氣划槳。到了晚上十點,撞擊冰山後二十四小時,「風勢轉強,海面升高,大浪多次打上來,船上所有人從頭濕到腳……周遭漂浮著冰山碎片,而冰山依然可見……雨愈下愈大,已經努力舀水好一段時間的大副放棄了,他對大家說︰『撐不下去了。老天啊,幫幫我。兄弟們,動手吧。』就在此時有些乘客大喊,『救生艇要沉了……上帝可憐可憐我們吧。』但船員沒有回應大副的命令。幾分鐘後,大副對著船員吼道︰『兄弟們,你們必須動手,不然我們全都會完蛋。』然後船員動手了……最後有十四名男性乘客加上兩名女性乘客」被拋出救生挺,迎向必然溺斃的命運。
根據生還者在法庭上的證詞,眾人花了好幾個小時才選定要被丟下海的十四個人;最後兩個人是直到黎明才被送進大海墓地裡。隔天天候好轉,一大早一艘船看到並救起了救生艇上的所有倖存者。小艇上的人也被另一艘船救起,不過那已經是他們在茫茫大海中熬過六天六夜以後的事情了。
一八四二年,沉船事件過後一年,費城聯邦法院以「觸犯聯邦法律」為由,判處一名船員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以及一千美元以下的罰金;他是所有船員中唯一獲罪的人;系爭罪名是「於公海犯下非預謀殺人罪」。(原注1)這整起案件餘波盪漾,被法院判刑的那個人不是船長,也不是大副,只是一名小船員。他的名字叫威廉‧赫姆斯(William Holmes)。
赫姆斯二十六歲,芬蘭人,年紀輕輕就當了船員,而且(再次引用法庭紀錄)有一副「宛若藝術模特兒的堅毅容貌和體格」。他是最後一個離開「威廉布朗號」的船員,英勇地營救那些茫然逃竄的乘客。在救生艇上,除了身上穿的衣褲,他把一切全給了其他女性乘客。也是他看到了救他們脫難的船隻,幸虧「他努力讓救生艇被發現,最終才救了大家」。在審判過程中,船長證稱赫姆斯「始終遵從上級指示。我從來沒帶過這麼優秀的船員。他是一流的人才。」看起來赫姆斯確實是這樣的人。
二、誰要被丟下海?
在當時的情境下,他們判斷認為服從大副的命令,是可以拯救最多人命的最佳做法。
事實描述至此。接下來我們要看看船員在決定誰應該被丟下海時,所採取的選擇原則;所有提到的原則將於章末再次條列。根據法庭證詞,大副命令船員「不要拆散夫妻,不要把女人丟下海」。(那兩名落水的姊妹不知是為了拯救兄弟,抑或因為兄弟將受死而絕望地跳海。)顯然大副忘了早先他自己提給船長的建議︰以抽籤決定誰要被丟下海。除了前述大副指示的夫妻與女性的條件,法庭紀錄顯示,「沒有其他的選擇原則。沒有證據可證明船員之間有聯合的行為(也就是說船員沒有共謀要淹死特定乘客)。沒有抽籤,乘客也沒有……被告知或一起商量要怎麼做。」遵照大副的指令,結果是除了兩個和妻子同在救生艇上的男子與一名小男孩外,其他的男性乘客全都被丟入海裡。
看來大副的命令與船員的行動所依循的選擇原則,可以稱之為「救家庭,救婦孺」(Save Families, Save Women, and Children)。然而,實際狀況並非如此。根據法庭紀錄,我們看到「沒有任何船員被丟下海」。這一點惹惱了法庭記錄員,於是加上一句不善之言︰「船員之一是廚子,還是個黑人。」沒有船員被拋下海絕非偶然,必然是刻意為之。若是如此,那麼船員似乎重新詮釋了大副最初指示的選擇原則;事實上他們顯然修改了原則。他們的行動準則看來是「救家庭與船員」(Save Families Plus Crew)(這裡的家庭可解釋為包括落單的女性、孩童,以及夫妻)。值得注意的是,沒有證據顯示大副反對這樣的解釋或修正,因此我們可以說,「救家庭與船員」(以下我稱之為「實際行動原則」)實則表達了大副沒有說出來的意圖。
赫姆斯與其他船員為什麼願意遵照「救家庭與船員」的原則行事?我們似乎可以合理推論,在當時那樣的情境下,他們判斷認為服從大副的命令,是可以拯救最多人命的最佳做法。重點就在於達到拯救最多人命這個目的。固然有其他可能的目的,然而這個我稱之為「拯救最多人命」(Save the Most Possible)的目的,對我而言最能夠理解大副的命令與實際行動原則作為達到目的的工具。(原注2)
這裡還有另一個原則起作用。若要理解赫姆斯與其他船員的行動,我們必須假定他們是遵照「服從命令是水手的職責」(Sailor’s Duty to Obey Orders)這個原則行事。根據事後回想,大副告訴船員︰「你們必須動手,不然我們全都會完蛋。」若沒有大副這樣的指示,就很難理解赫姆斯的行為。在審判中(若我們可以相信法庭紀錄),沒有人認為赫姆斯是自己決定「何時」要把乘客丟下海,或「要不要」把乘客丟下海,甚或要把「誰」丟下海。我們可以合理假設,如果大副命令赫姆斯遵照其他選擇原則行事,赫姆斯也會像依據實際行動原則一樣聽命行事。
「服從命令是水手的職責」相應於「上級命令抗辯」(Defense of Superior Orders),是用來為系爭行為辯護。從一九四○年代的紐倫堡審判(the Nuremberg Trials)與一九六○年代的美萊村屠殺的軍事審判(My Lai court martials)中,我們清楚看到未經審慎檢視與設限,不能援用這樣的辯護理由;赫姆斯的審判庭同樣明白這個道理。然而,水手赫姆斯既非行政官朱利亞斯‧斯特萊歇爾(Gauleiter Julius Streicher),也不是威廉‧凱利中尉(Lieutenant William Calley)。(原注3)這兩位軍官違反人權的罪行,不能僅憑執行上級命令這個理由就加以合理化。即使他們一開始並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有罪,但後來他們也應該明白,因為他們身處的環境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自己的命令,他們也具備足夠的智識與資訊去理解自己的行為會造成什麼後果。但我們是否可以將這些條件套在赫姆斯身上?我們是否可以假定說,在事發那個當下,他應該知道大副下達的命令不僅非法且不道德?我不認為可以。若要這麼假定,表示赫姆斯有時間思考並衡量大副下達的命令,也就是說一個小水手在危急關頭應該有能力分辨上級命令的正當與不正當,而且他應該能夠決定是否要遵守一個合法性有問題的命令。這些假設都無法讓人接受。因此,即便我們傾向認為大副的命令不合法也不道德,卻不足以指控赫姆斯遵從命令並依照自己的理解詮釋命令的行為有錯。
三、為了達成目的,必須採取什麼手段?
造成他人死亡的行為,可以以避免更多人死亡這個理由加以正當化?
現在我們來檢視實際行動原則的合法性問題。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部分:一、為什麼選擇這個原則而不選其他的原則?二、無論選擇任何原則,理由何在?我們先討論第二個問題。
這個案例很大程度取決於是否真的有必要把任何人丟進海裡。此問題顯然是重點,因為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赫姆斯的作為就有了強有力的理由。然而,單單這樣的理由並無法讓他完全免除罪責,因為有可能他們採取了錯誤的選擇原則來決定誰應該被犧牲;這一點我稍後會再論及。無論如何,赫姆斯的作為是否必要這個問題,不像蘋果落地這類問題一樣有直接的答案。沒有任何自然法則或人為規範(如同案例中出現的),可以支配救生艇上眾人的生死。主張救生艇上某些人必須要受死,只是一種偶然的必要性(contingent necessity),也就是說剛好只能拯救部分人命,以及剛好被丟出艇外的人沒有其他活命的可能性。所以這裡應該要回答的問題是:有必要把一些人拋出艇外任其溺斃,以增加救生艇上其他人的生存機會嗎?
答案取決於兩種截然不同的考量。一是事實的考量,也就是當時的海象、天候,特別是救生艇的狀況,以及大副、船員和乘客對於這些事情的看法。另一個考量是為了存活這個目的所採取的做法的可接受度。簡要而言,這個正當原則主張,若無法讓所有人活下來,以及若少數人的死亡是大多數人存活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那麼這樣的死就是有正當理由的。讓我們將此原則稱為「為達目的之唯一必要手段」(Sole Means Necessary to the End)。(原注4)前述「救家庭與船員」這個實際行動原則,只是為了實踐「為達目的之唯一必要手段」這個更基本的原則。讓我們更仔細地檢驗事實與這個新原則。
首先,我們來看看事實。法庭紀錄中有關海象、天候與救生艇的證詞並不明確;天候的實際狀況不明,大副、船員與乘客也說不清楚究竟天氣有多糟。但想想如果你是當時救生艇上那個如落湯雞般全身濕透又快要凍僵的大副。你要掌控全局,所有人的生命都懸在你的思考判斷間。你不知道海象會不會說變就變,而且變得更惡劣,你也不知道救生艇的漏水問題會不會愈來愈嚴重,以及若風力再增強,會有多少水再從艇首及舷側灌進來,你更不知道這艘救生艇還可以撐多久。不論依照哪種選擇原則行事,誤差範圍其實不大。若無論如何都會有所差錯,那麼寧可失之謹慎,選擇安全的做法――大副大可這樣想。儘管天候在幾個小時內轉好是事實,但若不是減輕了載重,漏水又超載的救生艇能否從晚上十點撐到黎明,永遠沒有人知道。別忘了救生艇上每個人都岌岌可危,我想很多人應該都會同意我的看法︰若要有機會活過那個夜晚,的確有必要把一些乘客拋下海,至少有經驗的水手會認為有此必要。
然而,如果我們達成這樣的判斷共識,明顯和赫姆斯的審判庭意見相左。檢察官喬治‧達拉斯(George M. Dallas)主張赫姆斯的殺人行為非屬必要,而承審法官亨利‧鮑德溫(Henry Baldwin)也同意這樣的看法,讓案子進入陪審團裁判。鮑德溫法官認為以必要性作為抗辯理由,必須是「危險已經迫在眉睫、勢不可擋、除了犧牲自己或他人生命外別無他法」。這番清楚的言論默示陪審團應當推斷事實不足以成立必要性的抗辯。陪審團最終加以採信,判定赫姆斯過失殺人罪成立。
然而,在同意檢察官、法官與陪審團之前,我們需要思考兩種反對意見。鮑德溫法官所定義的必要性,似乎顯示赫姆斯若確實依據必要性而採取行動,就不會是根據「救家庭與船員」的原則。法官的意思是,若要如此,赫姆斯的行動必然是依據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先抓到誰,就丟誰下海」(First Reached, First Overboard)的原則。在面臨「危險已經迫在眉睫、勢不可擋」,以及「別無他法」的情況下,這會個比較好的原則。在這個選擇原則之下,身處一片漆黑的暗夜狂潮中,面臨超載救生艇即將沉沒的威脅,赫姆斯或任何其他船員都可能把他們抓到的人就丟下海,根本不會多想性別、婚姻狀況這類細節,也不會停下來確認誰是船員、誰是乘客。赫姆斯未依循「先抓到誰,就丟誰下海」的這個事實,正好證明了出於必要性而行使防衛行為這個理由並不成立。或者應該說,這樣的論點暗示必要性並不存在。法庭證詞也強化了這個論點,因為從第一個人被犧牲到最後一個人被丟下海,歷經了六個小時或更長的時間。
這種論據的結果之一,是鮑德溫法官將必要性抗辯視為過失殺人的免責理由,而非正當性的理由。(原注5)也就是一個人承認自己造成他人傷害確實不對,但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確實別無他法,因此不能真的怪罪他。從而,若一個人實在別無他法只能傷害別人來拯救自己的性命,當下的環境也完全不容他多做思考,那麼就應該免除其法律的罪責。反過來說,所謂正當性的理由,則是當事人要證明自己是經過刻意且相當的考量後才做出那樣的行為,且在當時的情境下,那是正確(或最有利)的做法。事實上,鮑德溫法官建議陪審團,儘管赫姆斯的所作所為不具正當性,但若出於必要就可以免責。不過赫姆斯無法免責,因為他的行為並不符合必要性的法律要件。
我認為這樣的論據缺乏說服力,我也無法同意陪審團認為救生艇上的人不覺得減輕船身負載量具有立即的必要性。至於支持這樣的行為實屬犯罪的論點,也無法令人滿意。我以為大副必定相信超載的大艇每分每秒都面臨沉沒的危險,否則他為什麼要下令船員把人丟下海?若我們可以合理推斷赫姆斯信任大副,且假設大副真心相信救生艇就快要沉沒了,那麼救生艇沉沒是否真的迫在眉睫根本不重要。赫姆斯、大副以及其他所有船員實際上都根據「為達目的之唯一必要手段」這個原則行動,而若他們思考過這個原則,那麼造成他人死亡的行為就可以以避免更多人死亡這個理由加以正當化。
四、怎麼做可以救最多人?
減輕救生艇負重的必要性,難道就得和讓人溺斃的必要性劃上等號嗎?
現在暫且放下正當性原則的問題,讓我們把焦點擺在「救家庭與船員」這個實際行動原則,並思考其他的選擇。首先,設想一個可能完全不需要任何選擇原則的方案。在這個方案裡,減輕救生艇的負載量不等於要把人丟到海裡淹死。為什麼不採取權宜之計,讓大家輪流在海裡待一段時間?在船員的管理下,訂定一套交替規則,每次十幾個人爬出船外,攀著船緣在海上支撐半個小時後,再爬上船換另一批人浸在冰冷的海水中。這樣會不會所有人都可以活下來?或者至少這樣活下來的人會比後來實際存活的人多?減輕救生艇負重的必要性,難道就得和讓人溺斃的必要性劃上等號嗎?
然而,以訂定輪替規則來削弱丟人下海的必要性,聽起來未免不太可信;況且這個方法極其不切實際,就像其他幾種選擇原則。
為了說明,讓我們想想這類不可行的替代性選擇中的兩個。其一可稱之為「救狀況最佳的人」(Save the Best),這個菁英主義式的原則要我們根據身體條件,先保護乘客與船員中最健康的人。另一個原則常見於遣散與解雇的狀況,亦即根據年資,或說「後進先出」(Last In, First Out)原則。若船員們當時依照這兩個原則行事,後果將完全無法想像,原因毋須贅言。我們就忘了這些以及其他想像起來非常有吸引力但毫無實用價值的原則吧。在判斷相關與適當的原則時,我們必須牢記當時的天候與救生艇的狀況、乘客的驚惶失措、船員們猶豫是否要聽命行事,以及顯然得盡快減輕船身負載量的必要性,即使那表示必須把一些人丟出船外,且他們必然因此喪命。無論最後提出什麼樣的論點反駁實際行動原則,無可否認的它確實能達到「拯救最多人命」的目的。
順道一提,請注意,不論決定依據哪種選擇原則行事,實際執行時必然都會有灰色地帶。假設無論採用什麼樣的選擇原則,都必須有人離開船且必然會喪命,那麼問題依然在於︰多少人應該被迫接受死亡?為什麼要多達十幾個人,精確的數字是十六個人(或者若你寧願相信那對姊妹是自願跳海的,那麼就是十四個人)。為什麼不是十個人?八個人?六個人?這個問題沒有解答。也沒有任何線索可以看出,把「所有未婚男性乘客丟入海中」這個決定的原因;這顯然是赫姆斯接受了大副的命令後所做出的決定,或者至少得到了大副的默許。或許我們可以猜測赫姆斯與大副是這麼想的:第一,為了確保犧牲可以換來安全,所以多犧牲一、兩個比少犧牲一、兩個要好;第二,對所有未婚男性都公平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加選擇而犧牲他們所有人。或許這樣的理由不太有說服力,但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顯然大副或船員當時也是這麼想。
五、未經被犧牲者的同意,可以犧牲他嗎?
非經我自願且明確的同意,任何人皆無權將我作為工具以滿足其他人的目的。
再回頭談談「救家庭與船員」,我們必須留意這個原則(以及其他赫姆斯可能依循的替代性原則)備受責難的一點,就是在那樣的狀況下它並不公平:那些因為這個原則而生或死的人,從未同意以這個原則決定自己的生死。所有乘客在登船時並未簽署同意書,允諾在沉船時且需要犧牲部分人命的必要時刻,願意根據「救家庭與船員」原則被犧牲。救生艇上的乘客亦未投票表決是否都贊成依這個原則行事。因此一定會有人質疑,船長與大副憑什麼權利下令船員執行這個沒有人能確定所有乘客都接受的原則。當然,有些人會說乘客更有權利決定這件事。
我們為什麼會認為在執行一個原則之前,必須事先明確地經由所有人的同意?因為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方式可以同時尊重每位當事人相同權利。非經我自願且明確的同意,任何人皆無權將我作為工具以滿足其他人的目的,康德(Kant)之後的許多哲學家會這樣說,因此我把這樣的論點稱為「康德條件」(Kantian Condition)。(原注6)我們若接受「康德條件」,就必須反對救生艇上所採行的實際行動原則。甚且,若「康德條件」是正當執行原則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所有人都要明確且一致同意這個原則,那麼救生艇上的任何選擇方式應該都無法通過。所以看來「為達目的之唯一必要手段」這個原則也不可行,因為它以少數人之死是大多數人存活之必要作為正當化的理由,不論是否得到被犧牲者的同意。這樣的原則顯然無視「康德條件」。
所以我們看到大副與船員均忽視了「康德條件」。他們採行的選擇原則未經任何人(遑論所有人)的同意。許多人認為他們這樣做,不論立意為何,都侵犯了他人的權利。我們也可以說,給赫姆斯安上過失殺人罪的法庭,同樣漠視了「康德條件」;從法庭隱約支持抽籤是一種適當的選擇原則這一點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說過,如果一個人接受「康德條件」作為任何選擇原則的要件,那麼對救生艇上的人來說,任何選擇原則都不可能成立。這是個很殘酷的結論。或許我們可以轉而主張,實際行動原則無論如何都應該被接受,原因有二。第一,如我們所見,評估過其他適用原則後,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這個原則確實優於其他任何原則。第二,倘若所有的選擇原則都因違背「康德條件」而不被接受,那麼大家只能被迫選擇「共患難」(Shared Disaster)原則;也就是說,儘管以部分人的生命為代價或許可以讓大多數人活下來(或至少可能增加存活的機會),但既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活下來,倒不如大家一起死。
第一章 水手赫姆斯與「威廉布朗號」沉船事件
大副對著船員吼道︰「兄弟們,你們必須動手,不然我們全都會完蛋。」
然後船員動手了……最後有十四名男性乘客加上兩名女性乘客」被拋出救生挺,迎向必然溺斃的命運。
一、案件事實
被法院判刑的那個人不是船長,也不是大副,只是一名小船員。
一八四一年四月十九日夜裡大約十點,天氣又冷又濕。距離加拿大紐芬蘭省雷斯角(Cape Race)東南方約兩百五十哩的北大西洋中,駛往目的地美國費城的槳帆船「威廉布朗號」(William Brown)撞上了冰山。船上六十五名蘇格蘭與愛爾蘭移民,以及包括...
推薦序
公民的頭腦體操與權力者的兩難詐術
by輔仁大學法律系教授吳豪人
在日本與台灣,前後超過二十年的大學教員人生當中,我最常提醒學生們的一句話,就是:「強迫你只能二者擇一的人,如果不是資訊封閉的笨蛋,就是最壞的法西斯。」
這句話,通常都是為了戒除法律學徒天真的邏輯三段論惡習,多少讓他們品嘗一下辯證法數千年芬芳的開場白。
「呃,比方說吧,你劈腿了。同時愛上了A和B,而這兩位都堅持你只能選一個──魔鬼就藏在這裡。你因此陷入兩難,陷入道德與感情的天人交戰。就在痛苦迷惘之際,突然C經過你的身邊,而且回眸對你一笑。這個時候,第三條路便豁然出現!兩難因而被止揚,二者擇一困境就破了。」
至於日後又出現了D、E、F、G怎麼辦?依序比照辦理得了。唯一要提防的,只有小心,別被這些大寫字母們潑硫酸。此外,如果被劈腿的是你,原理相同。
除此之外,也為了告訴學生:一般而言,道德抉擇兩難情境的產生(自己造成的)或被賦予(他人造成的),很多時候都是假議題。最常見的,有兩種原因造成所謂「困境」。其一,資訊不足,便妄下結論以為兩難;其二則是故意造成資訊不足,而使人妄下結論以為兩難。換句話說,前者過度化約事態的複雜性,所以是笨蛋;後者則「故意」過度化約事態的複雜性,所以是法西斯的動員操作與洗腦。這兩種原因不需要互相獨立,反倒可以互為因果,甚至同時存在。
波蘭裔美國哲學家雨果‧亞當‧貝鐸的這本《道德抉擇的艱難》,雖然並不討論辯證法,但是他的基本立場,其實跟我杜撰的警句無甚差別,只不過在案例的挑選上,更為極端而已。他選的三個案例,都是「關乎自己和/或他人生死的重大抉擇」。用心很明顯,希望思考者鄭重其事,神入其中。但本質上,我認為貝鐸的目的也只有兩個。
首先,這本書是用來培訓現代公民獨立思考(也就是康德說的自我「啟蒙」)的「頭腦體操」。書中三個案例,在你我現實人生中遭遇的機會,大概跟中大樂透的機率一樣低。不過,想像中樂透之後如何使用彩金的種種可能性,也算庶民人生至樂。
其次就很嚴肅了。貝鐸警告我們:兩難情境很有可能是權力者(或其所豢養的傻鳥)佈下的騙局──例如簡化事實,只揭露對權力者有利的梗概或細節;或者故意讓邏輯跳躍,將自我犧牲竄改為強迫犧牲,把道德從修己偷渡成治人。這樣的例子,在人類歷史上汗馬牛充棟宇,原本無須我嘵舌舉例。不過,考量作者是個堅定的死刑廢止論者,讀者也許可以從死刑存廢的正反意見當中,嘗試去尋找看看有多少「傻鳥/反動修辭」。保證豐收。除了死刑之外,最近在台灣更具娛樂性的「傻鳥/反動修辭」之母,其實是轉型正義。
總之,當我們真實面臨這類故意犯所設的二者擇一陷阱時,日常的「頭腦體操」鍛鍊就顯出重要性──既可以讓我們看穿政客修辭中的謊言、冤獄案件的成因、媒體誤導輿論的手法等等,同時,也不會輕易被意識形態、同儕輿論綁架或洗腦動員。
值得注意的是,缺乏頭腦體操鍛鍊的人固然容易上當,但是真正的重點還不僅止防止上當,而是要牢記以下的事實:最經常而且最擅長簡化事態、蒙蔽他人判斷的,往往是政府、法律,以及媒體。這些權力者,習慣性的把自私的動機或輕率的決定,粉飾成某種緊急狀態下的不得不然,實際上卻是騙局詐術。貝鐸透過這三個案例,固然導出許許多多「選擇原則」,但他如果是「不能說服你,就搞暈你」的美國敗德律師,就變成權力者的同路人了。要知道,這許多「選擇原則」,只對尚有道德判斷力、或至少尚有道德需求之人才有意義。能夠導出越多合理的「選擇原則」,正好證明了道德判斷的基礎來源非常多樣,也就是提醒我們:進行決斷,不可耽溺於單一的道德想像。獨裁者,或說有獨裁傾向者,最容易耽溺於單一的道德想像。所以公民們如果也習慣於耽溺於單一的道德想像,就是鼓勵獨裁者的出現。
因此,最後我想特別談談本書的第三個案例「吉姆案」。第一案是真實案例,第二案是戰後復興自然法的富勒原創的虛擬教材,都具有相當普世的思辨價值。但是「吉姆案」呢,雖然同為虛擬,卻是一個非常惡劣、淺薄、非常好萊塢、而且非常具有新自由主義思維的虛擬。這個第三案原本不值一駁,但不曉得貝鐸教授是否因為目睹(或者預見)全世界人類的智力正在急速退化,才闢專章討論?無論如何,「效益主義者」居然虛擬得出這種案例,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嚴重道德危機的警訊了。本案中「陷入兩難的吉姆兄」,其存在與否根本不重要。因為「隊長」本來就準備/而且完全有能力要屠殺原住民了。誤闖行刑現場的吉姆,無論他做出什麼選擇,都只能是隊長的餘興節目。而且,除非吉姆當場格殺隊長或自殺,否則只要他決定開槍,無論結果是射殺、射傷、沒子彈,他就不只是餘興,而且立刻成為共犯。因為他居然認真去思考隊長的提案。這也是為什麼貝鐸特別提到:「不做受害者,也不當行刑者。」因為,輕信行刑有必要/不得已的人,最容易成為受害者、製造受害者。
過去,黨國就是這樣裹脅台灣人民的。如今,另一個孿生黨國,也正在如此裹脅中國人民。我們真正要努力的是,禁止任何人有權力玩弄他人、玩弄他人的道德抉擇。而不是俯首承認「事實上就是有些人有玩弄他人/玩弄他人道德抉擇的權力」,然後再去低聲下氣的討論:被玩弄者,還剩下哪些可悲的選擇。我要再次強調:任何持後者論調的人,若非法西斯,就是法西斯的奴才。唔,為了避免自我矛盾,一樣落入二者擇一的陷阱,我得辯證性地再加上另一種可能,「法西斯奴才的預備軍」。預備軍可以經由自我啟蒙而陣前逃亡,於是就脫離奴才的兩難陷阱。當今之世,「海峽兩岸」奴才輩出。任何不願意在精神上、智力上、美學上乃至於現實上被貶低為奴才者,都應該讀讀貝鐸教授這本書,學習一點高級防身術。
陶冶實踐推理能力,實現美好人生
by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謝世民
當我們面臨一組互不相容的行為選項時,我們為了做出決定而進行的推理,一般稱之為「實踐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實踐推理有兩個步驟最為重要:第一是去辨識相干的考慮,第二是去權衡和定位這些相干考慮之間的輕重緩急、優先次序、阻卻關係、綜合效力等等。良好的實踐推理,就概念層面而言,展現在行為主體正確辨識相干的考慮,並於恰當權衡和定位這些相干考慮之間的各種關係後,形成決定去做自己所看到的那個最佳選項。良好的實踐推理,就其為一種能力而言,不是天生的,而是習得的;我們需要陶冶、訓練才能具備良好的實踐推理能力。
就實踐推理能力而言,人是否可能經由陶冶、訓練(或其他方法?)而達到一種出神入化的境界,任何時候都不必經歷所謂的「推理」,不需要在意識層面上辨識、權衡、定位相干的考慮,就知道什麼是最佳的行為選項呢?我自己傾向於不相信這是人可以達到的境界。無論如何,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人,當他們出現時,恐怕也是平凡如我輩者無法認得的,因此,也不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對象。要成為我們學習的對象,他們必須說明為什麼他們看到的最佳選項確實是最佳選項:至少要明白點出他們看到的相干考慮是什麼,以及論證他們權衡、定位這些相干考慮之間關係的合理性何在等等。就這個標準而言,傳統和當代的許多道德哲學家的論述,才深具教育功能。
實踐推理並不是一個已經熄火的哲學主題,近年來重要的著作仍然不斷出現,不同傳統流派(效益主義、亞里斯多德主義、康德主義、休謨主義、契約論、第二人身理由論、理由基本主義等等),因為彼此的辯證詰難,各自的最佳版本也因而逐漸成形。不過,我們可以暫時不去深究這些複雜理論之差異何在,僅從選擇情境之分析來切入實踐推理。
選擇情境,可以依照艱難度來分,也可以依照重要性來分。在重要性無比巨大的選擇情境中,我們的選擇可以很簡單,因為目標明確、每個選項與目標實現之關係也很清晰,我們選錯的機率很低,但是,在這種情境中,我們的選擇也可以很艱難。這時,我們說的就不是中性的「選擇」,而是「抉擇」。
就結構而言,重大無比而又艱難的抉擇情境,可以初步分為三種:
第一,選項對抉擇者是否能活出一場美好人生,至為關鍵(選對了,人生成功;選錯了,人生失敗),但是因為資訊不充分(甚至不可能充分),抉擇者不確定何者正確。例如,一個人可能正在艱難地考慮是否要放棄根基穩固的本業,離開自己的國家,移民他邦,重啓爐灶或改行(從醫生變成貨運司機)。
第二,選項對抉擇者實現自己的美好人生(或讓親朋好友有場美好人生),至為關鍵,但卻不利於他人活出一場美好人生。採取這些選項必然涉及了嚴重傷害他人的行為(不是那種在公平競爭脈絡下所謂的「勝者傷害了敗者」而已),也許還必須有意地去製造這樣的傷害,或者,會讓抉擇者難有餘力去協助其他急難待援者,而降低了他人存活的機會。
第三,選項與抉擇者自己(或其親朋好友)的美好人生並無關係,但是,卻對他人的生死存亡(他人是否有機會活出一場美好人生),影響重大。例如,我們熟悉的電車問題,就是要我們去處理應該救誰的艱難抉擇。
貝鐸在本書中所討論的三個案例(沉船事件、洞穴奇案、吉姆與開墾森林的印地安人),涉及的抉擇問題主要是第二種和第三種,而不是第一種。第一種抉擇問題之探討,最受大眾歡迎,因為大眾關注如何活出一場美好人生,而且這樣的關注似乎也很普遍和自然正當。不過,我們也不應該忽視,其實第二種抉擇問題和第三種抉擇問題與抉擇者的美好人生也密切相關。因為第二種和第三種抉擇問題都要我們去面對自己對他人之義務,而美好人生之實現,並無法完全獨立於個人是否負責地去辨識自己對他人之義務是什麼、是否真誠地去恪盡這些義務。當代著名哲學家德沃金對此點曾提出相當具說服力的論證,他並且還主張,個人對於他人負有什麼義務,也不能獨立於恪盡這些義務對個人實現美好人生之影響的程度(例如,義務不得令行為主體必須放棄美好人生之追求)。簡言之,美好人生與義務,就內容而言,彼此相互依賴。如果德沃金是對的,關注美好人生的讀者有非常強的理由去讓自己熟悉第二種和第三種抉擇問題,以陶冶、訓練自己的實踐推理能力。
貝鐸的這本《道德抉擇的艱難》為我們闡明了他在三個著名案例裡自己的實踐推理,就陶冶、訓練我們的實踐推理能力而言,它是一本極佳的入門書。在細心閱讀本書時,讀者要不斷問自己:「我理解貝鐸的推理嗎?我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貝鐸的推理?為什麼?」這樣的閱讀才能有最大的收穫。
對道德思維的培養提供有用的材料
by台大法律學院教授顏厥安
此書是雨果•亞當•貝鐸(Hugo Adam Bedau)所撰寫,以決疑論(casuistry)來分析討論道德選擇難題的著作。決疑論是一種主要運用在道德與法律領域,以探索個案為主的推論思考方式。決疑論在歐洲有非常長久的發展歷史,一般認為是修辭學的一種方法,而與「原則主義」相對立。亞里斯多德與西塞羅都認為在實踐問題的領域,無法單純以原則為前提,透過演繹的邏輯推論就可得出正確答案,而必須在個案當中,透過典範、類比等思考方法,來協助我們做出判斷。決疑論曾經因為遭到一些重要思想家,例如帕思卡(Blaise Pascal)的批判,而趨向於衰微。二十世紀末期,因為一些學者的重新研究倡議以及應用倫理學的發展(例如醫學倫理學),決疑論重新獲得了重視與發展。本書可以說是在這個決疑論復興背景下的一本著作。
貝鐸在此書當中討論了三個案子:第一個是水手赫姆斯與「威廉布朗號」沉船事件。這是一個真實故事,「威廉布朗號」眼看即將撞上冰山沉船,船員與乘客分乘兩艘救生艇逃生。在一艘不夠大的救生艇上,船員不得不強制將一些乘客拋入海中,以保住其他人性命。赫姆斯是其中一位執行拋乘客入海命令的船員,事後受到審判,作者以決疑法來探討分析此案。
第二案「洞穴奇案與羅傑‧惠特摩之死」是個假想的案件,是著名的法理學家富勒(Lon L. Fuller)提出作為思考的案例,後來廣被引用。包括惠特摩在內的五人去登山,遇到意外被阻絕在一個洞穴內。因為攜帶的糧食有限,在救援成功之前,面臨了是否要殺死其中一人,食用其肉,以讓其他四人存活的抉擇。惠特摩就是擲骰子不幸被選中而遭殺害的人。
第三案「吉姆與開墾森林的印地安人」也是個假想案例。假想南美某國的軍隊逮捕了二十名參與抗議政府的原住民,準備將他們槍決,而一位在當地研究植物學的美國人吉姆正好也在場。軍隊隊長表示,若吉姆願意開槍射殺其中任何一名原住民,他就同意釋放其他十九人,否則他將處決所有二十位原住民。吉姆是否可以為了救十九人,而射殺其中一位無辜者呢?
作者貝鐸同樣使用決疑法的方法,來分析討論這兩個假想的道德困境個案。
決疑論在法律方法論發展史當中也有重要意義。羅馬法在體系化發展之前,主要是判例法與法官法,決疑論是這個階段的主要方法。十一世紀的羅馬法復興裡,歐洲法學家固然發展了更重視找出原則的決疑論,但是一般認為要到更為晚近的十九世紀,歐陸法才出現徹底體系化的方法。
本書處理的是道德困境難題,作者也是以道德論證的角度來運用決疑法。但是所有這些真實或虛構案件,都涉及到司法如何認定當事人的法律責任。就這個角度而言,道德論證與法律思維有高度的重疊性。也難怪法理學家阿列西(Robert Alexy)認為法律論證是一般性實踐論證的特殊個案。
本書對三個個案的討論都非常深入,作者也引用不少法學家的見解來協助思考,讀者可以自行閱讀瞭解。在此筆者只想指出三點:第一,在使用決疑法過程裡,會發現許多反覆出現,在許多個案中都需要加以斟酌衡量的一般性原則。但是,第二,在每一個個案中也都有一些不會重複出現的情境因素,正是這些因素使得每個個案成為充滿挑戰的難題。第三,雖然彼此有高度重疊性,但是法律判斷與道德判斷終究還是不同。法律判斷往往要處理是否有管轄權、程序是否正當、證據是否超越合理懷疑等層面,這些問題也可以使用決疑法思考分析,但畢竟與道德問題不同。
在漢語世界裡,對道德教條的訓示教誨,遠多於對道德難題的思考論證。盼望本書的出版,能對道德思維的培養,提供一份非常有用的材料。
公民的頭腦體操與權力者的兩難詐術
by輔仁大學法律系教授吳豪人
在日本與台灣,前後超過二十年的大學教員人生當中,我最常提醒學生們的一句話,就是:「強迫你只能二者擇一的人,如果不是資訊封閉的笨蛋,就是最壞的法西斯。」
這句話,通常都是為了戒除法律學徒天真的邏輯三段論惡習,多少讓他們品嘗一下辯證法數千年芬芳的開場白。
「呃,比方說吧,你劈腿了。同時愛上了A和B,而這兩位都堅持你只能選一個──魔鬼就藏在這裡。你因此陷入兩難,陷入道德與感情的天人交戰。就在痛苦迷惘之際,突然C經過你的身邊,而且回眸對你一笑。這...
目錄
作者序
第一章 水手赫姆斯與「威廉布朗號」沉船事件
道德準則或道德原則所扮演的角色,是限制我們的選擇以保護我們的價值,其中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對他人、他人的生命、他人的自主權,以及他人的福祉,給予同等的尊重。而在當時身處的境況下,赫姆斯能做的事情,就是他後來所做的事情。
第二章 洞穴奇案與羅傑‧惠特摩之死
天底下沒有任何規定要大家必須不計代價地讓部分人存活。所以在這起第五個人同意被殺,其他四人為了存活而同意殺害他並分而食之的案件中,我只能說,若易地而處,我會選擇不做受害者,也不當行刑者;或者應該說,理解人類的脆弱後,我希望我會這麼選擇。
第三章 吉姆與開墾森林的印地安人
舉一個和吉姆處境相似的例子:如果人類全體以及所有生物都遭到一個瘋子禁錮,而且這個瘋子威脅著除非如何如何(他確實有能力讓威脅成真),不然他就要毀滅所有人類。這時候,如果你殺害一名隨機選擇的無辜陌生人,就可以增加全體人類逃離這個威脅的可能性,你願意殺害無辜的陌生人嗎?
附錄 決疑論的歷史背景
原文附注
作者序
第一章 水手赫姆斯與「威廉布朗號」沉船事件
道德準則或道德原則所扮演的角色,是限制我們的選擇以保護我們的價值,其中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對他人、他人的生命、他人的自主權,以及他人的福祉,給予同等的尊重。而在當時身處的境況下,赫姆斯能做的事情,就是他後來所做的事情。
第二章 洞穴奇案與羅傑‧惠特摩之死
天底下沒有任何規定要大家必須不計代價地讓部分人存活。所以在這起第五個人同意被殺,其他四人為了存活而同意殺害他並分而食之的案件中,我只能說,若易地而處,我會選擇不做受害者,也不當行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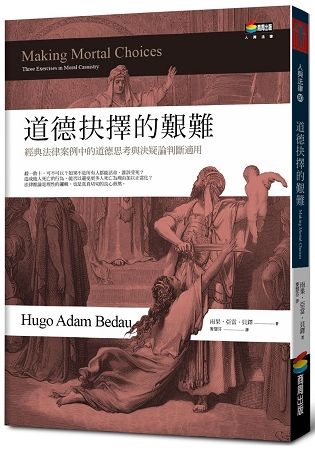

 共 1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