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簡 介 為敘說定位
個人敘說視為研究的資料
敘說研究
本書的組織
第一章 理論的脈絡
經驗的再呈現
關注經驗
訴說經驗
轉錄經驗
分析經驗
閱讀經驗
再呈現的限制
第二章 實作模式
生命的故事
敘說方法
問 題
從對談資料中聯結故事和意義
敘說方法
問 題
詩的結構和意義
敘說方法
問 題
第三章 進行敘說分析
訴 說
轉 錄
分 析
第四章 結 論
有效性
說服力
符合度
連貫性
實用性
無教條
敘說分析的使用和限制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的圖書 |
 |
$ 140 ~ 228 | 敘說分析
作者: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 譯者:王勇智、鄧明宇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9-22 語言:繁體書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敘說分析
Riessman的這本「敘說分析」的中譯本,可以說是在學習「敘說」的光譜上,有著關鍵性的開拓。Riessman這本「敘說分析」在理論脈絡下,討論了三種不同的敘說操作模式(models),讓讀者在讀敘說資料時,不僅只欣賞故事,還能進入分析性思考,接著 Riessman提供了如何分析的具體方法,最後討論評估標準及這種分析的限制。這樣的組織實在有助於有意學習敘說者很快地進入敘說分析的世界。
譯者簡介:
王勇智
現職:中國海事商業專科學校講師
學歷:輔仁大學心理研究所碩士
鄧明宇
現職: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講師
學歷:輔仁大學心理研究所碩士
--校訂者簡介--
丁興祥
現職:輔仁大學心理系教授
學歷: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社會與人格心理學博士
目錄
序
簡 介 為敘說定位
個人敘說視為研究的資料
敘說研究
本書的組織
第一章 理論的脈絡
經驗的再呈現
關注經驗
訴說經驗
轉錄經驗
分析經驗
閱讀經驗
再呈現的限制
第二章 實作模式
生命的故事
敘說方法
問 題
從對談資料中聯結故事和意義
敘說方法
問 題
詩的結構和意義
敘說方法
問 題
第三章 進行敘說分析
訴 說
轉 錄
分 析
第四章 結 論
有效性
說服力
...
簡 介 為敘說定位
個人敘說視為研究的資料
敘說研究
本書的組織
第一章 理論的脈絡
經驗的再呈現
關注經驗
訴說經驗
轉錄經驗
分析經驗
閱讀經驗
再呈現的限制
第二章 實作模式
生命的故事
敘說方法
問 題
從對談資料中聯結故事和意義
敘說方法
問 題
詩的結構和意義
敘說方法
問 題
第三章 進行敘說分析
訴 說
轉 錄
分 析
第四章 結 論
有效性
說服力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譯者: 王勇智、鄧明宇
- 出版社: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9-22 ISBN/ISSN:957113221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16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世界文學總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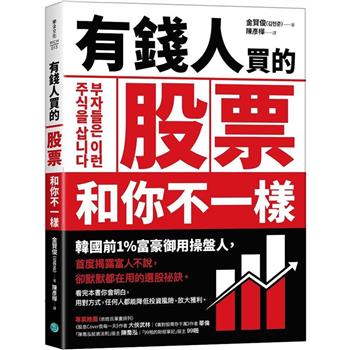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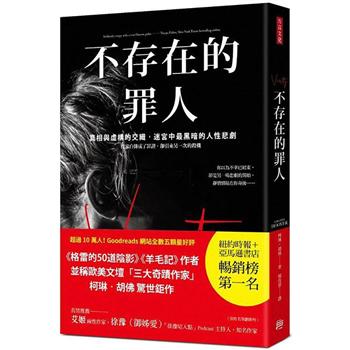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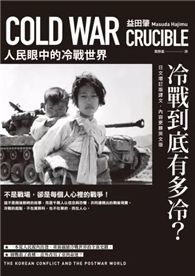
![2026【補充延伸實務趨勢與議題】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史地、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領隊人員][二十一版](領隊華語人員/外語人員) 2026【補充延伸實務趨勢與議題】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史地、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領隊人員][二十一版](領隊華語人員/外語人員)](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6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