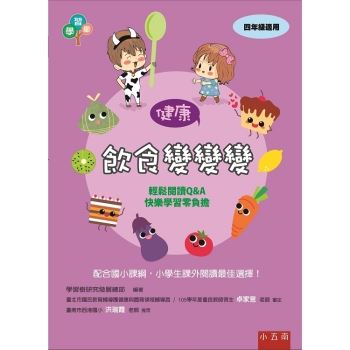序1
每個人都心碎
你跟我說過:「忘了我。」你還要我為這個發誓,發誓要去愛另一個人。我的嘴唇,含在你嘴唇裡面。「一定要忘記」,你這麼說。你是說,「忘記」,或是「忘記我」,我已經不記得。我的嘴唇一直含在你嘴唇裡,你把這句話傾注到我身上:「你一定要沒有我的活下去,你要為我發這個誓……」
我發了誓。
但在你背後,我兩根指頭畫了叉。
上面是《潮浪情緣》裡的一段描述。文字明暢簡單,但是寫出來的那個意味,卻讓人覺得內裡極為脆弱的什麼被觸到,觸得發痛。
那是女主角的情人在得了絕症之後跟她說的話。之後,男人死了,但是女人無法遺忘。雖然承諾了,雖然發了誓,雖然那是逝者生前的要求,但是活著的人把兩個指頭在背後交叉,在承諾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不守承諾,決定要痛苦,要悲傷,要墜落在黑暗裡,要讓自己的人生停頓,讓自己活在過去,永不超生。以半死狀態來悼念,與死者永遠在一起。
前幾年大陸流行所謂的「耽美」小說。我看了幾本,發現「耽美」小說雖然用言情包裝,非常講究文筆,有點民初清末「玉梨魂」「花月痕」之類豔情小說的意味。耽美小說的重點是要哀絕淒絕,要讓人看到心痛,心痛到不忍看下去,心痛到掩卷之後還要內傷許久。
就這一點看,《潮浪情緣》雖然是法國小說,在痛澈心扉的程度上,倒是非常合乎「耽美」的標準。
《潮浪情緣》該算是通俗小說。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看各種類別的通俗小說的,所以這句話真的不是貶意。我喜歡的作家,不論中外,多少都要帶一點通俗性格,例如張愛玲,例如瑪格麗特.愛特伍。
通俗文學或純文學的差別,有點「只能意會,不能言傳」,很難明確的訂出它的尺寸規格。對通俗小說的許多定義,事實上也適用於許多公認經典的純文學鉅作。甚至許多原本是「通俗文學」的,流傳百年之後成為經典。例如莎士比亞、珍.奧斯汀;例如曹雪芹、老舍的作品。甚至張愛玲。張愛玲最初被歸類為「鴛鴦蝴蝶派」,但是現在大約沒有人敢說她寫的不是「純文學」。
早期「純文學」的名詞出現時,有人刻薄說:「看不懂的就叫純文學。」就像也有人形容藝術電影:「看電影時睡著的人越多,影片的藝術成就越高。」似乎文學或藝術作品,和讀者(以及大眾)的距離越遠,純度就越高。
這當然只能當笑話,如果以此為標準的話,那許多政府官員在新聞媒體上的說話都得算「純文學」了,因為多半是我這一類小民「讀」不懂的。然則一個作品,是如何來決定那是不是純文學呢?我覺得主要在作者寫作時站的位置;也就是,要看作者是在哪一個層面上處理他的故事與人物的。這所謂的「層面」,講深入一點,便是境界和格局。如果作者關照作品的格局小鼻子小眼,就算處理的內容橫跨百年,人物上千,地域飛越三大洋五大洲,頂多是熱鬧的通俗小說,依舊不是純文學。相反的,可以通篇只寫一個人,只寫一件事,只寫一天,依然是了不起的經典,例如喬伊斯的《尤利西斯》。
不過,偉大的《尤利西斯》,我相當懷疑看完它的人有多少。我承認我沒看完,看了一年,只看到第三章,這本書很不容易讓人專心。可能映照我的渺小。站在巨人身旁,如果自己沒有巨大到某個程度,看起來就會有瞎子摸象之感,摸了這塊忘了那塊,或像拼拼圖,拼來拼去都只看到殘缺碎片。
我跟所有人一樣尊敬經典,不過真正帶給我閱讀快樂的,其實就是像《潮浪情緣》這樣的書。
克勞蒂.葛蕾(Claudie Gallay),以通俗作家而論,非常難得的擁有自己的氣味。她其他的書我沒看過。不過這一本,氣質絕佳。她的文筆清淡,安靜,而又帶詩意。雖然處理一個所謂的懸疑故事,但是不走緊張刺激路線(事實上我猜她也明白自己的筆路不適合這種風格),相反的,她的書寫帶出一種蕭瑟和荒涼的氣氛,在寂靜中隱含悲傷。
故事背景是法國西部的小漁港拉亞格(La Hague)。拉亞格多雨,每季且有固定發生的暴風雨。沒有比這樣的背景更適合發生《潮浪情緣》裡的故事了。
這是個奇怪的地方。人們靠海討生活,不可避免會遭逢所有討海人的命運。大海會給予,也會奪取。拉亞格海港裡的許多居民都有親人葬身在大海裡,然而大海不願意歸還這些人的屍體。因此,這些人的消失不太像是死亡,因為並沒有屍體來確認這件事。他們只是逸失,蒸發在海上,像是說了一半的話,一個不知道何時會結束的停頓。
這個停頓,同時讓生者的生命也隨之停頓。永遠停留在過去,活的人不做任何事,只是等待。等待某些事發生。這個小漁港的居民像陷在某種魔咒裡,所有的人原地打轉,孩子們長大,成年人老去,除了這些,沒有事情發生,沒有人結婚沒有人離婚,沒有人相愛沒有人相恨,沒有人回憶也沒有人忘記。他們活在某個永恆時空中,一切都是老樣子。
女主角來到這裡之後便愛上這裡,愛上的原因是因為這裡適合耽溺。她的情人在拉亞格每天死一次,也每天活一次。她與他的生他的死一起生活,而心痛難抑的時候她就覺得還和他在一起。她沒有忘記他,因為心還在痛,所以他還存在。雖然肉身早已腐朽,但精神長存。
男主角則正好相反。他離開拉亞格四十年,但是這四十年裡,他的生命停留在原地。他長歲數,變老,有糊口的職業,但是沒有家庭沒有事業沒有生活。雖然模樣俊帥,但是似乎也沒有愛情。四十年前他離開拉亞格的時候是個孩子,四十年後回來,光陰才從他離開的那一刻,重新開始走動。拉亞格就像是被他的離開封印住,成為某種活生生的時間膠囊,所有的記憶,文件,資料,痕跡,每個人的感受,都封住,冰凍。直到他回來,一切才開封,開始啟動。
男主角回來處理他父母的房子,追查他父母親的死亡真相。遇到了女主角,兩個人的人生開始互溶,之後化成了一片,鍥入了彼此。
我在看的時候,一直覺得看到畫面。這部小說如果能拍成電影,一定很好看。拉亞格的風景,海岸,燈塔,小酒館。尤其書裡的人際關係,沒什麼道理的,但是美極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在法國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像哈威爾對待女主角,那樣無求,卻非常溫暖的感情狀態;像麥克斯對茉根的癡愛,還有茉根的反應;茉根和哈威爾兄妹謎一般的關係,以及提奧對南老太太的保護和無法忘懷。這些情感都非常的動人美麗,然而總覺得不大像真的。如果有真人來演出,可能說服力會強一點吧。
我有個女朋友愛看偶像劇,雖然偶像劇不切實際,但是她就愛那種不切實際,與真實人生一點關係也沒有,似乎保存了某種純粹和完整。《潮浪情緣》也給我這樣的感覺,絕不實際也不實在,現實裡沒有那樣的愛恨沒有那樣的悲傷沒有那樣的痛苦……我們的愛恨悲傷和痛苦都要粗礪得多,在割傷別人之前先傷到自己。然而《潮浪情緣》裡的一切都是優美的,那些無可承擔的罪惡與同情都美麗而脆弱。脆弱的像水晶,並不會毀壞,不會消滅,只是藝術品,凝結著。最強烈的和最薄弱的都永遠存在,同時,各自剛強也各自單薄。
那些讓人心痛的描寫,看了便流下淚來了。白色的清澈的眼淚,一邊流淚一邊覺得很美。好像回到很早很早,不這樣年老,經歷不這樣多的時候。
讓每個人都心碎。無論生者死者,老者少者。這樣單純的傷感,輕揚沒有重量。哭過便忘了,留下輕微的夢影。但是似乎可以化解什麼,滌清了什麼。
袁瓊瓊(作家)
序2
The Outermost house
當我們孤單單一個人的時候,連石頭都會緊緊抱在懷中。(《潮浪情緣》)
多年以前,我在紐約MOMA看到馬蒂斯(Henry Matisse)的畫作時,曾在那個巨大的色彩震撼中思考許久。我必須承認當時的我關注的並不是什麼藝術品味之類的問題,而是對自己提出了一個這樣的質問:如果之前的知識系譜並不提供「馬蒂斯是偉大畫家」這樣的訊息,我是否能憑自己的直覺,尋繹出馬蒂斯畫作的迷人秘密?這使我之後養成了這樣的習慣:在做各種形式的閱讀之前,盡量對一無所知的作者保持一無所知。
因此當我收到《潮浪情緣(Les Deferlantes)》的書稿時,我遂習慣性地避開了作者介紹,先將長達二十萬字的書稿瀏覽了一遍。我必須承認,在初讀前五十頁時,我對整部小說的質感存有疑慮。但隨著書中人物的形象、性格逐漸在幾條相互「藏閃」的敘事線中呈現,我也漸漸在作者低調卻如潮浪般節奏的筆觸下,不知不覺地進入了閱讀小說最吸引人的提問:作者想要藉由這些人物或事件,帶我們到哪裡去?
我個人認為,這部小說的成功之處不在於小說一開始就佈下的謎題如何難解(事實上夠敏銳的讀者應該在小說中段,多少能掌握謎底的一部分),而在於作者鋪陳這個謎題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了她別具風格的特殊筆調,讓讀者彷彿置身於那個偏遠的海濱,面對看似一致,其實各不相同的潮湧,猜測它們將會把書中人物推向何方。
為避免妨礙讀者閱讀的樂趣,我並不擬重述本事,或揭露任何情節。但作為一個先各位讀者閱讀的人而言,我仍忍不住又盡可能小心翼翼地提醒您,在某些段落或許應放慢閱讀節奏,思考這些如波浪瞬間飛濺的水珠,所映現的剎那靈光:那可能是麥克斯不斷捕捉,又不斷在籠中死去的蝴蝶;可能是鼓動著巨大、美麗羽翼,在提奧面前撞上燈塔玻璃,血肉模糊的候鳥;可能是南老太太繡在衣服內,從未有讀者的一段故事;可能是茉根慎重其事托付給他人的老鼠;可能是哈維爾在未成名之前創作出的「祈求垂憐的女人群像」;也可能是「我」在海邊做鳥類調查,一段無心的鳥類活動紀錄或單調的觀察表。
我懇請讀者在讀到這些或許連情節恐怕都不算的段落時,試著停頓下來,假設自己坐在一間濱海偏遠家屋的老虎窗前,落筆寫下這些段落可能的心情。也許你或跟我有一樣的感受,這本書說的不是一次海難的故事,也不是海邊小村男女的情事,而是其他的什麼,比方說,或許在讀到最後一頁時,你和我一樣感受到,本書法文書名直譯「湧浪」的可能意涵。
做為一部不賣弄技巧的小說,克勞蒂.葛蕾(Claudie Gallay)筆下沒有一個人物虛設,而偶爾出現一些必要性的絕望詩意,常讓我頗感動心:「大海留下了一些逝者,所以他們無法與世間道別」,「無情的月光將藏匿起來的動物逐出巢穴,讓垂死的人哀哀呻吟」,「有人說這裡風實在太強了,有時候連蝴蝶的翅膀都會被吹掉」、「或許,原諒大海比原諒人容易」……,這雖然不是一部巨構史詩,卻是一部能夠打動人心的精品。據說在法國,這部小說因在讀者間口耳相傳,漸漸受到市場的肯定,甚至使得她原本在小出版社出版的幾部作品(《生者彌撒(L’Office des vivants)》、《單人威尼斯(Seule Venise)》、《在黃金歲月(Dans l'or du temps)》,重獲新生。
在讀這本小說書稿時,我正好在寫作一部長篇小說,不知道該說湊巧還是怎麼地,我已寫完的段落,主人翁也住在一幢「海上房屋」裡。而當我想像書中所寫的那個濱海小鎮的形象時,有一個句子一直闖進我腦裡來,那是自然書寫者亨利.貝斯頓的名著The Outermost House,有時被中譯為《最遠的家屋》。中譯其實很難抓住貝斯頓在岬角觀察鳥類時,一種心境與實境的雙重隱喻:家屋在眼前,家屋仍在遠方。就彷彿《潮浪情緣》中的許多角色,明明已經非常「接近」自己想要回歸的心靈居所,但又因種種原因,復往遠處漂流而去。
這一切,或許都是因為人世湧浪一波接著一波,永無止息的緣故吧。
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暨華文所創作組副教授)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