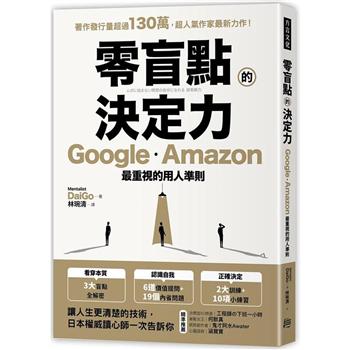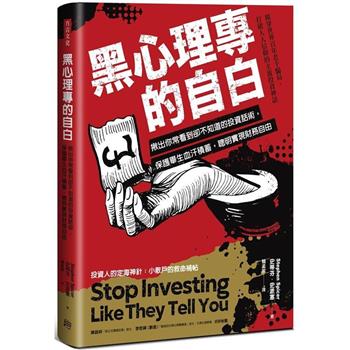中文譯本序言
這本小書,是當我在芝加哥大學做研究生時,於1966到1968年間進行田野工作後的一個成品。書中所描寫的地點,是位於台南縣的一個村落。遵循美國人類學家的傳統,我用了一個化名「保安」來稱呼這個村落。如同在本書第一版的謝辭裡我所表達的,我對極為慷慨的村民們始終心存感激,這些村民和我分享他們的人生,對我解釋他們的觀點,在我瞭解的增進中,感覺到每一天和村民的相處好像又都是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以當時的標準來說,本書初版的價格是昂貴的,所以購買者不多。當初版售罄,出版商詢問了一些在美國的教授,詢問他們是否願意用這本書當作整個課程的主要教科書,當然,結果可以想見,答案是否定的。在一間美國大學裡,有誰會願意用一整個課程來講授保安村的宗教?於是出版商又把這本書的版權還給了我,而這本書也就跟著絕版了。
在此同時,有幾個價格低廉的海盜版版本,在台灣卻賣得很好,我於是和敦煌書局簽了約,而出版了這本書的「第二版」,二版做了幾處校訂,不過基本上它跟一版還是一樣的版本。這個二版在市場上出現了好幾年,但是它現在也絕版了。(後來有第三版的出現,新的版本裡,將羅馬拼音系統轉換成了國際標準化的漢語拼音系統,我將它放在我所任教大學的網站上,提供給大眾使用。)
這本書在台灣曾印行的版本,不管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它比起美國的初版,都更大地影響了更多的人。而多年來,有各種專業的中國研究專家們曾告訴我,當他們過境台灣時所購買的和所閱讀過的這本書,在他們決定要將自己的生涯專注於中國研究或是台灣研究時,它曾發揮過很大的作用。
當我在保安村進行田野工作時,大陸正處在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動盪中;而在台灣戒嚴體制下的政府,仍然抱持著反攻大陸的希望,它對任何有台灣文化特色的事情都持著非常戒慎的態度,這兩種政治情況,都讓美國學者或是會將台灣當作是「真實中國」的一個代替品,或是有意忽視它其實並「不是真的中國」。而我當時是將台灣當作是一個南中國文明的真實而充分的展現,並且是一個多族群「大明」華人文化中的一部分,它有著一部分是獨特,一部分又是與其他地區有著共享模式的生活方式,我的這種看法,非常令人訝異的,竟然是與當時其他人的觀點非常不同。而在我的這個立足點上,同樣的,我的不把台灣文化放在戰後族群衝突、或經濟發展模式、或日本佔領的影響、或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等框架(所有這些都是在當時美國很流行,但是卻是易使人更產生迷惑的輕忽性的觀點)中來處理,在當時也是與別人非常不同。當時流行的觀點,也許是有趣的主題,不過我當時不認為這些流行的觀點,對於了解台灣人的生活方式而言是有幫助的。
那時,我對普通話的操控能力並不好,而對於閩南語基本上是全然不行,即使說我是亟需要運用到這兩種語言來與人進行溝通(我一直認為閩南語就像普通話一樣是一個中文系統,唯一的差別是它未被指定為是官方語言)。為了彌補我的缺陷,我持續地練習語言,經常使用錄音帶錄音,並依靠研究助理的長期幫助,書架上則擺滿了普通話和閩南語的辭典。我所能盡力做的,是盡可能去重複檢查文字、拼音、定義、和其他語言上的細節。幸好,我先前還受過語言學方面的訓練。(很可惜,我的普通話至今仍然很糟,而我閩南語的知識,到今天都仍然不足以達到流利操作的狀態。)
不過,文化不只是完全關於語言。當我住在保安時,當時有幾位耳聾的村民,他們使用著不是很具有系統性的手語動作。我觀察他們,發現他們雖然比我的語言能力還要差,但是比起我來,他們在掌控「台灣人屬性」上,卻比我能夠做到的好得太多。就像我在保安村所學習到的許多事情一樣,這一點是我至今都還在深切思考的可茲學習的課題。(就我所知,關於台灣鄉下聾人的世界,目前還有待人們去進行進一步的民族誌考察。)
除了對於那些我寫錯的部分以外──雖然我不知道我寫錯的是哪些部份,但無疑的書中一定曾出現不少這類錯誤──我認為這本書中所描述到的那些保安村民,應該會認為我書中寫到的許多事情其實都是平淡無趣的,因為這本書只是紀錄了村民已經熟知的習俗和間斷性發生的事件而已,況且書中的鋪陳,許多又和存在於村民習俗知識裡問問題的形式間有著很大不同。
對於今日的保安村民來說,這本書早就過時了:書中有著關於村民祖父輩們漸漸消逝中的世界的某種模糊性的、黑白照般的簡要的印象。更糟的是,當書中專注於宗教實踐的層面時,主要的內容包括了──鬼、附身、驅魔、改運等等這一類事情──這本書並沒有呈現人們生活中比較愉悅性的部分。我所描繪的宗教信仰與實踐,它們會吸引我的注意,有一部份是因為它們和英語世界讀者所知的有所不同,不過更主要的原因是,這些內容,正是這些人們用來對抗困境的文化資源,我希望我在書中已經呈現出來了:這些資源是多麼的有效和富有適應力(或者說至少它曾經是如此)。
我個人平凡的努力,能引起丁仁傑這樣已在人類學研究方面完成不少作品的優秀學者的興趣,並且這些材料能被他用以作為他自己對當代台灣宗教研究的歷史性觀點的依據,這讓我很感惶恐。對我這本舊書的完整的中文翻譯,可能會使我這本書獲得了超出它應得的注意力,我非常感謝丁博士。台灣人的生活方式充滿著宗教意味,我很高興我這本小書曾有助於英語世界裡的幾個世代認知到了這一點。我希望丁博士中文翻譯版的讀者們,在讀完這本書後,也能夠分享我的想法,也就是在台灣,傳統宗教非常有效地服務了這個地區的人們,而當這些宗教信仰與實踐幫助了台灣人安居於此,這一套文化世界看起來是如此的迷人。
譯者導言
一、前言
David Jordan這一本關於台灣地方民間信仰的生動活潑而且是有著獨特論點的民族誌,終於有了中文譯本。Jordan教授還特別為這個中文譯本寫了一篇序言,簡短回顧了這一個作品的形成背景、它在當時時代背景下所具有的某種獨特性,和Jordan本人對於保安村民間信仰的一些基本想法。Jordan教授謙虛的稱這一本書為「一本小書」,或許是因為它確實不是以宏大的理論建構為主要企圖,也或許是因為這一本書後來在學術圈並沒有產生強烈的激盪(至於為什麼會如此?這是另外一個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譯者在此並沒有明確答案,不過這或許和表面上看起來兩個彼此間相矛盾的可能解釋都有關:難道是因為這一本書太過生動活潑而讓它被擺在了學術經典之外?或是因為這一本書所書寫的地方性故事一般人很難深入了解,以致阻隔了人們去發現這本民族誌的學術價值)。然而,這一本書在民族誌書寫上的流暢性、涵蓋題材的廣泛程度、和理解漢人民間信仰議題上的分析上的敏感度來說,不僅有過人之處,更有其歷久不衰的學術價值。對於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如果譯者譯筆在此不致於產生太多誤導和錯誤的話,它更會是一本親切有趣,而且是能真正進入鄉村村民心理與實踐層次的民族誌分析與報導。我很高興在這本書出版了四十多年之後,還能有幸擔當了這本書的第一位中文譯者,剛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對本書的背景與內容做一個初步介紹。
本書書名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The Folk Religion of a Taiwanese Village(《神、鬼、祖先:一個台灣鄉村的民間信仰》,作者自己在二版的封面上所給的中文書名是《台灣鄉下信仰》),初版於1972年,197頁。書的內容是改寫自作者1969年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的博士論文“Supernatural Aspects of Family and Village, in Rural Southwestern Taiwan”。本書1985年曾再版,除了增加二版序言和改變一個註釋以外,內容並無更改。2000年以後,Jordan把二版全文公開在大學的網頁上,並將原用的拼音系統改為漢語拼音,還增加了許多照片。目前的譯本是根據1985年的二版,照片部分則依據網路版。另外,我在本譯本中還增加了一個附錄,是作者1994的一篇文章“Changes in Postwar Taiwan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Popular Practices of Religion”,這篇文章出自於Stevan Harrell and Huang Chun-Chieh 編的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一書,在該文中,作者討論了他在1980年代時所觀察到的台灣宗教活動的變遷模式,全文原長28頁。
《神、鬼、祖先:一個台灣鄉村的民間信仰》書中的主要內容,出自作者在1966年秋至1968年七月間,在台南縣西港鄉某村落所做的民族誌報導與分析。作者用了漢人世界觀裡相當典型的字眼「保安」(這也是村中公廟的名字),來做為這個村落的代稱。正如作者自己在序言中所說,在來到這個村落之前,他並不是要專注於宗教方面的主題,但是當長期參與村中居民的生活後,讓他改變了研究焦點,最後,他的保安村的田野考察,變成了完完全全是一本關於漢人鄉村宗教生活的個案研究。除此之外,我們或許還可以補充兩點:一、Jordan研究過程中的重新聚焦,其實正深刻反映漢人鄉村生活的現實──宗教生活是其中最核心也最戲劇性的環節;二、Jordan的重新聚焦,不僅反映在他博士論文寫作的過程裡,事實上他爾後一生的研究內容,都沒有離開過漢人宗教這個主題。
寫完博士論文後,Jordan還經常來台進行研究,一九九四年所出版的文章,對於當時台灣宗教與社會變遷提出了新觀察,文中他一方面對於都市化與工業化過程中台灣激烈的宗教變遷提出描繪,一方面卻又認為這些變遷,實質上並沒有太多改變民間信仰的基本內涵。我們將這一篇文章放於附錄,有助於將時間的向度納入考量,也有助於更凸顯Jordan的主要觀點。
二、西方人類學家與漢人民間信仰研究
196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末期大陸開放以前,西方人類學家的漢人研究,幾乎都是在台灣鄉村的田野工作中來收集資料,這和冷戰時期美國與大陸的隔閡、美國對於中國的研究興趣、以及台灣做為美國的戰略性腹地等當然都有關係。Gallin(1966)在彰化縣鹽埔、Pasternak(1972)對台南與屏東的比較、Jordan(1972)在台南縣西港、Arhen(1973)、Wolf(1974b)、Harrell(1982)、Weller(1987)等人的在三峽,Feutchwang(1974)在石碇、Baity(1975)在淡水、Cohen(1976)在美濃、Sangren(1987)在桃園大溪等等。這些田野民族誌,相當決定性地影響了西方人類學界的漢人研究,這些學者大部分至今也都是相關學術領域裡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學者。
較早期時,這些田野民族誌中圍繞著的主題常是關於血緣、家庭與宗法組織等與漢人社會整合方面有關的議題,而大部分著作所得到的相當一致的結論是:做為一個移民社會,Freedman(1958)著作中所曾出現的以父系血統,尤其是「宗族法人團體」作為漢人(中國東南)社會結構原則的主要特點,這並不適用於台灣,或至少是還需要經過很大的修正,反而是地緣性的民間信仰,和超地域的進香活動,在台灣社會裡,是更鮮明的有助於地方社會整合的要素。
關於民間信仰研究,西方人類學家根據台灣鄉村聚落而書寫的民族誌,具有著典範性的引導作用,除了因為在台灣這個移民社會中,民間信仰在整合人群上扮演的格外重要的角色,而使各民族誌中特別凸顯了民間信仰的社會面向以外,這更和民族誌的研究方法有關,因為人類學家到台灣鄉村進行田野研究,看到的當然不是菁英的儒家思想,或是以經典和教義為依歸的佛教與道教的教派活動,而通常所接觸的更為廣泛的,會是日常地域性脈絡裡的民間信仰活動。
在長期資料累積中,這些研究,大致上有幾個研究主題,出於本導言的性質,不便涉及太多理論性的爭辯,我們試著用比較素樸單純的方式來歸納這幾個主題。
第一個研究主題,也就是前述提到比較多的關於社會組成原則中民間信仰社會組織功能方面的問題,例如Sangren用「地域性信仰崇拜」(territorial cults)來描述漢人民間信仰,他指出(1987:55),「地域性信仰崇拜」背後包含兩個面向,文化的面向:是指在一個神明崇拜的基礎上凝聚起來的地域性祭拜,這尊神明被認為在一個特定空間上有管轄權。地域性的面向:是指地域崇拜在公眾性儀式裡有具體的構成。透過這些儀式。社區成員聚集在一起,以一個法人團體的形式來行動。雖然地域性廟宇是社區持續性的象徵,一個壇或廟並不構成地域性信仰,儀式才是主要構成體。
這個「地域性信仰崇拜」的概念,和台灣人類學界本土研究中所開展出來的具有指標性意義的「祭祀圈理論」其實是相當類似的,我們這裡也可以稍做說明。「祭祀圈理論」雖然很難被稱為是一種理論,不過它確實是很好的描述方法與討論起點,尤其是在配合歷史變遷層次之後,不失為觀照漢人民間信仰空間與組織層面的很好的研究方法,而且,它也是諸多理論視野中,唯一由台灣本土學者所發揚光大的詮釋框架。
祭祀圈或祭祀範圍,起先是岡田謙(1960〔1938〕)在1930年代調查台灣北部村落的特殊發現:發現通婚範圍、祖籍地的關係、市場交換關係等,與祭祀相共一範圍,岡田謙乃進而共同祭祀活動的形式與內容。這裡可以看得出來,漢人的民間信仰具有明顯的空間性,仍然是屬於自然團體(社會層次與宗教層次緊密交融在一起)中的一部分,這些性質當然和西方基督教差異很大。
後來祭祀圈的概念被台灣人類學者加以精緻化,被以之來作為描述漢人地方社會的工具,簡單的講,根據林美容(1987:105),祭祀圈是指一個以主祭神為中心,共同舉行祭祀的居民所屬的地域單位。它與地域性(locality)及地方社區(local community)有密切的關係,它有一定的範域(territory),其範域也就是表示一個地方社區涵蓋的範圍。相對應這個範圍的,則是範圍內的成員有各種權利與義務,成員也會組成各類神明會團體,於是不少研究也將焦點放在這種權利與義務的內容,和神明會的性質上。
「祭祀圈」概念有助於觀照到民間信仰的地域性屬性、成員構成和祭祀組織的形式,但一方面這些元素當然還必須要放在歷史時空變遷中來加以討論,一方面祭祀活動中除了地域屬性的內涵外還有更多象徵性的指涉(例如說儀式中與神明溝通的內容到底是什麼?),這是祭祀圈概念所無法加以說明的,這些方面,西方人類學家的其它討論中可以找到許多線索。
第二個研究主題,雖然其中各學者所關懷的問題其實不太一樣,但我們可以將它歸納統稱為是關於漢人宗教場域裡的同一性與差異性的議題,學者們除了討論漢人宗教場域中不同次場域間宗教內涵是否有同一性與差異性以外,更主要的關注點,是關於如何去理解這種同一性和差異性?如何解釋造成這些同一性與差異性的原因?以及進一步的說明漢人宗教場域內文化權力的操作模式和宗教象徵體系本身所具有的內在性質等。
關於漢人宗教場域內的同一或差異的議題,早在Arthur Wolf(1974a)早期所編的具有里程碑性質的文集《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裡,全書幾乎所有的論文都是在和這個議題對話。書中先以Freedman 所認為的「漢人社會可能存在著一個整合性的象徵系統」揭開序幕,而編者Wolf本人,他以「神、鬼、祖先」來呈現漢人世界觀裡的基本範疇,這看起來好像是要找出漢人世界觀裡的共通元素,但他實際上持著與Freedman完全相反的立場,而認為不同階層之對於「神或鬼」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1974a:9)。Wolf認為,基本範疇的存在固然是有意義的問題,但是為什麼人們會對基本範疇的內容產生看法上的差異,這可能才是人類學真正應該去探討的主題。《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書中Robert Smith所寫的結論,也強烈反對Freedman的看法,而認為漢人宗教系統裡的多樣性的問題,遠比整體性或相同性的問題還來得更為重要。
學者James Watson(1976:358)則在別處表達了對於Freedman觀點的比較同情性的看法,他認為Freedman不是完全反對差異性的存在,而是更想要去強調,不同階層如何可能以不同方式去轉化同一個象徵體系,而這個體系,又如何可能在一個抽象的層次上是統一的,其中關鍵性的環節是在於「轉化」,而不是一致性。
這個相同與差異性的問題,後來仍以不同方式不斷反覆出現著,譬如說Weller(1987)以普渡儀式為例,而強調同樣的儀式,背後會有不同的「詮釋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存在,而這種「詮釋社群」的差異,有著反抗國家的潛能。James Watson(1985)則使用了「標準化」(standarization)的概念,這個概念和Weller「詮釋社群」概念的指涉有些類似,但是理論意涵卻極不相同,Watson以媽祖信仰為例,強調的是在官方冊封系統運作下,民間原來並非是媽祖崇拜的系統,有可能被納入在媽祖的系統下,結果是,在表面統一的宗教符號的背後,容納著各種差異性,這使得漢人宗教能同時維持著統一性與多樣性,不過統一性所達成的並不是在教義層面,而僅是在儀式層面,「標準化」概念背後所隱含的權力相對位置與權力協商的議題,其實比Weller「詮釋社群」的概念還更動態的呈現出來了帝國王朝裡的宗教生態,和被這個生態影響之後所產生的民間信仰的內在性質。
第三個研究主題,和David Jordan比較有關:信眾日常生活情境中宗教活動的內在邏輯。研究者為了突破以官方或制度性宗教為「大傳統」,和以「無固定文本」的民間信仰為「小傳統」的這種分類上的不切實際,以及為了突破純以「制度性宗教」範疇(儒、釋、道等)來理解漢人宗教的錯誤,由田野出發的人類學家,於是嘗試在日常社區生活中找出漢人民間信仰的內在合理性。這種觀點,不一定就是「功能論式」的,但是,如果將宗教活動放在自然生態或族群關係中來考察,其實很難不帶有功能論的色彩;還有,若將這種觀點拉高到一個較一般性的層次,尤其是若是要去刻意探索漢人宗教體系內部的基本元素時,研究角度往往也會開始帶有著結構主義般的觀點(注意到信仰內部基本元素之間的一種較為持續性的「聯結模式」)。
我們先跳過Jordan不講,事實上,以民間信仰內在邏輯為基礎所進行的各類分析,Jordan所做的是最早的,不過Jordan的分析,較多的停留在一個比較素樸性的分析層次,在理論取向上還刻意保持著一種不確定性,我們後面會再回過頭來講Jordan。
早期,Wolf(1975b)所做的「神、鬼、祖先」的三分法,把民間信仰的內在邏輯,擺在「象徵的社會唯實論」的基礎上,認為它們所反映出來的是,農民對於外在社會世界(官員、乞丐、與家人)的投射,這已經揭開了這種「民間信仰內在邏輯」分析取向的序幕。Harrell(1975)深入於漢人民間的神靈觀,討論祭拜孤魂野鬼的有應公崇拜叢結中,鬼轉變成神的過程。Feuchtwang(1974b)早期著作,已經深受結構主義影響,注意到民間信仰祭祀行為中內在的象徵對比性,譬如拿香的數目上,拜祖先是雙數,鬼與神都是單數;燒紙的方式,對神是燒金紙,對鬼與祖先是燒銀紙;祭拜的方式,對鬼是取悅,對祖先與神則是祭拜等。最後,Feuchtwang結論道:神和現世官僚類似,是具有權威的陌生人,祖先是地方上的同盟者,鬼則是缺少正當性手段的外人,雖然得到的是和Wolf同樣的結論,但是Feuchtwang所關心的是平行在人間與超自然界間,共通的認知結構上的元素,而不是在於「超自然界範疇是否是模仿自人間社會世界」的這個問題上。
結構主義式的看待漢人民間信仰內在邏輯的角度,在一本關於台北縣淡水和關渡地區宗教活動的民族誌裡,有相當完整的呈現。Baity(1975)由一般民眾的世界觀與宗教需求,尤其是由其中關於處理死亡污染的問題來著手,進而發現,村民的需求,是經由不同廟宇與教派等不同管道中所共同提供出來的服務而得以達成,包括:神壇解決私人問題,公廟保護地方,佛教處理了死亡的污染等等,在其分析中,公與私,潔淨與污染等,是村民宗教內涵中對稱性象徵圖像裡的基本構成元素。
這種內在基本象徵邏輯的看法,到了Sangren(1987),有了相當大的發揮,他明白表達出來就是要以「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處理漢人民間信仰,他認為「陰與陽」(失序與秩序)元素間的關係,以及其間的媒介物「靈」等,加起來,可以說明整套漢人世界的社會組織模式和宇宙構圖。而陰與陽,是一種相對關係性的元素,所以當說「人是陽」的時候,鬼和神就都是陰的;但是當拿神與鬼來做比較時,神就是陽而鬼就是陰;而神明之間若互相比較,我們又可以說觀音是陰,媽祖是陽。接著,在Sangren的架構裡,認為在漢人民間信仰體系中,那種可以跨越陰陽間的東西,會以所謂的「靈」來做表徵,我們說神明或一個東西很靈,是因為他有能溝通陰陽,或是有能在陰陽間做轉介的能力。進而,Sangren把這一套結構主義的觀點,和馬克斯主義的分析角度又連結了在一起,而認為:那種被賦予在神明上所具有的超自然的力量(靈),它可以被理解為是關於「象徵符號之關係」的文化邏輯的展現,和關於「社會關係之物質性運作邏輯」的一個外顯的形式(2001:4)。Sangren的觀點的確幫助我們由某個側面(陰與陽),看到了漢人世界社會關係的基本組成模式和象徵符號世界的內在邏輯,和兩者之間更密切的內在聯結性,但是這種以結構主義出發而形成的極為抽象性的討論,也留下來了太多模稜兩可和未加解釋之處。
至於Sangren(2001)後來所做的關於進香理論的分析,以及他的用「個人主體生產」和「社會生產」的角度,以理解出來的「父系模式下的神話與宗教實踐」,則更繁複的將社會邏輯和文化邏輯扣連在了一起,他自己將其標示為這是一種「操控學式」(cybernetic)的處理(2001:第九章),也就是將漢人「相互套疊起來的階序性」(nested hierarchy)社會空間中,不同城鄉層次間的相互交迴性影響(如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甚至和時間上循環性的歷史交迴(如朝代興衰),以及時間與空間兩方面在交迴中的互動(如朝代興衰中的城市發展)等層面,都予以系統性考量的那種研究取向(也參考Sangren 2010),簡言之,這是注意到不同社會層次間如何相互來回作用而呈現出系統性之影響模式的一種觀點。
最近,Lagerwey的一本新書(2010),書中將民間信仰放在傳統「姓氏村落」(單姓或多姓村)間彼此高度競爭自然資源的生態環境中來做理解,其中,風水和儀式,正是處在這種高度競爭中,一個或多個姓氏團體,對於自己的族群如何能夠成功的嵌入於一個特定時間與空間裡的「傳說故事式的再現」。故事中,威脅性的環境就是鬼,利於生存的機會便是神,因此,宗教時空中密集性的神明與鬼,正是反映出社會性時空中密集性的困境與機會。結論性地來說,Lagerwey生動地說道:
如果一個關於生存的策略性的、機會主義式的手段,會被當作是關於漢人宗教與社會生活的主要特質,那麼,秘密性的方法、專門執事者、神話故事、神明啟示以及投機式的冒險,便成為了關係密切的衍生性的特質。在激烈競爭稀少性資源的脈絡裡,如何能獲得最好的專家──也就是那些少數知道怎麼樣來閱讀地景與曆法中的隱密性文本,並能採取適當行動的人──這一件事情至為關鍵。傳說故事裡解釋了是哪些人?和他們以什麼方式得到了成功或失敗?誇張的傳說故事則強化了這個競爭性的意象。
……訴諸神明啟示與投機式的冒險,或許是發生在競爭性脈絡裡最真實顯露的態度與策略,在漢人儀式生活裡,求助於神明啟示,幾乎已達到強迫性執著的頻率。在一個層次上,這表達了類似於前述所講的對於合適的行動的焦慮;另一方面,在一個更基本的層次上,這是在一個特定情境中避免衝突的方法,這個情境,根據定義來說,是一個複雜劇烈的情境:神明所代表的,不只是每個人都想要的物品,也是公共性的利益,而人們非常注意著,獲得這些利益的管道是否是有著公平性。
……透過神明啟示,讓事情由機運來決定,告訴了我們關於神明的一些基本性質:祂們代表著機運。在一個充滿競爭和充滿策略性運作的世界裡,機運是能超越在這兩者之上的事物,而它,也正是典型的漢人們之想像著超越性的方式。
簡言之,神明崇拜,其實是自然村落中姓氏團體憑藉以競爭資源和自我理解的一個結晶化的產物,它其實就是等同於「機運」(chance)之稀少性資源的「再現」,神明的支持,正是一場「機運」競爭中的想像,在此想像中,「神明式的再現」,幫助了特定姓氏團體或數個特定姓氏團體,使其得以落戶並繁衍在一個特定地區中,並以風水和儀式傳說化了其存在的歷史。
注意到自然與社會生態中民間信仰的合理性,其實一直是漢人民間信仰研究中的重要傳統。人類學家田野研究的研究取向,很自然地和這種研究傳統有著一定的親合性。Lagerwey(2010)的把風水和地方宗教儀式,看做是漢人農村聚落裡,不同人群在激烈資源競爭過程中所產生的生存策略與文化再現模式,這個結論,是「漢人民間信仰內在邏輯合理性」之研究傳統的最新版本。而本書這個Jordan在1972年出版的台灣鄉村信仰考察,則可以說是屬於這個研究傳統中,最早但卻是相當詳細的一本田野民族誌。
關於漢人民間信仰研究,除了以上這些主題(社會整合的組織原則、一致性與多樣性、民間信仰的內在邏輯)以及這些主題的引伸議題(祭祀圈信仰圈、地方與中央的差異與整合、地方性的反抗、超自然界不同範疇間的內在關係)以外,還有第四個主要的研究主題,歷史學家Duara(1988)所引發的「文化權力網絡」的議題,其所涉及的是地方性公眾場域與地方性文化權力生產的問題,這個主題受到更多歷史學家所主導,我此處暫時先不放在本導論的討論範圍之內。
導論(節錄)
本書是關於漢人宗教(Chinese religion)的一個個案研究,內容是關於一個村落中目前還活躍存在著的宗教活動。這個村落,本書暫時叫它為「保安」。保安,這個化名的字面意義是:「被加以安全保護好的平安」,保安村的宗教,其存在的目的也在此。平安是指什麼?什麼會威脅這個平安?用什麼手段保住平安?這些將是本書的主題。
我在寫這本書時,有三個主要目標。最明顯卻也是最不重要的目標是:描寫台灣南部的一個村落。就此而言,本書是少數以西方語言書寫的詮釋特定漢人村落的文獻之一,其焦點,是以現有資料來討論漢人農村生活及其跨區域性的變異。任何人想要藉由民族誌的解釋來瞭解中國社會的區域性變異,都會明白,各種民族誌解釋之間的差異是多麼難以捉摸,這種差異到底是由於研究的地區不同所造成的?還是人類學家各自的興趣與經驗不同所造成的?但如果同一個地區有更多的民族誌研究,圖像就會更清晰。近年來,對台灣及香港的研究多了起來,在這些地區終於開始有了較為深入的報導資料,讓我們可以去瞭解各個案間產生差異與相同的原因到底何在。本書的目標之一,即在增添這些方面的資料。
不過,第一個目標還低於我的第二個目標:經由聚焦在宗教信仰及行為,與社會結構(具體來講,書中所談包含家庭和村落結構)之間的密切關係,我試圖提供一個解釋漢人鄉村社會的新觀點。當我們從這個觀點(基本上是社會人類學)去研究漢人宗教時,吸引我們注意的就不會是大傳統下的習俗,譬如清明節掃墓,或農曆過年發紅包給小孩,而是一些和維繫地方社會之運作直接相關的行為,譬如:地方神祇的排名不斷重組,或地方上各類鬼魂的分佈等。我的第二個目標,因此是要去提出一種看法:台灣西南部的宗教是活躍動態社會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種風俗上的標本而已。
在處理這些資料時,我們明顯地看到,保安村的宗教,主要是和人與三種超自然存在(神、祖先、鬼)之間的關係有關。我們很難說其中哪一種最重要,這三種超自然存在對於整個系統的構成都一樣重要,但的確,比較起來,神明和其對應的廟宇,與「問事」來尋求神明指示等活動,是任何到了保安的訪客,在保安人的日常生活中,所立刻可以感覺得到的無所不在的部分。而如果,當分析者想要對構成保安當地人歷史與日常生活作息的事件,去尋找有關解釋與因果說明,將會發現,「鬼」是其中很關鍵的元素。基於此,當然很自然地,我花了大部分的注意力在鬼的層面上,較少在神明(及其神明諭示
![神?鬼?祖先:一個台灣鄉村的民間信仰[精]](https://img.findprice.com.tw/book/9789570840582.jpg)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