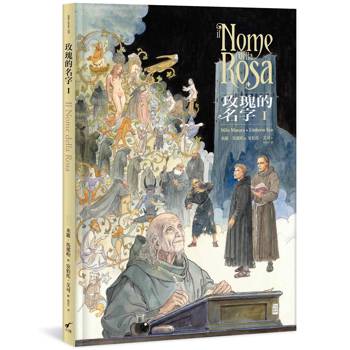推薦序
大腦決定人生
我是迪克.斯瓦伯教授的第一個中國學生。照老師的要求,我一直稱他為迪克。我的學生們則稱他為迪克教授,因為他們覺得直接稱迪克似乎有些不敬。看來,我的學生們比我更具有中國傳統文化。
早就聽說迪克最近寫了一本書在荷蘭異常「火」紅,近半年一直高居科普類暢銷書榜首。很遺憾我沒有機會讀到原書,因為他是用荷蘭文寫的。這讓我不由得想起 20年前,我決定要去阿姆斯特丹,在迪克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我和迪克討論我是不是應該先去學習荷蘭文,他回答說:「學習荷蘭文是浪費時間,請立即過來。」大多數的時侯我都同意他的觀點,但是這一點,我一直耿耿於懷。現在終於證明:如果我當時學了荷蘭文,我就可以在第一時間讀到迪克這本書。感謝眾多中文譯者所做的努力,特別是包愛民教授的辛勤工作,我們終於可以讀到中文版了。像往常一樣,我每次拿到老師的文章時都會迫不及待從頭到尾讀一遍。也跟迪克大多數的學生一樣,在有了自己的實驗室後,我們總是在腦研究的領域試著避開老師的影響。我已經嘗試了 20年,但是讀完本書之後,我又一次放棄了。
迪克的《我即我腦》,從時間上涵蓋了在子宮中誕生的「我腦」,到死亡後一直延續的「我腦」的資訊和編碼。從功能上來看,包括了人類最原始的性功能到最高階的認知功能。現在的準媽媽非常重視懷孕時母親對胎兒產生的影響,經常有「胎教」之說。讀完本書後,你會知道胎兒的大腦對母親有多大影響,告訴媽媽何時應該分娩的是胎兒的大腦。換句話說,「胎教」是胎兒對母親的教育。
如今的社會對於談論性取向或判別自己的性別身份已經十分寬容了。可是在 20年前,當迪克首次證明同性戀的大腦與異性戀的大腦有差異的時候,曾引起了軒然大波。書中描繪了當時社會上甚至包括科學界激烈反對的情況。幸運的是,當 五年後我們證明變性人�的大腦與正常人的不同時,社會上則是一片讚揚之聲。
我們國家已經進入老年化的社會,腦的老化和老年性失智是大家非常關注的話題。迪克在20年前就提出了在大腦老化過程中,大腦「用進廢退」的假說。已經有許多證據顯示:適當的刺激可以重新啟動在老化過程中失去活力的腦細胞,多鍛煉腦比鍛煉身體更重要。
腦科學研究最終是為了解決大腦疾病的問題,本書從作者經手過的病例中描繪了腦疾病發生時的表現和可能的原因。儘管可能還不是最終解答,但是醫學研究的美妙恰恰在於它的不確定性。腦科學從誕生開始就不可避免地與哲學「混搭」。
「我即我腦」可以說是「我思故我在」的一種拓展,也可以說是為意識的起源尋找物質的基礎。迪克不是一個哲學家,但是在他對意識、自由意志、道德、靈魂,甚至是宗教的描述中,我們也許可以期待「神經哲學」這門新學科的建立。事實上,完全可以這麼說,大腦決定了我們的人生。
在書的最後,迪克描述了另一幅美麗的畫面:腦組織在人死後,如果及時擷取,可以在體外培養並觀察到生命的跡象,即「死亡後的生命」。再進一步看,在志願者死後捐獻的腦組織中仍然存在大量的資訊,這是我們研究腦的功能和揭示腦疾病的病因中獨一無二的珍貴資源。
迪克是荷蘭人腦庫的奠基者。數十年來,荷蘭人腦庫為全世界的科學家提供了大量的腦組織標本,為神經科學的發展以及造福後人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我於 1998年回國的時候就希望在中國建立人腦庫,但是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取得進展。每每想起這件事,總是覺得愧對老師。也許,這個心願要由我的學生們來完成了。
中國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院神經生物學教授 周江甯
作者序
我所知道的大腦
我很明白,讀者沒有太大必要知道這一切,但我還是需要把這些告訴讀者。——盧梭
二十一世紀至少有兩大科學議題:宇宙從哪裡來以及我們的大腦如何運轉。我的研究領域剛好是針對後者。
我出生於一個特殊的家庭,聽著醫學各方面的有趣討論長大,這使我終生都熱愛這個領域。我的父親是一位婦產科醫生,他一直致力於生殖學中許多備受爭議的研究,例如男性不育、人工受精、避孕藥等。家中不斷有父親的朋友來拜訪,我後來才知道他們都是各自研究領域裡的領頭人物。
在孩童時期,我就從奎瑞多(Dries Querido)博士那裡學到了內分泌學的第一課。奎瑞多博士後來在鹿特丹建立了醫學院。我們一起去遛狗,當狗第一次抬起腿的時候,奎瑞多博士告訴我,是因為性激素作用於大腦後才引起了這個動作。寶思(Coan van Emde Boas)教授和他的夫人晚上時不時會來我家拜訪,並和我父母一起喝點東西,他是荷蘭第一位性學教授。對一個小孩子來說,他講的故事實在是太精彩了。有一次,他講了一個一整天都不願意配合他進行病情討論的病人跟他之間的談話。最後那個病人終於告訴寶思他為什麼那麼固執——因為他聽說寶思是個同性戀!寶思摟著他的肩膀說:「但是親愛的,你根本就不相信,對嗎?」寶思的反應讓那個病人一下子陷入了困惑。我們大家聽到這裡都忍不住捧腹大笑。
在父親面前,沒有什麼問題是不可以問的。週末,我可以和父親一起讀醫學著作,在他的顯微鏡下觀察污水中的單細胞生物和植物細胞。
上了中學之後,父親允許我陪他一起參加全國各地的演講。那場為了讓避孕藥在荷蘭使用而做的第一階段測試的演講,是我最難忘的,因為那場演講遭到了來自宗教界的攻擊和侮辱。當時,至少父親在表面上看來是平靜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我可是坐立不安、緊張得流汗。後來,我把這件事當做一次有用的經驗,讓我在研究過程中知道如何應對他人情緒強烈的反應。在那段時間裡,發明避孕藥的美國人平卡斯(Gregory Pincus)偶爾會來我們家,我可以和他一起去歐加農公司(Organon)的避孕藥製藥廠參觀。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實驗室。
後來,我決定主修醫學。每次吃飯的時候我會趁機跟父親熱烈討論醫學各方面的問題,討論的方式非常直接,內容也極其詳細,以至於母親常常大聲宣布:「討論立刻結束!」儘管1939年她在俄羅斯和芬蘭戰爭中擔任前線手術室護士的經歷,已經讓她多少習慣了這些話題。那時我也在偶然間明白了一件事:我不能只是提出問題,我需要學會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學醫之後,很快認識我的人都誤解了,他們把我當做是個可以免費諮詢各種疾病的專家。有一次,我實在是受夠了其中一位不停地嘮叨自己的事,就大喊起來:「尤比阿姨,這真是太有趣了,不如你把衣服脫掉讓我們檢查一下吧!」當時,整個生日宴會頓時一片安靜。這個方法很有效,尤比阿姨再也沒有在我耳邊嘮嘮叨叨。但是,其他人還是不停來問我問題。
學醫期間,我希望多瞭解一些實驗研究的背景知識,因為醫學中的概念通常是以實驗為基礎的。此外,我還想要經濟獨立,但這一點遭到了我父母的反對。醫學院學生通過「候選人考試」(在醫學院學習三年之後的考試)之後,在阿姆斯特丹有兩個地方可以在課餘時以學生助理身分參加實驗研究。這兩個地方是阿姆斯特丹大學藥理學系和荷蘭腦研究所。很快荷蘭腦研究所就有了一個空缺,就像是為我準備似的。根據我的家庭背景所選擇的課題,後來也證明了它成為神經內分泌學研究的新領域,即研究神經細胞分泌的激素以及神經細胞對激素的敏感性。與卡佩斯(Hans Ari.ns Kappers)教授的面試中,我提到對神經內分泌學相關課題很感興趣。卡佩斯教授立即把楊肯德(Hans Jongkind)教授找來,並解釋說:「這類課題屬於楊肯德的部門。」接著他們一起面試我,過程中他們發現我對文獻的瞭解很少。儘管如此,卡佩斯教授還是對我說:「我們同意讓你試一下。 」
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研究是經由實驗研究分泌激素的神經細胞的功能。當時我一邊學醫一邊進行這項研究,因此課餘時間我都全力以赴在所裡做實驗。1970年,當時我還在外科的佈雷瑪(Boerema)教授底下做實習醫生,一天下午我請了假,順利完成了我的博士論文口試。1972年,我通過醫學院的畢業考試之後決定留在腦研究所。1975年,我成為荷蘭腦研究所的執行所長。1978年,我當上了荷蘭腦研究所所長。1979年,我成為阿姆斯特丹大學醫學院的神經生物學教授。此後的三十年間,儘管我擔任各種行政職務,但始終都把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上。事實上,這正是我選擇這個職業的原因。迄今為止,我從研究室裡的大學生、博士生、博士後和同事身上學到很多,他們先後來自二十多個國家,都是有思想、具批判精神並富有才華的優秀人才,我現在還經常在世界各地的神經科學研究所和醫院中與他們見面。我們整個團隊還要感謝那些優秀的實驗技術員,他們確保了新研究技術的開發和品質。
在這段期間,我遇過來自不同病例的各種問題,有些問題已經超出我的專業領域。人們總是會把我當成一位醫生,即使我不看診而是專門做研究,他們在遇到實際發生的問題時也常常會來找我。腦科疾病會影響到一個人的個性,因此有人向我諮詢最嚴重的影響是什麼。某個星期天的早晨,一位熟人的兒子帶著幾張腦掃描圖來家中找我說:「我剛聽說我只有三個月的生命了,我現在該怎麼辦?」當我看到那些掃描圖時,我真的不敢相信他還可以到我家問我這個問題,因為他的大腦前側長了一個大腫瘤,現在竟然還活著。這個時候我能做的只有傾聽,替他們解釋研究的成果,為那些陷入絕望的人們在眾多的醫療方法中做些建議。我自己的孩子倒能正確明白我的能力,在他們發高燒的時候,如果我拿著聽診器坐在他們的床邊,他們就會堅決要求找一位「真正的」醫生。
1985年,我建立了荷蘭人腦庫(見第二十章第四節),正如外界所瞭解的,我研究死者的大腦。讓我驚訝的是,這些研究讓我開始思考生命最後階段的每件事物:安樂死、協助自殺、決定為科學研究捐獻大腦和屍體。簡言之,就是所有和生與死有關的事物(見第二十章第三節)。
這個領域的研究總是與這些研究對於個人和社會的影響緊密相連。我參加過一些勇敢母親們的聚會,她們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因為那些孩子患有精神分裂症並自殺去世。在伊希龍(Ypsilon)組織的旗幟下,這些母親聚集在一起,支持著其他的孩子。在關於普瑞德─威利症候群(Prader-Willi Syndrome,俗稱小胖威力症)的國際研討會中,我明白到這種疾病患者的家屬比我們這些研究者更瞭解這種疾病。研究人員與患者父母坐在一起討論,導致孩子們拼命吃東西、就算吃得很撐也不甘休的原因。父母們帶著過度肥胖的孩子從世界各地趕來,因為這些父母的參與,研究人員對這種疾病更加了解,也受到極大的鼓舞。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患者可以加入和研究人員共同討論病症。我們的研究團隊是第一個在荷蘭研究阿茲海默症的團隊,當時關於這種疾病是否會流行還只是臆測。我們觀察到,有些腦細胞可以成功抵制衰老和阿茲海默症(即老年失智症),而其他腦細胞則會遭到破壞,這些現象為我們研究這種疾病的治療提供了一個方向(見第十九章第三節)。由於社會邁向高齡化,我們不得不面對自己的親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由於失智而退化。大部分人也都很瞭解精神病對精神病患者、患者家庭及監護人造成的巨大壓力。身為腦部研究者,我們所面臨的大腦疾病問題是如此的尖銳和感性,也根本無從逃避。
普通人對我們每天奮力解決的問題根本不感興趣,他們完全誤解,以為我們已經瞭解關於大腦的一切。他們想知道諸如記憶、意識、學習與情感、自由意志和瀕死體驗等與大腦有關這些重大問題的答案。在公開討論的過程中,許多參與者會說出一些我並不知道的「事實」,例如人們僅僅使用了10%的大腦的這種「神話」。這種說法可能是真的,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神話」的依據。此外,人們因為老化每天失去數以千萬計的腦細胞的說法也是如此。在接連不斷的演講中,充滿興趣的參與者所提出的許多新穎問題也能促進我的思考。例如,有一位日裔荷蘭女孩想寫一篇關於歐洲人的大腦和亞洲人的大腦區別的論文,而這種大腦的區別是真實存在的。此外,我對人類大腦的研究每次都會引起一連串的質疑和激烈的社會迴響,我受邀舉行一系列公開討論會來解釋一些問題:大腦的性別差異、大腦與性取向和異性癖的關係、大腦發育和精神疾病(例如憂鬱症和進食障礙等),在第二章至第四章和第六章中,我會談到這些問題。
我積極參與這一領域研究的四十五年間,發生了許多變化,腦研究已經從一項孤立無援的特異研究漸漸發展為引領全世界科學研究潮流的主題,藉由數以萬計的研究和眾多的技術與學科快速出現大量的新發現。以往一般民眾對神經科學的恐懼已經完全被他們對腦研究的濃厚興趣取代,這些變化也得益於當今優秀的科學媒體。對我個人來說,沒有什麼科學問題是脫離社會存在的,超出我的研究範圍的大腦問題,每天都在不斷激發我的大腦去仔細思考,同時我也在思考如何才能把一切清楚地解釋給普羅大眾聽。就這樣,我自己的各種看法不斷湧現:關於大腦的某些方面和它的演化、大腦的發育和衰老、大腦疾病的致病原因、人的生與死。我在這本書裡整理了個人微不足道的觀點。
我被問過最多的問題就是,我是否真的可以解釋大腦是怎樣工作的。這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這本書只能試圖解答這個問題中的幾個面向。讀者會知道:大腦是如何分化成男性和女性,大腦在青春期會發生什麼變化,大腦如何保持個體和物種的生存,人們出現衰老、失智以及死亡的過程是怎樣的,大腦是如何演化的,記憶是如何運作的,道德行為是如何演變等等。除此之外,這本書還解釋了大腦疾病是如何形成的。不僅著重介紹了意識障礙、拳擊造成的腦損傷,以及成癮、自閉症、精神分裂症等腦疾病,還有治療這些疾病的治療與復原的最新進展。最後,這本書還討論了大腦和宗教、靈魂、精神、自由意志之間的關係。
本書中的章節都是獨立成篇的。這些短小的章節涵蓋了多個主題,因此不可能進行深奧的科學論述。這本書只是我們進一步討論,人們為什麼是現在的性格、大腦是如何發育和運作以及可能出現什麼疾病等問題的基礎。我希望這本書可以為一般民眾提供一些常見腦部疾病的答案,為學生和年輕的腦研究者提供更多神經科學的基礎知識,讓他們可以跨越自己的研究範圍,並試著與他人溝通。寫這本書當然是因為有必要讓大家看到腦研究的社會成果,但另一個目的也是希望我們的研究能夠得到整個社會的支持。



 共
共  2013/01/27
2013/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