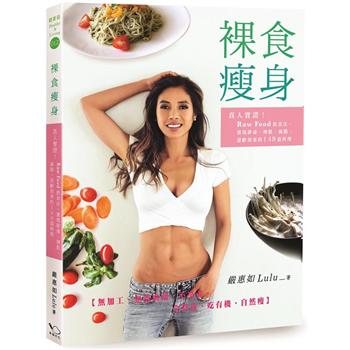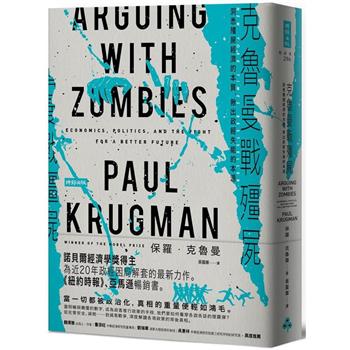第5章 個人困境作為社會議題:脈絡中的不孕敘事
在個人敘事中建構社會認同
Constructing social identities in personal narrative
我從一個研究訪談中擷取一個片段做例子,說明敘事分析的社會觀點。其中包含了詳細的逐字稿,這樣讀者才能在對話交流中細查敘事。我的理論興趣在於,當面臨到不孕的「個人困境」時,婦女如何建構她們的身份認同。我在一個故事中,分析一名婦女如何展演(perform)她的社會認同:她的「私密自我(private self)」受對立的現實環境所形塑,一方面是性別不平等,另一方面是促進社會正義的公共政策。此訪談取自於一大筆的訪談資料,針對無子的已婚婦女,1993至1994年完成於南印度的咯拉拉省(Kerala)的田野工作期間。在個別的時間點上,所從事的訪談都有錄音,並且在事後謄寫成逐字稿,必要的時候再予以翻譯,這些訪談〔七個是英文寫成,剩下的是馬來亞拉姆語(Malayalam)2都由我和我的研究助理Liza執行。〕我們鼓勵婦女廣泛地描述她們的處境,包括其他人的反應:丈夫、其他家人和鄰居。我們沒有訪問她們的丈夫,因此,他們對於不孕的看法是由這些受訪婦女所代言(對於方法的完整描述,請見Riessman(2000a)(2000b)之文獻)。
我調查這位被我稱為Asha的婦女的生命故事,之所以選擇她,因為她在我的調查樣本中年紀最大,並且也可能已過了生育年齡。對她而言,建構一個沒有親生孩子但卻有意義的性別認同,是她生命中的主要議題。Asha住在印度,一個強烈鼓勵生育的社會──婦女被期待結婚生子,但她住在咯拉拉省,那裡有著培養婦女自主權與經濟自足的悠久傳統3。然而,就如同其他在咯拉拉沒有小孩的婦女一樣,她面對著嚴重的汙名,因為她無法為人母(Riessman, 2000b)。例如,鄰居待她如machi,一個在英文裡找不到對譯文字的馬來亞拉姆語,意指無法繁殖後代的農莊動物。
在Asha的敘事中,我特別注意到社會定位與認同宣稱的關聯性。「定位……指的是,在個人故事論述建構中,分配給講述者流動的『部分』或『角色』」(Harrd & Van Langenhove, 1999, p.7)。當我們講述我們的生命故事時,我們就在展演我們的身份認同(Langellier, 2001; Mishler, 1999)。有幾個社會定位的層面,是我進入「個人故事(personal stories)」的分析要點。第一,它發展一種立即的論述脈絡──一個涉及聽者∕提問者的訪談。在這一層面上,Asha在一個對話過程中定位她自己,在這個案例中,她對特定的觀眾展現她喜好的身份認同──我的研究助理和我。我們也被放在社會空間中,並將不孕的觀點帶入交談中,將Asha定位在其中。第二,Asha的敘事被定位在一個更廣的文化論述,那是關於婦女在現今印度中更適宜的位置──在一個正在為女性發展勞動新空間(除了家庭與農田之外)的「發展中」國家中的位置。這個敘事也定位在咯拉拉省的性別政治中,在那裡,婦女由於進步的社會政策已有了一些優勢,但也仍受限於性別意識型態。我說明了注意轉換的文化脈絡與最切近的訪談脈絡,對詮釋是如何必要的。第三,Asha在她故事中,將她與醫師(和醫療技術),及具有權威的家庭成員的特定關聯中定位自己。綜合這三點,在敘事中社會定位的視角,提供一片透鏡,探究一位中年婦女如何在無法懷孕的情況下,努力建構一個正面的認同。
我們和Asha見面的那天,她正在一所政府醫院的不孕門診進行第二次的診療。根據她的陳述,她之前已在另一所醫院接受不孕的生物醫學(biomedical)治療。生物醫學在咯拉拉省的城鎮和村里都普遍可及;她這次前來求診的醫院是大轄區的第三級照護中心。我們從Asha的訪談(見以下摘錄內容)得知,她來得很勉強,但她對於受訪這件事卻未感為難;在她正在候診的時候,我們花了將近一小時的時間,在一間隱密的房間裡交談。我的研究助理Liza,二十六歲,她告訴Asha,我們想要「從婦女的觀點來了解沒有孩子的經驗」。開放式的訪談以馬來亞拉姆語進行,再一段段地翻譯給我聽,Asha說,這樣的方式讓她感到「舒服自在」。雖然我們大部分的問題,聚焦在不孕和社會反應等議題,但Asha卻直接將訪談轉移到其他對她重要的主題上。例如,在開始的前幾分鐘,當問到有關她的家庭組成與其他人口統計學的「事實」時,Asha的延伸回應暗示了性別關係上的錯綜複雜──她的丈夫比她年輕十二歲,不久就要失業──「我們接下來只有靠我的收入勉強生活下去」。這些議題的意義只有在後來的訪談才變得清楚。在這一點上,Liza問:「妳認為妳沒有小孩的原因是什麼?」我們就這一點切入訪談。
本書介紹
本書的出版,為質性研究應用於社會工作,定義了關鍵趨勢。在社會工作實務脈絡裡,放入了知識論及方法論的議題,同時也在研究實務上,提供採用質性方法的基礎。
原書編者Ian Shaw及Nick Gould在第一篇的導讀文章中,將質性研究放在社會工作發展及問題的脈絡裡。第二篇為本書的核心章節,特別委託各領域的首席學者編寫而成,每一章包含了關鍵的質性方法,以及與社會工作環境的關聯。第三篇則是回應質性研究在社會工作中的應用,並提出社會工作的思維與實務,如何透過研究而得到提升實務的操作方法。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