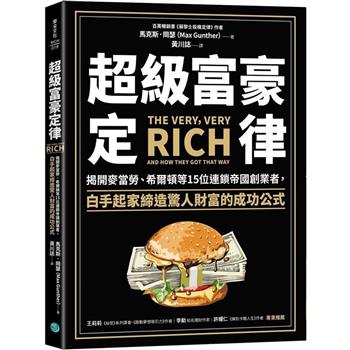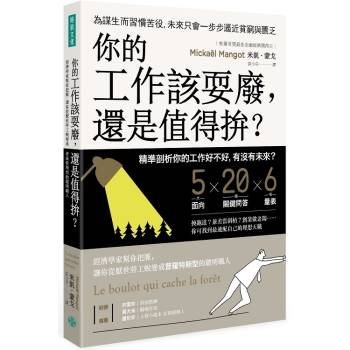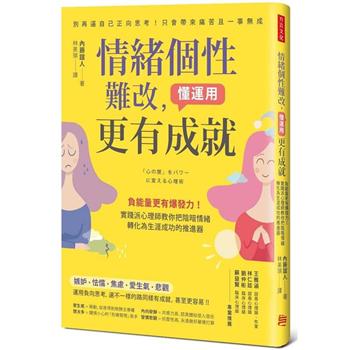最靠近彼此的那一刻,也是我們對愛情最盲目的時候!
★丹麥最擅長描寫愛情與婚姻的重量級作家!已譯介超過二十國語言!
★郝譽翔專文導讀!
如果沒有欺騙,沒有背叛,那麼,是什麼讓我們不愛了?
那是個沉默的十月的早晨,雅絲翠不說一句話,轉身離開了我們的世界。
至今我還記得我們的相遇。
自從那一夜,雅絲翠跨進我的計程車後座之後,命運就註定我們相愛。那時,我剛脫離一段令我瘋狂失智的愛情,茫然迷失了人生方向。而雅絲翠,她就像一道溫暖而堅強的曙光,闖進我的世界,照亮我、拯救我。
要是沒有雅絲翠,我不會甘於成為一個投身婚姻的男人,知道日子在瑣碎事務與孩子變化間是多麼幸福安逸。雅絲翠和我分享著這一切,我們成了最瞭解彼此的人,擁有無可比擬的默契。
但現在我卻猜不出雅絲翠的離開。
她無言離去,沒有一字一句,唯一留下的線索,只有她信用卡的刷卡記錄。我追索她的軌跡,發現她朝著葡萄牙的里斯本而去,那段,我們多年之前曾經踏上的愛情旅程。難道,這就是雅絲翠想給我的答案嗎?……
愛情與婚姻,是男女關係最難解的兩個課題,而龔達爾正是擅長敘寫此類題材的名家。他以敏銳而熟練的敘事手法、優美的文句詞藻,深入刻畫兩性之間幽微糾結的心理層面。《沉默的十月》讀來濃烈醇厚,字裡行間凝聚的情緒與張力,令人心跳隱隱加速地搏動與顫抖;跟著主角悠遠縝密的思緒,讀者彷彿也潛入了人物內心的深層世界,一同體會百轉千折的情感變換。
本書特色
◎入圍2002Impac文學獎!已譯介超過二十國語言!
◎亞馬遜網路書店★★★★★好評!
◎《INK印刻生活文學誌》2009年3月號「國際文壇」單元專文介紹!
◎郝譽翔專文導讀!
作者簡介
最擅長書寫愛情、婚姻,被譽為「文學界的柏格曼」的丹麥重量級作家 楊.克里斯提安.龔達爾(Jens Christian Gr?ndahl)
1959年生於哥本哈根,丹麥當今最重要的作家,在歐洲文壇享有盛名。他在26歲出版第一本小說,作品類型豐富,涵蓋劇作、散文及十一本小說。龔達爾的作品多在描繪現代婚姻生活的難題,呈現夫妻關係常會面臨的迷惑與失落;在充滿哲思的感情剖析中,隨處可見驚人的視野。他筆下的世界是如此平靜,卻滿溢令人動容的生命風采,也因此,歐洲文評更讚譽他為「文學界的柏格曼」。
龔達爾曾多次入圍「都柏林IMPAC」、「梅迪西翻譯書」、「費米娜翻譯書」等重要的國際文學獎,也獲得過「大使文學獎」、「金桂冠文學獎」等多項歐洲文學大獎。《沉默的十月》是龔達爾跨入英語書市的第一本小說,也讓他躋身為國際文壇名家。就如法國《世界報》書評所言:「龔達爾捕捉了生命的中心!」他的作品也將是我們細讀人生不可缺的指引。


 共
共  達爾,是鳥山明的原作漫畫《七龍珠》系列及其改編原作的動畫系列中登場的虛構人物。
達爾,是鳥山明的原作漫畫《七龍珠》系列及其改編原作的動畫系列中登場的虛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