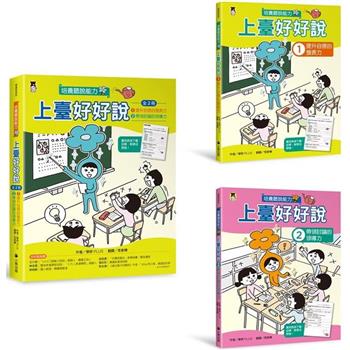「親愛的大海,謝謝你!你是唯一不需要簽證就接納我的地方……
親愛的魚,謝謝你們!你們對我的宗教或政治傾向不加過問就把我吃了。」
——2015年5月盛傳於網路上的敘利亞難民遺書
親愛的魚,謝謝你們!你們對我的宗教或政治傾向不加過問就把我吃了。」
——2015年5月盛傳於網路上的敘利亞難民遺書
難民,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他們為什麼不留下來,為自己的國家奮戰到底?
為什麼那些難民父母自己不工作,卻讓小孩負責打工賺錢養家?
明明是難民,竟然人手一支手機,也有辦法付給人蛇好幾萬美元?
橫越地中海的那些「死亡之船」上,究竟都發生了什麼事?
自2011年爆發內戰以來,敘利亞人民平均壽命整整降低了20年,760萬人流離失所,400萬人逃出敘利亞、成了你我口中的「難民」。
從兩伊戰爭到最近的內戰,伊拉克有4%的人口「被消滅了」;2014年初,約250萬伊拉克人在ISIS的武裝攻擊下逃離家園……
這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難民潮」,已經成了一齣日常的悲劇,淹沒在每分每秒攫取我們注意力的大小即時事件中。但如果他們不再只是一個數字,如果你可以聽見他們的故事,你會知道他們和我們沒什麼不同。
因為愛,他們都成了難民
當國家背叛你,連一點希望也不留,
你能做的,就是為了所愛之人渡海翻山,尋找一家的容身之地。
當大海的另一頭,雖然不是應許之地,卻是一家人
或許可以重新來過的唯一希望——你會怎麼做?
他們的故事,也是你我會做的抉擇。
關於那些被歐洲各國視為燙手山芋的難民,我們了解太少,自以為是太多;
事實是,當世界脫離正常軌道,一切不能再以我們習以為常的標準看待。
他們捨棄一切,逃往未知的命運。他們已經一無所有,仍拚了命要保住手機,
因為它是與留在家鄉的家人聯繫的唯一工具——卻也成了人蛇向其家人勒索的道具。
他們不是不想工作,是雇主只想雇用他們的孩子,因為童工的薪資低廉。
他們想要工作養活自己,但是在取得歐盟正式的庇護判定之前,他們沒有資格工作……
當世界越來越向右翼傾斜,當同溫層取暖取代了對話與溝通,世人被偏見與仇恨操控,兩位歐洲資深記者動用生涯中的所有關係,親自走訪中東、歐洲各難民營,只為將他們的人生故事帶出那片看不到希望的帳篷叢林,讓世人聽到他們的心聲、看到他們的面容;
他們登上地中海的小島蘭佩杜薩,走訪曾經親手拯救瀕死難民的漁夫,看後者因為眼睜睜看著難民從自己手中滑走、沉入深海而內疚;他們也探訪了那些僥倖活著登上歐陸的難民,揭露「死亡之船」上究竟發生了什麼悲劇;
他們還取得了義大利警方攔截的人蛇通訊內容,披露他們如何綁架難民、反覆榨取偷渡費用,藉此謀取暴利;最後,他們來到一個原本反對安置難民的奧地利小鎮,看當地居民如何從最初的恐懼與防衛,到後來終於明白難民不是洪水猛獸——他們只是希望有尊嚴地活下去——與你我並無不同,因此轉而全心協助他們在歐洲落腳,讓他們安心在此為自己重建全新的人生,以及與親愛家人團聚的不遠未來。
如果這個世界已經瘋了,唯有關心與行動可以讓人類再次偉大。
本書特色
.收錄 26 張現場與受訪者彩色紀錄照
.附中東、北非難民流亡路線圖
.在台灣的我們可以採取什麼行動?——提供可信賴的正式管道,傳達我們對人道救援行動的支持
名人推薦
udn《轉角國際》專欄作家黃哲翰專文導讀
彰化高中圖書館主任呂興忠.新北市丹鳳高中教務主任宋怡慧.
彰化縣土庫國小教師林怡辰.台北市中山女高國文老師張輝誠.
高雄市英明國中公民老師郭進成.凱風卡瑪兒童書店創辦人陳培瑜.
作家番紅花.熱血公民教師黃益中.作家楊婕
——為了更溫柔美好的世界真誠推薦(依姓氏筆畫序)
█來自教育界的聲音(依姓氏筆畫序):
國立彰化高中圖書館主任 呂興忠
為了頒發「台灣國際馬拉拉獎」給難民營兩位女高中生,我分別於2015年與2016年進入約旦的Zataari敘利亞難民營,短暫接觸了難民營的兒童和青少年。他們空洞的眼神是難民悲劇最令人心酸的部分,而想了解完整的故事,就要閱讀這兩位歐洲傑出媒體人合著的這本中東難民新書。
新北市丹鳳高中教務主任 宋怡慧
在富裕自足的今日,向左走,遇見愛;向右走,遇見情。你可曾停下腳步,聽一聽關於流離失所的真情呼喚?你可曾離開舒適圈,看一看天堂以外,沒有光的世界。閱讀時,淚水流淌的感同身受,當恐懼、飢餓、死亡襲捲而來,你還相信人間有情,生命有愛?讓他們勇敢活下去的理由,是因為我們都願意為他們提盞燈,未來之路,彷彿若有光……
彰化縣土庫國小教師 林怡辰
沉重,但不得不看的一本書。閱讀過後,久久無法忘記書裡的畫面。但此時此刻,六千萬人逃離了家園,正在受苦。我們能做什麼?如果我們是他們呢?想起海灘上永遠沉睡的孩子,我們都需要一起來閱讀,了解他們的傷和苦,坦誠面對自己的良知。
台北市中山女高國文老師 張輝誠
難民問題,離台灣太遠,彷彿是另一個世界,與我們不同存於一個時空。我去過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和埃及,似乎較能感受多一些些,過去也曾經稍微用心去閱讀、理解中東的歷史,以及當地人民的思維…… 中東問題複雜到台灣可能不容易、甚至不想也不願去多加關心,但是台灣和中東的命運又是何其驚人地相似,同樣都是大國之間角力的棋子……這本書帶領著讀者從各個角度探討中東和北非的難民問題,很值得閱讀,因為也許當我們多一點明白難民之辛酸、之悲哀、之痛苦後,台灣才可以有所警惕,不會重蹈覆轍,步上他們的後塵。
熱血公民教師暨《思辨》作者 黃益中
教育的可貴在於關懷弱勢並同理心他人的處境,人性的溫暖光輝就在此時逐漸綻放。
台北市景美女中輔導室老師暨作家 楊婕
愛和苦難,似乎是難民敍事無可避免的兩大主軸,開啟我們閱讀本書的旅程。期待有一天,人權不需藉由愛與苦難,也無有一絲削減損傷。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