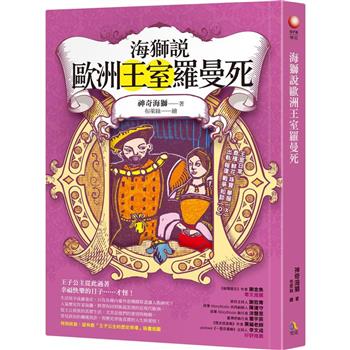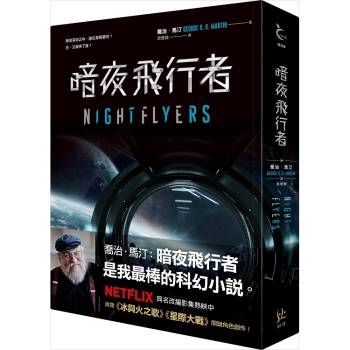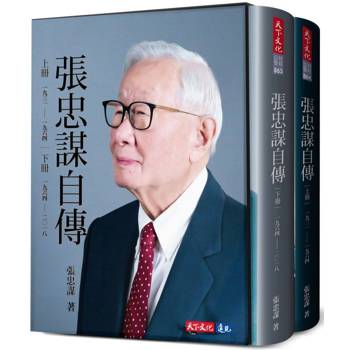嶄新的文學評論之作,重新認識夏目漱石,非讀不可的深度傳記!
大膽以夏目漱石的家庭背景為出發點,並以「母愛」為中心,探討夏目漱石的內心世界,有別一般文學評論作品。
日本近現代文學專家-林水福教授專文導讀。
日本一代大文豪說不出口的疑問:母愛真的存在嗎?
文豪夏目漱石,和愛因斯坦一樣,死後大腦仍被完整的保存。與森鷗外齊名,同為日本近代文學大家。以《我是貓》、《少爺》等作品廣為臺灣讀者所知,作家生涯一帆風順。一九八四年,他的頭像被印在日幣千元紙鈔上。
這些都是大眾所熟悉的漱石。
然而幼年時期接連更換兩個寄養家庭的過往,讓文豪困擾並懷抱終生的疑惑:「媽媽到底愛不愛我?」這種對母愛感到懷疑的心態,甚至延伸到了對人的不信任與猜忌的態度上。從《我是貓》、《少爺》等作品到後來的《明暗》,背後隱藏的其實是對自身價值的重重疑問;究竟在漱石人生的終點,是否已經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
作者簡介:
三浦雅士 Masashi Miura
1946年生於日本青森縣,編輯、文學評論家、舞蹈研究者。1969年曾進入當時日本知名出版社青土社任職,並參與文藝刊物《Eureka》的創刊計畫。對於文藝界的活動十分熱心參與,三浦為日本文化廳文化審議會的委員,也是日本文藝家協會的理事之一;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目前在新書館擔任主編,他同時也是立教大學文學研究所的特約教授,持續在每日新聞上發表書評。
三浦雅士為知名的文學評論家,曾擔任多項文學賞的評選人,並對日本近現代文學常有獨特角度的評價。著作豐富同時獲獎無數:《憂鬱的水脈》(獲SUNTORY學藝賞)、《所謂小說的殖民地》(獲藤村紀念歷程賞)、《身體的零度》(獲讀賣文學賞)、《青春的終點》(獲藝術選獎文部科學大臣賞、伊藤整文學賞)、《村上春樹和柴田元幸的另一個美國》、《出生的祕密》、《漱石—文豪消失的童年與母愛》等多本。
其中《漱石—文豪消失的童年與母愛》為三浦雅士以「漱石懷疑母親對自己的愛」為中心,剖析漱石作品人物間的交流與癖性,進而分析作品中透露出的漱石心態。
譯者簡介:
林皎碧
出生於台北縣新莊市,臺灣淡江大學東語系畢業,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文學碩士,專攻日本近代文學,以其專業多次在報章上發表研究報告和隨筆,〈為消逝的日本沉重嘆息〉、〈淺井忠與《湯島聖堂大成殿》〉、〈永不過時的美學精神:《達文西的筆記本》〉等多篇。譯著有《日本名畫散步》、《沙門空海之唐國鬼宴》卷一、卷二、《避暑地的貓》、《不可思議的金錢》、《春之夢》、《夢見街》、《不可思議的金錢》。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推薦序>貫穿漱石文學的基調 林水福
一、國民作家之美譽
日本近現代作家之中,有「國民作家」之稱的,並不多。有些出自評論者、愛好者主觀的推崇,其實無法「放諸四海而皆準」。
漱石,國民作家的美譽,在日本人心中,可說已成定論。
漱石初期作品《我是貓》、《少爺》、《三四郎》或者到《虞美人草》為止,給人印象是幽默,以老練的筆調鮮明描繪好人或壞蛋,作品中人物有如現實生活周遭人物,易懂,而且情節單純。全體而言可說相當「通俗」,日本人不拘年齡都會閱讀的。就此意義上稱之為「國民作家」。
漱石作品常碰觸倫理、正義等問題,就內容而言,作品中的男女關係,常是違反倫理的三角關係,其實已超越了「國民」的界限,對「人」普遍存在的問題深入挖掘。
漱石作品的另一個特色是,將日本近代背負的文明之苦,視為一己之責任,試圖在文學作品中「解決」。換言之,日本國民背負的文明之苦,由一己承擔,就此意義也可以稱為「國民作家」。
二、漱石生平簡介
夏目漱石,一八六七年生於江戶牛?馬場,父夏目直克,母千枝,千枝是直克前妻逝世後再娶的。當時民間迷信申日申刻出生的人,不是大好就是大壞,有可能當強盜,在名字加上金字可改運,而漱石正是庚申日而且是申刻(下午四時左右)出生的,因此命名金之助。
金之助上有五兄二姊,身為老么,但從出生起就不受歡迎,被送到「古物商」(即撿破爛)寄養,有一次姊姊路過看到金之助被丟在破爛堆中,不捨,抱回家,卻惹來父親不悅。
兩歲時送給新宿「名主」(約相當於今之里長)福原昌之助當養子。漱石在《道草》中說,記憶中養父管理已歇業的妓女戶建築物。養父母非常溺愛,但幼年時期相當孤獨。
明治四年(一八七三),金之助四歲時養父擔任淺草諏訪町的「戶長」(鎮公所行政官員),於是舉家從新宿遷居淺草。養父母常輪流問他:「你父親是誰?」「那你的母親呢?」漱石因此陷入自己真正屬於誰?屬於哪裏的不安。
後來養父母感情不睦,離婚。明治九年,金之助九歲時由生父母家領回。金之助和生母在一起的日子,只有明治九年到十四年母親逝世為止短短的五年。︿玻璃窗中﹀說:「母親的名字叫千枝。我至今仍然覺得千枝是令人懷念的詞彙之一。對我而言,那不只是單純的母親的名字,而是其他女人決不可使用的名字。」
回家之後,父親對金之助依然冷淡。金之助親近漢書籍,於《文學論》中言:「余少時好學漢籍,學習期間雖短,漠然從左國史漢得到的文學當如斯之定義。」左國史漢是《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的簡稱。明治十二、三年從東京府第一中學轉到以漢學聞名的二松學舍,目的在於喜好漢文,試圖深究漢學。
那時學校未開設英語課程。金之助為了迎接新時代的來臨,認為英語是必需的。明治十六年,轉到英語成立學舍,翌年進「予備門」。明治二十一年九月進入予備門(預科)後身的第一高等中學本科,決意專攻英文學。《文學論》中說:「竊思英文學亦如(如漢文學)是。如斯之物舉一輩子學習,亦不後悔。」同年級有正岡子規,受子規《七草集》刺激亦寫漢詩文集《木屑集》,開始使用漱石筆名。《晉書》〈孫楚傳〉提到孫楚向王濟說自己有意暫時隱居,把「枕石漱流」說成「漱石枕流」,王濟指其誤謬,但孫楚硬拗說:「枕流可以洗身,漱石可以磨牙」,漱石以此為筆名取其頑固、怪異之意。
漱時於明治二十三年入東大英文系,由於學業成績優異,第二年免學雜費。明治二十六年為外國人教師J‧M‧狄克遜翻譯鴨長明的《方丈記》,頗受好評,一時有以英文創作文學與英國人一爭短長的野心。
明治二十六年七月大學畢業,擔任東京高師英語教師,從這時候起神經衰弱症嚴重,又有肺結核症狀,為克服心理的不安,到鎌倉圓覺寺參禪。明治二十八年四月,突然辭去高師教職,擔任四國松山中學英語教師。
明治二十九年漱石與貴族院書記官長中根重一長女鏡子結婚。夫婦兩人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妻曾流產、精神歇斯底里,曾有投江自殺之舉。
明治三十三年,漱石三十三歲,以文部省公費派往英國研究英語。九月八日由橫濱出航,十月二十八日抵達倫敦。到明治三十六年一月歸國為止的這段期間,漱石從英文學者轉為作家。因為不久他體悟到,「漢學所謂的文學與英語所謂的文學,到底不是相同定義下可以概括的,是異類的東西。」以往試圖以英語創作和英國人一爭短長的抱負遭到挫折。漱石懷疑研究之意義,加上留學經費不足,家書稀少等因素陷入嚴重的神經衰弱狀況。撰寫《文學論》亦無法緩和症狀,回日本繼小泉八雲之後,任一高教授,東大文科講師時,亦未見改善。
明治三十七年年底,受高濱虛子之邀加入朗讀會「山會」,執創作之筆。翌年一月於雜誌《杜鵑》發表《我是貓》,大獲好評,連續發表《倫敦塔》、《幻影之盾》、《草枕》、《二百十日》等展現旺盛的創作力。
到這時為止,有森田草平、小宮豐隆、鈴木三重吉、寺田寅彥、野上豐一郎、松根東洋城、?元雪鳥等弟子聚集漱石身邊,形成所謂「漱石山脈」,地點在早稻田南町。漱石這時為應以文學為業或繼續擔任教職而猶豫不決。先有讀賣新聞社主筆竹越三叉,記者正宗白鳥邀其入社,但條件談不攏。明治四十年三月,東京朝日新聞社主筆池邊三山來訪,遂決定朝日新聞,於是婉拒東大教授職務,因為朝日新聞社的條件較優渥,生活得以安定。漱石在「入社辭」中說:「如果報社是做買賣的,那麼大學也是買賣。」《虞美人草》之後的作品,皆刊登於朝日新聞。
漱石負責的「朝日文藝欄」,成為反自然主義的大本營。
明治四十二年秋天,受滿州鐵道總裁中村是公之邀旅行滿韓,胃病加遽。翌年入院,八月於伊豆修善寺大吐血,徘徊於生死之間,即所謂「修善寺大病」。漱石拒絕東大文學博士學位,又讓社會震驚。
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十一月二十二日,《明暗》執筆中胃潰瘍惡化,十二月九日於創作中長眠。
三、三浦雅士之見解
三浦雅士《漱石--文豪消失的童年和母愛》主要是針對夏目漱石重要著(創)作的評論。不同於學者的研究論文,三浦氏評論夾雜漱石生平介紹,使讀來不覺枯燥無味。
三浦這本評論集的基調,認為漱石創作的根源是「不被母親喜歡的孩子」,如同有人認為川端康成初期作品的動力出自「孤兒意識」相彷彿。
《少爺》發表於明治四十年,以漱石任教松山中學的體驗為背景,描繪江戶子「少爺」教師富含正義的行為,是漱石初期的作表作。漱石以一星期時間完成,主題是勸善懲惡。這是一般的看法。
三浦指出,《少爺》這個書名,意味著女傭阿清對少爺無償、無私的愛。「少爺」遺傳自雙親的魯莽,從小盡做淘氣事,因此不被父母疼愛。母親病死的兩、三天前,少爺在廚房翻跟斗,肋骨撞到灶角痛得不得了,母親非常生氣,說:「再也不想看到你的臉!」少爺就負氣跑到親戚家。
這種不被人喜歡就走開的情緒表現也出現在任教四國中學時,三浦雅士認為,少爺「懷疑自己是否不被母親所喜愛,卻又對這種懷疑感到內疚,為了消除內疚認為只要做出不被喜愛的證據,就可以將這種懷疑正當化」。三浦認為少爺的性格「複雜又奇怪」與一般認為少爺單純、直性子受人喜愛的看法大異其趣。
三浦認為《我是貓》依然是同樣的主題:「不被母親喜愛的孩子」,只是變化成各種型態不斷重複。具體而言,漱石以譏笑、自殺、瘋狂等和母愛一樣,建立在無法證明的立足點,建構《少爺》的世界。
第三章拒絕上學者的孤獨,三浦談的是漱石受《七草集》刺激而寫下的《木屑集》與留學倫敦時撰寫的《文學論》。
三浦說明漱石進入漢學塾,即二松學舍的心境,以及在那裏研究的課程,諸如《唐詩選》、《孟子》、《史記》、《論語》……等,難怪漱石能寫漢詩文。至於《文學論》,三浦認為那只是「漱石的小說方法論而已。」
漱石先學漢詩文再轉唸英文,三浦認為無論《倫敦塔》或《幻影之盾》、《一夜》都是漢詩的擴大作品;而《草枕》是「漢詩中的漢詩」,瞇著眼睛看世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草枕》的核心所在,正是這種思想。」
至於《虞美人草》,三浦認為寫的是「不為母親所喜愛的孩子的復仇劇」,當然愛與恨常攜手並肩或糾纏不清。至於漱石心目中的永遠女性是誰?儘管眾說紛紜,三浦認為無論是大塚楠緒子,或者嫂嫂登世都是正確的,因為「她們都回歸母親」
《三四郎》、《從今而後》、《門》被稱為漱石初期三部作,「並非描述一個人的生長過程。主人公各有各的境遇,也各有各的性格。」初期三部作的潛在主題,再三重複的是「未察覺被愛之罪」以及「未察覺愛之罪」。三浦雅士對於「未察覺被愛之罪」文中有詳細且深入的剖析與說明;認為《從今而後》最傑出,是「沒有一處細節是不必要」的「完美作品」。
儘管漱石小說中表現技法有所不同,但三浦認為「不被母親喜愛的孩子」這根本主題未曾消失。《過了彼岸》是由︿風呂之後﹀、︿停留所﹀、︿報告﹀、︿下雨日﹀、︿須永的話﹀、︿松本的話﹀六短篇構成的,漱石自認為並未達成當初的「意圖」。三浦詳論《過了彼岸》與《從今而後》之間的關係,並指出六短篇中以〈須永的話〉最為精彩。
《過了彼岸》、《行人》、《心》稱為後期三部作,以《心》最為傑出。全書分為︿老師和我﹀、︿雙親和我﹀、︿老師和遺書﹀三部分,前二部分可說是最後︿老師和遺書﹀的伏筆,重點在這部分。前半(即一、二部分)透過「我」間接描寫老師,與後半的告白體形成對照,一般認為「老師」仿乃木希典大將之殉死,為「明治精神」而自裁,也藉此透露漱石身為明治人的心情。
三浦雅士認為《心》是漱石作品集大成者。但見解與一般不同,仍然沿著「不被母親喜愛的孩子」這條軸線闡釋漱石之《心》。
對於《道草》,三浦雅士雖然以孤獨的角度探究作品中人物的內心世界,但仍未脫離「不為母親喜愛的孩子」的主題。
至於漱石未完成的遺作《明暗》,「把所謂世間、所謂社會生動又精彩地描寫」,三浦仍然認為未脫離上述漱石一貫的主題。
四、結語
文學研究有內在,即作品本身,及外緣,即相關之社會、政治等的研究方法。一般對於漱石作品常從外緣切入,闡明在世界文明進步中,漱石的焦慮與關懷。三浦雅士可說純粹從作品內部剖析,著眼於漱石幼時被送離家,一生與母親只有短暫的五年時光所衍生出來的「不為母親喜歡的孩子」的主題,儘管漱石以不同形式、技法創作多部作品,但始終未脫離這一主題。
名人推薦:貫穿漱石文學的基調 林水福
一、國民作家之美譽
日本近現代作家之中,有「國民作家」之稱的,並不多。有些出自評論者、愛好者主觀的推崇,其實無法「放諸四海而皆準」。
漱石,國民作家的美譽,在日本人心中,可說已成定論。
漱石初期作品《我是貓》、《少爺》、《三四郎》或者到《虞美人草》為止,給人印象是幽默,以老練的筆調鮮明描繪好人或壞蛋,作品中人物有如現實生活周遭人物,易懂,而且情節單純。全體而言可說相當「通俗」,日本人不拘年齡都會閱讀的。就此意義上稱之...
章節試閱
【專文導讀】
貫穿漱石文學的基調 林水福
--我讀漱石--《文豪消失的童年和母愛》
一、國民作家之美譽
日本近現代作家之中,有「國民作家」之稱的,並不多。有些出自評論者、愛好者主觀的推崇,其實無法「放諸四海而皆準」。
漱石,國民作家的美譽,在日本人心中,可說已成定論。
漱石初期作品《我是貓》、《少爺》、《三四郎》或者到《虞美人草》為止,給人印象是幽默,以老練的筆調鮮明描繪好人或壞蛋,作品中人物有如現實生活周遭人物,易懂,而且情節單純。全體而言可說相當「通俗」,日本人不拘年齡都會閱讀的。就此意義上稱之為「國民作家」。
漱石作品常碰觸倫理、正義等問題,就內容而言,作品中的男女關係,常是違反倫理的三角關係,其實已超越了「國民」的界限,對「人」普遍存在的問題深入挖掘。
漱石作品的另一個特色是,將日本近代背負的文明之苦,視為一己之責任,試圖在文學作品中「解決」。換言之,日本國民背負的文明之苦,由一己承擔,就此意義也可以稱為「國民作家」。
二、漱石生平簡介
夏目漱石,一八六七年生於江戶牛?馬場,父夏目直克,母千枝,千枝是直克前妻逝世後再娶的。當時民間迷信申日申刻出生的人,不是大好就是大壞,有可能當強盜,在名字加上金字可改運,而漱石正是庚申日而且是申刻(下午四時左右)出生的,因此命名金之助。
金之助上有五兄二姊,身為老么,但從出生起就不受歡迎,被送到「古物商」(即撿破爛)寄養,有一次姊姊路過看到金之助被丟在破爛堆中,不捨,抱回家,卻惹來父親不悅。
歲時送給新宿「名主」(約相當於今之里長)福原昌之助當養子。漱石在《道草》中說,記憶中養父管理已歇業的妓女戶建築物。養父母非常溺愛,但幼年時期相當孤獨。
明治四年(一八七三),金之助四歲時養父擔任淺草諏訪町的「戶長」(鎮公所行政官員),於是舉家從新宿遷居淺草。養父母常輪流問他:「你父親是誰?」「那你的母親呢?」漱石因此陷入自己真正屬於誰?屬於哪裏的不安。
後來養父母感情不睦,離婚。明治九年,金之助九歲時由生父母家領回。金之助和生母在一起的日子,只有明治九年到十四年母親逝世為止短短的五年。〈玻璃窗中〉說:「母親的名字叫千枝。我至今仍然覺得千枝是令人懷念的詞彙之一。對我而言,那不只是單純的母親的名字,而是其他女人決不可使用的名字。」
回家之後,父親對金之助依然冷淡。金之助親近漢書籍,於《文學論》中言:「余少時好學漢籍,學習期間雖短,漠然從左國史漢得到的文學當如斯之定義。」左國史漢是《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的簡稱。明治十二、三年從東京府第一中學轉到以漢學聞名的二松學舍,目的在於喜好漢文,試圖深究漢學。
那時學校未開設英語課程。金之助為了迎接新時代的來臨,認為英語是必需的。明治十六年,轉到英語成立學舍,翌年進「予備門」。明治二十一年九月進入予備門(預科)後身的第一高等中學本科,決意專攻英文學。《文學論》中說:「竊思英文學亦如(如漢文學)是。如斯之物舉一輩子學習,亦不後悔。」同年級有正岡子規,受子規《七草集》刺激亦寫漢詩文集《木屑集》,開始使用漱石筆名。《晉書》〈孫楚傳〉提到孫楚向王濟說自己有意暫時隱居,把「枕石漱流」說成「漱石枕流」,王濟指其誤謬,但孫楚硬拗說:「枕流可以洗身,漱石可以磨牙」,漱石以此為筆名取其頑固、怪異之意。
漱時於明治二十三年入東大英文系,由於學業成績優異,第二年免學雜費。明治二十六年為外國人教師J‧M‧狄克遜翻譯鴨長明的《方丈記》,頗受好評,一時有以英文創作文學與英國人一爭短長的野心。
明治二十六年七月大學畢業,擔任東京高師英語教師,從這時候起神經衰弱症嚴重,又有肺結核症狀,為克服心理的不安,到鎌倉圓覺寺參禪。明治二十八年四月,突然辭去高師教職,擔任四國松山中學英語教師。
明治二十九年漱石與貴族院書記官長中根重一長女鏡子結婚。夫婦兩人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妻曾流產、精神歇斯底里,曾有投江自殺之舉。
明治三十三年,漱石三十三歲,以文部省公費派往英國研究英語。九月八日由橫濱出航,十月二十八日抵達倫敦。到明治三十六年一月歸國為止的這段期間,漱石從英文學者轉為作家。因為不久他體悟到,「漢學所謂的文學與英語所謂的文學,到底不是相同定義下可以概括的,是異類的東西。」以往試圖以英語創作和英國人一爭短長的抱負遭到挫折。漱石懷疑研究之意義,加上留學經費不足,家書稀少等因素陷入嚴重的神經衰弱狀況。撰寫《文學論》亦無法緩和症狀,回日本繼小泉八雲之後,任一高教授,東大文科講師時,亦未見改善。
明治三十七年年底,受高濱虛子之邀加入朗讀會「山會」,執創作之筆。翌年一月於雜誌《杜鵑》發表《我是貓》,大獲好評,連續發表《倫敦塔》、《幻影之盾》、《草枕》、《二百十日》等展現旺盛的創作力。
到這時為止,有森田草平、小宮豐隆、鈴木三重吉、寺田寅彥、野上豐一郎、松根東洋城、?元雪鳥等弟子聚集漱石身邊,形成所謂「漱石山脈」,地點在早稻田南町。漱石這時為應以文學為業或繼續擔任教職而猶豫不決。先有讀賣新聞社主筆竹越三叉,記者正宗白鳥邀其入社,但條件談不攏。明治四十年三月,東京朝日新聞社主筆池邊三山來訪,遂決定朝日新聞,於是婉拒東大教授職務,因為朝日新聞社的條件較優渥,生活得以安定。漱石在「入社辭」中說:「如果報社是做買賣的,那麼大學也是買賣。」《虞美人草》之後的作品,皆刊登於朝日新聞。
漱石負責的「朝日文藝欄」,成為反自然主義的大本營。
明治四十二年秋天,受滿州鐵道總裁中村是公之邀旅行滿韓,胃病加遽。翌年入院,八月於伊豆修善寺大吐血,徘徊於生死之間,即所謂「修善寺大病」。漱石拒絕東大文學博士學位,又讓社會震驚。
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十一月二十二日,《明暗》執筆中胃潰瘍惡化,十二月九日於創作中長眠。
三、三浦雅士之見解
三浦雅士《漱石--文豪消失的童年和母愛》主要是針對夏目漱石重要著(創)作的評論。不同於學者的研究論文,三浦氏評論夾雜漱石生平介紹,使讀來不覺枯燥無味。
三浦這本評論集的基調,認為漱石創作的根源是「不被母親喜歡的孩子」,如同有人認為川端康成初期作品的動力出自「孤兒意識」相彷彿。
《少爺》發表於明治四十年,以漱石任教松山中學的體驗為背景,描繪江戶子「少爺」教師富含正義的行為,是漱石初期的作表作。漱石以一星期時間完成,主題是勸善懲惡。這是一般的看法。
三浦指出,《少爺》這個書名,意味著女傭阿清對少爺無償、無私的愛。「少爺」遺傳自雙親的魯莽,從小盡做淘氣事,因此不被父母疼愛。母親病死的兩、三天前,少爺在廚房翻跟斗,肋骨撞到灶角痛得不得了,母親非常生氣,說:「再也不想看到你的臉!」少爺就負氣跑到親戚家。
這種不被人喜歡就走開的情緒表現也出現在任教四國中學時,三浦雅士認為,少爺「懷疑自己是否不被母親所喜愛,卻又對這種懷疑感到內疚,為了消除內疚認為只要做出不被喜愛的證據,就可以將這種懷疑正當化」。三浦認為少爺的性格「複雜又奇怪」與一般認為少爺單純、直性子受人喜愛的看法大異其趣。
三浦認為《我是貓》依然是同樣的主題:「不被母親喜愛的孩子」,只是變化成各種型態不斷重複。具體而言,漱石以譏笑、自殺、瘋狂等和母愛一樣,建立在無法證明的立足點,建構《少爺》的世界。
第三章拒絕上學者的孤獨,三浦談的是漱石受《七草集》刺激而寫下的《木屑集》與留學倫敦時撰寫的《文學論》。
三浦說明漱石進入漢學塾,即二松學舍的心境,以及在那裏研究的課程,諸如《唐詩選》、《孟子》、《史記》、《論語》……等,難怪漱石能寫漢詩文。至於《文學論》,三浦認為那只是「漱石的小說方法論而已。」
漱石先學漢詩文再轉唸英文,三浦認為無論《倫敦塔》或《幻影之盾》、《一夜》都是漢詩的擴大作品;而《草枕》是「漢詩中的漢詩」,瞇著眼睛看世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草枕》的核心所在,正是這種思想。」
至於《虞美人草》,三浦認為寫的是「不為母親所喜愛的孩子的復仇劇」,當然愛與恨常攜手並肩或糾纏不清。至於漱石心目中的永遠女性是誰?儘管眾說紛紜,三浦認為無論是大塚楠緒子,或者嫂嫂登世都是正確的,因為「她們都回歸母親」
《三四郎》、《從今而後》、《門》被稱為漱石初期三部作,「並非描述一個人的生長過程。主人公各有各的境遇,也各有各的性格。」初期三部作的潛在主題,再三重複的是「未察覺被愛之罪」以及「未察覺愛之罪」。三浦雅士對於「未察覺被愛之罪」文中有詳細且深入的剖析與說明;認為《從今而後》最傑出,是「沒有一處細節是不必要」的「完美作品」。
儘管漱石小說中表現技法有所不同,但三浦認為「不被母親喜愛的孩子」這根本主題未曾消失。《過了彼岸》是由〈風呂之後〉、〈停留所〉、〈報告〉、〈下雨日〉、〈須永的話〉、〈松本的話〉六短篇構成的,漱石自認為並未達成當初的「意圖」。三浦詳論《過了彼岸》與《從今而後》之間的關係,並指出六短篇中以〈須永的話〉最為精彩。
《過了彼岸》、《行人》、《心》稱為後期三部作,以《心》最為傑出。全書分為〈老師和我〉、〈雙親和我〉、〈老師和遺書〉三部分,前二部分可說是最後〈老師和遺書〉的伏筆,重點在這部分。前半(即一、二部分)透過「我」間接描寫老師,與後半的告白體形成對照,一般認為「老師」仿乃木希典大將之殉死,為「明治精神」而自裁,也藉此透露漱石身為明治人的心情。
三浦雅士認為《心》是漱石作品集大成者。但見解與一般不同,仍然沿著「不被母親喜愛的孩子」這條軸線闡釋漱石之《心》。
對於《道草》,三浦雅士雖然以孤獨的角度探究作品中人物的內心世界,但仍未脫離「不為母親喜愛的孩子」的主題。
至於漱石未完成的遺作《明暗》,「把所謂世間、所謂社會生動又精彩地描寫」,三浦仍然認為未脫離上述漱石一貫的主題。
四、結語
文學研究有內在,即作品本身,及外緣,即相關之社會、政治等的研究方法。一般對於漱石作品常從外緣切入,闡明在世界文明進步中,漱石的焦慮與關懷。三浦雅士可說純粹從作品內部剖析,著眼於漱石幼時被送離家,一生與母親只有短暫的五年時光所衍生出來的「不為母親喜歡的孩子」的主題,儘管漱石以不同形式、技法創作多部作品,但始終未脫離這一主題。
【書摘試閱】
後記
在人類的歷史裡,不被母親所喜愛的孩子並非罕見啊!何以漱石特別要去面對這個問題呢?為何得和這個問題格鬥呢?對於這些問題,社會變化應該是第一個理由,然而不被母親所喜愛孩子的主題,不只是近代文學特有。這個問題,並非單純因近代家族的形成而產生。這種事,譬如民間故事中的繼母、繼子的主題並非罕見,神話中也有不被母親所喜愛孩子的故事廣為流傳於世界各角落,這些都是很明顯的。
當然,不被母親所喜愛孩子的主題,曾經是公共議題,不過從某一階段就被看成私人的問題。譬如家族、親族、部族,在以血緣為基盤的社會裡,所謂被母親喜愛、不被母親喜愛的主題,某種程度上屬於公共議題。若是移到以別種事物為基盤的社會裡,公私的區分法就變成在滑坡上移動。
漱石的小說被廣為閱讀,這種公私的區分法就會被質疑。政治、經濟、社會屬於公共問題,戀愛、結婚、家族屬於私人問題,雖然這是一般人的想法,毋寧說正好相反吧!難道「公」不正好就是「私」?「私」不正好就是「公」嗎?譬如驅使人從事革命、政治、戰爭,未必是公的思想或理論。往往是私人的感情。這種私人的感情,屢屢可以回溯到幼年時期所受的屈辱體驗,大抵是其背後受屈辱的母子關係或戀愛關係,因此產生而潛藏在內心的癖性。
許多的小說和電影都是如此設定,而且令讀者、觀眾感動,這顯示公私逆說,對人來說是一種根源性的東西。甚至令人覺得所謂主體性,難道不就是公私逆說嗎?從徂徠到漱石的這一個文脈上,不是有必然性的展開嗎?在《過了彼岸》中,松本把市藏的乖僻和漱石本身的〈現代日本的開化〉的問題重疊,暗示漱石本身也有如此的想法。對《從今而後》中的代助而言,對三千代的戀情既自然也是天命。
反正,不被母親所喜愛孩子的主題,不可能是私人的問題、個人的問題。為什麼呢?因為每一個孩子都有母親,任何人都是由母親生下來。雖然愛這種感情是很清楚,想讓他人完全接受幾乎是不可能。因此,原理上誰都有可能成為不被母親所喜愛的孩子。懷疑自已是否不被母親所喜愛的孩子的心癖,原理上誰都有可能。因為有可能,在內心深處誰都會受傷害、也會去傷害別人。
漱石是否不被母親所喜愛,只有問漱石本身才知道,可是卻辦不到。把自己的心路歷程誠實寫出來就好,對於自己是多麼不了解自己而感到驚訝!寫下這些的是二十九歲的漱石、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當教授的漱石。總之,這是漱石本身對於漱石一無所知的告白。因此,才會終其一生持續探索。因此,死後眾多的漱石論只有持續探索。總而言之,如同漱石對自己本身不了解般,至今仍是一個謎團。以謎團般地活下去。不只漱石如此而已。任何人都是如此。毋寧說這正是所謂文學的基本構造。
閱讀漱石,最令人驚訝莫過於探索這個謎團之徹底。
漱石逝世於一九一六年、也就是大正五年十二月九日,從那一年元旦開始連載《點頭錄》。《明暗》則是從五月二十六日開始。雖然《點頭錄》的連載很短,卻在《明暗》執筆之前,從這裡我們知道漱石到底在想什麼?就是第一回文章中「又到正月了」。
又到正月了,回顧過去宛如一場夢,不知不覺中已進入這年歲了,真是不可思議!──開頭如此寫著。接著又寫著;過去只是一場夢。不過是一個假象。若是如此,現在不也是假象嗎?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天地所覆蓋的當下卻是千真萬確。對於生命的這兩種看法,毫無矛盾地同時並存,有關超越一般理論的異樣現象,自己現在一點也不打算說明。
作為新年用文章,這有些破例。曾經為這般的文章可以上元旦報紙版面而感動。甚至還認為難道現代文明,只是把人弄得淺薄而已嗎?
現在正是最不可理解的事──十九世紀的某思想家所說。這和漱石所敘述一樣。死者可以看到人,生者可以看到鬼怪──另一位思想家所說,這好像在詮釋漱石所敘述的事。
所謂人,就是一個異樣現象。這是漱石所確信的事。自己這種東西,其實就是一個異樣現象。
小學生輕率就自殺,因為認為縱使自殺,所謂自己的現象依然持續。不只是小學生而已。這是人實際的感覺。認為自己會歸於無,這個思考方式確實是人為的,只有人為才會說出如此賢達的話。
謎團的探索,從《我是貓》到《明暗》,一成未變地持續。所謂我的現象,在結構上屬於永遠。說起來,卻是脫離現實。儘管如此,人還是為現實所束縛。《明暗》正在書寫中,如此的思想正在?石的腦中盤旋吧!
自己是否不被母親所喜愛呢?這小小的懷疑砂礫,雖然傷害母貝,還是成為大顆真珠,吸引讀者、引人深深思索。可以認為?石的教科書就是這如此產生。現在還讓人在思考……不,現在不得不更加深思。
【專文導讀】
貫穿漱石文學的基調 林水福
--我讀漱石--《文豪消失的童年和母愛》
一、國民作家之美譽
日本近現代作家之中,有「國民作家」之稱的,並不多。有些出自評論者、愛好者主觀的推崇,其實無法「放諸四海而皆準」。
漱石,國民作家的美譽,在日本人心中,可說已成定論。
漱石初期作品《我是貓》、《少爺》、《三四郎》或者到《虞美人草》為止,給人印象是幽默,以老練的筆調鮮明描繪好人或壞蛋,作品中人物有如現實生活周遭人物,易懂,而且情節單純。全體而言可說相當...
目錄
第一章 不被母親喜愛的孩子──《少爺》
第二章 棄兒會考慮自殺──《我是貓》
第三章 拒絕上學者的孤獨──《木屑錄》和《文學論》
第四章 處罰母親──《草枕》和《虞美人草》
第五章 逃離母親──《三四郎》《從今而後》《門》
第六章 被母親處罰──《過了彼岸》
第七章 面對面的困難──《行人》和《心》
第八章 孤獨的意義──《道草》
第九章 承認的鬥爭──《明暗》
後 記
第一章 不被母親喜愛的孩子──《少爺》
第二章 棄兒會考慮自殺──《我是貓》
第三章 拒絕上學者的孤獨──《木屑錄》和《文學論》
第四章 處罰母親──《草枕》和《虞美人草》
第五章 逃離母親──《三四郎》《從今而後》《門》
第六章 被母親處罰──《過了彼岸》
第七章 面對面的困難──《行人》和《心》
第八章 孤獨的意義──《道草》
第九章 承認的鬥爭──《明暗》
後 記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