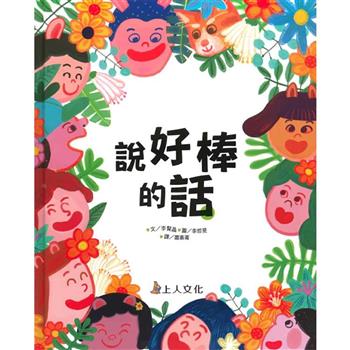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mathilde fasting的圖書 |
 |
$ 199 ~ 450 | 歷史終結之後:法蘭西斯.福山訪談集 (電子書)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Mathilde Fasting) / 譯者:區立遠 出版社:開學文化 出版日期:2022-12-02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初版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歷史終結之後》提供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讓我們得以走進當代一位偉大的政治思想家的心靈。
美國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他一九九二年的暢銷書《歷史終結與最後之人》中主張,自由民主制的優越性標誌了人類政治與意識形態發展的終結。三十年後,隨著民粹的興起以及全球自由民主國家數量的減少,福山重新審視了他的著名論斷。
《歷史終結之後》一書中,編輯馬蒂爾德‧法斯廷對福山進行一系列深度訪談,對當今的自由民主提出了廣泛的分析。本書談到福山在身分認同、生物科技與政治秩序方面的著作,對威權主義的崛起以及民主在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威脅提供了深刻的看法。
福山仔細檢視川普的意外當選、美國社會政治規範的破壞以及中國崛起等議題,巧妙剖析了自由民主的困境,並探討我們如何防止它進一步衰退。他也談到一些個人的事,對他的生活與生涯、他思想的發展以及他最重要的幾本著作做了省思。
作者簡介
馬蒂爾德.法斯廷
馬蒂爾德.法斯廷是挪威最具影響力的智庫之一 Civita的研究員與計畫主持人;她每週固定在 Civita 有一個播客節目。她出版的作品包括《選擇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公民與社群》(The Citizen and the Community)以及《托爾克-阿斯克豪申與挪威的歷史經濟思想:對一位被遺忘的挪威前驅經濟學家的再審視》(Torkel Aschehoug and Norwegian Historical Economic Thought: Reconsidering a Forgotten Norwegian Pioneer Economist)。法斯廷在挪威經濟學院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在奧斯陸大學獲得思想史的學士與碩士學位,並在德國埃爾福特大學(University of Erfurt)獲得經濟思想史的博士學位。
法蘭西斯.福山
法蘭西斯.福山是「弗里曼–斯波格利國際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FSI)的「奧利維爾–諾梅利尼資深研究員」(Olivier Nomellini Senior Fellow),「福特–多爾西國際政策碩士學程」(Ford Dorsey Master's in International Policy)主持人,以及史丹佛大學FSI「民主、經濟發展與法治研究中心」的莫斯巴赫主任(Mosbacher Director)。他在與民主化和國際政治經濟相關的議題上著作甚豐,包括他開創性的著作《歷史終結與最後之人》。他最新的一本書是《身分政治:尊嚴訴求與怨恨政治》。
譯者簡介
區立遠
區立遠,德國杜賓根大學古典文獻學碩士畢,譯有《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卡爾.洛維特)、《山屋憶往》(東尼.賈德)、《歷史終結與最後之人》(法蘭西斯.福山)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