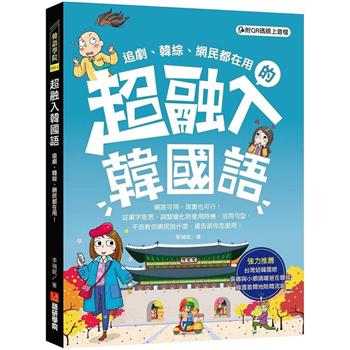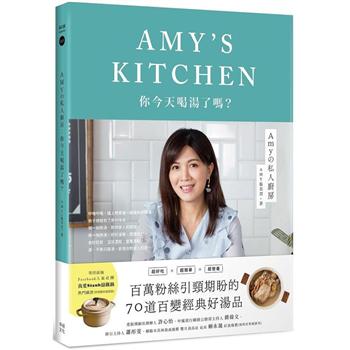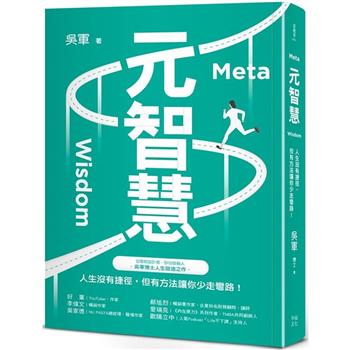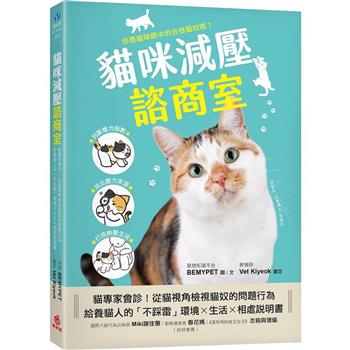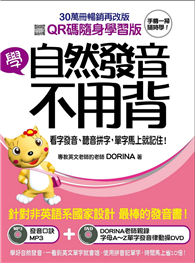★坊間少見的從心理學、精神分析和發展階段探討父子關係的創新著作,令人驚艷。
★結合心理學、心理治療、親子教養、發展歷程等概念,幫助即將成為爸爸或是已經當了爸卻不知道該怎麼養育兒子、一起面對人生的男性,以及成長過程中與父親溝通有困難甚至情感受傷的男性,另一種思考方法與視角。
成為父親,是生命最珍貴的贈禮
解鎖親子關係中的父愛密碼
當一個「夠好的爸爸」
父親是孩子一生的榜樣,更是孩子闖蕩世界的底氣——但「當爸爸」卻是男人一生最大的挑戰之一,因為許多男人不知道怎麼「當爸爸」。
本書作者戴蒙德是鑽研父子關係超過30年的心理治療師,他打破了當前的教養觀,認為「當爸爸」對父子雙方的發展同等重要——不僅父親會形塑兒子,同時也被兒子形塑。
那麼,到底男人要怎麼教養孩子?戴蒙德提出「夠好的父親」概念:一個能夠培養情感、全身心投入孩子內心世界、促進孩子成長的人。他也重新界定「男子氣概」:不是粗線條、暴力、陽剛,而是包含著陰性特質的成熟男性氣質。
書中用生命的階段說明父子關係的變化:青年爸爸是呵護幼兒的「守護者」;中年爸爸引導成年兒子成為男子漢,允許他獨立;最後,老爸接近生命終點,父子關係又再次拉近。
戴蒙德給出詳盡的教養建議,並發現子女是否出色,關鍵正在於父親。
本書讓我們重新認識父親的角色和力量,是新爸爸、老爸爸都要懂、所有媽媽要送給爸爸、每個孩子都要饋贈給父親的書。
作者簡介:
邁克.戴蒙德(Michael J. Diamond)
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博士、臨床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師。他在洛杉磯精神分析研究院暨學會(Los Angeles Institute and Society for Psychoanalytic Studies)完成了精神分析訓練,曾被研究院評為年度傑出精神分析師,目前是該院的訓練分析師和督導。
戴蒙德博士目前居住於洛杉磯並從事臨床實務。他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醫學副教授,並在洛杉磯賴特學院擔任教學和督導,在精神分析理論和技術、性別和男子氣概、養育和父親、創傷、分離和催眠等領域發表了許多文章。他的工作在國際上廣受認可,並因其寫作、教學及分析臨床實務獲得多個獎項。
除本書外,尚著有《美國心靈的裂痕:在危險時代遏制破壞性的民粹主義》(Ruptures in the American Psyche: Containing Destructive Populism in Perilous Times, Phoenix Publishing, 2022)、《男子氣概及其困境:男性心理與成熟男子漢的內在矛盾》(Masculi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Male Psyche and the Inherent Tensions of Maturing Manhood, Routledge, 2021)、《成為一位父親:當代社會、發展理論與臨床視角》(Becoming A Father: Contemporary Social,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s, Springer, 1995;與J. L. Shapiro及M. Greenberg合著)等。
譯者簡介:
孫平
湖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翻譯專業學士、南京師範大學基礎心理學碩士、南京師範大學發展與教育心理學博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2016-2021)。中國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美國精神分析學會(APsA)會員、國際精神分析自體心理學會(IAPSP)會員、美國加州研究型精神分析師。心理諮商專業十五年,長期與中美兩國來訪者進行雙語諮商工作,累積臨床時數超過一萬五千小時。微信公眾號「孫平的Psychology」主理人。與太太育有一兒一女,目前生活和工作於加州洛杉磯。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在孩子(尤其是男孩)的不同人生階段,父親可以從育兒中「賺取的福利」──自身人格的逐漸成長、自身能力的逐漸完善、男子氣概的日漸充盈、對女性的逐漸看見和尊重……一個高度參與孩子成長的父親,不光可以影響和充盈孩子的一生,父親本人也會在獲得父性的過程中,逐漸成長、成熟為一個大寫的男人。——譯者孫平
對母性及母職的討論如汗牛充棟,對父性與父職的研究卻如鳳毛麟角……本書最衝擊讀者之處,在於作者提出父親並不是一個疏遠而陌生的角色,事實上,他終其一生都會同時受到自己父親與兒子的影響,從而將「父親」一詞所代表的價值觀給傳遞下去。——鐘穎
誠摯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王浩威 | 精神科醫師、榮格分析師
洪仲清 | 臨床心理師
賴杞豐 | 家族治療師
鐘穎 | 心理學作家、愛智者書窩版主
名人推薦:在孩子(尤其是男孩)的不同人生階段,父親可以從育兒中「賺取的福利」──自身人格的逐漸成長、自身能力的逐漸完善、男子氣概的日漸充盈、對女性的逐漸看見和尊重……一個高度參與孩子成長的父親,不光可以影響和充盈孩子的一生,父親本人也會在獲得父性的過程中,逐漸成長、成熟為一個大寫的男人。——譯者孫平
對母性及母職的討論如汗牛充棟,對父性與父職的研究卻如鳳毛麟角……本書最衝擊讀者之處,在於作者提出父親並不是一個疏遠而陌生的角色,事實上,他終其一生都會同時受到自己父親與兒子的影響,從而將「父親」一...
章節試閱
引言
直到十七歲那年,我還一直在打青少年棒球聯賽。在那個年齡階段,大多數孩子的父親已經不再來觀賽了,即使他們之前經常定期參與。男生們開始覺得,如果自己這麼大了父親還來學校抛頭露面,那可就太不酷了。我瞭解我的父親,當時他只不過是想坐在露天球場看我打場球,而且還是他曾經點燃了我對棒球的熱愛。但因為我需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所以我當時執意讓他待在家裡,不要過來。如果他在場,我想我沒辦法忍受那種尷尬。似乎他的出現會使我顯得沒那麼成熟。
一天下午,在經歷了一場讓人特別激動的球賽後我回到家中,父親問我打得怎麼樣,我用那種典型的青少年的口氣隨意回了句:「蠻好的。」
「我聽說有一輪你打出二壘安打了。」他說。
「咦,你怎麼知道的?」我突然懷疑地問。父親表現出明顯的慌張,他結結巴巴地說自己剛好碰上教練,但我知道他在撒謊。
「我看了比賽。」他終於承認了。
「怎麼看的?」我窮追不捨地問。那天看臺上只有稀稀疏疏的觀眾,他不可能坐在看臺上。
「呃,靠近左外野手的護欄後面的灌木叢裡,有個缺口來著……」他說。
「待在那裡可以看比賽,但你看不見我。」
聽到他的這個回答時,我嚇呆了。除了震驚以外,對於他的冒犯,我感到憤怒,甚至是暴怒。他怎敢不尊重我的隱私!為什麼窺探我?!當然,我不得不承認,我當時對於他見證了我的出色表現,內心有一部分還是竊喜的。我也感激他採用了一種不讓我知曉的方式見證了這一切,儘管一想到他在我身邊鬼鬼祟祟我就有些不自在。當時的我還真搞不懂為什麼自己會有這麼多強烈的、自相矛盾的情緒,更不用說去應對它們了。於是像大多數遭遇這種情形的青春期男生一樣:我封閉了自己。
直到今天,當我也成了一個青春期男孩的父親時,我才充分理解父親當年內心的矛盾:他必須在尊重我的隱私需要和看我們兩人都深愛的球賽之間做出權衡。我兒子現在也忙著跟我劃定界限:看看什麼要與我分享,什麼不要。所以直到今天,我才可以體會到父親當時的那種矛盾心情。
我現在完全理解我的父親,並且深深地感激他當時所做出的充滿愛的努力:他既尊重了我的隱私,又見證了我的成就,從未缺席。
我只是希望他今日依然健在,這樣我便可以親自向他表達我的理解與感激。我還想問他一個問題:「你是怎麼做到的?」我只是想知道,他怎麼發現並尊重我的需求(做為一個青少年從家庭中分化),同時又理解:我仍然很想做為這個家庭的一分子。還有,他當時是怎麼感知到我既渴望獲得他的欣賞和尊重,又希望保護自己的獨立和隱私的?
今時今日,我不但是一個父親,而且還是一個精神分析師。我廣泛地研究人類的發展,在治療病人的臨床實務中以及見證自己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我仔細觀察過這種發展。我終於認識到:我的父親之所以可以看到我身上那對相互矛盾的需要(既渴望獨立,又希望保持聯結的需要),是因為他自己在做男孩的時候,也經歷過同樣的矛盾。
我可以肯定,就像我自己一樣,這兩種需要也曾存在於他身上,兩種需要雖然有衝突,但是任何一方都不能把另一方抵銷。他識別出自己曾經的內在衝突,這使得他起碼在棒球賽這類事件中,可以做一個承受得住我的憤怒和失望的父親。他知道我當時生他的氣,也知道我排斥他,但他沒有往心裡去,因為沒往心裡去,他就不會想要報復,又或者讓自己沮喪抑鬱,並因此退出我的生活。相反地,他做為一個父親,在我的生命中一直在場。他的這種在場,今時今日又讓我自己做為一個父親在面對兒子的過程中,同樣成為一個不退場的榜樣。
既渴望認同,又渴望分化;既可以回頭理解自己的父親,又可以向前展望去想像自己兒子未來的生活。這一系列複雜的互動和情感的交流,構成了父子關係的核心。
毫無疑問,儘管人類父子之間的情感紐帶會一直存在,但是一般說來,隨著時代的變遷,父親與孩子間的聯結的力量和親密度還是會有增減的。比如曾經在農耕社會,父親通常會高度參與孩子們的生活,充當他們的老師、指導者和引領者。但是父親的參與程度隨著十九世紀中葉工業革命的到來開始逐步下降。一個家庭從農村搬到城市之後,男人就必須離開家去外面工作,結果,他在家庭中的影響力就會下降,以至於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人們已經很少再把父親這個角色,視為一個對孩子健康成長有益的因素。相反地,父親這個詞開始變得有些臭名昭彰,因為他們的缺席,因為他們對孩子的破壞性影響。他們要嘛施暴,要嘛忽視孩子,要嘛過早離世。很多人告訴我,他們已經不再記得還有「成功的父親」這檔子事了。
高效能的父親不僅退出了大眾的想像,實際上他們也從專業文獻中消失了。學術文獻大量記錄的是母親、母性,以及她們對於孩子的影響。社會科學家都不自覺地貶低父親角色,對父親的研究嚴重匱乏。即使在今日,我們每每提起父親,也只是聚焦於一些具體且外在的東西:幫忙換尿布,去開家長會,教孩子踢足球,當然還少不了電影裡爭奪孩子監護權勝利後的場景。與此同時,一些更重要的議題卻乏人問津,如一個男人成為父親,會發生怎樣的改變?一個男人成為父親,會對他的伴侶產生什麼影響?一個男人成為父親,會對這個男人與他自己父親的關係產生什麼影響?父親和兒子,彼此對對方的感覺到底怎樣?一個男人,在成為父親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情緒,如希望和害怕,歡樂與痛苦,到底是怎樣的體驗?直到今日,這些議題大都乏人問津。
每當父親出現在文學或者心理學文獻中的時候,作者總是象徵性地讓他們過個場,並未將他們對兒童發展的實際正面影響當回事。父親的現實參與(父親對孩子的生活能夠產生,並且也確實產生了豐富且深遠的影響)統統都被忽略掉了。這種忽略造成了很多讓人不快的後果。其中之一就是我們的社會極度輕視父親的積極貢獻,從此母親對孩子的發展負全責—只要父
親不壞到極點,孩子的成長就沒他什麼事情了。
所幸,我們輕視或者忽視父親影響力的趨勢,因為下列原因,在二十世紀七○年代後有了改變。隨著女權運動的萌芽和女權理論的發展,社會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女人成群結隊地湧入職場,雙薪家庭開始成為家庭常態以後,男人在育兒方面也不得不變得更為積極,這使得男女之間的性別角色劃分不再那麼僵化。與此同時,產科和兒科的發展也使得父親可以更直接地參與妊娠、接生以及新生兒護理的過程。比如拉梅茲自然生產課程(Lamaze natural childbirth)在這個時期就廣受歡迎,這個課程鼓勵丈夫做妻子的懷孕教練,而且還會訓練他們的助產技能。最後,多虧了行為和心理-生理學觀察技術的進步,研究者得以真正開始考察父親與孩子之間情感連結的重要性。
今天,我們承認父親在兒童養育過程中所扮演的獨特且必要的角色。父親並不單單是幫母親打打下手、做個替補那麼簡單,他和母親的角色本就是高度互補的。他是一個男人這個簡單的事實和他所懷揣的父愛,將對孩子產生一種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會從妻子的懷孕之日開始,一直延續到父親本人過世,甚至延續到孩子過世的那一天。要知道,即使孩子沒有父親,他們也能感受到父親的影響。這是因為他們會根據現實和自己的想像,以及存在於家族和文化中的傳說,來創造一個內在的父親形象,並被這個形象影響一生。
上述所言皆為常識,至少對處理父子關係的專業人士而言是常識。不太為人所知的是:不僅父親會深刻地影響兒子,兒子也會影響父親。這並不意味著父親和女兒之間沒有重要的相互影響,他們有。然而基於生理、文化以及心理上的多重原因,父子關係會顯得尤為錯綜複雜。父子間獨特的情感連結,自然緣於他們兩人都要互相認同彼此的男性身分,也就是說緣於他們生理上的相似性。這種強烈的相互認同(mutual indentification),會使得父與子在彼此生命的歷程中相互影響,表現尤為複雜多樣。
我的研究表明,父子關係的發展會跨越某些特定的發展里程碑—從嬰兒期到學步期,從童年期到青春期,從成年早期到中年,父子間的互動會經曆一些嚴峻的考驗。一方會全方位地影響另一方。但我們需要明白一點:在一段錯綜複雜的父子關係當中,影響總是相互的而非單向的。所以在理想的狀態下,父子二人會一同成長和發展。
根據這種理解,成為父親,做為一個男人生命之中最大的挑戰之一,絕不只是他生活的一個分水嶺事件那麼簡單。在成為父親的過程中,這個男人會影響他兒子的發展,與此同時,他的兒子也會促使自己產生相應的蛻變,這是一個複雜的互動系統。在生命中的任何一個階段,父與子都要各自處理自身的發展議題,但他們的關係又是如此獨特,以至於兩人可以相互促進對方成長,攜手進入下一個發展階段。
在本書中,我自始至終都會探討父親在兒子成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此同時我也會描述在兒子發展的過程中,父親有哪些成長歷程也將被開啟。我將追隨父與子的生命週期,看看他們是怎樣合作的,又是怎樣彼此爭鬥的。為了考察這種特殊的人類關係的複雜性,我將尤其關注父子兩人在各個成長階段,在彼此的影響之下產生的各種內在情緒體驗。
將一個人的生命分成若干階段,難免有武斷之嫌。一個人成長的重要標記和里程碑,如果像清單一樣被列出來,總歸會有侷限。因為這是理論,但人不是理論。每一個活生生的人,其人生軌跡都是獨一無二的。然而,為了開啟父子終生相互影響這個主題,我仍然需要把某些發展階段,以及各階段中父子各自的角色特點進行些許概括。
比如,為了保護嬰幼兒,父親要承擔起一系列新的責任,而且得重新定義何為真正的「男子氣概」(masculinity)。為了把自己的兒子帶入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男人要領會什麼是「他者」(otherness),即認識到他人有與自己不同的存在方式,而這種認識,正是同理心(empathy)的基礎。當男孩需要把父親當作自己的榜樣並學習其行為時,男人則需要及時地發展出父權意識及個人責任感。當男孩開始進入「伊底帕斯階段」(oedipal stage)時,父親要學會面質、涵容,以及更為恰當地表達自己的「困難情緒」,尤其是憤怒、嫉羨(envy)、妒忌(jealousy),以及競爭性。在兒子進入學齡期(上小學的階段),父親則需要發展出教育和指導的能力。青春期男孩的父親則要學會如何「坐雲霄飛車」(學會如何在兒子對自己時而認同,時而貶損的起伏過程中維持自己情緒的穩定),還要學會如何管理自己人格中脆弱的部分。當男孩步入成年早期後,父親要學會「放手」(letting go),要學會在兒子飛速成長的自主性面前,放下自己的權威—即使這會讓自己明顯體驗到失落。做為一個成年男人的父親,他需要學會直面自己的依賴需要,還要想方設法為子孫後代留下一筆可被他們銘記的精神財富。最後,一個父親要學習面對和接納自己的死亡,而這通常也是在年長的兒子的幫助下完成的。
在這段生命歷程中,一個積極養育孩子的父親,通常也會與父母和解,有機會與父母完成一些未解決的事件(unfinished business)。透過成為一個父親,通過持續性地養育孩子,一個男人會經歷情感、心理、品德甚至是身體面貌上的改變。精神科醫師及作家凱爾・普魯特(Kyle Pruett)的研究表明:通常參與度高的父親情感會更加豐沛,頭腦會更加靈活,思想會更加開放,並且身體會更加健康,壽命也會更長。我相信,隨著時代的進步,父親和孩子之間的相互影響會變得越來越明顯,越來越深刻。
做為一個私人執業的心理治療師、伴侶治療師,以及專門研究父子關係的精神分析師,我汲取了自己超過三十年的工作經驗寫就本書。這本書的內容以我的臨床觀察和研究發現為基礎,輔以大量的個案材料。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開始考察男人在成為父親的過程中產生的焦慮、夢境,還有希望。之後數年,我對為人父會如何塑造男人的男子氣概這個主題進行了研究。之後不久,我又致力於理解父親在兒子一生的生命週期中所產生的具體影響;然後反過來,再研究兒子會怎樣影響父親的發展。二○○○年左右,我的研究聚焦於理解父親怎樣幫助兒子塑造靈活且健康的男子氣概,而這種男性身分認同(masculine identity)在一個男人的一生之中又會如何轉變。
我對父子關係的各種形態及其益處的探索,還有我對性別角色的探討(即一個「男人」意味著什麼),基於一種關於「男子氣概」的新視角—-這種視角最近才出現在美國人對性別和性特徵的主流論述當中。之前學術界涉及男性性別的探討往往容易落入兩端:一端視男子氣概為生理所決定,由物種演化傳遞下來,因此是無法改變的;另一端則視男子氣概為社會所建構,由環境和文化所創造,因此是變化無窮的。我的目標是避免執此兩端,取中道而探索,即摒棄非黑即白的思維,採取兼容並蓄的態度。
在美國文化當中,所謂的男子氣概必須要經歷一次又一次的社會檢驗,只有個男兒身可不夠。追本溯源,視男人為男人最重要的標誌就是:他不是個女人。所以做男人,有時不得不變成一場零和遊戲:一個被視為有男子氣概的男人,不得不磨滅自身所有的女性化特徵。鑒於此,本書所認定的男子氣概,則植根於下列理念,即一個真正的男人,需要承認和接納屬於自己的所有面向,這也包括將那些被社會界定為「女性化」的特質視為自己男子氣概的固有組成部分。
需要強調的是,我在這裡並不只是想提出一種「更友善、更溫和」的男子氣概定義。一個男人並不需要在自己身上掛個奶瓶,假裝給寶寶餵奶,來確認自己的女性化特質,但他也不需要在肩上扛一把突擊步槍巡山,或者時不時秀一秀肱二頭肌來證明自己是一家之主。與這些各執一端的視角不同,我認為一個有男子氣概的人,可以接納這樣一個看似矛盾的心理現實──終其一生,他所體驗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特質都會纏結在一起,無法全然分離。
我在本書中的見解來源廣泛,它們來自我做為一個精神分析師和心理治療師對自己病人的傾聽;來自我與其他分析師同事以及相關研究者的交流;來自該領域的主要理論家(如佛洛伊德和溫尼考特等人,也包括現代學者)對於為父之道和男性發展等主題的研究結論;來自我周遭生活中所能觀察到的普通父子的互動,這也包括我在孩子的班級旅行中以及棒球場上與其他父親的對話,這些父親來自不同的社會經濟階層,很多人這輩子都沒進過心理治療師的辦公室。最後,這本書反映了我自己在做兒子、做丈夫以及做父親的過程中,對這些生命角色所產生的寶貴的理解和體驗。
我們對於父子之間獨特聯結的理解仍在發展和演變。我寫這本書,正是希望盡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以推進、普及這些正在被緩慢積累和拓展的知識。同時我也希望激發閱讀這本書的男性讀者,促使他們以一種嚴肅的態度、堅定的決心進入父親這個角色。實際上,為人父是一種召喚,他們需要聽從這種召喚,從而開啟一段全新的內在旅程。他們將與自己的兒子一同開啟這段旅程,最終兩人也將共同成長。在此旅程中,我們終將理解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那句智慧箴言的含義—「是孩子,造就了一個男人」。
引言
直到十七歲那年,我還一直在打青少年棒球聯賽。在那個年齡階段,大多數孩子的父親已經不再來觀賽了,即使他們之前經常定期參與。男生們開始覺得,如果自己這麼大了父親還來學校抛頭露面,那可就太不酷了。我瞭解我的父親,當時他只不過是想坐在露天球場看我打場球,而且還是他曾經點燃了我對棒球的熱愛。但因為我需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所以我當時執意讓他待在家裡,不要過來。如果他在場,我想我沒辦法忍受那種尷尬。似乎他的出現會使我顯得沒那麼成熟。
一天下午,在經歷了一場讓人特別激動的球賽後我回到家中,父親問我打得怎...
推薦序
推薦序一|勇於表達關愛,療癒你內在神聖的國王
鐘穎/心理學作家、愛智者書窩版主
有多少為認同所苦的孩子,可能就有多少同樣困惑的父親。
當工業時代將男人從土地送進工廠,商業時代將男人從工廠送進辦公室時,父子間的隔閡最終演變為嚴肅的父親議題,父不知如何教子,子不知如何敬父。迷惘最終成為了時代的通病。
這個時代病的最大徵兆是無意義感,進一步衍生為職業角色的難尋、親密關係的恐懼、以及激情的國族主義認同。激進的黨派理念與強調對立的政治思想因此成為了替代的父親。
現實中的父親或者當個甩手掌櫃,不管不顧;或者拒絕站在孩子的對立面,只想當孩子的聖誕老公公。無論是何者,這時代的父親都被迫落入管教的兩極。其所反映的,是現代社會對父性或父親角色的認識貧弱,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不僅是民眾,即便是心理專業人員或教養專家,也不見得了解該如何成為一個男人或父親。因為對母性及母職的討論如汗牛充棟,對父性與父職的研究卻如鳳毛麟角。
《爸道:影響一生的父子關係》用四次的「分離—個體化」階段詳細說明了父子關係的變化,強調了父子間「彼此」的形塑作用。我之所以對彼此二字加上引號是要說明,父子間的互動不僅是父親形塑了兒子,兒子也會同時形塑父親。
這本書最衝擊讀者之處,就在於作者邁克.戴蒙德(Michael J. Diamond)讓我們明白,父親並不是一個疏遠而陌生的角色,事實上,他終其一生都會同時受到自己父親與兒子的影響,從而將「父親」一詞所代表的價值觀給傳遞下去。
男人都在綿延不斷的父子關係中滾動修正,我在孩子身上看見自己,又在自己身上看見我的父親,即使父子間的職業傳承早已不如農業時代那樣普遍存在,但父子間的情感依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這份聯繫常因為「男子氣概」而無法說出口,父子間的矛盾糾葛,是諮商室中常見的主題。
雖然深度心理學經常用母性來形容無意識,但建立深度心理學的兩位重要人物,亦即佛洛伊德與榮格,卻都有著強烈的父親情結。他們對無意識現象的熱衷,或許矛盾地反應了他們對個人的父親議題有著必須加以解決的急迫動力。
想要當個「真男人」的願望如此迫切,以至於多數男性在成長的過程中總會囫圇吞棗地緊抓有害的男性文化不放,例如校園幫派、有濃厚厭女情節的網路社群、或者父權社會的陰暗面。
如果不去逞兇鬥狠,不去貶低女性,這些男性就不曉得該如何守護自己的陽剛氣質。這樣的焦慮以及書中所說的「陽具自戀」會反覆出現,直到更整合性的男子氣概能發展起來。而一個願意承認錯誤與局限,肯展現與接納自身保護性特質的父親則是重要的支持角色。
但不是每個兒子都能有這樣的好父親。
好險,改變與療癒自我的機會仍舊存在,人不僅可以透過學習而成長,也不需要很完美才能成為好父母。因為孩子會以其特有的方式療癒和教育父親,但前提是做為父親的我們願意被眼前的孩子療癒和教育。
在男人由兒子變成一位父親的過程中,他將經歷一系列階段的變化,從孩子成為英雄,從英雄變成凡夫,如果能熬過這段被稱為「中年之路」的日子,就有機會由凡夫成為智慧老人。
在這段旅程中,兒子會成為父親的嚮導。你陪伴他成長,他陪伴你走向無常。而後你會透過這一生的智慧留給他最後一項禮物,那就是,從容不迫地面對死亡。
我跟許多男性一樣,並沒有一位理想父親。但我們很幸運,可以透過這本書自我教育,看見自己受傷的父性。我會把它推薦給在父子議題中掙扎的每個人,因為本書是男人療癒內在神聖國王最具啟發性的作品。
希望每個父親都能勇於對自己的兒子和他人提供關愛,如作者所言,因為你的示範將使他無須激烈地捍衛自己的男子氣概。
願每個在成長中備感困惑的男性都能因此成為一個成熟的男人。
推薦序二|孩子就是鏡子,可以照見父親
曾奇峰/心理治療師、精神分析醫師
甲骨文中的「父」字— ,是右手持棒的形狀。《說文解字》解釋為「父,矩也,家長率教者。從又舉杖」,意思是父親即規矩,可以手持棒子對子女實施教戒。古人造字,當真是全身心投入,用極簡的筆劃就呈現了父親的主要功能,數千年之後仍令人膜拜不已。
這還只是「父」字立意的表面意思。精神分析更在乎的是潛在的內容:持棒是為「舉」,表示棒子是懸空的,沒有落下;如果落下,那就是「擊」或者「打」了。一個「父親」不管以什麼理由打孩子,都是在以向孩子洩憤的方式掩蓋自己的無能──那個棒子本來是應該落在他自己身上的。時光流逝,文明也在長大。在這個已不是造字而是造AI的時代,我們知道了更多的父親的功能,以及如何才能做一個好的父親。在眾多的標準中,以下三點值得被特別關注:
第一,好父親能夠看見並接納自己內在未長大的小男孩,所以他不會通過巨大的外在成就來掩蓋小男孩的弱小和無助。在他跟孩子在一起的時候,他不害怕孩子氣的玩耍會動搖他不穩定的所謂男子漢氣概。而缺席孩子成長過程的父親就恰好相反:他們需要太多的金錢、地位和榮耀等,來彌補自己人格的發育不足。在這個意義上,孩子就是鏡子,可以照見父親人格的形狀和成熟度。
第二,好父親掙脫了「純爺們」的咒語,這個咒語暗示了一種絕不存在的「物種」,即只有陽性特徵而沒有絲毫陰性特徵的人類個體。很多被詛咒的男性,用酗酒、說髒話甚至鬥毆的方式來呈現「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而更加隱蔽的方式是,對自己的溫情視而不見,賦予健康的愛以母性的特徵而加以排斥。殊不知,真正健康而美麗的人格,一定是雌雄同體的,這個世界上最美的藝術作品,莫過於英氣逼人的母親和溫情脈脈的父親了。
第三,好父親整合了成為自己和成為父親的衝突。這在哲學上是合理的。以主體間 哲學為基礎的精神分析理論和實踐證明,當一個人成為他自己的時候,就自動具有共情他人的能力,即主體性包含客體性。所以一個男人充分成為他自己的同時,也成了一個好的父親。我們因此不會被愛撕裂,這是造物主對人類的最大恩賜,需要永遠銘記和感恩。
那些「民間偏方」式的關於父親的說法,都需要被與時俱進的洞見重新審視。例如,父愛如山。這是一個比喻。作為文學描述,用比喻無可厚非,但是,如果用於描述父親的功能這樣抽象的物件,比喻的模糊性和非完全對稱性就會有大問題。父愛如山想表達的是這種愛的厚重與穩定,但也可以被意識與潛意識識別為對父子或父女雙方的重負。我不知道,有多少父親因為無法給予如山父愛而逃避,以及有多少子女同樣因為如山父愛而受傷。父愛可以是輕盈的,像漫天飛舞、香氣襲人的花瓣雨,或者餐桌邊一個輕描淡寫卻意味深長的玩笑,或者山崩地裂時真假莫「辨」的淡定從容。我這裡也用了比喻,但願兩個比喻如正反物質相遇一樣走向湮滅,從此為人之父不再沉重。
還有「嚴父慈母」的刻板說法。嚴肅是對內心深處的輕佻、戲謔甚至色情的掩飾。或者說,當一個人無力把控自己豐富而激越的情感時,他就會選擇嚴肅,以不變壓制萬變。從關係上來說,嚴肅的父親幾乎肯定地在潛意識層面跟子女邊界不清,嚴肅是他在表面上採取的消除融合焦慮的措施。如果說抑鬱的母親是「無臉」(faceless),那麼嚴父就有一張恐怖之臉,可能變成子女一生無法驅散的噩夢。相信所有在臨床一線工作的心理諮詢師都會認為,這不是過於誇張的說法。
再要說到責任。當做為父親的責任被過多強調的時候,愛就被淡化了。這是用低級的精神內容替代了更高級的。愛有無限寬廣的疆域,它涵蓋了責任。我們甚至可以說,愛的能力不足的時候,才用責任來補充。太多的責任感也會破壞做父親的天然樂趣,使父親成了一種職業或勞役。沒有人願意看到,父親對自己好只是在盡責而已,因為責任多少有一點強迫與無奈,而愛是全然的自願,還有著從心底裡溢出的輕鬆與歡喜。
在好父親的標準中,可以再加上一條,即願意變得不一樣的父親就是好父親,因為這表示他的人格具有極其珍貴的特徵──靈活性。我會認為,讀著這本書的那個你,已經開放了自己的心門,願意讓跟以前不一樣的風雨吹進來,此時此地,你就是這樣的好父親了。
本書的譯者孫平博士,是我認識多年的朋友。他是受到了非常好的專業訓練的年輕精神分析師。我現在的生活樂趣之一,就是看孫平的微信朋友圈,絕大部分內容是他帶著兩個孩子有時優雅有時瘋狂地玩耍,沒有「舉而教之」。我知道我是在鑒賞一個可以垂范的父親,因為,套用《金剛經》的句型,他陪玩的時候不像是個好父親,所以是個好父親。
序寫到這裡,一個疑問在心中升起:一個男人是在有了孩子才成為父親的,這就意味著父親是孩子「製造」的,那到底誰是誰的父親呢?
2023年5月30日
於武漢東湖
譯序|成為一個不退場的父親
孫平/本書譯者
於我而言,這是一本奇書。
雖然我個人本科學習翻譯專業,但我其實並不喜歡做筆譯。筆譯的過程枯燥、漫長且不能過多自主創造,對我而言曾是一種不大不小的折磨。比起口譯的那種即時性、現場感,筆譯的過程多少有些孤寂。
但我依然記得六年前拿起這本書開始閱讀時的那份激動和暢快。當時我的兒子剛剛降生,而我做為一個新手父親,從裡到外則充滿了無所適從。毫不誇張地說,正是邁克的這本書,讓當時的我獲得了一種穩定感和一份確信。
因為全書想表達的一個中心意旨在於:一個高度參與孩子成長的父親,不光可以影響和充盈孩子的一生,這個父親本人,也會在獲得父性的過程中,逐漸成長、成熟為一個大寫的男人。
這歸根結底是一次父親同孩子的相互成全,彼此成長。
但是,在十五年的心理諮詢師生涯中,我也見證過太多的父親缺席和不稱職。在中國執業的那九年時間裡,我逐漸熟稔了「偽單親育兒」這個詞;在美國執業的這六年裡,我看到了太多美國孩子,尤其是少數族裔的孩子,缺少並渴望著一個父親。如果說中美兩國之間有一個最相似的家庭結構性問題,那可能就是父親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肉身抑或情感缺席問題。
我依然記得,曾經有一位拉丁裔的青少年男孩,坐在我的諮詢室裡,看似輕描淡寫地告訴我他對自己親生父親的失望──父親和母親離婚後,幾乎很少來探望;而他一旦出現,就會情緒崩潰,哭訴自己移民美國後的生活不易,壓力太大,以至於他自己也覺得對不起孩子,因此父親在兒子面前哭泣。
這位來訪者總結道:「你知道,我爸爸在我面前,比我更像一個孩子。」我想,在中國,這位父親應該可以被稱為「巨嬰」。
我們當然可以諷刺、批判,乃至鞭撻這些自己都沒有長大,因此根本為孩子提供不了父親職能的「巨嬰」男性。但在我的臨床經驗中,我也發現,在這些男性的成長史中,幾乎從來沒有人好好地教過他們,鼓勵且看見過他們的成長。更讓我震撼的是,多少「巨嬰」,他們自己的父親也是缺席,或者是失功能的存在。
因此缺席的父性,真的會代代相傳。導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內心懷揣著似乎怎麼也填不滿的「父親饑渴」(father hunger)。這些孩子哪怕長大以後,也會急切地希望有「師父」、「貴人」、「前輩」來帶領、來指導,甚至保護自己,但又在一次一次的理想化破滅中,感到對男性權威的失望。
讀了這本書以後,你會發現:這些被守護、被指導、被陪伴的需要,幾乎全都是重要的父性職能──在孩子成長的關鍵期,這些職能不入場,那麼有些孩子終其一生都會變著戲法兒地去補償,去追尋,哪怕讓自己翻來覆去,遍體鱗傷。
所以我發心要翻譯這本書,因為我知道這是一個極重要的議題。
這本書不但讓我在一定程度上學會了做一個父親,更重要的是,它也讓我明白了在孩子(尤其是男孩)的不同人生階段,一個父親自己可以從育兒中「賺取的福利」──自身人格的逐漸成長、自身能力的逐漸完善、男子氣概的日漸充盈、對女性的逐漸看見和尊重……。
長期以來,父親育兒被蒙上了一層義務感和責任性。實際上,學習成為一個父親,獲得邁克所說的「父性」(fatherhood)的過程,是一個男人在與孩子玩耍、學習、交流、相互欣賞乃至崇拜的過程中,不斷修通自身,讓自己更有主觀幸福感、充實感且獲得自身生命意義的過程。
你若想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男人,那麼先把孩子頂在自己的肩膀上。
另外一個非常值得一說的點是:這本書裡所說的「男子氣概」,是一種整合了女性化特徵的男性氣質。一個男人,要想成為一個不退場的父親,一個大寫的男人,那麼他或多或少要看見、整合、接納那些傳統意義上被視為女性特質的品質:連結、愛、共情、悲憫……。
整合這些特質會讓男人成為一個非常在場的父親,也會讓男人看見且尊重女性(尤其是自己的伴侶),還能讓這個男人充滿著因愛和悲憫而自然生成的堅毅性和守護性。我們的力量不光來自義務和責任,它更應來自由內而外真實的愛。
這本書的作者邁克・戴蒙德與我亦師亦友。在翻譯的過程中,我不斷地與他溝通,向其請教,請其澄清。雖然新冠疫情期間,我們兩家哪怕只相隔四十分鐘車程,也只能苦於在網上相見,但每一次相見我都收穫極豐。
就在一週前,我們終於在洛杉磯的疫情緩和下來後,第一次線下見了面。我把我的妻子、兒女全都帶去拜訪了他和他太太。我的妻子第一次見邁克,她告訴我對他的印象──「第一次見到一個男性,帶著有如女性般的溫和」。我當時心裡想著,但沒有告訴妻子的是,其實這個領域裡很多的高手,都有著雌雄同體的特質。
其實能夠走到寫譯者序這一步,我最想說「謝謝」的,是我的妻子。她直接翻譯了這本書的兩個章節,但她認為這是在我成為父親的路途上很重要的一本書,因此堅持要求不署名。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最最愉悅的體驗,就是在小咖啡館裡,和妻子兩人一同商量如何翻譯才能做到「信達雅」,如何遣詞造句才能呈現出我們深愛的中文的美,但又不失作者本意之過程。我們一起完成了這本書的翻譯。沒有她,筆譯會像我開頭說的那樣,是一個枯燥且孤寂的過程。但實際上,這個過程愉悅、辛苦,且一直被陪伴著。
最後,我想用自己曾在公眾號裡寫過的一段話,來為這篇譯者序結尾。我知道哪怕不可能全然如願,也願天下人都有一個足夠好的父親,或者有一個哪怕不是父親卻也能懂你、愛你、守護你的人:「所以父親們,『活下來,活下去』(be alive and stay alive),在孩子的童年,不死亡,不退場,熬過生活的艱辛,熬過妻子從對你向對孩子的情感轉移,熬過孩子對你的親近和依附,熬過他們對你的理想化,熬過他們的憤怒,熬過他們的失望,熬過他們把你一會兒視為神和一會兒視為蟲的戲劇性起伏,最終在他們心中成為一個普通的卻深愛著他們的老男人。
你還站在那裡,你還堅韌地存在著, because you are a FATHER。」
2022年10月13日
於加州洛杉磯
推薦序一|勇於表達關愛,療癒你內在神聖的國王
鐘穎/心理學作家、愛智者書窩版主
有多少為認同所苦的孩子,可能就有多少同樣困惑的父親。
當工業時代將男人從土地送進工廠,商業時代將男人從工廠送進辦公室時,父子間的隔閡最終演變為嚴肅的父親議題,父不知如何教子,子不知如何敬父。迷惘最終成為了時代的通病。
這個時代病的最大徵兆是無意義感,進一步衍生為職業角色的難尋、親密關係的恐懼、以及激情的國族主義認同。激進的黨派理念與強調對立的政治思想因此成為了替代的父親。
現實中的父親或者當個甩手掌櫃,不管...
目錄
推薦序一︱勇於表達關愛,療癒你內在神聖的國王/鐘穎
推薦序二︱孩子就是鏡子,可以照見父親/曾奇峰
譯序|成為一個不退場的父親/孫平
引言
第1章 積極準備:將為人父
第2章 從出生到嬰兒期:一個父親的誕生
第3章 學步期:父親把孩子帶往世間
第4章 童年早期:父親把伊底帕斯階段的男孩領進男人的世界
第5章 童年中期:鼓勵孩子擁有掌控力、勝任力以及驕傲感
第6章 青春期:從英雄到狗熊
第7章 成年早期:在場邊指導
第8章 成年中期:男人對男人
第9章 老年期:父子角色反轉
第10章 結語:生命的弧線
致謝
註釋
推薦序一︱勇於表達關愛,療癒你內在神聖的國王/鐘穎
推薦序二︱孩子就是鏡子,可以照見父親/曾奇峰
譯序|成為一個不退場的父親/孫平
引言
第1章 積極準備:將為人父
第2章 從出生到嬰兒期:一個父親的誕生
第3章 學步期:父親把孩子帶往世間
第4章 童年早期:父親把伊底帕斯階段的男孩領進男人的世界
第5章 童年中期:鼓勵孩子擁有掌控力、勝任力以及驕傲感
第6章 青春期:從英雄到狗熊
第7章 成年早期:在場邊指導
第8章 成年中期:男人對男人
第9章 老年期:父子角色反轉
第10章 結語:生命的弧線
致謝
...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