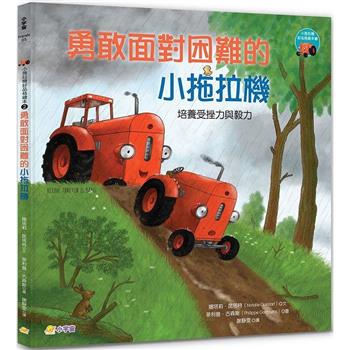一個橫跨大西洋,關於參戰的父親和留在家鄉的兒子之間的故事。
戰爭場面逼真駭人,人物角色性格鮮明。
戰爭場面逼真駭人,人物角色性格鮮明。
「我們不是在那座山嶺揚名立萬,就是粉身碎骨。」──《伊里亞德》
當安格斯的大舅子──他妻子的哥哥──在前線失蹤時,安格斯決定自己也上戰場,以便找回情同手足的艾賓。投筆從戎的時候,安格斯以為自己可以待在倫敦,也就是在後方,發揮他的藝術長才,擔任製圖員就好,未料,他卻被編進永遠缺員的步兵團,手上拿的不再是畫出生命的粉彩筆,而是結束生命的手槍。
同時,他才13歲的兒子賽門.彼德在家鄉的日子也很難捱,他挺身捍衛德國籍的本地學校老師,因為這個小漁村的眾人都被悲傷所撕裂了。或是,不得不拋開過往,開創新生活,正如安格斯的妻子本來是生性浪漫的小婦人,但當家中的男人缺席時,她一肩扛起家族事業,並且做得有聲有色。
以如史詩般的宏偉,如畫般的優美筆觸,P. S. 達菲揮灑了一個關於一次大戰的故事,關於那些永遠被改變的生命,不管是上戰場的,或留在家鄉的,他們的生命從此都不一樣了。
也許上帝之所以安排這個舞臺,只為了成就這一幕戲──好提醒我們,在最黑的暗夜裡,光明仍然存在。
書評
多虧達菲建構的周全細節,兩組故事都躍然紙上──再怎麼微不足道的角色都有鮮明的性格;情節緊扣著刻畫入微的捕魚生活和壕溝戰爭;她耐心地扶植角色陣容,造就了一部出奇精彩的小說。此外,在航運與戰場上命運未卜的未知疆界,跟角色們摸索走過衝突、失落、變局、重建彼此情感並在最後拾回自我的心路歷程,恰恰形成深刻的隱喻。──《書單》重點評論
達菲令人讚嘆的第一部小說將戰爭場面寫得逼真駭人,以周詳的細節,描寫緊密的袍澤情誼以及纏著他們不放的回憶。總結一句話……歷史小說愛好者及戰爭故事迷絕不容錯過;高度推薦。──《圖書館雜誌》重點評論
達菲優美地呈現自然的地貌及情感的風景,手法新穎,鮮活地披露戰爭轉變一個人的威力。細膩的人物及精心設計(但照樣出人意表)的情境使這部小說成為來勢洶洶的出道作品。──《出版人週刊》
達菲……了解人類行為的細微處,以及歷史上較大的打擊對社會留下的印記。在《無人地帶的製圖師》中,她把這些複雜的線索都編成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華盛頓郵報》,Frances Ita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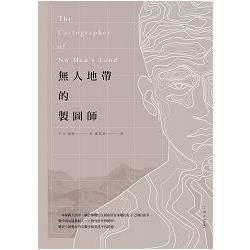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