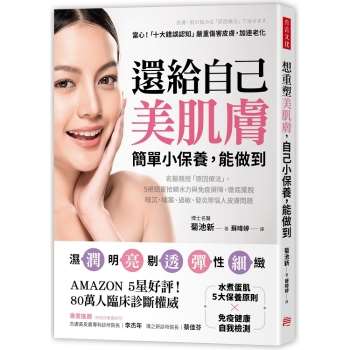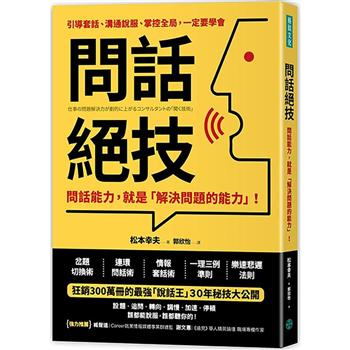自序
恭喜你得了諾貝爾獎!
杜赫堤
我們還住在田納西州的曼菲斯時,某個涼爽10月天的清晨四點二十分,電話鈴突然響起。我太太潘妮接起電話,心想可能是遠在澳洲的年邁父母出問題了。但是話筒傳來的不是澳洲腔。一聽到對方說:「我是諾貝爾基金會的林格茲......」潘妮就把話筒轉給我說:「你的電話。」
遠在瑞典那端的林格茲告訴我,我將與瑞士籍的友人兼同事辛克納吉(Rolf M. Zinkernagel, 1944-),共同獲得1996年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獎原因是我倆在二十多年前得到的一項發現。他也警告我說,只能給我們十分鐘通知家人,之後他就要對外公布得獎名單了。同時他還很輕描淡寫的補上一句,我們家的電話線將會變得很忙碌。就我記憶所及,當時我們真是有點兒呆住了。
我早就曉得自己有可能得到諾貝爾獎,不過這類謠言傳了好幾年,一直到不久之前我都不太在意。得獎的前一年,辛克納吉和我共同獲得拉斯卡基礎科學獎,那是美國的一項科學大獎,通常是未來諾貝爾獎的風向球。有些同事甚至賭我有百分之三十的機率會去斯德哥爾摩,但我沒有太興奮。一方面是自我防衛心理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深信,來自澳洲鄉下的男孩不可能贏得諾貝爾獎。
然而就在那天早晨,再也沒有什麼好懷疑的了。掛上那通電話後不到十五分鐘,我們果然接到了一堆來電,包括來自路透社、比利時,甚至哥倫比亞波哥大的談話性節目以及《雪梨晨鋒報》等等。通話紀錄顯示,我們在清晨4:27打出一通電話,接下來直到5:32才又打出了另一通電話。這顯然不是一個正常的週一早晨。事實上,我們往後的生活再也沒有回歸正常。
鄉下孩子意想不到的人生
當然,每個人對「正常」的定義不同。從小生長在亞熱帶城市布里斯本的我,可能根本就不會把在各大洲跑來跑去,多半時間都泡在實驗室的科學生涯,視為正常。二十世紀中葉,我在昆士蘭度過的童年相當平靜,沒有什麼知性活動。對於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我所知不多,而且也沒有太多資訊可取得。現在回頭看,那種生活真的不像能把人送進高層次的科學發現行列。
我生長在奧克斯利郊外的勞工階級社區,當地中小學生有半數在念完八年級之後就離校,到當地的「培根工廠」(也就是豬隻屠宰場),或水泥工廠、造磚廠做工,要不就當學徒。我雖然是滿聰明的小孩,卻感覺學校歲月很漫長;老覺得無聊,也表現不佳。更糟的是,我天生瘦弱,運動協調不佳,而且幾乎比班上所有人都小了足足一歲。不管怎麼努力,在任何競技運動中,只要有我加入的那一隊,就會遭我拖累。
十三歲進高中後,情況終於改善許多。那是一所全新的高中,剛剛成立,因此沒有舊生立下的規矩,沒有了不起的圖書館,也沒有學生社團。但是有一群大學畢業的老師,致力獻身於國民教育,是他們解救了我。我進入升學班,打下扎實的物理、化學與數學基礎,同時也培養出對歷史、經典名著以及英文劇作的愛好。我第一次接觸外國文化,就是在高中的法文課。雖然現在我的法文說得零零落落,閱讀能力也不太好,但能浸淫在法國歷史與文化中,令人大開眼界。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我當選了法國醫學科學院(French Academy of Medicine)的海外院士,為此我深以為榮。
再回來談談當年的布里斯本,它是相當孤立的偏遠小鎮,位在一個幾乎沒有人會注意的國家裡。我年輕時候對世界的了解多半來自電影和閱讀──不過,我的歷史課本裡對美國的描述只有一小章,名稱是「英王喬治三世以及美洲殖民地的喪失」。因此,我對美國歷史觀既是以英國觀點出發,一方面也受到約翰.韋恩的影響。這種情況一直沒變,1956年,也就是我上大學的前一年,澳洲開始有電視,但只是提供了更多西部片以及澳洲的運動節目。電視並沒有讓我們更了解我們的近鄰:我們對於亞洲這個北邊的鄰居所知不多,僅局限在各國在二次大戰以及歐洲殖民時的經歷。
我的未來以及可能要走的路,跟我的家庭背景沒什麼相干。我的父母雙雙在十五歲時輟學,和許多與他們同齡的人一樣,只受過有限的正規教育,能說文法正確的英文,也能寫出通順的信。我母親繼續學習成為鋼琴老師,因此家裡充滿了德布西、蕭邦及莫札特的樂聲。我父親曾經受過好幾種在職訓練,他剛開始是電話技工,後來成為電話公司的管理階層。他非常勤於閱讀,幾乎什麼書都讀。然而,他們還是不了解高等教育。
事實上,我們那個地方除了醫生和牙醫之外,鮮少有人拿過大學文憑;也沒有什麼人可以提供職業生涯的建議。奧克斯利有一堆裝著護牆板、架高的屋子,瀰漫一股半城市、半鄉下的調調,是布里斯本周邊諸多「搖搖欲墜的小鎮」之一。
我有兩位朋友住在鄰近較富裕的市郊,他們的父親都是專業人士,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去向他們父親討教前程與教育問題。另外,我還有一個大我十三歲的堂兄雷夫(Ralph Doherty),他住在這個幅員廣大的城市的另一端,人非常聰明,課業成績傲人。他是我們家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以極為傑出的成績自昆士蘭大學醫學院畢業,後來從事熱帶公共衛生及傳染病研究,而當時正要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我模模糊糊知道一些關於他的事蹟,但是不記得曾經和他認真討論過科學議題。此外,大家也公認雷夫實在太聰明了,是沒有人學得來的。
進入高中後,我對於將來想做什麼,沒什麼清楚的概念,我確實考慮過一個可能性,就是去布里斯本的當地報社《信使郵報》擔任實習記者。
我非常喜歡看書。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的作品,讓我接觸到理性的年代。同時,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小說,像是《迦薩盲人》和《針鋒相對》,把他那個時代(1920及1930年代)的科學議題,寫入他所處的英國上流社會裡各色人物的生活中,也讓我接觸到另一種文化:尋求啟發以及講求證據的科學研究世界。
譬如說,赫胥黎運用當時的發生生物學思維,鋪陳出一些情節,來探討激情與心靈生活之間的張力。十六、七歲的孩子,怎會對激情不感興趣?
我在學校沒念過生物學,但卻覺得從事某些生物學領域的研究,似乎很有意思(我懷疑,男孩沒能上生物學,和現在宗教界保守派人士反對性教育的理由一樣)。要怎樣才能踏上這條路?我不想讀醫,因為就我當時的認知,大部分的醫生一輩子都要跟病人或是神經質的人打交道。那種生活在我看來沒多大意思。
受美女召喚一腳踏入獸醫學
參加昆士蘭大學獸醫學系所舉辦的「開放參觀日」,改變了我的一生。當時昆士蘭大學是紐澳地區唯二兩家有獸醫系的學校。一看到胚胎學、解剖學和病理學的展示,再看到看顧展示攤的那名懶洋洋、不停抽菸、年輕又性感的實驗室女技術員,我的興致馬上就來了。在那個炎熱的布里斯本夏日,她除了一件白色實驗袍之外,顯然沒穿太多其他衣物。這名「熟女」(她那時起碼有二十二歲了)一點都不像電影裡,緊裹著白袍的科學怪人博士。
即便是四周陳列著生病的器官,以及瀰漫在空氣中的熱臘與福馬林怪味,都很令人興奮。這些和我十六年生命裡接觸過的東西,完全不一樣。它看起來很真實,而且最重要的是,看起來很有趣,而且行得通。從那時候起,我就迷上了病理學。
病理學顯然很能讓青少年興奮。那些陰森森的電視影集裡,充滿了浮屍、切骨頭的電鋸,以及成天披著白色塑膠罩袍、忙著將組織切割成小塊裝進瓶子裡的頑固主角,常常讓青少年看了之後便立志研讀法醫學。即使到現在,我還保有當年對疾病和死亡的著迷:沒錯,許多富有創意的研究科學家始終像長不大的青少年。「疾病偵探」遊戲能夠不斷帶來驚喜,而且一點都不無聊。
醫學、牙醫學和獸醫學在美國都是學士後課程,但是澳洲學制和英國一樣(至少當時如此),高中畢業就可以攻讀這類專業科系。要是我能先進入美國四年制大學的文學院,現在我可能更有學問,而且還會變成歷史學家。即使後來我成為科學家,還是習慣從歷史角度去從頭解釋起,而且我對歷史和政治的著迷,始終不減。
我不想只醫小動物,我要用所學幫助更多國家
我十七歲進入獸醫系,五年後,在1962年12月的一個炎炎夏日畢業。又過了整整三十四年後,也就是1996年12月,發覺自己竟然來到蕭瑟寒冷的斯德哥爾摩,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諾貝爾獎。
是什麼將我從少不更事的獸醫系學生,帶向免疫學,帶向這種尋求發現的科學,而且這發現的結果偶爾還會讓人得獎」?想當年,我和其他同學並沒有太多差別,但其中有一項差別在於,打從一開始,我就立志要當研究科學家。我心中的利他主義思想令我相信,改善家畜、家禽的健康,對開發中國家太重要了,值得投入。因此我畢業後,沒有走臨床獸醫,而是去研究牛、豬、雞、羊的傳染病,先是在昆士蘭,後來又到蘇格蘭並在那兒完成博士論文,主題是由蜱所媒介的羊隻病毒性腦炎跳躍病。
完成愛丁堡的研究後,我的長程目標是進入墨爾本的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擔任獸醫研究員,那是大型的國家級應用科學研究機構。但是我得先前往坎培拉澳洲國家大學的約翰柯廷醫學研究院(John Curtin School of Medical Research)學習細胞免疫,才能更了解宿主對病毒的反應,而當時我原以為這安排只是暫時性的。
於是,1972年我開始在實驗室小鼠身上從事病毒感染實驗,而且生平首次接觸到有活力、以追求知識為導向的基礎醫學研究環境。我的科學之旅接下來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稍後會詳述。但不用說,從那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返回獸醫學的世界了。
此後我分別在美國和澳洲做過研究,但是讓我贏得諾貝爾獎的發現,是在坎培拉完成的,而其中的知識架構是辛克納吉和我,在1973到1975年間,為了解釋之前那些結果所發展出來的。不出幾年,我們都成為免疫學界公認的重要人物,也一直保持這種地位。
當然,獲得諾貝爾獎後,名利又給推到截然不同的層次。剛開始,全球媒體的強烈關注,在瑞典頒獎那週後沒多久就消失了,但是現在我明白,我們受到的肯定,持續的時間遠比媒體熱長得多,事實上,這份肯定持續了一輩子。「諾貝爾獎得主」是終生的職銜。當然,名聲的持久,跟獎項的地位與得主本身的成就都息息相關。
當年那個心思單純的奧克利斯男孩,要是能偷窺一眼水晶球,看到自己多年後在斯德哥爾摩,從大飯店窗口眺望對面的瑞典皇宮,不知會做何感想?要是有人預先告訴他,未來他將擁有享譽國際的事業,並獲頒全世界最尊榮的大獎,又會怎樣?我其實不確定當時的我是否聽過諾貝爾獎,是否知道有哪些澳洲同胞得過這個獎。贏得諾貝爾獎並不是我立定的志向,而且就我來說,實在是很不可能的結果。怎麼會是我呢?
對於這個獎項,我個人的看法和許多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一樣:我受到肯定,是因為我做出了突破性的發現,能改變盛行的觀點,也就是造成哲學家孔恩所謂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我們做了一些滿簡單的實驗,然後對結果提出當時算是革命性的詮釋。隨後,許多傑出科學家利用其他領域的先進科技,解釋我們的發現以及接續而來的新發現。他們的故事,精采程度絕對不輸給我們的故事,而且所有人也都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包括人事、地點、機會以及知性環境。真正獲得諾貝爾獎的人雖少,但凡是在最前線發現及解決問題的人,全都屬於這項傳統,不論他們是科學家、作家,還是致力世界和平的人。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