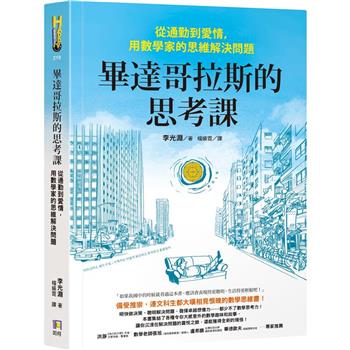農業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主要議題之一。農業能不能成為開發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源泉,應該如何改造開發中國家的傳統農業,一直是經濟學家們爭論和研究的中心問題。關於開發中國家農業問題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然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舒爾茨在1964年發表的《改造傳統農業》一書卻獨樹一幟,至今仍有深遠的影響。
舒爾茨一生專注研究農業發展過程所面臨的經濟問題,用理論方法去解釋低所得國家傳統農業停滯的源由,並以實證來檢定其假說,由此進而確認傳統農業的轉型是有利經濟成長的來源,且討論包含新式生產要素投入與農業人力等的投資。準此,本書確認傳統農業可被現代化,它成功指出最重要的改變策略。
於理論方面,本書提出傳統農業現代化之理論,首先了解傳統農業之特性,其次是指出影響傳統農業邁向現代化之影響因素,最後提出要現代化之策略。為達成上述,本書提出經濟效率假說和零值勞動邊際假說,說明傳統農業是處在一特殊類型之經濟均衡狀態,也提出所得流量之價格理論,接著是整合人力資源投資與農業現代化之關係;由此,本書被視為一本敘說「舒爾茨理論」的書籍。
於實務方面,舒爾茨挑戰一九四○至一九七○年代的發展經濟學者、重農主義等對傳統農業的不同論點,他也引用一些在印度和瓜地馬拉的實務數據來佐證其假說和論述;強調農業人力資源的投資,不但提升農民素質,而且是開啟農民接受創新要素之門。
「希歐多爾‧威廉‧舒爾茨是一位過渡時期人物,他縮小了舊式學院研究與近代經濟學的差距。」──James Joseph Heckman,《紐約時報》
「對於貧窮國家的農業和發展問題,多年來的經驗及反思(本書)集其大成;並結合了關於對人類投資的新思維。」──Mary Jean Bowman,經濟學名譽教授,對 Schultz 著作的評論。《芝加哥大學紀事報》
作者簡介:
希歐多爾‧威廉‧舒爾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
出生於美國南達科他州阿靈頓郡的德國移民家庭,父親是小農場主。舒爾茨沒有上過中學,在農業學校學習幾年後,進入南達科他州立學院學習農學專業,之後受教於威斯康星大學。畢業後先在衣阿華州立學院任教,開始「窮人經濟學」研究之路,四十年代後轉至芝加哥大學任教,成為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60年當選美國經濟學會會長,1972年退休。此外,他還曾在美國政府農業部、商務部、聯邦儲備委員會、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兼職。
代表性著作還有:《不穩定經濟中的農業》、《農業經濟組織》、《向人力資本投資》、《經濟增長與農業》、《人力資本投資》等。1979年因對發展經濟學和農業經濟學的貢獻,與威廉‧阿瑟‧劉易斯一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譯者簡介:
梁小民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山西省霍縣人,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曾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研究;曾任教於北京大學、北京工商大學,出版專著、譯著等60多本,多部著作在港台出版。退休後,在清華大學、上海交大、同濟大學、廈門大學等20多所院校兼職教授。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問題的提出
(節錄)
一個像其祖先那樣耕作的人,無論土地多麼肥沃或他如何辛勤勞動,也無法生產出大量糧食。一個得到並精通運用有關土壤、植物、動物和機械等科學知識的農民,即使在貧瘠的土地上,也能生產出豐富的糧食。他無須總是那麼辛勤而長時間的勞動。他能生產得如此之多,以至於他的兄弟和一些鄰居可以到城市謀生;沒有這些人也可以生產出足夠的農產品。而使得這種改造成為可能的知識,是資本的一種形式,無論這種資本是農民使用物質投入的一部分,還是他們技術和知識的一部分。
完全以農民世代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為基礎的農業,可以稱之為傳統農業。一個依靠傳統農業的國家必然是貧窮的,因而就要把大部分收入用於糧食。但是,當一個國家像歐洲的丹麥、近東的以色列、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和遠東的日本那樣發展農業部門時,糧食就比較豐富,收入就會增加,而且國家收入用於糧食的部分也會減少。如何把弱小的傳統農業改造為一個高生產率的經濟部門,是本書研究的中心問題。
從基本上說,這種改造取決於對農業的投資。因此,這是一個投資問題。但是,它主要並不是資本供給問題;確切的說,它是決定這種投資應該採取什麼形式的問題,這些形式使得農業投資有利可圖。這種研究方法把農業作為經濟成長的一個來源,而分析的任務是要確定透過投資,把傳統農業改造成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能夠實現多麼廉價而巨大的成長。雖然對經濟成長的研究非常活躍,但這個問題卻很少受到注意。事實上每個國家都有農業部門,而且在低收入國家農業部門總是最大的,但除了少數例外,研究成長問題的經濟學家為了集中解決工業問題,都撇開了農業。同時,許多國家不同程度的正在進行工業化;其中大部分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的同時,並沒有採取相應的措施來增加農業生產;某些國家以損害農業來實現工業化。只有少數國家從工業和農業中都得到了大幅的經濟成長。成功的發展自己的農業部門,使農業成為經濟成長的真正來源的,只是個別例外的國家。
但是,並不存在使任何一個國家的農業部門不能對經濟成長作出重大貢獻的基本原因。的確,僅使用傳統生產要素的農業,是無法對經濟成長作出重大貢獻的,但現代化的農業能對經濟成長作出重大貢獻。對於農業能否成為經濟成長的強大引擎,已不再有任何懷疑了;然而,要得到這樣的引擎就必須向農業投資,而這件事並不簡單,因為它主要取決於投資所採取的形式。用激勵的辦法去指導和獎勵農民是個關鍵,一旦有了投資機會和有效的激勵,農民將會點石成金。
本書的研究目的是要說明有一種合乎邏輯的經濟基礎,它可以解釋為什麼僅使用由它支配的生產要素的傳統農業,除了以高昂的代價之外無法成長,以及為什麼按過去的成長標準來看,對現代農業要素投資的報酬率可能是很高的。因此,真正重要的問題是想以儘量低廉的代價實現經濟成長的國家,在發展農業中應該做些什麼。
對顯而易見的事情作詳細闡述是有風險的,但還是要審慎的說明一下什麼是「農業部門」(agricultural sector)。農業是生產特殊種類產品的經濟部門,這類產品主要來自於植物,以及包括家禽在內的動物。其中某些產品由纖維和其他工業用的原料組成。但是,大部分最終作為糧食使用。把農業部門的生產活動分為以下幾類是恰當的:(1)農民所從事的生產(在本書研究所用的術語中,小農和耕種者都是農民);他們可能主要是為家庭消費而生產,或者完全為市場而生產;(2)不由農民從事,而由一些供給者從事農業要素的生產,農民由這些供給者裡獲得這些要素;(3)不由農民完成的農產品銷售、運輸和加工的生產。
但是,為什麼對農業的經濟潛力缺乏瞭解呢?部分是由於經濟學知識的狀況;部分是由於廣泛承認的關於農業部門的學說所引起的混亂。在知識界,農業經濟學家把自己的研究主要局限於一些小國的農業,在這些國家,農業有效的對國民收入作出了貢獻。他們考察了這些國家農民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但並不是從農業的角度來研究經濟成長。一般說來,他們忽視了傳統農業,把它留給人類學家去研究,人類學家作出了一些有用的研究,這一點以後會說明。同時,成長經濟學家編制出了大量宏觀模型,除少數外,這些模型既沒有適當的把農業的成長潛力理論化,又不能用於檢驗農業作為一種經濟成長來源的實證行為。
當然,經濟學家和有識之士正在意識到各國在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速度方面的巨大差別;在農業現代化最成功的那些國家,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比工業快得多。人們還意識到在農業生產成長率方面相應的巨大差別;但是,對這些差別沒有作出解釋。成長經濟學家在進行高度理論化時,除了少數例外,都把脫離現實的「資本」和「勞動」作為基本的解釋變數,然後有一種歸屬於﹁技術變化﹂的剩餘。當把這些模型用於分析實際資料時,結果是大部分的經濟成長隱蔽在「技術變化」的名下。因為這是一種剩餘,對它就沒有作出什麼解釋。同時,那些稍微注意到農業部門情況的人,總是厭惡農民的落後保守。他們的結論是:當農民學到了﹁勤勞與節儉﹂的經濟美德,從而有了儲蓄和投資時,就會克服傳統農業的經濟停滯狀態—但絕沒有想到對傳統農業投資的利益。
毫無疑問,經濟學知識的缺乏引起了各種學說。關於農業可以對成長作出貢獻就是如此。某些學說是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教條(political dogmas),某些只是經濟學家已經消亡了的思想。能說明這些學說是錯誤的,就是為這個問題的有用概念掃清了道路。非常有希望的是,在一定時期內,相信經濟分析的宣告可以摧毀政治教條的城牆,並不完全是幼稚可笑的見解。
更重要的是這些學說導致了對「農業在經濟成長中的作用是什麼」這一問題的錯誤回答。教條式的回答如下:來自農業的成長機會是最不引人注目的成長來源;農業可以為窮國進行工業化提供所需要的大部分資本;它還可以為工業提供無限的勞動供給;它甚至可以以零機會成本提供大量的勞動,因為在邊際生產率為零的意義上來說,農業中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力是過剩的;農民對正常的經濟刺激沒有反應,往往還會作出錯誤的反應,其含義是農產品的供給曲線向後傾斜;為了用最小成本生產農產品就需要大的農場。
第一章 問題的提出
(節錄)
一個像其祖先那樣耕作的人,無論土地多麼肥沃或他如何辛勤勞動,也無法生產出大量糧食。一個得到並精通運用有關土壤、植物、動物和機械等科學知識的農民,即使在貧瘠的土地上,也能生產出豐富的糧食。他無須總是那麼辛勤而長時間的勞動。他能生產得如此之多,以至於他的兄弟和一些鄰居可以到城市謀生;沒有這些人也可以生產出足夠的農產品。而使得這種改造成為可能的知識,是資本的一種形式,無論這種資本是農民使用物質投入的一部分,還是他們技術和知識的一部分。
完全以農民世代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為基...
作者序
當我看到大多數國家在增加農業生產方面收效甚微時,我就懂得了為什麼人們會深信,精通農業是一門難能可貴的藝術。如果說精通農業是一門藝術,那麼,少數國家在這方面是非常內行的,儘管它們似乎還不能把這種藝術傳授給其他國家。這少數精通農業的國家在用於耕作的勞動和土地減少的同時,生產一直在增加。但是,只要把增加生產的經濟基礎作為一門藝術,我就毫不奇怪實現農業生產增加的經濟政策基本上仍然屬於神話的領域。現在,在制定政策方面,一個接一個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就像過去按月亮的變化來播種穀物的農民那樣老練了。
農業是一個定居的社會中最古老的一項生產活動,但令人驚訝的是,人們對於在農民受傳統農業束縛的地方之儲蓄和投資的刺激瞭解很少。更奇怪的是,在分析窮國農民的儲蓄、投資和生產行為方面,經濟學倒退了。對於這些環境下適用的特殊類型的經濟均衡,老一輩的經濟學家比現代經濟學家要懂得多一些。
雖然傳統農業的弱小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弱小性並不是一套獨特的、與工作和節約相關的偏好的函數,這一點並不明顯。同樣不明顯的是:傳統農業的弱小性主要是由於農民已耗盡了作為他們所支配的投入和知識的一部分的﹁生產技術﹂的有利性,而對於農民的儲蓄與投資以增加再生產性資本的各種形式的存量,幾乎沒有什麼刺激。本書研究的目的是要說明,傳統農業的基本特徵是向農民世代使用的那類型農業要素投資的低報酬率;此外,還要
進一步說明,為了改造這類型的農業,就要發展並供給一套比較有利可圖的要素。發展和供給這種要素,並學會有效的使用這些要素,是一項投資—向人力和物質資本的投資。
糧食和農業問題一再被作為檢驗新概念與分析工具的場所。相對於土地而言,勞動和物質資本的收益遞減與李嘉圖式的地租都是例證。從恩格爾統計學開始的需求收入彈性,以及後來亨利.舒爾茨(Henry Schultz)的不朽研究和吉爾西克(Girshick)、哈威爾莫(Haavelmo)、史東(Stone)、托賓(Tobin)、巴克(Buck)、霍薩克(Houthakker)、戈倫克斯(Goreux)等的研究也是例證。最近納洛夫(Nerlove)對遞延分配的解釋價值進行了檢驗,格里利切斯︵Griliches︶對生產函數的特別偏重,以及對雜交玉米這種新投入品的研究成本和社會收益都作了檢驗。本書的研究,我試圖檢驗在確定來自農業來源的收入流價格中,供給和需求方法的有用性。
當我開始研究時,曾打算收錄一個相關文獻的廣泛書目。但是,我很快就明白,儘管可以得到許多有關窮國農業特徵的文獻,然而一般說來這些文獻與本書研究核心的基本經濟問題都無關。因此,我又決定,與其單獨列出書目還不如把它作為附註。結果,許多我所提到的公開發表的文獻條目,代表了支持與我的分析不一致的學說和政策方法的觀點及論述。
自從一九五九年下半年開始本書的研究以來,我要感謝許多人。當我向自己的學生提出本書研究的中心思想時, 與他們的討論使我收穫頗大。我的同事茲維.格里利切斯(Zvi Griliches)、D.蓋爾.詹森(D. Gale Johnson)以及戴爾.W.喬根森(Dale W. Jorgenson)閱讀了本書的主要章節,他們的批評使我獲益匪淺。弗農.W.拉坦(Vernon W. Ruttan)閱讀了全部初稿,我幾乎接受了他提出的所有建議。艾布拉姆.伯格森(Abram Bergson)、理查.A.馬斯格雷夫(Richard A. Musgrave)和勞埃德.雷諾茲(Lloyd Reynolds)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問題。我的妻子埃絲特.沃思.舒爾茨(Esther Werth Schultz)校對了打字稿,核對了參考書目,並多次使我認知到,我自認為清楚的東西實際上表述得並不夠清楚。耶魯大學出版社的瑪麗安.尼爾.阿什(Marian Neal Ash)
小姐慷慨的獻出了自己的編輯才能。我的秘書佛吉尼亞.K.瑟娜爾(Virginia K. Thurner)辛勤地校對了樣稿。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使我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間從學校的工作脫身。更要感謝的是我所要歸功的口授傳統,這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專題討論工作坊的一部分。
希歐多爾.W.舒爾茨
一九六三年五月於芝加哥大學
當我看到大多數國家在增加農業生產方面收效甚微時,我就懂得了為什麼人們會深信,精通農業是一門難能可貴的藝術。如果說精通農業是一門藝術,那麼,少數國家在這方面是非常內行的,儘管它們似乎還不能把這種藝術傳授給其他國家。這少數精通農業的國家在用於耕作的勞動和土地減少的同時,生產一直在增加。但是,只要把增加生產的經濟基礎作為一門藝術,我就毫不奇怪實現農業生產增加的經濟政策基本上仍然屬於神話的領域。現在,在制定政策方面,一個接一個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就像過去按月亮的變化來播種穀物的農民那樣老練了。
農業是一個...
目錄
導 讀
譯者前言
序 言
第一章 問題的提出
各種學說的遺產
需要撇開的問題
未解決的問題
第二章 傳統農業的特徵
一個經濟概念
如何改造傳統農業?
一個難題
第三章 傳統農業中生產要素配置的效率
經濟效率的假說
瓜地馬拉的帕那加撤爾:十分貧窮而有效率
印度的塞納普爾:貧窮而有效率
結論與含義
第四章 零值農業勞動學說
「零值勞動」學說的各種根源
對理論的屈從
實證的檢驗
根據印度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流行性感冒後的情況所作的檢驗
第五章 收入流價格理論的含義
成長模型忽視了的內容
理論框架
非成長類型
成長類型
第六章 傳統農業收入流的價格
收入流價格較高的假說
反對這一假說的觀點
瓜地馬拉的帕那加撤爾
印度的塞納普爾
結論性的含義
對要素份額的說明
第七章 投資有利性問題的引言
第八章 農場規模、控制和刺激
專業化
不在所有或居住所有的控制和農場規模
偽不可分性和農場規模
對地租的壓抑
關鍵是農產品和要素價格
第九章 隱藏在﹁技術變化﹂中的生產要素
隱藏要素的把戲
檢視技術變化所掩蓋的內容
全面生產要素概念的含義
需求和供給的方法
第十章 新的有利生產要素的供給者
供給者的研究和發展
供給者所進行的分配
第十一章 農民作為新要素的需求者
接受的速度
對新要素的尋求
學會使用新農業要素
第十二章 向農民投資
農業成長和人力資本的回顧
工業化的教訓
教育的價值何在
引進技術的經濟學
向人力資本投資
索 引
導 讀
譯者前言
序 言
第一章 問題的提出
各種學說的遺產
需要撇開的問題
未解決的問題
第二章 傳統農業的特徵
一個經濟概念
如何改造傳統農業?
一個難題
第三章 傳統農業中生產要素配置的效率
經濟效率的假說
瓜地馬拉的帕那加撤爾:十分貧窮而有效率
印度的塞納普爾:貧窮而有效率
結論與含義
第四章 零值農業勞動學說
「零值勞動」學說的各種根源
對理論的屈從
實證的檢驗
根據印度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流行性感冒後的情況所作的檢驗
第五章 收入流價格理論的含義
成長模型忽視了的內容
理論...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