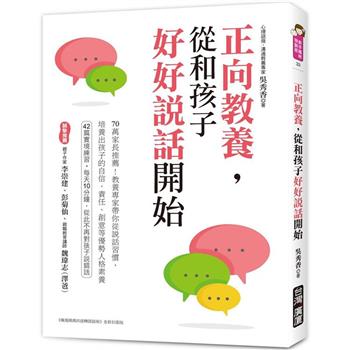第一章 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
我曾應邀向一大群聽眾演講,演講開始時間是晚上8點。我跟隨接待人員從講台後門進入大廳,站在講台側面,此時我脖子上已掛著麥克風。我看到前面十二排空無一人,心想學術聚會就是這麼一回事:8點是指8點15分。當主持人走上台,向空蕩蕩的座位點頭並開始介紹我時,我心中頗感疑惑。雖然有點不情願,我還是走向講台。
結果發現,從第13排到大廳後面牆壁之間,密密麻麻坐滿了800人。我開始演講,感覺像是隔著一條河向對岸的群眾說話。事後我問主持人,為什麼做這樣的座位安排。他說無此安排。
現場沒有座位安排,也沒有引座員。聽眾是依其偏好自行選定座位的。我們要思考的是,聽眾的偏好究竟是什麼?
可能每個人都希望所有聽眾全擠進靠後面的24排,讓最前面的12排空出來。但任何人除了自己可獨樹一幟外,對其他人要坐哪裡他是無法控制的。人們並非按照某種座次表選擇座位,而只是走在通道上掃視會場,從所見到的空位中挑選他們想要的座位。
我們能否推測人們是遵循什麼法則來選擇座位?在此應一提的是,就我所知,坐在不同排的人彼此之間並沒有任何差異。坐在靠前面或靠後面的人,不見得比較老、衣著比較光鮮或主要為同一性別。坐在最前面(第13排)的人看起來比較專心,可能他們心知肚明,即便在這樣的距離下,他們若閉上眼睛或打起瞌睡,我可是一目了然的,因此,他們的警覺心要比其他人高一些。
好奇如我者,卻忘了問主辦人有關各排滿座的順序。聽眾是依序由後往前坐滿空位?任意坐進後面的24排?或先來的人坐滿第13排,後到的人依序往後面就座?最後這種情況應不可能發生:假如最先到者選定了前面的就座界線,使得後到者剛好可坐滿界線內的座位,這也未免太巧了。須知,此一情形與人們進入一個密集地區時應該是一樣的,這種就座動能並不知道其後還有多少人會到達現場。
我們可能基於幾個原因,而對呈現這種就座模式的聽眾之行為、想法和意圖感到興趣。第一個原因是,我們不想見到這樣的結果;我們希望他們全坐在前面的24排,而不是後面的24排,或分散於整個聽眾席中。假如我們想在盡可能不進行組織或不干涉聽眾偏好的情形下改變就座模式,則必須瞭解是否可巧妙改變他們的誘因或對聽眾席的認知,使他們「自願」選擇較佳的就座模式。
做此事之前,我們應該先瞭解聽眾是否喜歡自己選擇的座位安排,以及他們這種選擇座位的方式能否證明他們一定對結果感到滿意。
令我們感興趣的第二個原因是,這個過程所含的某些因素使我們想起其他類似的情況,例如,人們依某種模式自願選擇的地點卻不具有明顯的優勢。居住地點的選擇就是一個例子。這種聽眾席內的實驗指點我們遭逢其他情況時應注意哪些因素。
我請讀者思考促成這種就座模式的動機,目的不是想研擬一份聽眾席管理手冊,也不是要推測人們選擇居所的方式、群眾行為或停車場的使用模式,而是要為本書的內容舉出一個生動的例子。本書討論的是社會科學中一種偏重理論性的重要分析,這種分析旨在探討構成某些社會群體的個體的行為特徵與群體特徵之間的關係。
此一分析有時會基於我們對個體意圖的瞭解來預測群體的行為:假如我們知道進入聽眾席的人都有坐在其他人旁邊的群聚願望,但又總想彼此之間隔著一個座位,則我們可預測所有聽眾全到齊後所呈現的就座模式。或者,此一分析可進行我請讀者做的工作──設法瞭解什麼樣的個體意圖或行為模式會導致我們所觀察到的模式。假如有數種行為可能導致這種模式,我們即可從中找出選擇這些行為的證據。
當然,有些情況是非常單純的,我們可從中發現總體只是個體的外推結果(extrapolation)。如果知道每位駕駛都會在天黑時自行打開車燈,我們料將可從直升機上看到某地區的所有車燈約略在相同的時間亮起來。我們甚至可以依據機上的羅盤方位看出麻薩諸塞州高速公路上的亮光隨著天色變黑而由東向西移動的情形。但如果大多數人是見到迎面而來的汽車已亮燈才打開自己的車燈,我們從直升機上看到的將是另一番景象。在第二種情況下,駕駛對彼此的行為做出反應,也互相影響對方的行為。人們對某種環境做出反應,其中有些人另外對自己的環境做出反應,而在這個環境中,又有人對其他人的反應做出反應。有時候這種動態具有單向連貫性:如果你的車燈導致我打開車燈,我的車燈可能又會促使第三者打開車燈。有時候這種動態具有相互針對性:聽到你按喇叭,我也按喇叭,如此一來,你於是更急切地按個不停了。
在人們的行為或選擇取決於其他人的行為或選擇的情況下,通常無法以簡單的總結或外推來獲知群體的行為。為找出其中的關聯,我們通常必須檢視個體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互動體系,也就是個體與其他個體或個體與集體之間的互動體系。有時結果會出人意表,有時不易猜測;有時分析工作很困難,有時甚至無法獲得結論。但即便是沒有定論的分析也可以提醒我們,不應依據觀察到的群體行為而做出有關個體意圖的草率結論,也不應依據所瞭解或臆測的個體意圖而做出有關群體行為的草率結論。
回頭討論聽眾就座的問題,並稍加思考人們選擇座位的動機(毋需假設他們都有相同的動機)。哪些推測──即不同的假設──可說明為什麼這些聽眾會形成我所描述的結果?如何評估每個假設所造成的結果?如何以不同的假設來影響結果?每個假設能允許偶然性或組織架構(architecture)擁有多大的發揮空間?我們能否深入研究這幾個假設,從中做出選擇,或放棄所有假設,繼續尋尋覓覓?
最明顯的一種可能性是每個人都想盡可能往後面坐。最先來的人會坐在最後面,晚到的人可能會後悔沒能早點來;但對整體聽眾而言,變換座位對最後的結果並無裨益,因為只要把一個聽眾換到後面的座位,就有另一個聽眾必須換到前面的座位。如果我們真想把所有聽眾的座位向前移12排,封鎖最後12排座位即可達到目的。
第二種可能性的情況有所不同,也就是每個人都想坐在別人後面──不是大廳的後面,而只是其他人的後面(或許他們想在散場時搶先離開)。他們可能希望別人盡量往前坐,這樣他們也可跟著盡量往前而猶能保持在別人後面。為了坐在別人後面,先來的人會選擇相當後面的座位,以便留出座位給後到的人,但後到的人卻坐到他們的後面,不是前面;另一種情形是,如果先來的人認為後到的人會有這樣的行為,他們只好選擇最後一排座位,否則將會有人擠到他們的後面。同樣的,如果我們想要他們全都往前坐,可以封鎖最後12排座位;也許他們也想往前坐,只是事實上沒有如此做罷了。
第三種可能性是每個人都想坐在靠近別人的位子,這可能是人的群聚性使然,也可能是為了避免自己明顯落單。如果最早來的少數人恰好坐在靠後面的位子,則後到的人會聚集在他們周圍,直到人群擴散到最後一排為止。自此以後,只有往前的方向才有空位,後到的人為了能靠近別人,會選擇緊臨人群前緣的座位。如果我們能使最早來的少數人坐在前面,則同樣的過程將導到相反的結果:晚到的人發現前面已坐滿,將選擇緊鄰人群後緣的座位。不論是哪種情況,先來的人都會被團團圍住,接著所有人會簇擁在一起。只是前一種情況人們是集中坐在後面,後一種是集中坐在前面。
第四種可能性是每個人都想看別人進入會場的情形,如同賓客在婚禮中的行為一樣。人們為避免伸長脖子探望或被發現自己正揪著目標看,會盡量往後面坐,並看著別人在走道上行進。一旦聽眾都就座後,坐在後面的優勢不復存在──不論是坐在別人後面或大廳後面。如果我們能估出人群的數量,並據以封鎖後面幾排座位,則每個人的座位都可朝「正在發生的事」前進12排,而得以一飽眼福,而且,也不會出現演講者與聽眾之間隔道鴻溝的尷尬情形。或者我們可以使人們從前門而不是後門進入會場,先來者就會選擇前面的好位子,以便觀看後到者的來臨。
另外一種假設是,大多數人已經在其他時間與地點養成了自己的就座習慣,並從中發現坐在前面的諸多缺點。他們一如往常不假思索就往後面坐,但後來想清楚在這個場合可能不會有老師走上前來問問題,他們大可往前坐,以便看和聽得更清楚。其他狀況依此類推。我們甚至可假設,人們在進入大廳後,只是因為疲倦的緣故而選擇最近的空位坐下來。但這種行為應該考慮禮儀原則──即每一排第一個就座的人必須坐在兩個走道的正中間,接下來的就坐者必須往裡面靠,以盡量減少後到者得跨過別人的情況──如此我們才能觀察這個「最不費功夫」的假設造成的結果。
我還發現另一種有趣的假設,可能性雖低,卻也言之成理。這個假設認為,沒有人在乎自己坐在哪裡,只要不是在最前面──也就是已經有人坐的第一排就行。在已經坐了人的24排座位中,人們並不在乎他會坐在其中23排的哪一排,但就是不想坐在第一排。
事實上,每個人可能都想盡量往前坐,唯一的條件是他不要坐在第一排。在不知道會來多少聽眾的情形下,人們為求安全起見,會往後面坐;當看起來似乎大多數聽眾已經到場後,人們會跨過已就坐者,在人群中找空位坐,而不會坐到大夥前面那一排空蕩蕩的位置上。
當然,有些人終究還是坐在所有人的前面;而如果全體聽眾都往前移12排,他們可能會同樣高興,或更高興。坐在其他23排的人勢必也樂見整個人群往前移動。
可能性更低的另一種假設是,人們甚至不在乎坐在第一排,只要緊接其後的各排都坐滿人,使得坐在前排的他們不會特別顯眼就行。這種情況可能導致同樣的結果。
有目的的行為
應注意的是,所有這些假設都包含一個概念:人們有自己的偏好,會追求目標,會盡量避免費力或尷尬的事,盡量增大視野或舒適感,尋求或避免他人的陪伴,及以其他或可稱之為「有目的」的方式展開行動。而且,這些目標、意向或目的與別人及他們的行為有直接的關係,或受別人尋求他們的目標、意向或目的時所處的環境之限制。這種因變行為(contingent behavior)──行為本身取決於別人的所作所為──乃為我們常見的行為模式。
在其他科學中,比如有時在社會科學中,我們會以比喻的方式指出行為是有其動機的,因為有些行為看起來好像是欲達成某種目的。水往低處流,大自然厭惡真空,肥皂泡將表面張力降至最小程度,光雖然在不同介質中有不同的速度,卻總是循著費時最短的路徑行進。但如果我們將水注入J形試管,並封住底端,試管中的水將無法往低處流,此時沒有人真正認為水會有挫折感。如果我們打開試管底端,大部分的水會潑灑到地上,此時沒有人會認為水為了往低處流而潑灑了一地是種短視的行為。
我們多數人都不認為光是在忙著趕路。最近,最近有人認為向日葵會因為跟不上太陽的移動而苦惱,而且我們還得知,樹葉會在樹上尋求光源充足的位置,以達成最有效的光合作用。如果我們從事伐木業,會希望樹葉長得茂盛,但不是為了樹葉本身;我們甚至不清楚樹葉的行為是自發性的,或只是受某種酵素所驅使,或屬於我們完全無法用「目的」或「尋求」之類的字眼來歸類和評估的化學體系的一部分。
人的問題就不一樣了。當我們分析人們逃離火災現場的行為時,我們認為他們真的是設法想逃命,而不僅僅表現出「好像」不喜歡遭到焚燒的樣子。人不同於光線和水,我們通常認為我們是在自己的知識限度內、在有關如何克服環境困難朝目標前進的理解下,做出有意識的決定或調適,以追求近期或遠程目標。事實上,我們常常可以認定人類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經估算或依直覺判斷,以瞭解如何從當前處境邁向所望境地的能力。如果我們瞭解一個人所欲解決的問題,並認為他確實能解決這個問題,而且我們也有能力解決,我們就可以設身處地研究如何依他能理解的方式解決此一問題,從而得以預判他的行為。這種「代理問題解決法」(vicarious problem solving)乃微觀經濟學大多數理論之基礎。
討論「尋求目標」的無意識物質,如往低處流的水,或生物學中尋求自保和擴散的基因,有一個優點是,我們不會忘掉我們所指陳的動機只不過是一種圖方便的表達方式、一種具提示性的比喻、或一種有用的公式。至於人類,我們不免因為我們具有尋求目標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得意忘形。我們可能忘掉人們會追求錯誤的目標,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有時還會受到某些潛意識過程的影響而對目標有錯誤的認知。而且,我們會在人們達成我們認為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時,誇大了此種成就。
儘管如此,這種方式的分析顯然有待評估。當人們的行為有其目的時,我們很難只探究所發生的事而不對結果是否符合目的感到好奇或關心。社會科學家比較像是森林看守員而不是自然主義者。自然主義者可能對某一物種滅絕的原因感興趣,但並不在乎此物種是否真會滅絕(如果此物種已絕種100萬年,他的好奇心當然就不含關心的成分)。森林看守員關心的是美洲野牛是否會消失,以及如何使牠們與環境維持妥善的平衡。
使這項評估變得既有趣又困難的是,我們必須評估群體行為的總體結果,而不只是每個人在環境的限制下所展現的行為。在一棟失火的大樓內,快跑而非慢走至最近的太平門或許是明智之舉,尤其是別人都在跑的時候;然而,我們必須評估的是,如果每個人都竭盡所能想逃生,而導致所有人都跑向太平門,那究竟有多少人能逃出大樓。前來聽我演講的每個人在進入大廳時,都會盡可能選擇眼前最好的座位。(在所有800位聽眾都就座後,某些人可能因為看到別人就座的情形和到達現場的人數,而希望他們當初能夠稍微往前坐。)但最有趣的問題不是有多少人在看了別人就座的情形後會想換座位,而是其他的座位安排能否讓許多、大部分甚至全部聽眾更稱心如意。
每個人如何充分適應他所處的社會環境,與他們能集體為自己創造多麼令人滿意的社會環境,可說是兩回事。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thomas c. schelling的圖書 |
 |
$ 210 ~ 342 | 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
作者:湯瑪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 / 譯者:高一中 出版社:臉譜 出版日期:2008-10-17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精裝 / 288頁 / 14.8*21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
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湯瑪斯.謝林最新著作!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指出,獲獎的謝林和奧曼從事賽局理論的研究,有助於解決商業貿易上的矛盾衝突,甚至於戰爭糾紛。
瑞典皇家科學院則指出:「為何某些個人、組織和國家集團能夠順利推動合作,某些集團卻因彼此衝突而蒙受損失?針對這個古老的問題,湯瑪斯.謝林和羅伯特.奧曼的研究已將賽局理論或互動決策理論拱上主要分析途徑的寶座。」
早晨交通尖峰時間,高速路上湧現進城的車潮,突然間,煞車燈紛紛亮起,車輛開始減速,車流也慢了下來。原來是出城的車道發生交通事故。但是,為什麼進城的車道會出現擁塞的情形呢?因為駕駛為了看一眼對向車道的車禍狀況,都把車速放慢。如此一來,大批通勤者多花了十分鐘的開車時間,只為了那十秒鐘的ㄧ瞥。換句話說,每位駕駛為了看車禍現場花了十秒鐘,但卻因為前方駕駛的好奇心而耗掉了九分五十秒。這真是不划算的事。
《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就是在討論這類的狀況。這些狀況有的很嚴肅,有的很怪異,但全都涉及一種行為模式:一個人對他所處的環境做出反應、因應及適應的同時,卻渾然不知或不在乎,他的行為與其他人的行為結合起來後,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謝林教授使用大家耳熟能詳、淺顯易懂的例子來說明當集體行為不只是個體行為的單純總和時,會發生什麼狀況;為什麼社會成員經常無法察覺他們的個別決定所造成的整體結果;以及為什麼以集體現象來推斷個人意圖,是一種弔詭且根本行不通的做法。但他並沒有就此打住,而是設計了一些不算艱澀深奧但也非可以一目了然的模型,或稱之為基本分析系統,俾用以探討因為種族、性別、年齡和收入的區隔現象所行程的社會問題。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我曾應邀向一大群聽眾演講,演講開始時間是晚上8點。我跟隨接待人員從講台後門進入大廳,站在講台側面,此時我脖子上已掛著麥克風。我看到前面十二排空無一人,心想學術聚會就是這麼一回事:8點是指8點15分。當主持人走上台,向空蕩蕩的座位點頭並開始介紹我時,我心中頗感疑惑。雖然有點不情願,我還是走向講台。結果發現,從第13排到大廳後面牆壁之間,密密麻麻坐滿了800人。我開始演講,感覺像是隔著一條河向對岸的群眾說話。事後我問主持人,為什麼做這樣的座位安排。他說無此安排。現場沒有座位安排,也沒...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湯瑪斯.謝林
- 出版社: 臉譜 出版日期:2008-10-14 ISBN/ISSN:9789866739804
-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288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