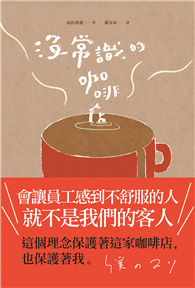本書是宗教改革的奠基性著作之一,也是路德自己最喜愛的一部作品。書中不僅將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罪人唯靠基督因信稱義—闡釋得淋灕盡致,而且有力地駁斥了宗教改革時期教皇黨人和一些極端改革派的謬論。書中不乏釋經書的考究和嚴謹,又充滿了雄辯的激情和改教必勝的凱旋氣勢,讀來令人激情澎湃。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德國神學家,宗教改革家,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與奧古斯丁、阿奎那、加爾文齊名。最主要的著作有《基督徒的自由》、《意志的捆綁》、《桌邊談話》等。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德]路德的圖書 |
 |
$ 204 | 《加拉太書》注釋
譯者:李漫波 出版社:[德]路德 出版日期:2011-11-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44頁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加拉太書》注釋
內容簡介
序
在當今的全球時代,“文明的沖突”會造成文明的毀滅,因為由之引起的無限戰爭,意味著人類、動物、植物和整個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則帶來文明的更新,因為由之導向的文明和諧,意味著各文明自身的新陳代謝、各文明之間的取長補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處以及全人類文化的繁榮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對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經典之翻譯。就中西兩大文明而言,從17世紀初以利瑪竇(Matteo Ricci)為首的傳教士開始把儒家經典譯為西文,到19世紀末宗教學創始人、英籍德裔學術大師繆勒(F.M.Mtiller)編輯出版五十卷《東方聖書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經典在內的中華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譯介紹到了西方各國;從徐光啟到嚴復等中國學者、從林樂知(Y.J.Allen)到傅蘭雅(John Fryer)等西方學者開始把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著作譯為中文,直到20世紀末葉,商務印書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和其他有歷史眼光的中國出版社組織翻譯西方的哲學、歷史、文學和其他學科著作,西方的科學技術和人文社科書籍也被大量翻譯介紹到了中國。這些翻譯出版活動,不但促進了中學西傳和西學東漸的雙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華文明的新陳代謝,以及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
清末以來,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取長補短”的歷程,經歷了兩大階段。第一階段的主導思想是“師夷長技以制夷”,表現為洋務運動之向往“船堅炮利”,追求“富國強兵”,最多只求學習西方的工業技術和物質文明,結果是以優勢的海軍敗于日本,以軍事的失敗表現出制度的失敗。第二階段的主導思想是“民主加科學”,表現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尊崇“德賽二先生”,中國社會在幾乎一個世紀中不斷從革命走向革命之後,到現在仍然需要進行民主政治的建設和科學精神的培養。大體說來,這兩大階段顯示出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由十分膚淺到較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從物質層面深入到制度層面。
正如觀察一支球隊,不能光看其體力、技術,還要研究其組織、戰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樣地,觀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業、技術,還要研究其社會、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靈性。因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質、制度和精神三個不可分割的層面,合其一則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覺或不自覺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到了20世紀末葉,中國終于有了一些有歷史眼光的學者、譯者和出版者,開始翻譯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層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從而開啟了對西方文明的認識由較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從制度層面深入到精神層面。
與此相關,第一階段的翻譯是以自然科學和技術書籍為主,第二階段的翻譯是以社會科學和人文書籍為主,而第三階段的翻譯,雖然開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實際上,基督教對世界歷史和人類社會的影響,絕不止于西方文明。無數歷史學家、文化學家、社會學家、藝術史家、科學史家、倫理學家、政治學家和哲學家已經證明,基督教兩千年來,從東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經極大地影響,甚至改變了人類社會從上古時代沿襲下來的對生命的價值、兩性和婦女、博愛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勞動和經濟、科學和學術、自由和正義、法律和政治、文學和藝術等等幾乎所有生活領域的觀念,從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這個誕生于亞洲或“東方”,傳入了歐洲或“西方”,再傳入亞、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現在因為信眾大部分在發展中國家,被稱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來就不屬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國家沒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經不僅僅在宗教意義上,而且是在現實意義上展現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質。
因此,對基督教經典的翻譯,其意義早已不止于“西學”研究或對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對世界歷史和人類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這里所謂“基督教經典”,同結集為“大藏經”的佛教經典和結集為“道藏”的道教經典相類似,是指基督教歷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師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視為唯一神聖的上帝啟示“聖經”。但是,由于基督教歷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師名作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絕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樣結集為一套“大叢書”,所以,在此所謂“經典譯叢”,最多只能奢望成為比佛藏道藏的部頭小很多很多的一套叢書。
……
“文明的交流”最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對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經典之翻譯。就中西兩大文明而言,從17世紀初以利瑪竇(Matteo Ricci)為首的傳教士開始把儒家經典譯為西文,到19世紀末宗教學創始人、英籍德裔學術大師繆勒(F.M.Mtiller)編輯出版五十卷《東方聖書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經典在內的中華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譯介紹到了西方各國;從徐光啟到嚴復等中國學者、從林樂知(Y.J.Allen)到傅蘭雅(John Fryer)等西方學者開始把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著作譯為中文,直到20世紀末葉,商務印書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和其他有歷史眼光的中國出版社組織翻譯西方的哲學、歷史、文學和其他學科著作,西方的科學技術和人文社科書籍也被大量翻譯介紹到了中國。這些翻譯出版活動,不但促進了中學西傳和西學東漸的雙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華文明的新陳代謝,以及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
清末以來,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取長補短”的歷程,經歷了兩大階段。第一階段的主導思想是“師夷長技以制夷”,表現為洋務運動之向往“船堅炮利”,追求“富國強兵”,最多只求學習西方的工業技術和物質文明,結果是以優勢的海軍敗于日本,以軍事的失敗表現出制度的失敗。第二階段的主導思想是“民主加科學”,表現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尊崇“德賽二先生”,中國社會在幾乎一個世紀中不斷從革命走向革命之後,到現在仍然需要進行民主政治的建設和科學精神的培養。大體說來,這兩大階段顯示出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由十分膚淺到較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從物質層面深入到制度層面。
正如觀察一支球隊,不能光看其體力、技術,還要研究其組織、戰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樣地,觀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業、技術,還要研究其社會、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靈性。因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質、制度和精神三個不可分割的層面,合其一則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覺或不自覺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到了20世紀末葉,中國終于有了一些有歷史眼光的學者、譯者和出版者,開始翻譯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層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從而開啟了對西方文明的認識由較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從制度層面深入到精神層面。
與此相關,第一階段的翻譯是以自然科學和技術書籍為主,第二階段的翻譯是以社會科學和人文書籍為主,而第三階段的翻譯,雖然開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實際上,基督教對世界歷史和人類社會的影響,絕不止于西方文明。無數歷史學家、文化學家、社會學家、藝術史家、科學史家、倫理學家、政治學家和哲學家已經證明,基督教兩千年來,從東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經極大地影響,甚至改變了人類社會從上古時代沿襲下來的對生命的價值、兩性和婦女、博愛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勞動和經濟、科學和學術、自由和正義、法律和政治、文學和藝術等等幾乎所有生活領域的觀念,從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這個誕生于亞洲或“東方”,傳入了歐洲或“西方”,再傳入亞、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現在因為信眾大部分在發展中國家,被稱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來就不屬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國家沒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經不僅僅在宗教意義上,而且是在現實意義上展現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質。
因此,對基督教經典的翻譯,其意義早已不止于“西學”研究或對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對世界歷史和人類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這里所謂“基督教經典”,同結集為“大藏經”的佛教經典和結集為“道藏”的道教經典相類似,是指基督教歷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師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視為唯一神聖的上帝啟示“聖經”。但是,由于基督教歷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師名作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絕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樣結集為一套“大叢書”,所以,在此所謂“經典譯叢”,最多只能奢望成為比佛藏道藏的部頭小很多很多的一套叢書。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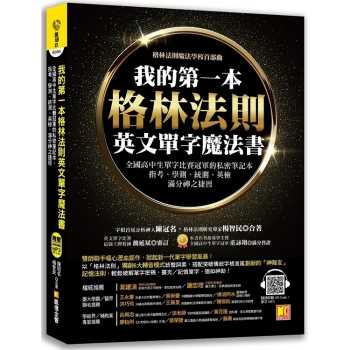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