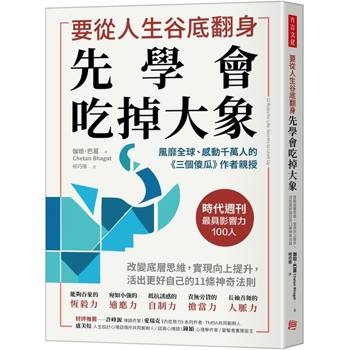中譯本序
我非常有幸能為中國讀者寫下這份序言。我在這本書中想要強調兩點。第一點,與很多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家一樣,我寫這本書受到了19 世紀政治家、理論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1805— 1859)的啟發。他的家庭生活遭到大革命的重創,儘管如此,他還是承認了大革命的偉大之處,寫出了《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 年)這部經典著作。由於他患上肺結核而早逝,這部著作並未完成。 1831 年, 年僅26 歲的托克維爾曾經到“新世界”遊歷,出版了早期社會學的經典著作《論美國的民主》(2 卷本,1835 年,1840 年)。
托克維爾對於法國大革命的主要觀點是中央權力的連續性,從路易十四(1638—1715)到1799 年通過軍事政變奪權的拿破崙?波拿巴, 強有力的中央集權一以貫之。儘管在法國大革命初期,國民公會試圖通過民主和地方機構來使決策去集權化,1792 年革命戰爭的需要促使革命家們再一次將權力集中。在托克維爾看來,大革命最根本的變化在於摧毀了“封建主義”的機構,這些機構既包括由貴族主導的傳統團體也包括全國各地封建制、領主制的殘餘。大革命試圖用基於人民主權和自由的新體制來取代古老的封建制度。但是法國與美國不同的是,美國社會的發展建立在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之上,法國人民仍然依賴中央權威。
托克維爾認為大革命起源於教士、貴族和第三等級這三個傳統的等級之間日益擴大的分裂。上層貴族主宰了法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教會在內,那些位高權重的人越來越不履行他們的義務(法國諺語有云“位高則任重”)。大多數貴族對於1789 年前必要的財政和社會改革根深蒂固的敵視源於兩個長期因素。首先,正如托克維爾總結的那樣,君主制國家決策的壓力由於治理和保護殖民帝國的支出而進一步加劇,進而損害了貴族特權。其次,貴族面臨著比他們人數更多、更富有、更具批判精神的資產階級的挑戰,農民對於貴族的財產、等級和社會地位也越來越感到不滿。
法國的社會政治體制在18 世紀80 年代處於危機之中。王權及其貴族精英的合法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質疑,來自社會的批評空前尖銳和深刻。領主體制及其繁多的特權日益成為一種收入來源而不是社會秩序的支柱。托克維爾認為,到了18 世紀80 年代,領主幾乎很少出現在社區之中,農民交納的封建租稅與從領主那裡獲得的貧困救濟、保護和幫助已經不再對等。儘管托克維爾出身貴族,他明白貴族制度已經“失效了”,因為理論上貴族特權的合法性已經不再合理了。一個日益富有的、人數眾多的中間階級(資產階級)開始追求自身利益, 而且在托克維爾看來,這個階級中有一些理想主義的個人,深受啟蒙運動抽象概念的影響。到了18 世紀80 年代,階級分化已經完成,產生了大革命時期的社會對立在《論美國的民主》的結論中,他對整個西半球的根本性變化充滿了信心,但也擔心這些變化導致的結果:
我們時代的國家無法阻止人類的境況走向平等,但是平等的原則究竟帶給我們的是自由還是奴役,文明還是野蠻,繁榮還是痛苦,都取決於我們自己。
20 年後,他在寫作《舊制度與大革命》時,在結論中寫到法國大革命實際上帶給法國人的是奴役、野蠻和痛苦,但是這個悲觀的結論來源於他個人從1848 年開始對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敵視。
很少有人在提及托克維爾的卓越思想時將他的個人經歷考慮在內, 人們經常將他描述成一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但是他一直處在國家動盪和痛苦的旋渦之中。他於1805 年出生在一個顯赫的諾曼貴族家族, 他的祖先曾經參加過1066 年黑斯廷斯戰役和對英格蘭的征服。他所處的家庭和社會等級深受大革命的創傷。他的父親埃爾韋是托克維爾伯爵,曾經擔任路易十六衛隊的軍官,他的母親路易絲?瑪德萊娜?勒佩勒捷?德羅桑博是法國著名政治家沃邦和拉穆瓦尼翁的親戚。他們在1793 年結婚。第二年差點被送上斷頭台。路易絲的祖父拉穆瓦尼翁(路易十六的首相和最終判決的辯護律師)和雙親都被判死刑,她的大姐和姐夫也同樣喪命。
雖然托克維爾的家族在大革命中遭遇悲慘, 但在七月王朝(1830—1848)和第二共和國(1848—1851)時期,托克維爾本人試圖將有限的選舉和立憲君主制融入法國的政治生活中。他曾經擔任議會代表和部長,在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於1851 年依靠軍隊奪權後,他放棄了從政。他從此以後全身心投入《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寫作中。他的傑作深受他1848 年後兩次短暫的從政經歷的影響:他對1848 年6 月的內戰感到恐懼,隨後被路易?拿破崙的政變排斥出政壇之外。因此,他認為1789 年後革命變化的暴力打碎了傳統的社會秩序, 他所處的時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階級分化和衝突。托克維爾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在自己家族的命運之上思考他所處的時代變遷。
我想強調的第二點是我在這本書中試圖闡釋法國大革命的特殊途徑。在全球化的21 世紀,我們更加重視法國大革命的全球意義及其國際影響。歷史學家曾經認為法國大革命本質上是一場動亂,但是現在我們不僅意識到了大西洋和北美在法國大革命起源上的意義,還進一步看到了法國大革命在西歐之外的影響,尤其是在大西洋沿岸地區和地中海地區。革命戰爭的確是“第一次總體戰”。與所有大革命一樣—英國、美國、俄國和中國的革命—法國大革命在內戰和外國干預中誕生。但是這些革命最終取得勝利的代價都是數不清的生命。
而與所有大革命一樣,這同樣是一場全國范圍的革命,革命的成果不僅體現在首都之中,還體現在擁有97% 的全法國人口的鄉村和城鎮之中。各地對於革命的態度來源於特殊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狀況。各地的人民無論歡迎還是反對變革,都不能拒絕變革。與托克維爾和幾乎所有之前的大革命研究不同是,我不僅試圖將大革命置於全國和國際的背景下來理解,還試圖將其置於每個社區的每個家庭之中來理解。革命給人們的經歷各不相同,卻影響了所有人。革命對於日常生活的衝擊遠比托克維爾的描述更加複雜和深刻。例如,我在書中強調了繼承法的改革和臨時廢除砍伐樹木與開墾荒地禁令的影響。
現當代的每一次大革命—17 世紀的英國革命、18 世紀的法國革命和20 世紀的中國革命—都具有其獨特性,它們都是特殊的社會、歷史和危機的產物。但是所有的大革命都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遷,也由此產生了影響深遠的國內和國際衝突。所有的大革命對於每個親歷者來說都是一場從根本上改變生活的劇變。我試圖在這本書中抓住的就是法國人鮮活而厚重的經歷。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