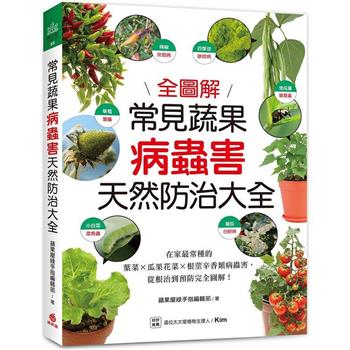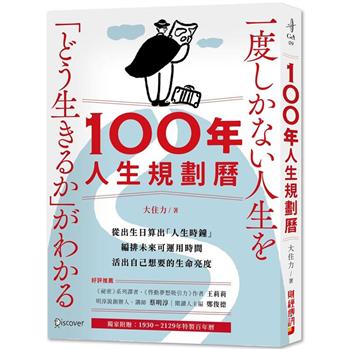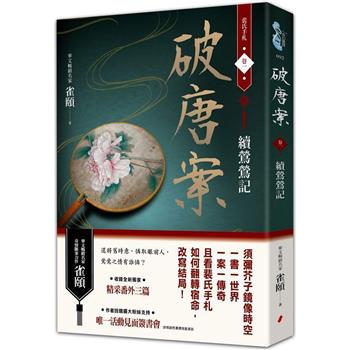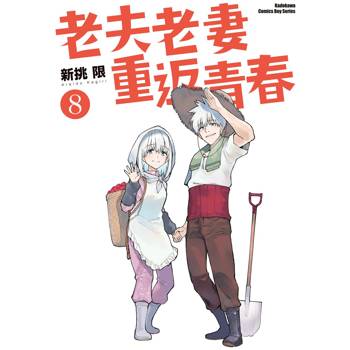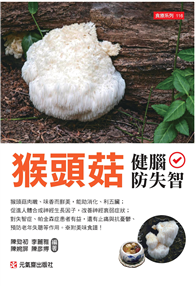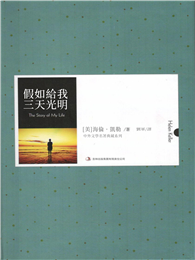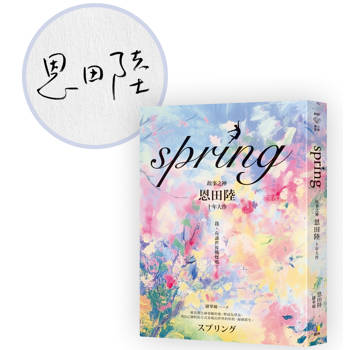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丹麥〕齊克果的圖書 |
 |
$ 276 ~ 332 | 哲學片段
作者: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 譯者:翁紹軍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25-03-28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56頁 / 14.8 x 21 x 1.2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齊克果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哲學片段
內容簡介
丹麥哲學家齊克果以哲思的方式來考察或描述基督教的信仰,將主耶穌的信仰敘事與蘇格拉底之求知相並置,在知識與信仰、蘇格拉底遺訓與福音書之間的緊張中展開思想論辯,揭示了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出發點和立場,論述了信仰是什麼,解釋了在信仰中永恆與瞬間的關係:信仰是神對人的愛、降卑的神對人尋找和拯救;而在人的這一方面,永恆和歷史統一在一種悖論中,需要作為跳躍的信仰去把握。據此,齊克果批判了其生活時代基督教信仰知識體系化及世俗權威氾濫等傾向。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齊克果(丹麥語:Søren Aabye Kierkegaard,又譯索倫·奧貝·克爾凱郭爾、祈克果、吉爾凱高爾等;1813年—1855年)是丹麥神學家、哲學家、詩人、社會批評家及宗教作家,一般被視為存在主義的創立者。創作許多關於制度性宗教、基督教、道德、倫理、心理學、宗教哲學的批評文章,這些文章常充斥著隱喻、諷刺和寓言。他的哲學作品主要關注人如何成為「單一的個體」,注重人類現實而非抽象思考,並強調個人選擇和實踐的重要性。他反對當時唯心主義知識分子和哲學家的文學批評,並認為那些所謂的「學者」還未能完全理解史威登堡、 黑格爾、費希特、謝林、施勒格爾、安徒生等人的思想。
齊克果的神學作品關注基督教倫理,宗教團體,基督教客觀證據間的差異,人神之間性質上的無限差異,個體與神人耶穌基督之間源於信仰的主觀關係。他的許多作品都與基督教之愛相關。對20世紀的哲學、神學、文學均有深遠影響。
譯者簡介
翁紹軍
廣東潮陽人,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外國哲學研究室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古希臘哲學、存在主義哲學、古代宗教、現代宗教倫理。
目錄
《哲學片段》導 讀
中譯本前言
緒 言
第一章 思考方案
一
二
1.先前的狀態
2.教師
3.信徒
第二章 身為教師和救世主的上帝—一個詩人的冒險
第三章 絕對的悖論—一個形上學的奇想
附錄 悖論的冒犯—一種聽覺的幻想
第四章 與主同時的信徒的處境
插曲
一、趨向實存
二、歷史的
三、過去的
四、對過去的理解
附錄:應用
第五章 再傳的信徒
一、再傳信徒的區別
1.第一代再傳信徒
2.新近一代再傳信徒
3.比較
二、再傳信徒的問題
跋
譯者後記
人名索引
齊克果年表
中譯本前言
緒 言
第一章 思考方案
一
二
1.先前的狀態
2.教師
3.信徒
第二章 身為教師和救世主的上帝—一個詩人的冒險
第三章 絕對的悖論—一個形上學的奇想
附錄 悖論的冒犯—一種聽覺的幻想
第四章 與主同時的信徒的處境
插曲
一、趨向實存
二、歷史的
三、過去的
四、對過去的理解
附錄:應用
第五章 再傳的信徒
一、再傳信徒的區別
1.第一代再傳信徒
2.新近一代再傳信徒
3.比較
二、再傳信徒的問題
跋
譯者後記
人名索引
齊克果年表
序
導讀
一、.齊克果的生平與思想背景
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一八一三–一八五五)出生於丹麥哥本哈根,是位憂鬱且多產的作家。他在哥本哈根大學攻讀神學學位,亦涉獵歷史、文學、哲學與心理學,作品涵蓋神學、文學批評、心理學和宗教學。他對當時的社會和基督教的改革提出許多針砭之言,對於哲學更有重大的突破性見解。他在短短四十二年生命裡,寫下無數的作品。《哲學片段》是在一八四四年出版的,當時以約翰尼斯‧克利馬科斯 (Johannes Climacus) 為託名,並註明為齊克果所編。
約在一八四二年十一月至隔年四月間齊克果撰寫一部以懷疑為主題未完成的自傳式作品,他過世後才以《懷疑者》的書名出版。此書披露了齊克果的性格與興趣,以及和父親的關係,因為論述的主題和《哲學片段》有許多關聯,藉之我們可從他的自述直接了解其生平,也可對他環繞終生的問題,關聯到所傳承與改造的思想來做剖析。
總體而言,我們在《懷疑者》裡看到齊克果掙脫體系性思維,在突破黑格爾的思想;他批判哲學之以懷疑為起點,在超越蘇格拉底、皮浪(Pyrrho,西元前三六○–二七二),與笛卡兒的懷疑論。齊克果走向了信仰之路,但這個信仰不同於傳統以及當時教會對信仰的理解。我們在這裡看到齊克果從時代的背景脫穎而出,走向自己之路。
再仔細言,我們在《懷疑者》的「引子」裡,讀到齊克果以約翰尼斯‧克利馬科斯為託名的自述:他「享受淡泊隱逸的生活」,外表纖柔、空靈,靈魂富理性、重精神,女人和美色打不動他,熱戀著思考(頁五十六)。父親是「方正古板」的人,看上去是「寡淡無味」,但「在粗獷樸素外表下隱藏的卻是光芒萬丈的想像力」(頁五十九)。他在經常與齊克果外出散步中,無所不知地對於周遭事物細緻描繪,讓齊克果以為「這世界彷彿是在談話過程中才形成的」,而種下齊克果豐富想像力的因,父親許以「將自己最漫無邊際的狂想與幻念嵌入這世界」(頁六十)。齊克果更耳濡目染了父親常與人對談時,如何將想像力與辯證法結合在一起:父親讓對手說盡了才開始回答,但剎那間,對手覺得明確的突變成可疑的。鑑於父親一個字就扭轉全部,齊克果也學到如在直述句中加了假設語氣,就可將整個句子賦予新的含義(頁六十二–六十三)。他也在父親的影響下,堅信志向可以解決所有道理,從而常鼓舞著自己奮鬥冒險(頁66)。
他自幼受即接受豐富的精神糧食,拉丁文、希臘文的文法及箇中的哲學意涵,讓直覺的想像力往無盡的時空延伸。想像力的神遊包括感情與理性,但對於事物的感受力也被陶鑄得極為敏銳(頁六十一–六十二)。故齊克果從幼年起觀念世界開發,但對於現實世界的信念不改,甚至觀念世界成為他的現實世界,或期待從現實中找到觀念世界。這個現實與觀念的結合,成了齊克果在《懷疑者》與《哲學片段》裡論述的根本訴求,從哲學思維轉到信仰的關鍵所在。
我們在其他 (維基百科:「索倫‧奧比‧齊克果」) 關於齊克果的介紹裡,讀到其父親邁克爾‧齊克果(Michael Pedersen Kierkegaard)原來是位羊毛富商,他在二十九歲那年妻子病故,隔年娶了安妮‧索倫斯坦德(Anne Sørensdatter)。安妮陸續生下六個孩子,索倫‧齊克果是他們最小的兒子。自從再婚以後,麥克爾就不再經商,寧願把更多的時間放在讀書與研討宗教問題上。在哲學方面,特別影響到齊克果的是柏拉圖對話錄裡蘇格拉底的形象:他以懷疑、對於「無知」的自覺為出發點,常以譬喻與反諷的語言來談話,繼而以接生婆的方式傳授真理,成了齊克果畢生一方面傳承,但另一方面批判的最重要資產。在宗教方面,父親將幾位孩子夭折早逝,歸之於自己受到上帝的懲罰,因他早年曾輕率地詛咒上帝,有幾位孩子又是安妮生前懷孕。鑑於此齊克果日後主張,人在受到上帝寬恕後應該不再承受罪惡與懲罰的負擔,他在《懷疑者》、《哲學片段》,及其他著作裡對之有所呼應,強調在「瞬間」的懺悔、信仰、愛,從而能讓許多罪移除掉(《愛在流行》,頁二七八)。至於母親安妮從未在齊克果的著作中提及,但其兄弟彼得在作品裡多次提到母親的話語,表達出母親始終保護與眷顧著索倫與彼得,她實也對孩子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齊克果的思想特徵
我們不欲對齊克果的思想特徵全面介紹,而寧願先指出其要點,為了之後對《哲學片段》的思想闡發做準備。由於《懷疑者》是對於作為相關問題結論之《哲學片段》的思考過程,故值得先對《懷疑者》梗概地說明。
眾所周知,齊克果曾將人生分為「感性」、「理性」和「宗教性」三個階段,《非此即彼》就分別以唐璜、威廉法官與亞伯拉罕為代表這三階段的人物,當然就齊克果而言,蘇格拉底仍停留在倫理的階段,至少不是基督宗教的階段。而齊克果的著作就表達與論述的方式而言分為哲學與宗教兩個時期。這兩種不同的表達與論述方式反映到齊克果分別以託名與否為其作者。而據《懷疑者》的審譯者與《哲學片段》的譯者翁紹軍之見,宗教性的著作是齊克果基督教信仰的直接表達,故不需要託名,託名則是齊克果間接地傳達真理。翁紹軍以為這個時代需要引導人去反對自己的意志,才能把真相顯示給人;他以為齊克果在模仿柏拉圖對話錄裡描述蘇格拉底的辯證法,像蘇格拉底只是真理的助產婆一樣,不直接將真理給予對方(《懷疑者》,頁七十二–七十三)。
這就是所謂的「間接溝通」(indirect communication)方法,據之我們不直接以表達義理的方式來傳遞某個哲學或思想的意涵,而以諷刺、類比、隱喻、敘事等方式來表達意涵;換言之,就是不直接以出自意識、具主動的、因而出自意志的知性概念來表達,而以富有感情的、具文學性或詩性的語言表達,讓讀者不只知性的,更是感性地、同理地,甚至情韻共鳴地來具體理解思想的意涵。
蘇格拉底對於真理以助產士的方式傳達,固然也屬於間接溝通,但這種間接性並非齊克果所訴求的。這就涉及蘇格拉底的懷疑、自覺無知,從而對之化解,對齊克果而言只留在倫理,而未達到基督宗教的存在層次。齊克果對於懷疑議題的提出,在基督宗教裡到底有什麼建樹呢?
齊克果從哲學層次的懷疑問題,走向宗教層次的懷疑問題。鑑於哲學層面的三個命題:哲學由懷疑開始、哲學思考前先有懷疑、近代哲學由懷疑開始 (頁八十七),他主要提出它們是哲學史的時間前後問題,或是哲學系統的邏輯先後問題,後者其實是在觀念性的永恆層次。所以齊克果就討論歷史中個別提出或思考懷疑問題的人,是否包含在屬於觀念性懷疑問題的系統之內(頁一一○)。他繼而從哲學有起於驚訝與起於懷疑的不同說法,區別前者是當下的,後者是反思的(頁一二六),進而關聯到一般的說法:當下的意識是不確定的,對它的懷疑是一種反思,反思需要以觀念性語言去建立與之前當下意識間的關係。但不論是否定或肯定原先的當下意識,都需要觀念性語言對於當下意識做判斷,這是永恆與時間之間關係的問題。觀念性語言是否就扮演著它們之間的中介角色,而即便如此,這個角色可以完成嗎?(頁一八一–一八三) 這就涉及後面要說的宗教層次之永恆與時間結合的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齊克果提到希臘皮浪的懷疑主義是對於周遭的事情抱持著無利害的態度,因而可以寧靜地過生活(頁一二八),這應該也是對於早先蘇格拉底的提問:「人應該怎麼生活?」的一種回答。它既然涉及實踐生活,那麼這個懷疑雖是「抱持無利害的態度」,但皮浪學派的懷疑主義卻是涉及個人的存在,而非認識的問題,故它是一種對於存在有利害關係的懷疑主義。這個「利害」的德文字Interesse拆解為Inter-esse,意義是「介入存有」,指的就是對於存在有利害關係。笛卡兒的懷疑方法欲謀求一個不容懷疑的「我」,是將原先人的存在生活以一個不動搖的基礎來做起點,這個經過反思所建立的「我」卻是從原先有利害的存在性轉為無利害的知識性活動的主體,故笛卡兒的懷疑主義基本上是沒有介入存有的(頁一八五–一八七)。蘇格拉底提出「人應該怎麼生活?」的問題,他與皮浪仍處在倫理的層次,皆不滿足於齊克果經由懷疑所訴求的基督宗教生活。《哲學片段》就在針對此做討論。
三、《哲學片段》的精髓
本書一開始就在討論齊克果與蘇格拉底有何不同。蘇格拉底認為真理不能直接傳達,他在市集與他人展開辯證式的交談,是在提醒他人對無知的自覺,從而回憶起已經知道的東西,這樣蘇格拉底就扮演助產士的角色,讓他人自己尋回真理。蘇格拉底也相信神明,但神明委託他只扮演助產士的角色,讓每個人自己尋獲真理,自己認識自己以及神明的意旨(頁十二–十九)。蘇格拉底這種不以權威自居的性格(頁二十–二十一),反照出齊克果當時教會牧師的權威性。鑑於此齊克果雖讚許蘇格拉底,但以為教師不可能幫助門徒回憶起自己已經知道的真理,教師只提供門徒認識真理的條件(頁二十五)。甚且這個條件是門徒自己失去的,又因爲他們遠離了上帝,故為本質的而非偶然的失去。門徒因自身的過錯而處在沒有真理的狀態,他們一旦擺脫這被稱為罪的自我束縛,那麼就能得到解脫(頁二十六–二十七),沒有真理的狀態就會全然消失,從而門徒回到與上帝的親近關係。蘇格拉底在倫理的層次,而齊克果在基督宗教的層次,它們的區別更要從時間與永恆的關係取得根本的意義。
蘇格拉底扮演著讓每個人從自覺無知到回憶已知的真理之一種中介的角色,但蘇格拉底在對話裡表示對於至善追求是在無限的的歷程中,從具時間性的存在生活裡試圖回答「人應該怎麼生活?」之具永恆性的實踐真理,似乎因為答案沒有終點而一直不能超出時間而至永恆。齊克果主張的基督宗教就其本質而言,從無知到知,從時間性到永恆性,「瞬間」扮演著中介的環節。由於在一霎那間的短暫,「瞬間」的中介讓時間與永恆結合起來。其實作為教師的上帝也扮演著中介的角色,但上帝之為中介是轉化為人子的耶穌,上帝同時具有時間性與永恆性。
齊克果對於作為中介的瞬間、耶穌闡發甚多。因為門徒不是以回憶去尋回自己固有的真理,它反而要回憶自己沒有真理,故重新親近上帝獲得真理是從「無」到「有」轉變的重生(頁三十三–三十七)。經由永恆在「瞬間」臨現於時間,上帝以最低賤的身分顯現在人間,這個顯現是出於上帝的愛。但上帝以奴僕般低賤的身分去愛人類,不易得到人以愛來回饋,終至要以自我犧牲為代價。這樣的「上帝讓自己生根在人的弱點之中」,才能使人「成為一個新人和一個新的容器」(頁五十九–六十七)。
在「瞬間」人與上帝遭逢,時間與永恆接觸,是經由一種「悖論」發生的,故「悖論」也是一種中介。人與上帝之間本存在著差異,而當上帝轉化為人子,與自己也產生差異,讓人既與耶穌等同,在等同中發現差異,又繼而和上帝親近,這些關聯被描寫為「悖論」(頁八十八–九十)。因為人與上帝的接觸不是靠理論,而是靠存在的關聯,齊克果在各種著作對這個關聯闡發,但總是從人的存在生活 (頁九十一–九十二),而非既定的教條出發。於是我們常讀到一些概念,如「冒犯」就是其一。
對於人與上帝間的差異不能了解,但故做遭逢,就產生了「冒犯」,同時也在於不了解耶穌的角色是作為人與上帝的中介而來。唯這不是認識的冒犯,而是存在的冒犯。冒犯的根本原因在於尚無罪的意識。罪起源於於人與上帝的隔離,人子的身分似乎要將這個隔離轉為親近,但親近並非差異的消失,既差異又親近的關係就顯示了一種悖論。唯不了解這種悖論,從而心生冒犯,就是有罪,但尙沒有罪的意識 (頁九十四–九十九)。一旦上帝轉化為人子的過程啟示了人罪的意識,才有在差異中親近上帝的可能。這個罪與冒犯的進程,透過人對自己存在生活的絕望問題,進而產生在瞬間中的信仰,成了後來《致死之病》的論述主軸。
本書最後的重點是循著在瞬間中悖論而生信仰的這個論述發展而來的,是探討與上帝真正同齡的意義是什麼?齊克果常對照教師作為蘇格拉底與教師作為上帝:蘇格拉底是讓他人回憶自己固有的真理,故蘇格拉底對於學生是在歷史上一種機緣的遭逢;上帝轉化成人子與當時的門徒或同時代的人遭逢,若要區別於蘇格拉底之僅為機緣的,那麼就要循著上述的在「瞬間」的悖論問題,且在罪的意識中產生信仰,唯有在「瞬間」中的信仰才能形成不論一般人、門徒、幾世代的再傳信徒與上帝為真正同齡的條件 (頁一二七–一二八)。
四、從《哲學片段》看齊克果對後世的影響
齊克果在《哲學片段》裡,以基督宗教的立場和希臘哲學的立場做區別,去論述上帝與蘇格拉底作為教師之分別與學生的不同關係、不同傳達真理的方式。真理涉及永恆性的觀念,人在時間中企圖和永恆性做連結。蘇格拉底哲學指出人必須經由時間的回憶去尋獲永恆的真理,其後的黑格爾哲學試圖將永恆轉化成人的歷史行程,讓真理在歷史的辯證發展中逐步實現。不論希臘或黑格爾影響到齊克果時代以及後世的基督教神學,就形成了自由派神學以人類歷史的觀點對於《新約聖經》過度強調耶穌之神性記載做批判式的解讀(李麗娟,頁一一六)。
齊克果在《哲學片段》提醒我們,「問題的實質是上帝曾經顯身人樣來到人世間這個歷史事實,而其他歷史細節並不那麼重要。」(頁一九四)而與主同時代的人僅留下這句話就綽綽有餘:「我們確曾相信過,上帝在某年顯身為謙卑的奴僕,他生活在我們中間,教導我們,然後死去。」(頁一九五)若純以人類歷史的觀點來看,當時信徒與上帝的遭逢也是一種機緣。但從「我們確曾相信,上帝顯身於我們中間,教導我們,然後死去」的上帝基於愛從永恆轉向時間,人基於信從時間轉向永恆的觀點而言,這卻是「瞬間」的事。這個主張影響到後世包括辯證神學在歐陸的興起(李麗娟,頁一一七)。
辯證神學傳承了齊克果對於以人本主義、啟蒙運動,從而以人的智慧來解經的教會的批判。《哲學片段》對於歷史來看之與上帝同時的信徒和再傳信徒間關係差別無關緊要的主張,啟示了巴特(Karl Bath)訴諸於人要直接領受上帝話語,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則從存在主義出發,共同去論述在瞬間之悖論與信仰的關係 (李麗娟,頁一一七,維基百科:「新正統神學」) 。這對於現今的教會界仍扮演著暮鼓晨鐘的角色。
參考資料:
李麗娟。〈祁克果的「同時性」、「瞬間」概念論詮釋與神學〉,《台灣神學論刊》二○一二年三十五期,頁一一三–一三六。
索倫‧克爾凱郭爾(齊克果)。《非此則彼》,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七。
齊克果。《懷疑者》,臺北市:城邦文化,二○○五。
齊克果。《愛在流行》,臺北市:商周出版,二○一五。
齊克果。《致死之病》,臺北市:商周出版,二○一七。
齊克果。《哲學片段》,臺北市:五南書局,二○二五。
維基百科詞條:「索倫‧奧比‧齊克果」、「新正統神學」。
汪文聖
二○二五年一月國立政治大學達賢圖書館學人研究室
|
 索倫·奧貝·齊克果是丹麥神學家、哲學家及作家,一般被視為存在主義之創立者。
索倫·奧貝·齊克果是丹麥神學家、哲學家及作家,一般被視為存在主義之創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