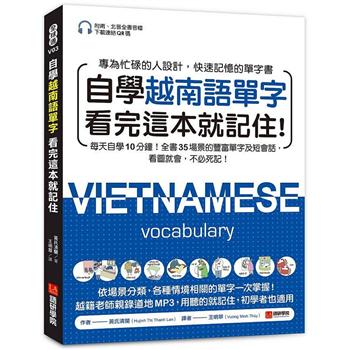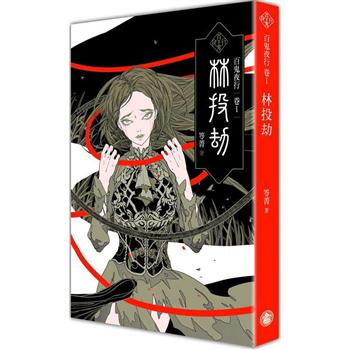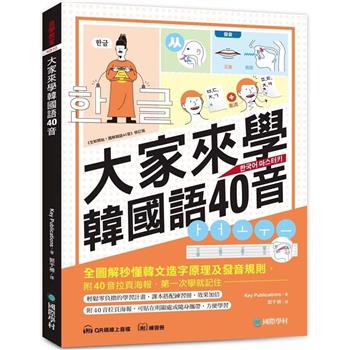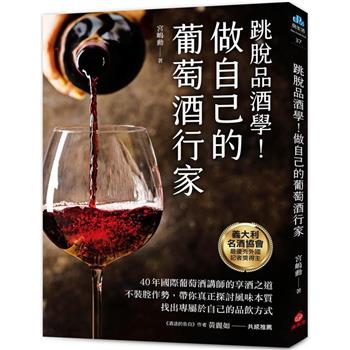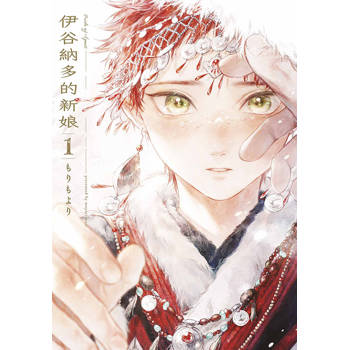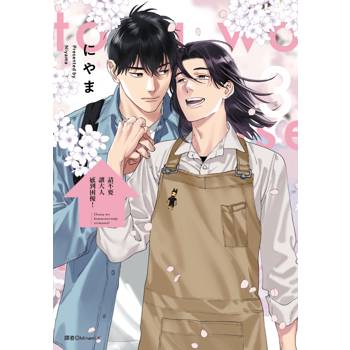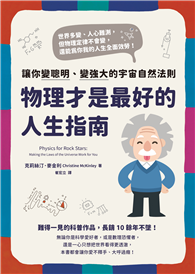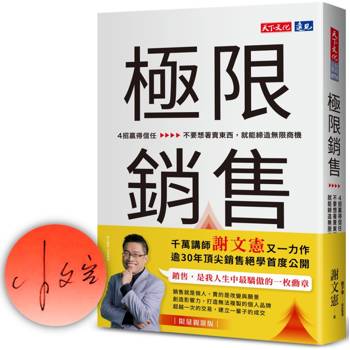第二章 身為教師和救世主的上帝
一個詩人的冒險1
1.《哲學片段》作為一個「想像的建築」,其構想者,當然就是一個詩人。正在這個意義上,「作者」克利馬科斯常自稱「詩人」,並把《哲學片段》稱為一首詩。
讓我們思考一下蘇格拉底,2他實際上也是一位教師。他生於一個特定的處境,受到家鄉父老的薰陶;他到了更成熟的年紀,便受到一種召喚和激勵,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去開導別人。蘇格拉底一度是個尋常人,一旦時機看來成熟時,他就以教師身分的蘇格拉底出現。他本人受周圍環境的影響,同樣,他也對周圍環境施加自己的影響。他內心對自己所提的要求,就像別人可能要求於他的那麼多,為了完成他的任務,他都同樣的給予滿足。以這種方式去理解—而這實際上就是蘇格拉底的認識—教師介於一種交互的關係之中,因為生命及其處境是他成為一個教師的機緣,而他同樣又是別人學到一點東西的機緣。因此,他的關係總表現出自療﹝autopathy﹞的特點,就像感應對等的特點那樣。3
蘇格拉底也是這樣去認識這一關係的,因此他拒絕為從事教育而接受榮譽、地位和金錢,因為他斷定對這一切無動於衷的人是收買不了的。多麼難得的知足—這在當今更為難得,當今教育界的貪婪是再多的金錢和榮譽都滿足不了的,而它又只配用這世上的黃金和榮譽去酬賞,因為它們是等價的。但我們的時代畢竟有講究實際的一面,並且有這方面的行家,而蘇格拉底就缺乏這一面。4但要評價這種缺乏是否說明他的褊狹,那大概要以他熱衷人類的事務,以及他用跟訓誡別人一樣之神的妒忌5來訓誡自己,並因此作為熱愛神的根據。在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這是最高的關係:學生是教師了解自己的機緣,教師是學生了解自己的機緣;教師死時,並沒有留下任何要求給學生,只有學生能要求教師歸還他一點東西。要是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就成了某個柏拉圖,要是在聽到蘇格拉底時,我像阿爾基比亞德6那樣,內心怦怦劇跳,跳得比科里班忒們7更劇烈,要是我不向那位非凡的人獻上讚美的熱情,內心就平靜不下來,8那麼,蘇格拉底無疑就會譏笑我說:「我親愛的朋友,你肯定是位不誠實的情人,因為你是為了我的智慧才想把我當偶像崇拜的,而且你本人想成為最了解我的人並用你的讚美來套牢我,使我無法分身—你實際上不就是一個誘惑者嗎?」他解釋說,他能給我的就像我能給他的一樣多,要是我還不了解他,那麼,他無情的嘲諷,大概會使我心灰意冷。多麼難得的正直,不矇騙任何人,甚至不矇騙人們說他可以用自己的永恆幸福去下賭注。在當今年代這是多麼難得,當今年代不論在自我評價方面,還是在受惠於學生方面,在渴求社會承認方面,在把肉麻的讚美當有趣方面,每個人都是蘇格拉底所望塵莫及的!多麼難得的忠誠,不誘惑任何人,甚至對使盡所有誘惑技術,甘心想受他誘惑的人也一樣!9
2.如果說,在上一章中,更多地從認識論方面討論蘇格拉底,那麼在第二章,則更多地把蘇格拉底描寫成實踐的教師。
3.感應是相互對等的,因此,教師也是學生,學生也是教師。
4.這也許指黑格爾和黑格爾學派批評蘇格拉底缺乏積極的方面。比如,我們可以舉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卷二的兩段話,他說:「善是一個自身具體的原則,不過這個原則的具體規定還沒有被表達出來;在這種抽象的態度中,存在著蘇格拉底的原則的缺點。積極的東西沒有講出來,因為善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他還說:「我們所看到的,毋寧說只是現存法律在消逝;我們首先遇到的乃是:由於培養反思的意識,那在意識中有效的東西、習俗、合法的東西都發生動搖了。在這裡可以舉出,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約西元前四四六—西元前三八五,古希臘喜劇作家—譯者注﹞就是從這個消極的方面來理解蘇格拉底哲學的。阿里斯多芬對蘇格拉底的片面性的這種認識,可以當作蘇格拉底之死的一個極好的前奏,它說明了雅典人民如何對他的消極方式有了很好的認識,因而將他判處了死刑。」﹝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五七年版,第六十二頁,第七十六頁﹞
5.神的妒忌是指,「妒忌的」眾神不能容忍在他們之外有任何更偉大的東西存在。「神的妒忌」也是古希臘悲劇的一個主題,眾神為維護他們的特權,對於因傲慢﹝hybris﹞而超越自身界限的人類,往往由妒忌轉而變為懲戒。
6.阿爾基比亞德﹝Alcibiades﹞,蘇格拉底的學生和密友。他後來叛國,蘇格拉底被控蠱惑青年,這也是主要依據之一。
7.科里班忒們﹝the Corybantes﹞,信奉酒神的祭司,他們主持酒神的祭典,祭時擊鼓狂舞,以瘋狂的亂跳亂舞表達宗教熱忱。
8.齊克果的這些描寫跟柏拉圖的《會飲篇》﹝Symposium﹞有關。《會飲篇》講的是,悲劇家阿伽松﹝Agathon﹞的劇本上演得獎,他邀請蘇格拉底、喜劇家阿里斯托芬等人歡飲慶祝。他們決定由在座的每位依次輪流對愛神厄洛斯﹝Eros﹞作一番禮讚。當他們依次作了頌辭後,當權的青年政治家阿爾基比亞德帶著一些人前來祝賀,大家請他也作一個禮讚,他卻不去頌揚厄洛斯神而去頌揚蘇格拉底。他說:「朋友們,拿我自己來說,要不是怕你們說我完全醉了,我可以發誓,蘇格拉底的話對我產生過一種特別的效果,這種效果即使到現在我還感覺得到。我一旦聽他說話,心就劇跳起來,比科里班忒們在狂歡時還跳得更厲害;我的喉嚨像被什麼堵住一樣,眼淚奪眶而出,不僅是我,許多聽眾也有這樣的激情。」﹝215d-e﹞
9.見《會飲篇》﹝二一六—二一八﹞。阿爾基比亞德接著向在座的人說了自己向蘇格拉底求愛並遭到拒絕的情況:當燈熄了,傭僕退出之後,我直截了當地向蘇格拉底求愛,然後不容分說就溜進他的破大氅之下,雙手擁抱這個人,他卻真正令人驚奇,就這樣無動於衷地躺了一夜。我使盡所有誘惑招數都只能引起他的鄙視,他對於我引以為豪的美貌簡直就是一種嘲笑和羞辱。我和蘇格拉底睡了一夜,卻就像跟父親或兄長睡覺一樣。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哲學片段的圖書 |
 |
哲學片段 作者: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 譯者:翁紹軍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25-03-28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56頁 / 14.8 x 21 x 1.2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76 |
德奧哲學 |
$ 277 |
📌宗教79折起 |
$ 315 |
德奧哲學 |
$ 315 |
宗教命理 |
$ 326 |
中文書 |
$ 332 |
宗教命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哲學片段
丹麥哲學家齊克果以哲思的方式來考察或描述基督教的信仰,將主耶穌的信仰敘事與蘇格拉底之求知相並置,在知識與信仰、蘇格拉底遺訓與福音書之間的緊張中展開思想論辯,揭示了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出發點和立場,論述了信仰是什麼,解釋了在信仰中永恆與瞬間的關係:信仰是神對人的愛、降卑的神對人尋找和拯救;而在人的這一方面,永恆和歷史統一在一種悖論中,需要作為跳躍的信仰去把握。據此,齊克果批判了其生活時代基督教信仰知識體系化及世俗權威氾濫等傾向。
作者簡介:
齊克果(丹麥語:Søren Aabye Kierkegaard,又譯索倫·奧貝·克爾凱郭爾、祈克果、吉爾凱高爾等;1813年—1855年)是丹麥神學家、哲學家、詩人、社會批評家及宗教作家,一般被視為存在主義的創立者。創作許多關於制度性宗教、基督教、道德、倫理、心理學、宗教哲學的批評文章,這些文章常充斥著隱喻、諷刺和寓言。他的哲學作品主要關注人如何成為「單一的個體」,注重人類現實而非抽象思考,並強調個人選擇和實踐的重要性。他反對當時唯心主義知識分子和哲學家的文學批評,並認為那些所謂的「學者」還未能完全理解史威登堡、 黑格爾、費希特、謝林、施勒格爾、安徒生等人的思想。
齊克果的神學作品關注基督教倫理,宗教團體,基督教客觀證據間的差異,人神之間性質上的無限差異,個體與神人耶穌基督之間源於信仰的主觀關係。他的許多作品都與基督教之愛相關。對20世紀的哲學、神學、文學均有深遠影響。
譯者簡介:
翁紹軍
廣東潮陽人,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外國哲學研究室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古希臘哲學、存在主義哲學、古代宗教、現代宗教倫理。
章節試閱
第二章 身為教師和救世主的上帝
一個詩人的冒險1
1.《哲學片段》作為一個「想像的建築」,其構想者,當然就是一個詩人。正在這個意義上,「作者」克利馬科斯常自稱「詩人」,並把《哲學片段》稱為一首詩。
讓我們思考一下蘇格拉底,2他實際上也是一位教師。他生於一個特定的處境,受到家鄉父老的薰陶;他到了更成熟的年紀,便受到一種召喚和激勵,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去開導別人。蘇格拉底一度是個尋常人,一旦時機看來成熟時,他就以教師身分的蘇格拉底出現。他本人受周圍環境的影響,同樣,他也對周圍環境施加自己的...
一個詩人的冒險1
1.《哲學片段》作為一個「想像的建築」,其構想者,當然就是一個詩人。正在這個意義上,「作者」克利馬科斯常自稱「詩人」,並把《哲學片段》稱為一首詩。
讓我們思考一下蘇格拉底,2他實際上也是一位教師。他生於一個特定的處境,受到家鄉父老的薰陶;他到了更成熟的年紀,便受到一種召喚和激勵,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去開導別人。蘇格拉底一度是個尋常人,一旦時機看來成熟時,他就以教師身分的蘇格拉底出現。他本人受周圍環境的影響,同樣,他也對周圍環境施加自己的...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哲學片段》導讀
一、.齊克果的生平與思想背景
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一八一三–一八五五)出生於丹麥哥本哈根,是位憂鬱且多產的作家。他在哥本哈根大學攻讀神學學位,亦涉獵歷史、文學、哲學與心理學,作品涵蓋神學、文學批評、心理學和宗教學。他對當時的社會和基督教的改革提出許多針砭之言,對於哲學更有重大的突破性見解。他在短短四十二年生命裡,寫下無數的作品。《哲學片段》是在一八四四年出版的,當時以約翰尼斯‧克利馬科斯 (Johannes Climacus) 為託名,並註明為齊克果所編。
約在一八四二年十一月至隔年...
一、.齊克果的生平與思想背景
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一八一三–一八五五)出生於丹麥哥本哈根,是位憂鬱且多產的作家。他在哥本哈根大學攻讀神學學位,亦涉獵歷史、文學、哲學與心理學,作品涵蓋神學、文學批評、心理學和宗教學。他對當時的社會和基督教的改革提出許多針砭之言,對於哲學更有重大的突破性見解。他在短短四十二年生命裡,寫下無數的作品。《哲學片段》是在一八四四年出版的,當時以約翰尼斯‧克利馬科斯 (Johannes Climacus) 為託名,並註明為齊克果所編。
約在一八四二年十一月至隔年...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哲學片段》導 讀
中譯本前言
緒 言
第一章 思考方案
一
二
1.先前的狀態
2.教師
3.信徒
第二章 身為教師和救世主的上帝—一個詩人的冒險
第三章 絕對的悖論—一個形上學的奇想
附錄 悖論的冒犯—一種聽覺的幻想
第四章 與主同時的信徒的處境
插曲
一、趨向實存
二、歷史的
三、過去的
四、對過去的理解
附錄:應用
第五章 再傳的信徒
一、再傳信徒的區別
1.第一代再傳信徒
2.新近一代再傳信徒
3.比較
二、再傳信徒的問題
跋
譯者後記
人名索引
齊克果年表
中譯本前言
緒 言
第一章 思考方案
一
二
1.先前的狀態
2.教師
3.信徒
第二章 身為教師和救世主的上帝—一個詩人的冒險
第三章 絕對的悖論—一個形上學的奇想
附錄 悖論的冒犯—一種聽覺的幻想
第四章 與主同時的信徒的處境
插曲
一、趨向實存
二、歷史的
三、過去的
四、對過去的理解
附錄:應用
第五章 再傳的信徒
一、再傳信徒的區別
1.第一代再傳信徒
2.新近一代再傳信徒
3.比較
二、再傳信徒的問題
跋
譯者後記
人名索引
齊克果年表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