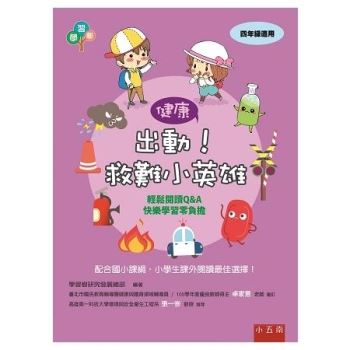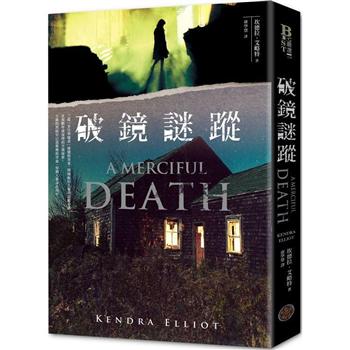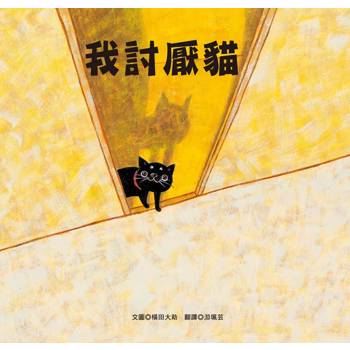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Pütz版編者說明
在錫爾斯—瑪利亞最後一次逗留時,約1888年8月底和9月初之間,尼采放棄了一直計畫的《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他決定發表出自手上已有材料的一個摘錄,標題為《一個心理學家的閒逛》。根據加斯特的異議,他用更具挑戰性的《偶像的黃昏》,代替了原先聽上去平淡乏味的簡單標題。那計畫分成四篇的《重估一切價值》的其他部分,發表在他的第一本書中,即在《敵基督》中。也就是說,這篇文字和《偶像的黃昏》產生於《權力意志》的筆記,而繼這樣的決定之後,後者在尼采的計畫中已無位置,除了那兩本經作者同意的書,它只能被當作遺著來讀。一個主要由施勒希塔(Karl Schlechta)和蒙梯納利(Mazzino Montinari)調查出的結果,而它徹底修正了關於所謂《權力意志》在接受史上頗具影響力的誤解。《偶像的黃昏》1889年才發表;尼采在前一年的11月已收到最初的樣書。這本新書產生於有關華格納的論著的範圍內,這由其新標題證明。它是對華格納的四部曲《尼伯龍族的指環》中第四亦即最後一部《神界的黃昏》的諷刺模仿性改變。尼采自己意識到這個衝擊方向,所以在1888年9月27日對加斯特寫道:
此外,格斯多夫(Gersdorff)鄭重其事地警告我小心華格納的女追隨者。偶像的黃昏這個新標題,也將在這個意義上被人聽見,也就是說,依舊是針對華格納的惡作劇……
簡短的前言解釋了標題:整個針對的是充斥著世界的許多偶像,而世人被不公正地和並非為了他們自己的幸福犧牲給他們。考察的方式是用錘子進行敲打(《如何用錘子進行哲學思考》),以便聽到,他們用腳站立的基礎如何不穩,發出的聲音多麼沉悶,又是多麼空洞。錘子在這裡的功能,不是建築或者摧毀的工具,而彷彿是心理學家的音叉。尼采把自己的書,理解為反對超時代地行之有效的偉人和權威、反對所有類型的理想及神祗的戰爭,而對他們的頂禮膜拜,他覺得是有違人類尊嚴的偶像崇拜。標題的第二部分可能語意雙關:它涉及虛假價值的沒落,就像華格納歌劇裡那些英雄如何沒落、眾神城堡的大廳如何燃起熊熊大火一樣,可它也指向早晨新的開端,那時新的意識開始蘇醒,明白眾神只是偶像,對它們的揭露有利於人類的自我解放。這個暮色降臨和晨曦初現(Abend- und Morgendämmerung)的雙重含義以後更清楚地得到表達,如平圖斯(Kurt Pinthus)就把他的表現主義作家文集稱為《人類的朦朧》(Menschheitsdämmerung, 1920)一樣。這個文集既宣告了與舊形式的決裂,也宣告了一種新人的誕生;面對那最恐怖的深淵,它沒有視而不見,而是充滿希望地把它提升到最陡峭的山頂。對於新生和沒落、價值顛覆和價值確立之張力具有典範意義的,是霍迪斯(Jacob van Hoddis)的詩歌《世界末日》以及策希(Paul Zech)的《新的山上寶訓》。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同樣具有這種雙重的識別力。
緊接著《偶像的黃昏》的前言,是帶有標題的十篇文字。第一篇(「格言與箭」)由警句組成,它們與尼采以前論著中的警句相似,比如在《朝霞》和《快樂的科學》中。其他篇章由較長的段落連接而成,它們在思維和表現風格上接近短小的散文,除了基本上是比較簡短和銳利的警句外,同樣給人以上所提兩本書的印象。《偶像的黃昏》的結尾由出自《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三部中要求堅硬的錘子的演說組成。
警句
「格言與箭」針對的是認識論、道德和心理學之基本準則形式中的偶像,針對的是這些基本準則那長久的效用或者甚至宗教上得到認證的莊嚴,還有讓那些偶像成為不可侵犯的原則,以及被人不假思索地接受的公理。這被視為千百年來對無條件地尋求真理的敦促,同樣被看作是對博愛的要求、信仰和良心的合法證明,並以同樣的方式被視為幸福追求的目標及目的。
打破固定僵化的觀點,發現偏見和指出「真理」之反面的合適的邏輯及修辭手段,是反題、顛倒和訛謬。對此有一個典型的例子:「男人創造了女人——究竟用什麼?用他的上帝的一根肋骨——即他『理想』的……」最初的顛倒在於,不是舊約中的上帝用男人的肋骨創造出女人,相反,這個男人(「用什麼做的?」),但不是用他自己的,也許用他的上帝的肋骨,創造了女人。可是那個上帝,那個男人從他身上取下一部分東西、似乎由此證實其肉體之事實性的上帝,其實並不存在,僅僅是男人為了安慰自己而創造出的虛構的理想。因為,根據尼采的觀點,他的生命力已經衰退,所以他需要一種精神和宗教的補償。於是,用他的材料被捏成的女人,根據其出身,如同理想,依舊被證明是虛構,也就是:上帝。與他一樣,她也極佳地適合頹廢。那個生命力衰退的男人,為了分散別人對他自己的衰弱的注意力,把女人抱上祭壇,然後對上帝和女人頂禮膜拜。那個據說是真實的女人繼續保持隱蔽狀態,也可能與他捐贈肋骨的行為一樣,是非現實的。因為兩者的存在既無法證實,又無法證偽,男人就根據自己的意願和妄念製作他們。
在少量句子裡,在一個單句或如同這裡在一個簡潔的問答模式中的集中和強調,它們會追求警句的句式。在這樣的句式中,多維度的思緒彷彿彙集一處,同時具有新的啟發思維的功能。「警句」(Aphorismus)這個概念來源於希臘語動詞aphorízein,表示「區分」(abgrenzen)。因此,透過標明與其最臨近的更高一級的普遍性之特殊的差異,來突出一種現象,這樣一個任務對他來說恰好相宜。但事實上,警句針對的不怎麼是一種形式邏輯的確定,而更是一種與有效事物的「區分」。在《偶像的黃昏》裡,他正是想對這樣的事物,透過叩問和傾聽的方式,進行審視,批判,必要的話還進行糾正。與警句不同,諺語在其使用的語境中含有論證的特點,被使用在一篇演講的某些地方,常常組成一項修辭闡述的高峰。諺語在字面上結束一個思維進程,而警句首先想做的,是啟動一項思維活動。比如「遭火燒者,見火就怕」這樣的短語,建立在常年的經驗上,被視為正確,受到多數人的證實。但一個這樣被認可的真理同時會變得多餘,成為陳腐之理。相反,警句與眾不同,打破常規,以其自身具有的違逆,道出新意。它那強調意外的傾向性,讓它作為傳奇小說(Novelle)的近親或者傳奇出現;它與戲劇性辯論的戰鬥性一樣,具有好鬥的姿態。由於它表現的剛好不是一清二楚和容易把握的事,就讓聽眾和讀者感到不那麼輕鬆,相反要求別人,為了理解的緣故,做出更加聚精會神的努力。警句並非易懂好記,它要求好思者對它深究。
警句在許多方面受主體性的影響。如果說諺語大多來源不清,那麼警句反對業已穩定的一致,並且源自某個作家,而這個作家絕不拒絕獨自和執拗的思維及感覺方式。其內容並非建立在一種可以客觀化的洞見上,相反依據的是一名個體人的經驗和認識。所以,它表述的不是一個群體、一個階層、一個民族或者一個文化階段的智慧,同樣,它也放棄對通用的座右銘和格言之普遍有效性的要求。與其說通過其邏輯,不如說通過其修辭,它具有更強烈的效果。與其說它是明智的,不如說它是挑釁的。它還以接連不斷的提問,製造出更多新的騷動,而不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它既不宣告可以證明的事實,也不羈留在任何一個穩固可靠和輪廓清晰的系統中。它的任務不是建立廣泛的關聯,而是對某個單獨的觀點進行推向極至的個別化,而這個觀點能為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提問開闢嶄新的視野。
警句對認識之總體關聯的放棄,經常被視為一種危機的徵兆。人們或者僅僅相信作家具備有限的能力,至多在微末小事中具有創造性,或者一些偏愛警句的時代,被人視為深受激盪和急劇崩潰的時代。儘管任何時代都有解體和過渡,事實上在警句的繁榮和某些歷史時期之間,還是可以看出某種姻親關係。這樣的歷史時期,與其說是在對現存事物持續的推行和總結中,不如說在與過去的劃清界限和在一個堅定不移的新開端中,樂於見到自己的任務。針對傳統價值和現存準則的疑慮不管何時增長,對體制的攻擊不是透過體制對峙表達自身,相反,警句(和散論)作為銳利的武器發揮作用,人們以此能在要害中心擊中敵方的關鍵部位,並且進行突破。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觀察到那些啟蒙運動者(利希騰貝格,Lichtenberg),早期浪漫主義作家(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諾瓦利斯,Novalis),還有尼采,持有同樣的目標。此外,「黃昏」也是進攻之時。偶像此時還無法清晰地辨識逼近的敵人。
警句的個性化與警句作者的個人主義相稱。警句如此自主獨立,不必首先從一個比較全面的關聯中獲取自身意義,就能讓人明白。諺語和格言只適合於某個特定的語境,並且依賴於它,因而它們僅僅在這樣的語境中能被引用,而警句卻自給自足。其對讀者的效果與它的個性化類似──通俗易懂,但高雅孤傲,並非是大眾化的,相反是知識型的。鑒於其文本關聯和在接受上高要求的特殊性,其內容和形式的排他性,又與它的孤立相適。為了不屈服於它最大的敵手,即陳詞濫調,它需要藝術的純熟精湛和修辭的高超技巧。與所有肯定判斷的類型一樣,它必須避免簡單和膚淺的斷言。取而代之的是,為了敞開出人意料的層次多重和深奧莫測的意義之維,它使用反題和顛倒、矛盾和訛謬、使人詫異和感應心靈的一切能想像的手段。
警句儘管自給自足,獨立於一種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語境和廣大讀者的多數同意原則,它還是很少個別地出現,而通常可在較大的彙編中找到。它與其他文字一起被印出和閱讀,但這並不妨礙它的獨立性,因為它同樣可以放棄與其他警句的鄰居關係。另外,它的主體性和片段式的片面性,從一個變化的立場出發,力求延續或矛盾、完備或者反方案。那些互相連接、彼此間又時常相左的警句,是不斷以新的思維開端和透視的方式把握認識對象的嘗試。並非是一個作家的無能或者一個時代的無創造性,而是那難於認識的問題,要求警句式的、也就是說接近真理的不斷嘗試的形式。倘若對啟示的信仰以及古代形而上學的基本原則不再能為一種「知識大全」(Summa)提供基礎,那麼認識儘管會零星化,並且在這樣的過程中慶賀主體性的解放,但同時會傾向於克服其獨居的實存,並且尋找聯合的新形式。結果不是歸納和演繹的系統,而是對探照燈的一種安置。這些探照燈的光束既非集中,也非擴散、搜查黑暗、尋找真理。
形體多樣的偶像
與在其早年的論著中,尤其與在《道德的譜系》中一樣,尼采的方法是,把所有的現象嚴格地歸結到其生理條件上。譜系的研究就此得到延續,即除了道德的起源,其他「偶像」的祖先,比如真理、理性、美感等,也將受到探究。篇章的順序遵循從一般開始,轉移和集中到特殊的表現方法。此書首先討論具有超越時代效力的哲學及道德的觀念和理想,然後探討當代現象,比如新建立的帝國及其社會和文化關係,然後把目光轉移到一些傑出人物身上。這些人物的名字代表著某些定理和思維立場。此書以對非偶像的、具有標準設立之意義的形象,比如歌德和古代羅馬人的展望收束。
尼采那歸結的思維手段,幾乎在所有情況中是一樣的,它擊碎原因和結果、說明者和被說明者之間那人們以為無法扯斷的鏈條,展現出,那表面上的第一,其實早已是第二,因為它是有條件的。那自以為自由的意志,於自身發現它的行為的原因;可事實上,它僅是一個更強勢力完成任務的器官,本身已是行為的結果。那以為自己是堅定不移的理性,根據自身的靈性相信認識,在理想的意義中,甚至認為世界是自己的創造物,由此認為自己是造物主,但是,就其被創造性來看,它自身只不過是一個隱藏更深的意志那實施指令的工具,並就它的命令進行思考和認識。教徒只能把他的上帝想像為最最實在者(ens realissimum)和他自身的原因(causa sui),但此刻他沒意識到,一切事物的根源,其原因在人自己身上,是人自己,按照其最深邃的本能的指令,把那個至高無上者創造為理想,以便在塵世的艱難辛勞中,替自身減輕負擔。人類置於其開端的一切,事實上已經是個大多遲一些的、占統治地位的、或已受損害之趨動力的衍生物。對尼采來說不是太初有道,而是太初有「生命」。在生命中,他見到的不僅是原初,而且還有一切存在者的目標;它包容了起源和結果,原因和目的,開端和結束。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會履行「生命」的功能,並從生命那裡獲得自己唯一和真實的合法性。
尼采論著中的這個主要術語,不能在一種狹窄的、僅僅是生物的意義上,被與人的生命體、與同人的身體聯繫起來,相反,作為一種概念比喻,它包含的東西要多得多。鑒於它的不確定性,尼采研究對它顯得相當無可奈何,而每種對「生命」的更精確的定義,都會導致一種不能容許的界定,以至於有必要進行考慮,相應地使用諸如「廢除邊界」或者「普遍化」這樣的範疇。「生命」在尼采那裡涉及的是一種幾乎無法精確描述的原因和關聯。這種關聯創立、包容和評判一切存在者。對這個整體繼續作任何條分縷析的說明,會束縛其對整體的要求,使自己陷於矛盾和對立。一項概念的定義,會導致它的普遍性的損失,而在歷史現實中,當它在為其弱點的服務中自我限制和傷害時,甚至不得不容忍這樣的損失。不過,即使借助理論和理想的「生命」的自我閹割,也是按其意志發生的,不過是一種病態的意志。
屬於「生命」之整體的有極端的敞開狀態,對破壞性力量對抗的肯定,還有作為整體之一種補充要素的虛無。尼采眼中的虛無主義,不是對虛無的認知和承認,而是對虛無的否認,或者透過基督教和道德觀念,賦予虛無以安慰和希望。不管「生命」這個術語的含義如何地不確定,作為克服錯誤的、尤其是有害的對抗哲學的工具,它還是重要的,因為正是「生命」應該把握和接受這種對抗性:阿波羅那清醒和維持秩序的知性活動與狄俄尼索斯那取消邊界的迷醉,同樣還有善與惡、同樣還有謊言和真理。甚至那自相矛盾也包含在「生命」中,並且可以服務於對它的刺激。即使它以窮困潦倒甚至病病歪歪的樣子出現,意欲自我否定和自我毀滅,但正是這樣的意志證明其不可遏制的力量,儘管它作用於頹廢中。它催放出最最絢麗的花朵,培育出一種變得愈來愈美妙,如同在現在派中愈來愈精緻的敏感性和唯理論,在這個基礎上,人最先獲得這樣的能力,認識到他的匱乏之物、即百折不撓的強大生命力的充分價值。只有病人才有能力,領會健康的意義,覺悟到,「生命」的狀態決定依賴於它的所有現象的價值,並且確定,這些現象是一種憑藉本能之意志的表達,容或是對意志的否定,這些現象孰好孰壞。
在「格言與箭」之後,《偶像的黃昏》轉向一個業已在尼采的處女作《悲劇的誕生》中占據中心位置的形象,即蘇格拉底。在那裡,他被視為第一個「理論家」,曾以自己那區別和證明的藝術,摧毀了太古時代希臘文化那包容世界、容忍光明和黑暗的神話,而眼下,他自身作為一種大體上走到盡頭之生命力的純粹的工具,作為一種趨向本能衰竭的最突出代表出現。這種本能衰竭還涉及旁人,首先是隨後的幾代人,而這個善於辭令的辯證論者由此得到別人的仔細傾聽,並且能夠提升和促進由他的疾病所推行的事業。倘若蘇格拉底與許多哲學家一樣(比如叔本華)自以為能夠評判或者甚至貶低「生命」,那麼,尼采駁斥了這種大膽行為的可能性,因為對一個生存者來說,「生命」從來不是評判的客體,而始終是主體,生命借助它自身的特性規定評判者,肯定或者否定生命。對尼采來說,不存在獨立自主的理性判斷,而只有對本能的反應;因為人按照意志的指令進行思維。透過評判「生命」,人為其自身的此在價值作證。唯理論由此被歸結到人的生理條件上。
在蘇格拉底的例子中,尼采關心的是少量流傳下的關於他性格的情況,尤其是他的長相。對心理學家尼采來說,它顯得如此怪異,直至扭曲變形為漫畫,所以被用作對一個徹底墮落的生靈的受歡迎的證據。他那低賤的出生,據說同樣是罪惡和醜陋的本性,根據尼采的表達,同時是反對所有高貴的怨恨的原動力,而代替高貴的,是對概念自以為是的使用。辯證法成了身處劣勢者的武器,他們用它嘗試著對所有強權者進行報復,其方式為,他們強迫每個人,使用他們的手段進行抵抗,或者被當作白癡。同他經常對頹廢所做的分析一樣,尼采在目前這個例子中見到的也不僅僅是陰暗面,他甚至證明蘇格拉底,說他用辯證法創造了一個嶄新的、鬥爭性論辯的理想化形式,由此豐富了希臘人的生活。
就尼采看,蘇格拉底的精神在基督教中得到加強,並在現代(在叔本華和華格納那裡)慶賀自己那有害的勝利。關於這種精神的巨大作用的原因,尼采認為存在於從希臘人那裡開始的對本能的刺激,而本能在其雜亂無章的亢奮狀態中,不再能被約束,以至於作為最嚴重之病例的蘇格拉底,能夠把理性、德行和幸福的三迭系,當作臆想的、受到眾人貪婪地抓取的藥物提供。但是,尼采以為,帶有如此不純之出生的理性觀和道德觀,在病理學上是有條件的;因為對於患病之本能的不斷增長的抵抗,其自身僅是一種疾病的症狀。一種健康的此在不與本能鬥爭,而是任其自然——當然僅在這樣的條件下,即它們是健康的。疾病存在於單體的分離和部分那散亂的並存和對立中;相反,健康是個平靜的整體,它允許內在的矛盾,但不是在黑格爾的揚棄意義中,但或許在容忍對立的意義上。一種走向沒落之生命的確實無疑的徵兆,它們同時也是驅動力,在同時壓制甚至消除對立面的時候,它們是對單個理念和理想的片面催生和絕對化,比如為了明亮對付黑暗、為了道德對付本能、為了邏各斯對付神話。
對於尼采,最受崇拜、同時最危險的偶像之一,是把絢麗多彩和變化多端之現象的世界,製成一種僵化和假定為能比一切更經久之存在的木乃伊。形而上學家們把這種存在的、可能的產生和滅亡,歸諸於一種誤入歧途的想像力。他們由此在認知者身上尋找謬誤根源,並且在其感官中找到,而這太適合那業已不斷被宣揚的肉體仇視了。透過反駁的顛倒,尼采再次審核那通行的等級秩序:說謊的不是感官,相反,那真正的說謊者藏在那個被他們借助諸如「統一」、「主體」等概念進行施暴的主管機構之後,也就是躲在理性之後。他同意希臘人赫拉克利特(Heraklit)的觀點,這個存在是個純粹的發明,他反對埃利亞學派的(Eleaten)的意見,比如巴門尼德(Parmenides),以為存在是永恆的,而且他還反對其對手,比如德謨克里特(Demokrit)在傳統的存在概念重壓下,把最後的、不可分的和不會變化的統一設定在原子中。與此相反,尼采捍衛感覺器官的認知力量,認為尤其鼻子是最有效的,因為那是神經最為靈敏的認識工具之一。
不管存在作為所謂真實和不可改變的世界,事實上如何地處於不斷變化中,在不同的哲學前提下得到不同的解釋,尼采還是指出了西方思維史的六個階段。在柏拉圖的唯心主義中,真實的世界僅對智者開放。他透過擺脫一切感官的約束,嘗試獲得對那永久有效之真理的直觀。對基督徒來說,這個真實的世界處在一種不可企及的、但孕育著彼岸的此在中,而虔誠者和此岸的懺悔者能替自己獲得這種此在。對康德來說,世界自體在理論上不可證明,但在實踐領域中,是個道義的使命,而作為道義的使命它並非純粹的幻象。真實的世界對實證主義者來說是陌生的。他們不知有何手段,能消除這個不良狀況,但還是勉強接受這個絕望的狀況。現代的無神論者,那些廣博的懷疑論者和不可知論者,一方面從中接受著教訓,一方面主張取消作為一種陳舊和無用的理念的真實世界。在第六和最後的、暫且是最高的階段,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就站在此上,意識覺醒,發現隨同真實的世界,虛假的世界也失去了它的意義。反思以其最先進的形式,要克服的不僅是真實的世界,而且還有對一種對真實和虛假世界之區分的原則上錯誤的假設。適應「善惡的彼岸」的是這個假設:「存在與假象的彼岸!」
在「四大謬誤」這一篇裡,尼采把他那完全占主導地位的思維手段的基本概念作為題目。當他把理念歸結到其生理學的條件上時——系統地表達,始終分析著第一和第二,原因和結果的聯繫;透過對兩者進行顛倒,他對這種關係做了一種徹底的檢查。對尼采來說,第一個謬誤存在於對原因和結果的通常的混淆中,正如他曾就不同的分類對它們進行分析那樣,現在他再次用對特種飲食的錯誤信仰解釋它們。這類特種飲食據說是長命百歲的動因,可事實上卻是「無法再能正確進食」的結果。追求健康的動因也就不是應當之規定,而是疾病。道德和政治領域中的情況與此相應,倘若有人想出手段和途徑,以改正錯誤,而其實它們的來源已經受到毒害,是沒落的生命的結局。對尼采來說,一切強大者不是依靠應當,而是依靠存在活著,其本能的自信,以泰然自若的輕鬆和歡快表現出來,而這種歡快,它認識和忍受可怕的事物。在此意義中,即使德行也不是緣由,而是幸福的結果。
基本的謬誤存在於對一種緣由關係的錯誤相信,這種緣由關係驅使人們,不斷地去尋找新的原因,而事實上它們只是由受本能控制的想像所組成。尼采的批判首先針對唯心主義的全部的形式,這種唯心主義以對所謂自由的主體之啟動力的著重高估,在原子或者自在之物中見到的不是別的什麼,而只是自身精神的自我美化的投影。人要麼沒有準備,要麼沒有能力承認事情確實這樣。相反,他們孜孜不倦地進行著原因研究,只是在這種研究——反正是錯誤的——結束後才接受現實,因為他們現在能把這新的東西回溯到某種以前熟悉的東西上去,由此贏得一種安全感,也就是一種權力意識。對於陌生者的恐懼,剝奪其新意,拒絕其自身成為一種新開端之緣由的可能。在宗教和道德中,所謂的緣由,比如良心和服從天命,服務於解釋那折磨人的集體經驗,並使之變得輕鬆。不過此外,這類心靈狀態是生理條件的結果。對於上帝之善的信任,是內心堅強的表達,而負罪感則相反,透露的是軟弱。
就尼采看來,對一個自由意志的假設,乃是一個基本謬誤。這樣的意志被作為所謂產生決定性作用的緣由而發明,其目的是,能夠讓物和人依賴自身,並對它們進行懲罰。為了可以宣布某人有罪,必須事先迫使他接受自由。與此相反,尼采認為,就人的存在或者行為的所有一切而言,人全然不負任何責任。「生命」的厄運讓目的成為多餘,而目的在自然中同樣完全是多餘的。因為每個個體是整體的一部分,它就無法在不涉及整體的情況下遭到譴責。對於一名個人的有罪判決,它同時也譴責宇宙。只有當世界不再被回溯到第一個緣由時,它的解放才開始;只有當上帝被取消時,它才得到拯救。
與宗教一樣,就尼采來看,道德也建立在對於現象的想像和誤解上,但它還是在某些方面具有一種認識價值,即它在其不同的表現形式中,對與其有關的根基、即「生命」的長處和短處提供資訊。倘若道德關注的是人的改善,它原則上使用兩種不同的方法:馴服或者培育。前者導致一種無情的屈辱,就像中世紀早期日爾曼人被改變信仰和強迫臣服於十字架時所經歷的那樣。培育則相反,印度文化為其等級制地劃分的人種和階層想到的就是這點。它導致一種對下層社會有目的的軟化,而且使用聞所未聞的殘酷手段,比如為最底層的賤民而設的禁令和規定所證明的那樣。針對這種帶有培育和優待原則的印度式種族理論,猶太——基督教的學說面向所有的窮人和被侮辱者。兩者都把自身理解為道德,但是,它們奴役世人,以服務於一種它們無意識的和業已患病的生命意志;因為健康的生命意志讓一切生存者自得其所,不會強迫它們戴上一種應當的桎梏。
繼哲學、宗教和權力的偶像之後,尼采針對政治的偶像發難:針對德意志帝國。為了標明自己的不敬無禮,他始終用引號指稱這個帝國。他的主要保留、涉及的是強權對於精神、國家對於文化、俾斯麥對於書籍的替代。「德國,德國高於一切」這個口號,把以前那個思想者的國度,貶低到了法國教養的水準,而這個國家再也無法到處展示諸如歌德和叔本華那種獨一無二的享有名望的人。除了缺乏合適的教育家和偉大的典範,尼采目睹的還有多種麻醉劑,比如酒精、,基督教和新的德國音樂,這裡他指的是華格納,以及一種缺乏精神的科學工作。它帶著消除差別的匆忙,不再為高尚的事業留有迴旋餘地。沒有受到真正的召喚——尼采就是這樣,這個青年男子就得(無論如何指的不是青年女子)以23歲的年齡選擇一個職業,儘管在30歲的人身上,每種有教養的文化還肯定會發現那是個初學者。不過有關的前提似乎處在觀察、思考、說話和寫作方式的一種徹底改變中。平靜的泰然自若和一種針對任何魅力的傲然抵抗,還有舞蹈者那高雅的距離感和輕盈的步履,它們都不可或缺,而且深深地耦合一處。但德國人平庸粗笨,與此相距甚遠,無法企及。
在論著最長的篇章裡,在「一個不合時宜者的漫遊」中,尼采以被各方承認的、代表某些思維立場和價值設定的權威人物的形象,論述了一大批偶像。他常常只是在行進途中用他的錘子觸碰他們一下,由此從中引出一個持續短暫的聲響,而這個聲音對傾聽者來說已經足夠,來宣布自己的判決。那偶爾不經意和倨傲而作的標籤,為惹惱人提供了誘因,比如他試圖把席勒當作「塞京根的道德小號手」取笑,或者用一種對英語和法語詞「cant」戲謔的影射,讓康德作為假正經出醜。尼采的廢黜方法在這裡同樣是把定理歸結到原動力上,而此時它們與定理處於矛盾狀態中:無神論者勒南(Renan)在內心中下跪祈禱,聖伯夫(Sainte-Beuve)被證明是沒有自由的革命家,而且帶著復仇欲反對一切更強大者,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起先供奉他們的上帝,然後根據英國的習俗供奉道德,喬治.桑(George Sand)忸怩作態,扮作有男子氣的女人,龔古爾兄弟(Concourt)推行一種所謂深邃的心理學,方法是與自然主義者們一樣,屈服於表面事實,而卡萊爾(Carlyle)對於信仰的要求與他的無能形成強烈對照,以至於這個出了名的能言善辯者面對自身變得笨口拙舌。
與所有的現象和觀念一樣,對尼采來說,美也不是自給自足和無動於衷的實體,而是「生命」對於事物的一個投影。在美之中映現的是健康,而在醜之中,表現出的是頹敗者對其可能性之惡化的憎恨。因為美學也受心理的制約,所以尼采反對叔本華關於美是性關係的女拯救者的理論,相反,他贊同柏拉圖,而對後者來講,一切美的東西刺激創造性和生育。即使和恰恰那個自以為業已擺脫藝術外部條件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時代綱領,在尼采眼中,依舊錯誤地與被否定的關係密切相連;因為藝術從來不是無目標和無目的的,而一直是「生命」的反射,同時也是對它的激勵。它正是在表現醜陋的和違忤生命的現象時忠實於這個使命,因為它不恐懼地展現恐懼,不回答地承受成問題。經歷苦難考驗的英雄,最可能在悲劇中為自己的此在那無法度量的價值歡呼。
繼政治(「帝國」)和藝術的偶像之後,輪到當代的傾向和機構,就是它們以自己那所謂的進步性,在尼采看來,也證明自己是生理退化的結果。這既針對與基督徒一樣抱怨一種貧乏的「生命」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也針對抹殺高貴和卑賤之分的自由主義。因為只有必須做到堅強的必要性,才使人變得堅強,高雅的社會形態比民主的社會形態更適合促成自由和偉大;因為自由和偉大以人們必須克服的阻力和危險的程度作為自己的尺規。同樣前後一致和對異議具有挑戰性的,是尼采關於習俗之削弱、關於工人問題和所謂愛情婚姻的判斷。與此相對,不過他在保守主義中看不到其他可能性;因為沒有後退之路,而被鄭重宣告的進步,註定要逐步地走進更深的頹廢中。尼采也把現代法律視為偶像。這種法律對罪犯,也就是說在不利的情況下被弄成病態的、堅強的人,出於復仇和怨恨而進行迫害和懲罰。
在《偶像的黃昏》的結尾處,尼采把許多受審判的偶像與有典範意義的形象進行比照,而在這些形象中,歌德對他來說卓絕超群。他以為,歌德代表了自然的整體和宿命。他出於堅強推崇寬容,以其對最具緊張度的對抗的肯定,是最後一批狄俄尼索斯式人物中的一個,而以他作為基點衡量,那整個19世紀僅僅意味著沒落。尼采視歌德為最偉大的德國人並對他表示自己的尊重。尼采還完全以自己晚期著作中過度興奮的自我標榜風格,褒揚他自己的使命,並且稱《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為人類擁有的最深刻的書。
在回溯他感謝古人什麼時,較之希臘人,他更強調羅馬人的重要意義。與溫克爾曼關於「美的心靈」的觀點不同,他認為希臘人曾在巨大的張力下受到傷害,而這種張力在不斷重複的敵對行為和令人如癡如醉的節慶日中得到釋放。他一方面稱讚羅馬人、特別是薩盧斯特(Salust)和賀拉斯(Horaz)身上之風格的高貴,而這種風格的整體力量透過最簡約的手段形成。另一方面他強調早期希臘文化的狄俄尼索斯的強力。他在自己的處女作,在《悲劇的誕生》中已經認識和闡釋過這點。他在那裡選取的是一條相反的路,方法是從希臘人出發,追溯自蘇格拉底以降的衰敗,並視華格納為一個可能的拯救者。但眼下他從現代那淒涼荒蕪的狀況開始,把華格納看作其最最病態的體現,並且對值得接觸和繼續的東西進行回顧。此刻他自稱為狄俄尼索斯最後的門徒,以及永恆輪回的老師。早期的希臘文化,羅馬的修辭學家,歌德和尼采——這是針對蘇格拉底、基督教和理查.華格納的其他選擇。

 共
共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著名德國語言學家、哲學家、文化評論家、詩人、作曲家,他的著作對於宗教、道德、現代文化、哲學、以及科學等領域提出廣泛的批判和討論。他的寫作風格獨特,經常使用格言和悖論的技巧。尼采對於後代哲學的發展影響極大,尤其是在存在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上。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著名德國語言學家、哲學家、文化評論家、詩人、作曲家,他的著作對於宗教、道德、現代文化、哲學、以及科學等領域提出廣泛的批判和討論。他的寫作風格獨特,經常使用格言和悖論的技巧。尼采對於後代哲學的發展影響極大,尤其是在存在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