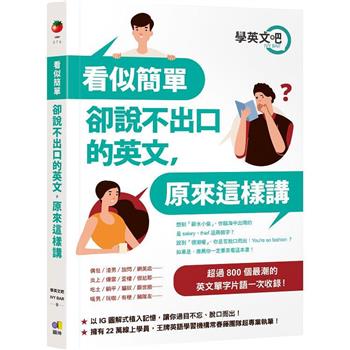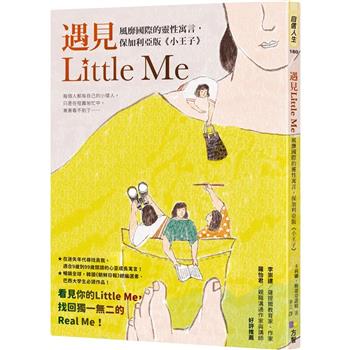導論
陳靜容在探討中國「山水詩」詩類名稱之晚出原因時,經尋繹歷代文學總集或選集中的分類,發現均未出現「山水詩」之分類詩目,反倒是《文苑英華》在「謌行」的「圖畫」一類下繫「山水」,收有「畫山水」七首。—— 其實,如果要談「山水」的次文類,《文苑英華》還有一點令人驚異:它在「銘」下分出了「山川」一類,這可能是現存最早為銘文分類且分出「山川」類的總集,而在歷代總集或選集中,無論是為銘文分類或分出「山川」一類,皆相當罕見。《文苑英華》在宋代的影響力或許有限,不管如何,這樣的銘文類目,透露此類銘文的存在已獲編選者認同,也標誌了此類銘文「本質」的初步確立。
然而深入究察「山川」類銘文,會發現它們與「山水詩」、「山水賦」的成類意涵差別甚大。《文苑英華》為「銘」分出「紀德」、「塔廟(附畫像)」、「山川」、「樓觀(附關防橋樑)」、「器用」、「雜銘」六類,分類標準的不一致並非特例:「紀德」是從內容意旨來分,「塔廟(附畫像)」、「山川」、「樓觀(附關防橋樑)」、「器用」是以銘刻的載體或詠物的主角來區分(兩者時而重疊,又常與題目相合),「雜銘」則是不屬上述類別的集合。單就「山川」類所收的銘文觀察,首先,與一般熟知的山水文學最明顯的不同是,其內容以描寫自然風物為主的篇章非佔多數,倒是都可以在銘文的傳統分類中找到歸屬。回顧古典文論,關於銘文的分類、源流、義用、風格等,最完整的論述當屬《文心雕龍.銘箴》: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虡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誡之訓。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于昆吾,仲山鏤績于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勛于景鐘,孔悝表勤于衛鼎,稱伐之類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
劉勰於篇首即追溯了銘文的兩種源流,直到篇末時,藉由與箴文的互相對照,明確點出了銘文「褒讚」和「警戒」的功能。劉勰的論述實則有所承繼,最明顯的線索即綜合了《左傳》裡臧武仲的說法與蔡邕的〈銘論〉。《左傳》襄公十九年有一段記載魯國借晉國兵力討伐齊國之後,季武子以所得於齊國的武器鑄鍾,銘刻魯功於其上,於是臧武仲對他說:
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從這段常被後代用來說明銘文功能的文字可以發現,銘功於彝器原來不僅是因為能「以示子孫」,也是深植在有關身分階級(諸侯稱伐則從大夫之例為下等)、功勞歸屬(借人之力,功非己有)、言動得時與否(妨民多矣)、國際關係與國勢強弱(大勝小或小勝大),一套逐步形成的規範(禮)之中。蔡邕基本上也是照著臧武仲的框架──「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進行說解的: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槃杅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毚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阼,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進人主,勖于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冶;漢獲齊侯竇樽于槐里,獲竇鼎于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式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大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益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父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于鼎,晉魏顆獲泰杜回于輔氏,銘功于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
「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已對「天子令德」完成舉例說明,在還沒開始談到「諸侯言時計功」之前,從「黃帝有巾几之法」至「銘之以慎言」一段即列舉諸例,顯明銘文具有「警戒」的功能,而警戒「亦」是為了「勖于令德」。比較之下,劉勰不同的地方是將「鑒戒」與「天子令德」分開,不再放在「天子令德」之後,讓「警戒」第一次與「褒讚」並舉,假如其中有「徵聖」的因素,「警戒」可能已被提升為銘文的典範性功能。 (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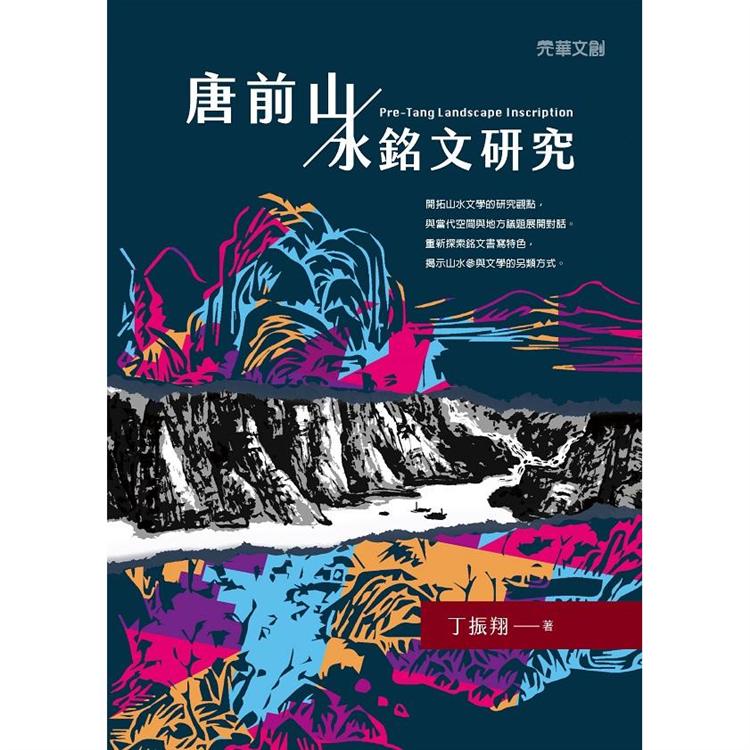
 共
共 ![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2023全新增修版] 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2023全新增修版]](https://cdn.kingstone.com.tw/book/images/product/20156/2015630770320/2015630770320m.jpg?Q=263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