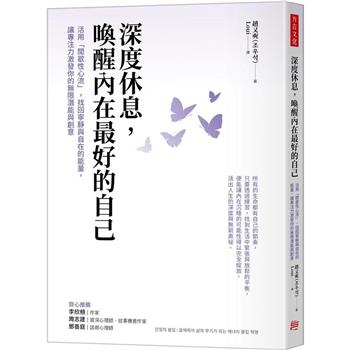言有盡而意無窮:唐詩與傳奇/江濤
那時的詩人,無論見面、離別,宴會、遊邊、隱居,都要寫詩。
新體式與新制度
開元年間的一天,下著小雪,詩人王昌齡、高適和王之渙一起到一個叫旗亭的地方喝酒。此時酒樓上正有十幾位伶人表演,三人一邊擁著火爐欣賞,一邊祕密約定:「我們都以詩齊名,一直難分高下,今天正好可以悄悄觀看眾人表演,如果誰的詩被唱到最多,則為優勝。」
不一會兒,有歌伎唱道:「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齡便在牆上畫道:「一絕句。」很快,又有歌伎唱道:「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高適也在牆上畫道:「一絕句。」下面的歌伎接著唱道:「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扉共裴回。」
當王昌齡在牆上畫到「二絕句」時,一旁的王之渙坐不住了,他指著其中最漂亮的一位歌伎說:「前面幾位庸脂俗粉,所唱不過下里巴人曲子,如果她演唱的還不是我的詩,我就拜你們為師。」果然,接下來的歌伎所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正是王之渙的名作,眾人於是笑作一團。
這是一則記錄在中唐文人薛用弱傳奇小說集《集異記》中的逸事。或許再沒有比這樣的情景,更能說明唐詩的興盛還有傳奇的特點了。有唐一代,詩歌、傳奇,並稱奇作,達至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長期以來,唐詩已成為人們審美想像的某種標竿。詩歌為何以唐為盛,或者說,最好的詩歌為何會出現在盛唐?除了詩學內部的因素,葛曉音將其總結為:「盛唐之所以令詩歌恰逢其時,是因為這是一個情感超過思理的時代。盛唐詩人對於詩歌雖有自覺的追求,卻沒有系統理論的約束;對於時代雖有認真的思考,卻沒有深刻的理性思辨。熱情、爽朗、樂觀、天真、富有幻想和進取精神—盛唐詩人所有的這些性格,乃是屬於純詩的品質,因而最高的詩必然出現在盛唐。」
即便如此,唐詩並非一出世便不同凡響,為開元、天寶年間詩壇的繁榮,它足足準備了百年之久。這一被稱為初唐的時期,雖然也有「四傑」、陳子昂這樣少數的革新者,但它仍屬於宮體詩的時代。
南北朝時期,詩歌代表的美學成就已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精英階層的標誌,北朝以扣留出使的南朝詩人表達這種文化上的欽慕,當時的大詩人庾信、王褒、徐陵都是例子。這種軍事上的強勢、美學上的弱勢,一直延續到唐太宗以後的皇帝。作為宮廷娛樂活動的重要內容,宮體詩的興盛不難理解,用學者吳光興的話說,初唐前三十年詩人的典型特徵是,「腦袋都被徐陵摸過」。
然而,一個世紀的時間並未浪費,正是宮體詩為後來被稱為「唐詩門戶」的律詩這樣一種新體式的最終確立,奠定了基礎。律詩體式的確立,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唐詩興盛最為核心的內因。吳光興說:「站在文學史的本位看,因為唐人發明了律詩的體制,唐代雖然滅亡一千多年了,人們寫古詩還是要用這套東西。」
當然,這一體制的建構更為漫長,從建安時期寫詩注重對句,到南朝齊武帝永明年間發明「四聲」,到後來的調平仄、三部式結構,一直到八世紀初,律詩才由唐中宗時期的宮廷詩人沈佺期、宋之問確立。美國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在他的著作中,敏銳地發現了這種律詩寫作的三部式結構—頭兩句介紹事件、中間寫對句、結尾表達旨意,與宮體詩寫作的內在聯繫:「在宮體詩中,對偶句是詩體的興趣中心。『對屬能』是迅速作詩的首要必備條件,一旦掌握了這一技巧,朝臣們就能很快寫出中間部分,把精力用來寫出精巧的結尾。」
這種富有規則感的寫作模式,聽起來似乎是對想像力的侮辱。其實不然,正因為有了法度,詩歌寫作變成可以快速習得的技能,隨著寫作群體的擴大,才能超拔者自然不再受到法度的限制。
事實上,唐人正是這樣學習寫詩的。在《舊唐書》中記載了一次有趣的家宴,宴會上,大家玩起了用四聲詠物品的遊戲,結果不等大家發言,四歲的楊綰便指著鐵燈樹說「燈盞柄曲」,一時震動。
儘管如此,在初唐這樣一個門閥制度尚存的時代,詩歌依然帶有濃厚的貴族文學的特點。如何讓它與更廣泛的人群發生關係,便需要新制度的支持。這便是隋代創立、至唐已發生變化的科舉制度。
唐高宗永隆元年(六八○),詩歌寫作被引入了進士考試。在當時,做官最主要的途徑依然是世襲,科舉制度不過是面向寒門和大家族的遠支開放了一條上升通道。據陸威儀在《哈佛中國史(三)世界性的帝國:唐朝》唐代卷的統計,整個唐代,只有十%的官員通過科舉選拔而出。儘管如此,張說、張九齡這兩位玄宗朝的宰相,盛唐詩壇最主要的扶持者,正是科考出來的寒門子弟。
與之後科舉制度不同,唐代科考有所謂「溫卷」的傳統。宋人趙彥衛在《雲麓漫鈔》中的一條紀錄,「唐世舉人,先借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被普遍認為與唐代詩歌和傳奇的興盛密不可分。汪辟疆在《唐人小說》的序言中便據此議論:「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蓋此等文備眾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贄。」儘管後來學者已論證趙彥衛的記載並不準確,但無可置疑的一點是,唐傳奇的傑作多出自進士之手。
對舊詩歌秩序最後的致命打擊,來自玄宗在七二二年發布的詔令。這條詔令禁止諸王招攬大量賓客,如宇文所安所說,這無疑結束了宮體詩的一個重要支持根源,也關閉了在京城獲得詩歌聲譽的舊途徑。
在新的體式與制度之外,不應忽略宮體詩反對者的貢獻。陳子昂的批判是當時詩壇的一股清流,所謂「彩麗競繁,興寄都絕」,就是說那些採用新體寫作的宮體詩,雖然文辭華麗,但並沒有什麼個人的主意。綺麗的句子,風格化的寄託,加在一起,就是浮現在地平線上的盛唐詩歌。
作為生活方式的文學
在唐人眼裡,並沒有所謂盛唐詩歌的概念。就事實而言,即使是唐代的頭號詩人杜甫,最重要的詩學成就也是在安史之亂以後的中唐取得的,中晚唐的詩歌,更是此起彼伏,高潮迭起,似乎很難以開元、天寶年間的詩歌寫作,來囊括唐詩的全部成就。確切地說,對盛唐詩歌的推崇,宋人嚴羽的《滄浪詩話》厥功至偉,後來更逐漸被建構為一種詩學常識。
但不管怎樣,盛唐是一個大詩人輩出的時代,作為一種只能被追慕的想像力與美學標準,經過嚴羽下面這段論述而深入人心:「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這種唯在興趣的寫作,如果換一個說法,那就是在盛唐時代,詩歌完全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呈現。假如你是一個盛唐的讀書人,不會寫詩那是難以想像的。
對那些聚集在長安或者往返於長安與各地之間的詩人來說,詩歌就是一種必要的社交手段。那時的詩人,無論見面、離別、宴會,都要寫詩。據載,那個以寫作七律〈黃鶴樓〉著名的狂放詩人崔顥,有次拜見開元時代的文壇名士李邕,獻給他一首以女子為主人公的詩。結果李邕十分厭惡,不但拒絕接見他,還對身邊的人說:「小兒無禮。」
科舉、入幕、從軍、隱居,唐代文人的生活選擇豐富多采。由此帶來的分別場合,產生了大量著名的餞別行旅詩。早在初唐,王勃便以詩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寫下了那個時代的昂揚。
盛唐時期的詩人亦各有名篇。長安大詩人王維寫下的「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入樂之後更成為當時的流行曲目,一直到宋代還為人仿作。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則將汪倫的名字永遠留在了詩歌史上。
出遊同樣少不了詩歌。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岑參、高適、杜甫、儲光羲、薛據等人一起在長安遊歷,登上慈恩寺塔(大雁塔),興盡之餘,五人都寫有紀遊之作。在這幾首難得的同題詩創作中,宇文所安發現了盛唐時期兩代人在風格上的差異:「長輩詩人儲光羲和高適的詩較為正規和較講裝飾,杜甫和岑參的天寶風格較有氣勢和較富想像力。」
盛唐詩歌中,後來被引為大宗的邊塞詩,與詩人們遊邊從軍的選擇密切相關。比起後來的王朝,唐代一直是開疆拓土的擴張性國家,這也為詩人提供了棄筆從戎的機會。在吳光興看來,某種程度上,「遊邊也是為了取功名,由於邊關將領有舉薦的權力,可以陞遷更快」。
邊塞詩是一個古老的題材,從王翰的〈涼州詞〉、高適的〈燕歌行〉到李白的〈戰城南〉,包括王昌齡也寫下了大量邊塞詩,其中就有那首被稱為「唐代七絕壓卷之作」的〈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但邊塞詩的集大成者,無疑屬岑參。
岑參能寫好邊塞詩並不奇怪,自天寶八載(七四九)出任大將高仙芝的幕僚後,岑參跟隨他抵達在中亞庫車的駐地安西。戰爭慘敗後,他又在名將封常清幕府擔任判官,在中亞的北庭和輪臺待了幾年。用現代學者鄭振鐸的話說:「唐詩人詠邊塞詩頗多,類皆捕風捉影。他卻句句從體驗中來,從閱歷裡出。」
岑參的詩歌,不但寫到西域邊塞的寒冷,「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同樣寫到極具異國特色的火山:「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雲厚。火雲滿山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
隱居之風,在盛唐也非常流行。這與君主為了粉飾太平,熱衷徵召山野的隱逸高士密不可分。唐代士人仕宦失意,多隱居終南山,因為這裡臨近長安,易於流播聲名,以便為朝廷徵召。當時的著名道士司馬承禎便帶著不屑說,終南山是「仕宦之捷徑」。當然,對於更多士人來說,半官半隱的生活無疑最為理想。唐代官員,待遇優厚,十日一休沐,讓他們有條件購買別業,享受田園山林之趣。這也促進了盛唐詩歌中另一大宗山水田園詩的興盛。
據研究者葛曉音的考證,王維大約在開元十八年(七三○)隱居於淇上,後來又在終南山輞川邊得到宋之問當年的別業,過著流連山水、半官半隱的生活。其間,王維寫作了大量山水田園風格的詩歌,其中諸如「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等簡淡自然而又意蘊深遠的描寫,在當時人看來代表了詩歌的最高成就。
換句話說,在開元、天寶年間,王維才是當世頭號大詩人。對於這種代表盛唐感受的詩美,吳光興分析道:「山水,只是他的面具。雖然不是每句寫景,但最用心的地方要有一段景象,寫景象,但裡面有個主意,有詩人的審美感受。為什麼唐詩高不可及,就在這裡。」
儘管作為長安詩人的代表,王維為當世推崇,但李白很快從蜀地把誇張的想像力帶到了長安。「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此前,有誰像李白那樣以狂放不羈的想像力寫作?長安的許多讀者和年輕詩人為之著迷。與此同時,在同樣狂放不羈的賀知章的舉薦和「小迷弟」杜甫的描述中,李白傲然於世的詩人形象得到了空前塑造,所謂「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不過,李白在去世後的幾十年裡顯得聲名沉默,直到中唐另外一位大詩人韓愈,將他與杜甫一起奉為盛唐最偉大的典範詩人。
站在韓愈另一面的大詩人白居易、元稹,顯然對杜甫更為推重。在寫給杜甫的墓誌銘中,元稹將杜甫視為一切詩歌體式的集大成者:「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兼擅各體之外,杜甫在安史之亂後寫了以「三吏三別」為代表的「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使他的成就溢出盛唐詩歌的範圍,隱隱開啟一個新時代的先聲。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丘濂的圖書 |
 |
$ 199 ~ 405 | 盛唐美學課: 七種主題, 教你做個唐朝文化人
作者:蒲實/丘濂/ 編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8-24  共 1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盛唐美學課:七種主題,教你做個唐朝文化人
從唐朝多元豐富的文化,領略生活之美,回到騷人墨客獨領風騷的夢幻朝代
穿越唐朝,美食珍饈在舌尖上飛躍,桃面花靨落金鈿,胡姬賣酒舞助興,文人雅士鬥詩歌,是文化鼎盛的黃金時代。
*全書共有七十六幀壁畫、人物肖像、金玉器、唐代樂器、古蹟城市、古書字畫等精美彩圖。
唐朝之美,美在城市各有風情,服飾豐富多采,文人墨客宴飲賦詩,信仰兼容並蓄。它的美獨出於中國其他朝代,具有獨特的氣質,生活在大唐,成為現代人傾慕古代文化最美好的想像。
唐朝以上國自居,領土遼闊壯美,善用他族管理邊疆事宜、任為朝卿,允許各族往來貿易、居住,對外來文化從不排斥,隨處可見胡餅、胡器,漢胡夾雜自在穿梭。受游牧文化影響,女性地位較為平等,可著男士胡服,腰佩短刀、打火器等器玩,在當時蔚為風潮,妝容衣著也變化多端。盛唐詩歌最盛,鬥詩鬥酒,行令助觴,燭光香霧,男女同席,歌聽雜作,胡樂胡舞助興。胡風與漢文化的雜融,造就唐朝奔放飛揚的氣質。
遊歷三城,帝都長安,曲江池、樂遊園,是皇家與平民遊宴之地,俯視京城,盡收眼底,坊里市場四方珍奇皆所齊集,路上有進京趕考士子,波斯、大食胡商與各國僧侶,蕃坊中各國僑民依照各自的風俗信仰生活,為世界級的大都市。揚州富庶繁華,河道縱橫,是盬商、茶商、手藝人的商業天地。廣州充滿異域風情,南方林邑、爪哇、僧伽羅人漫步其中,檀香、茉莉、廣蒮香氣撲面而來。與世界接軌的唐朝,沒有思想束縛,寬容大度,承載遠方而來的物料、文化、信仰,展現自信與雍容,一派繁盛。
盛唐萬千氣象,至今仍留在詩歌、壁畫、金玉器、唐三彩、歷史遺址中,令世人憧憬傾慕。此書以城市、唐詩、酒文化、女性、胡風、美食等主題,細繡唐人生活裡的諸般文化、生活美學,重現它的盛世風華,以夢回大唐。
作者簡介:
蒲實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法學學士和碩士,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經濟學雙學位學士。《三聯生活周刊》資深主筆。出版有圖書《大學的精神》(合著),發表封面報導〈最美的數學:天才為何成群到來〉、〈「一戰」百年啟示〉、〈郎朗:天才的冒險〉、〈伊朗:被曲解的文明〉、〈從卡薩布蘭卡啟程〉、〈看懂大英博物館:在一座建築裡思考整個世界〉等。
丘濂
清華大學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專業學士,美國貝勒大學國際新聞專業碩士。二○一○年正式加入《三聯生活周刊》,現任主筆。寫作領域廣泛,愛好美食、博物和傳統文化,專注城市發展和消費趨勢變化。出版有圖書《匠人匠心》(合著),代表封面報導有「環球尋味」系列、「夏日美食」系列。
章節試閱
言有盡而意無窮:唐詩與傳奇/江濤
那時的詩人,無論見面、離別,宴會、遊邊、隱居,都要寫詩。
新體式與新制度
開元年間的一天,下著小雪,詩人王昌齡、高適和王之渙一起到一個叫旗亭的地方喝酒。此時酒樓上正有十幾位伶人表演,三人一邊擁著火爐欣賞,一邊祕密約定:「我們都以詩齊名,一直難分高下,今天正好可以悄悄觀看眾人表演,如果誰的詩被唱到最多,則為優勝。」
不一會兒,有歌伎唱道:「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齡便在牆上畫道:「一絕句。」很快,又有歌伎唱道:「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高適也在...
那時的詩人,無論見面、離別,宴會、遊邊、隱居,都要寫詩。
新體式與新制度
開元年間的一天,下著小雪,詩人王昌齡、高適和王之渙一起到一個叫旗亭的地方喝酒。此時酒樓上正有十幾位伶人表演,三人一邊擁著火爐欣賞,一邊祕密約定:「我們都以詩齊名,一直難分高下,今天正好可以悄悄觀看眾人表演,如果誰的詩被唱到最多,則為優勝。」
不一會兒,有歌伎唱道:「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齡便在牆上畫道:「一絕句。」很快,又有歌伎唱道:「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高適也在...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城市、女性、詩歌、胡風
唐與世界
世界的唐
四大帝國的全球政治
唐墓壁畫和盛唐胡貌
盛世胡華:陝西歷史博物館唐代文物精粹
城市
長安:當年世界第一城
三城遊記:廣州、揚州與長安
唐詩與酒文化
言有盡而意無窮:唐詩與傳奇
天地一壺通:唐代酒文化
女性
女女的黃金時代:武則天、楊玉環、魚玄機
域外顏色:唐朝女子時尚
宗教
三教歸一的氣度:佛教、道教、景教
求經與傳宗:玄奘、義淨和鑒真
胡風
天中戀明主:留學生、遣唐使與胡商
正倉院唐物記
美食
在舌尖飛躍的味道
唐與世界
世界的唐
四大帝國的全球政治
唐墓壁畫和盛唐胡貌
盛世胡華:陝西歷史博物館唐代文物精粹
城市
長安:當年世界第一城
三城遊記:廣州、揚州與長安
唐詩與酒文化
言有盡而意無窮:唐詩與傳奇
天地一壺通:唐代酒文化
女性
女女的黃金時代:武則天、楊玉環、魚玄機
域外顏色:唐朝女子時尚
宗教
三教歸一的氣度:佛教、道教、景教
求經與傳宗:玄奘、義淨和鑒真
胡風
天中戀明主:留學生、遣唐使與胡商
正倉院唐物記
美食
在舌尖飛躍的味道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