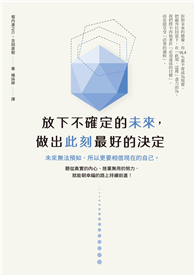▌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界/王德威(節錄)
■ 摘要
「華夷之辨」是中國研究中一項歷久彌新的課題。清末以來的中國面對世界現代化衝擊,與東洋、西洋接觸頻繁,華夷秩序因此有了新的變動。如何描述、定義現代的「中國性」成為不斷辨證的話題。近年華語語系研究崛起,論爭立場各有所執,但也每每暴露理論掛帥,史觀和史識的不足。在這樣的語境裡回顧近世華夷論述消長,因此具有迫切意義。本文處理三個方向:近世以來由日本、朝鮮發出的「華夷變態」論及中國的反應;現代中國「華夷共同體」的打造過程;以及新世紀以來,「華夷風起」的現象。本文重點是,近三百年來華夷論述的激烈轉換如果能夠提供我們任何省思,正是華夷之「辨」與華夷之「變」間的辯證性。同樣面對歷史,前者隱含區分種族、文化、政治立場的「畛域化」設定,後者則藉「風」與「勢」的能動性,更新、甚至翻轉華夷關係的可能。華夷之「辨」與「變」的關鍵之一,就是對「文」─文字,文學,文化,文明─的梳理。也因此,當中國與周邊的關係面臨又一次洗牌的時代,人文學者對華夷論述的重新闡述,佔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關鍵詞:華夷風、「華夷變態」、風、勢、變
■ 一、前言
「華夷之辨」是中國研究中一項歷久彌新的課題。有關華夷的論述可以遠溯上古;黃河中下游漢族聚落形成的農業文明自居華夏(諸夏),與周邊遊牧、狩獵文明形成「華夷」分野的觀念。這一觀念最初可能以地緣方位作為判準,乃有「中國」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區別,文化高下的寓意已經可見其中。華夷之辨的論述在中國歷史上層出不窮,影響所及,東亞從日本到韓國皆相互比照,作出具體而微的回響。
清末以來的中國面對世界現代化衝擊,與東洋、西洋接觸頻繁,華夷秩序因此有了新的變動。在這漫長的互動過程中,如何描述、定義現代的「中國性」成為不斷辨證的話題。二十世紀中國歷經內憂外患,民族國家主義主導了政治思想論述,其極致甚至導向民粹極權。新世紀以來「中國崛起」,「天下」、「王霸」、「朝貢體系」等傳統理論捲土重來。與此同時,有識學者紛紛提醒重新理解、反省「何為中國」的必要。如許倬雲教授強調華夏文明的複雜多義自古已然;當代中國之所以如是,是民族千百年來內與外、「我者」與「他者」交鋒與交流的結果。葛兆光教授則提出「從周邊看中國」的方法學,認為欲瞭解中國,必先瞭解中國周邊諸國家地區如何想像、銘記、接觸中國。
近年華語語系研究崛起,反離散、去中國、在地化的聲浪此起彼落,甚至導致「寧夷勿華」的結論。論爭者的立場固然值得尊重,但也每每暴露理論掛帥,史觀和史識的不足。在這樣的語境裡回顧近世華夷論述消長,因此具有迫切意義。值得關心的是,如果華夷論述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有論述價值,我們應該如何提出問題,如何尋找答案?據此本文將處理四個方向:近世以來由日本、朝鮮發出的「華夷變態」論及中國的反應;現代中國「華夷共同體」的打造過程;新世紀以來,「華夷風起」的現象;以及「華夷之變」的芻議。本文前兩部分多有受教前賢之處,論述重心則放在第三、四部分。
我的論點是,近三百年來華夷論述的激烈轉換如果能夠提供我們任何省思,正是華夷之「辨」與華夷之「變」之間的辯證性。同樣面對歷史,前者隱含區分種族、文化、政治立場的「畛域化」(territorialization)設定,後者則藉「風」與「勢」的能動性,更新、甚至翻轉華夷關係的可能。我認為,華夷之「辨」與「變」的關鍵之一,就是對「文」─文字,文學,文化,文明─的梳理。也因此,當中國與周邊的關係面臨又一次洗牌的時代,人文學者對華夷論述的重新闡述,佔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 二、「華夷變態」
「華夷」之說濫觴於上古時期生活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華夏族(諸夏)─漢族先民的古稱。華夏較早進入農業文明,與周邊以遊牧乃至狩獵為生的族群交往過程中,因為文明發展而產生高下,從而萌發了「華夷」分野的觀念。相對於中土、中原或中國,周邊域外即有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稱。從「夷」的最初意義看,「夷」、「狄」實無明確褒貶義,但夷夏既然有別,華夏之於「夷」「狄」,還是暗含了文化優越感。但考古學者已經一再提醒我們,早期華夏部族即已雜糅夷狄蠻戎等不同成分,因此所謂「華夷」之分並非絕對判準。
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帝國,為華夷秩序構築了最初的基礎。兩漢時期將日本列島的倭奴國,朝鮮半島的三韓諸國,以及中南半島和南洋諸小國納入這一體系。華夷秩序在唐代有了長足發展,甚至跨越中亞、與阿拉伯帝國及伊斯蘭體系爭鋒。兩宋王朝一直受到北方遼、金、西夏政權的威脅,但向東、向南的發展則繼承且超越了唐代。蒙元帝國雖然保留了華夷秩序的框架,但軍事征伐之外,卻未能延伸這一體系的文化內涵。明初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艦隊七次下西洋,達到非洲東岸,一時所向披靡,以朝貢體系為準的國際關係達到巔峰。但明代後期華夷體系開始產生質變。傳教士文化、殖民勢力東來、滿清入主中原都為華夏文明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
1644年,滿族滅明,建立大清皇朝。漢族知識份子視此為正朔衰亡,天崩地解的時刻,而東亞諸國也莫不為之震動。日本幕府儒官林春勝(1618-1680)、林信篤(1644-1732)父子所編《華夷變態》一書,即記載明清易代之際中國的種種變化。林春勝在序言(1674)中寫道:
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雲海渺茫,不詳其始末。如《剿闖小說》、《中興偉略》、《明季遺聞》等,概記而已。朱氏失鹿,當我正保年中,爾來三十年所,福漳商船,來往長崎,所傳說有達江府者,其中聞於公,件件讀進之,和解之,吾家無不與之。其草案留在反古堆,恐其亡失,故敘其次第,錄為冊子,號《華夷變態》。頃間〔聞〕吳鄭檄各省,有恢復之舉。其勝敗不可知焉,若夫有為夷變於華之態,則縱異方域,不亦快乎。
《華夷變態》的形式源於德川幕府時期的唐船風說書,意即通曉中文的官員對往來中國船隻所作盤查的報告,其內容不僅包括中日貿易、天主教會地下活動,也及於中國與世界形勢。林春勝所言充分反映當時日本學者對大明亡國的看法。所謂「華夏變於夷之態」,意味明清鼎革其實是華夏禮儀之邦變成蠻夷的過程。以往的華夷秩序淪為失序狀態。隱含其下的,則是日本居高臨下、自命為華夏正統的微妙立場。
明亡後,日本、朝鮮、及越南初時皆不承認清朝。流傳東亞和東南亞的「小中華」觀念在此時變本加厲。「小中華」一方面可以指涉海外靈根自植的期許,一方面也意味「去」中華並取而代之的野心。朝鮮、阮朝及日本都將自己視為華夏正統的海外延伸。日本儒學者山鹿素行(1622-1685)在《中朝事實》把日本國稱為「中華」。朝鮮稱清帝「虜王」,阮朝自稱「中夏」,並在中南半島執行「改土歸流」、和「以夏變夷」。當時日本圖鑒、書籍仍然把大明人和大清人看成兩國人。清朝鞏固多年後,日本等國才承認滿人統治華夏的事實,但是否視清朝為華夏正統則另當別論。
早在漢代,日本即已進入雛形時期的華夷秩序,之後諸部落間通過征戰形成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向中國派遣使節,行朝貢之禮,藉中國王朝來確立權威地位。但日本天皇很早即有與中國對等的意識。公元607年聖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使「唐」,因所持國書稱天皇為「日出處天子」,令隋煬帝不悅,終迫使日本自承為避居海隅的「夷人」。爾後日本建立自為的華夷秩序,稱朝鮮為「西藩」;大化革新後,視大唐、朝鮮半島諸國及日本列島諸部族為「化外」。以後千年,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此消彼長,從「三國一」(中國,日本,印度)說到「神國觀」,從足利義滿被冊封為日本國王到豐臣秀吉兩度攻打朝鮮、撼動明朝宗主國地位,可以為例。德川時代的日本思想從朱子學,到古學,到國學,成為明治時代意識形態之底色,再加上西潮東漸之後的「和魂洋才」,即是「華夷變態」之延續。
在朝鮮,「箕子朝鮮」說其來有自,各代均有詮釋,因十六世紀性理學(朱子學)大興而更為發展。然而以「檀君」取代「箕子」作為創始先祖之說後來居上。不論如何,「小中華」的思潮一直持續不輟。壬辰倭亂後,朝鮮全盤流行崇華思想和「崇明」意識,甲申之變因此帶來極大衝擊。遲至十八世紀,士人金鐘厚(1721-1780)致信出使清帝國的洪大容(1731-1783)謂,「所思者在乎明朝後無中國耳,僕非責彼(指中國人)之不思明朝,而責其不思中國耳。」更進一步,朝鮮對於中國,「所貴乎中華者,為其居耶?為其世耶?以居則虜隆亦然矣,以世則吳楚蠻戎鮮有非聖賢之後者矣」。樸趾源(1737-1805)雖提出「近夷狄而師之」,但更著眼經世厚生的實學立場。
我們也必須注意臺灣在近代浮出歷史地表的意義。十七、八世紀漢人大量移民臺灣前,臺灣已有來自各方的土著。這些民族雖同屬南島語系,但語言文化、社會組織繁雜。1661年鄭成功攻陷臺灣,驅逐荷蘭殖民者,所依據的名號正是「明招討大將軍」。以後二十三年鄭氏家族經營臺灣,率皆以海外正統自居。1683年鄭克塽降清,明宗室後人寧靖王朱術桂(1622-1683)自縊於臺南,島上大明香火告終。
誠如楊儒賓指出,明亡之後,儒家傳統學者勤王之舉不絕,如劉宗周之於福王;黃道周之於唐王;王夫之、方以智之於永曆帝;黃宗羲、朱舜水之於魯王,皆為顯例。臺灣明鄭雖未必有大儒為其後盾,「但在亡國、亡天下的雙重道德壓力下,中國東南地區的士人會隨鄭氏政權入臺,這是可以想像的事。」然而臺灣不僅賡續由明宗室代表的中華正統,也同時促動東亞和東南亞的「華夷變態」。鄭氏家族明末橫行東亞與東南亞水域;因為與日本的血緣與貿易關係,江戶文明頗見其影響。如日本禪宗黃檗宗開創者隱元禪師東渡,即由鄭氏水師護衛。而西班牙在菲律賓的殖民政權對鄭成功、鄭經兵力戒慎恐懼,與對馬尼拉漢人的高度鎮壓,亦可窺見深層結構因素。
更重要的,華夷之辨發生在中國以內。滿人統領中原後,遺民志士以種種方式抗清未果,他們於是改弦易轍,強調正統興亡不再繫於一家一姓的宗室朝代,而訴諸源遠流長的禮樂道統。遺民如顧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等力倡亡國事小,亡天下事大。顧炎武曾有亡國、亡天下之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呂留良(1629-1683)則有言:「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義。」這類討論所在多有,不再贅述。
雍正一朝對中國的統治逐漸堅固,然而批判其僭越華夏正統的聲音不絕如縷。1728年,漢族文人曾靜(1679-1735)、張熙受呂留良華夷之辨影響,試圖遊說川陝總督嶽鍾琪反清,事發而下獄。雍正親自介入此案,合上諭、口供、以及曾靜自述《歸仁錄》等為一書,命名《大義覺迷錄》,廣為發行,不但對曾靜等的指責進行辯解,更為滿清的正統地位作出強而有力的陳述。雍正宣稱清朝政權得自天命,不容「華夷之辨」否定:
蓋從來華夷之說,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詆南為島夷,南人指北為索虜,在當日之人,不務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譏,已為至卑至陋之見。今逆賊等於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謬生忿戾,豈非逆天悖理,無父無君,蜂蟻不若之異類乎?
雍正呼應《孟子》章句,強調「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
弔詭的是,雍正以文化、德行,而不以地域、族裔、血緣,作為判斷華夷的準繩,其實呼應的正是傳統華夷論述的理想(未必是實踐)。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他對漢族正統觀作出巧妙回應。當然,夷夏之防如果真只是以聖德、明君分高下,也就不會有如此錯綜暴烈的歷史;隱藏在文化、德行之下種種動機的合縱連橫,不容小覷。以往學界多強調清帝的高壓統治,近年學者如楊念群等則指出其懷柔策略的效應。尤其江南士人經過甲申之後的激烈反抗,如何逐漸改變立場,接受清室正朔,不僅意味夷夏之防意識的艱難轉換,也意味識時務者委曲求全、甚至共謀唱和的種種考量。
不論如何,經過明清鼎革,十七世紀的「中華」已由滿人瓜代,形成「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的「大中華」觀。而海外的「小中華」則由日本、朝鮮、越南等國所發揚光大。學者藤井倫明以十七世紀末日本山崎闇齋學派為例,指出其所發展出的華夷論述可以三種不同方向界定:道德風俗優劣;主客自他關係;地理地形環境。第一指向我們所熟悉的文化決定論,強調種族血緣不是決定華夷之分的絕對原因;文化的積澱養成才更具有決定因素。第二則指向主體名分的自我決定論,強調政治實體必須就自身立場為出發點,作出我者、他者之別。而第三指向環境決定論,強調地緣環境可以成為華夷分野的因素。白永瑞則以韓國為例,說明東亞諸國在「去中華」、「再中華」的拉力中,將傳統「絕對的華」相對化,甚至異質化,以此創造政治的「際」,折衝其中,產生自為的「柔軟的主體」。
儘管立場各異,這些論述者都是從東亞周邊立場反思中華的意義,並從文化、主體、地理因素挑戰原本想當然爾的中原華夏傳統。至此華夷結構已經改變,其極致處,甚至將「中華文化」的母體中國也逐步排除在「中華」之外。十七世紀的日本對「華夷變態」的觀察,已為日後淩駕中國的野心埋下伏筆。「中國」或「中華」成為不斷播散、置換的時空場域和想像共同體。「中國」不論虛實絕續,畢竟形成有如區域鏈的脈絡關係。無可諱言的是,華夷之變雖每以文化、文明為論述要素,但政經、軍事、族群甚至環境因素始終無從規避。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 第34期(pod)的圖書 |
 |
$ 270 ~ 285 | 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 第34期(POD)
作者:中國現代文學學會 出版社:中國現代文學學會 出版日期:2019-03-05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48頁 / 19 x 2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文學
 文學,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是任何單一的書面作品。更嚴格地說,文學寫作是一種藝術形式,或被認為具有藝術或智力價值的任何單一作品,通常是由於以不同於普通用途的方式部署語言。
文學,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是任何單一的書面作品。更嚴格地說,文學寫作是一種藝術形式,或被認為具有藝術或智力價值的任何單一作品,通常是由於以不同於普通用途的方式部署語言。 它的拉丁詞根literatura/litteratura被用來指代所有的書面記錄,儘管當代定義將術語擴展到包括口頭或唱歌的文本。文學可以根據是虛構作品還是非虛構作品進行分類,也可以根據是韻文還是散文進行分類;可以根據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等主要形式進一步區分;作品往往根據歷史時期或者遵守某些美學特徵或期望進行分類。
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現實的藝術,包括韻文、散文、劇本、小說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以不同的流派表現內心情感和再現一定時期和一定地域的生活。
這個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了意義:現在它可以擴大到非書面的口頭藝術形式,可以與語言或文字本身配合,因此很難就其起源達成一致。
印刷技術的發展使得書面作品的分布和擴散成為可能,最終導致了網絡文學。
文學並不一定是客觀的,一名成功的文學家能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展現自己對於文學的主觀看法,抒發自己的情緒和感觸,但藉由嘗試建立一個「客觀的標準」,有時對能幫助作家了解「讀者的感受」以求將內心之情感與藝術表現完整的體現在讀者心中。
有時也能藉作家主觀想法帶給社會不同面相去省思現況,例如女性文學的興起。
![]()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 第34期(POD)
一群愛好文學的夥伴,深覺現代文學的應用性高過於古典文學,據於時代的需要,應該更重視現代文學的創作和研究,於是共同發起成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期望凝聚現代文學的愛好者。為凝聚現代文學的愛好者,開發新世紀現代文學的新境界,《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2004年3月正式創刊。
*本刊為有審稿制度的學術性刊物,於每年六及十二月份出刊。歡迎投稿。
章節試閱
▌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界/王德威(節錄)
■ 摘要
「華夷之辨」是中國研究中一項歷久彌新的課題。清末以來的中國面對世界現代化衝擊,與東洋、西洋接觸頻繁,華夷秩序因此有了新的變動。如何描述、定義現代的「中國性」成為不斷辨證的話題。近年華語語系研究崛起,論爭立場各有所執,但也每每暴露理論掛帥,史觀和史識的不足。在這樣的語境裡回顧近世華夷論述消長,因此具有迫切意義。本文處理三個方向:近世以來由日本、朝鮮發出的「華夷變態」論及中國的反應;現代中國「華夷共同體」的打造過程;以及新世紀以來,「華夷風起...
■ 摘要
「華夷之辨」是中國研究中一項歷久彌新的課題。清末以來的中國面對世界現代化衝擊,與東洋、西洋接觸頻繁,華夷秩序因此有了新的變動。如何描述、定義現代的「中國性」成為不斷辨證的話題。近年華語語系研究崛起,論爭立場各有所執,但也每每暴露理論掛帥,史觀和史識的不足。在這樣的語境裡回顧近世華夷論述消長,因此具有迫切意義。本文處理三個方向:近世以來由日本、朝鮮發出的「華夷變態」論及中國的反應;現代中國「華夷共同體」的打造過程;以及新世紀以來,「華夷風起...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五四」新人文導言/鄭毓瑜、高嘉謙
論近現代中國人文學,「五四」絕對是百年間發展的關鍵;因巴黎和會失敗所引發的愛國運動不僅牽涉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如果將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整理國故、實驗主義、馬克思主義、科玄論爭也納入一併考量,這無疑是晚清啟蒙運動以來最龐深的知識界革命。周策縱先生於「五四」五十周年時,解釋intellectual Revolution(知識革命),不僅是知識、思想、理性,同時也是改革行動;並認為「五四」追求真理與事實,不求諸古聖賢的新作法,是「中國文明發展史上最重大的轉折點」。而林毓生先生在「五...
論近現代中國人文學,「五四」絕對是百年間發展的關鍵;因巴黎和會失敗所引發的愛國運動不僅牽涉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如果將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整理國故、實驗主義、馬克思主義、科玄論爭也納入一併考量,這無疑是晚清啟蒙運動以來最龐深的知識界革命。周策縱先生於「五四」五十周年時,解釋intellectual Revolution(知識革命),不僅是知識、思想、理性,同時也是改革行動;並認為「五四」追求真理與事實,不求諸古聖賢的新作法,是「中國文明發展史上最重大的轉折點」。而林毓生先生在「五...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特稿】
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界/王德威
【專題論文:「五四」新人文】
「五四」新人文導言/鄭毓瑜、高嘉謙
「五四」新學之修辭學:語言思想之現代嬗變/林少陽
星際迷航:近現代文學中的宇宙視野與自我意識/潘少瑜
俄蘇文學在中國:由翻譯統計探政治與文藝的角力與權力/陳相因
論胡適的「科學方法」─以其《水經注》研究為例/朱先敏
【一般論文】
黼黻與風騷─試論楊牧的《長短歌行》/劉正忠
論葉聖陶《稻草人》審美「轉向」的可能性/金莉莉
延安講話:新中國的詩歌緊箍咒/陳大為
前期篇目
稿約
撰...
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界/王德威
【專題論文:「五四」新人文】
「五四」新人文導言/鄭毓瑜、高嘉謙
「五四」新學之修辭學:語言思想之現代嬗變/林少陽
星際迷航:近現代文學中的宇宙視野與自我意識/潘少瑜
俄蘇文學在中國:由翻譯統計探政治與文藝的角力與權力/陳相因
論胡適的「科學方法」─以其《水經注》研究為例/朱先敏
【一般論文】
黼黻與風騷─試論楊牧的《長短歌行》/劉正忠
論葉聖陶《稻草人》審美「轉向」的可能性/金莉莉
延安講話:新中國的詩歌緊箍咒/陳大為
前期篇目
稿約
撰...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