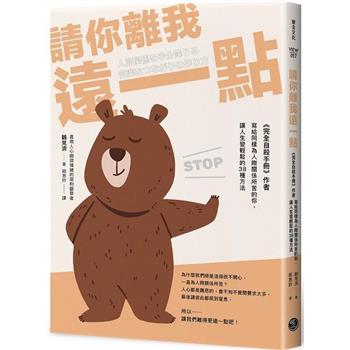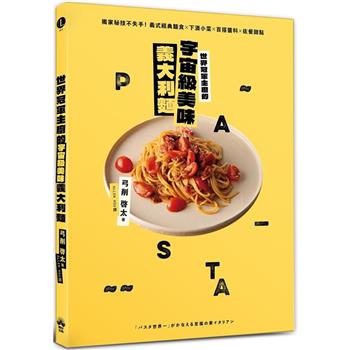誰都年輕青春,又誰都蒼老廢敗,
中年老年少年,也相同,都一樣,
既活過也死過,既劇變也不變;
戲院是奇妙的時空穿梭機,
我們坐在裡面,眾生平等,「有目共睹」。
所以我們執迷於看戲。
旁觀者都喜歡意外。
電影中出乎預料的停格,音樂裡震攝人心的休止符。
弦外之音於是柳暗花明。
所有影像閃爍眼前再霎然停止,
天地無聲,一切靜默,
這是戲中最高潮的時刻。
一如中年。
《中年廢物》是馬家輝散文選集,由三輯構成,分別是「桃紅」、「柳綠」與「藍調」。行經中年,他站在那裡看戲,聽音樂,參與奇人軼事並說給我們聽。
他寫張愛玲生前叮囑要送人的錢包,細膩考究。他談唱情歌的羅大佑,反諷自己在愛情裡的滄桑。他細細刻畫《葉問》中的甄子丹和洪金寶,帶觀眾重回硬朗的中國,擂臺上的男人面對屈辱不閃躲不退讓,我們的記憶得以悲壯還鄉。《哈利波特》戲中,男女主角與成人世界對抗,戲外,演員卻反而在演藝世界提前長大。他精準點出作品中悲涼、荒謬、動人、諷刺的一幕。
馬家輝借影抒情,以極小的框格停攝住一景一幕,藉此顯現人生如戲,一切如電如影如音似幻,我們的人生既無常流轉,也同時在戲裡永恆凝結。
作者簡介
馬家輝
入世且多情 旁觀自己的瀟灑
一九六三年生,香港人,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威斯康辛大學博士。曾任雜誌社記者、廣告創意設計、報社副總編輯,並擔任電視及電台節目主持,亦為香港《明報》世紀副刊創意顧問,文章散見於港臺及內地報刊,結集作品有《李敖研究》、《女兒情》、《都市新人類》、《愛戀無聲》、《江湖有事》、《死在這裡也不錯》、《在廢墟裡看見羅馬》、《日月》、《明暗》、《關於歲月的隱密情事》、《回不去了》等。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