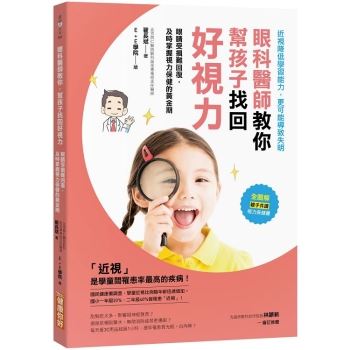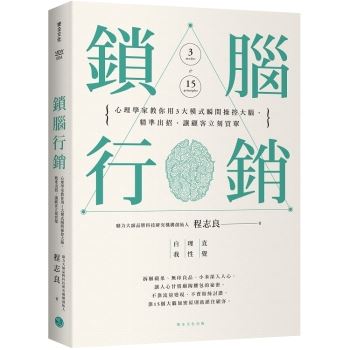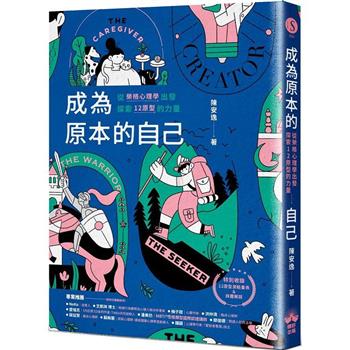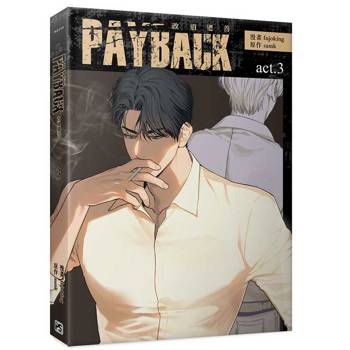英語文壇最高榮耀曼布克獎得獎作
他是僕役、哲學家、企業家、殺人兇手、總理的企業家精神導師
他是「白老虎」
巴蘭‧哈外是個說故事高手,在一盞華麗水晶燈下,他花了七個晚上對中國總理溫家寶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巴蘭出生在印度中心的小村莊,雖然來自最低種姓人家,卻是全村最聰明的孩子;家人為了生計卻讓他退學去茶館工作。他在敲木炭和擦桌子時幻想著逃跑,希望擺脫黑暗、貧窮、沒有明天的農村生活。
直到一個有錢地主雇他為司機,巴蘭的機會來了。他在本田汽車的方向盤後面第一次看到德里,看見跟他一樣身分低下的僕人與腰纏萬貫的主人在大都市裡積極鑽營權力、財富與酒色。在蟑螂、水牛、客服中心、妓女、三千六百萬零四個神、貧民窟和購物中心之間,巴蘭的人生教育就此展開。
他想要當一個忠僕,卻又壓抑不了過好生活的慾望;他學到了新印度最重要的新道德,開始策劃老虎該如何掙脫牢籠:每一個成功人士在往上爬的路上,總要流一點血吧?
故事詼諧、緊湊,敘事獨特,扣人心弦。沒有莎麗、瑜伽、塔不拉鼓,卻有對經濟新興國印度精確露骨的觀察。從黑暗的農村生活到光明的企業成功,巴蘭的旅程完全沒有道德,精采得肆無忌憚,令人難忘且愛不釋手。
作者簡介:
亞拉文‧雅迪嘉(Aravind Adiga)
一九七四年生於馬德拉斯(Madras),曾居住過印度、澳洲、美國及英國,目前住在孟買。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和牛津大學深造。曾擔任《時代》雜誌駐印度特派員。
在紐約擔任特派記者期間,曾經訪問過唐納.川普。擔任《時代》雜誌駐印度特派員時,曾走訪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尼泊爾、孟加拉,各國總理都是他的採訪對象。其報導與評論可見於《金融時報》與《時代》雜誌。
《白老虎》是他的處女作。
譯者簡介:
李佳純
天蠍座O型。輔大心理系、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媒體研究系畢業,目前從事翻譯與DJ。譯有《喬凡尼的房間》、《管家》、《藍調百年之旅》(合譯)、《生命中不可抗拒之喵》、《等待藥頭》、《安迪沃荷經濟學》等。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2008年曼布克獎
名人推薦:
〈專文推薦〉世界的確不是平的
彭蕙仙
站在「第一世界」觀看的湯瑪斯‧佛里曼,曾以「世界是平的」的角度,讓「第三世界」的印度在國際經濟價值鏈上成為新焦點,他眼中的外包聖地——印度班加羅爾正是平了的世界起點,但是在印度裔作家亞拉文.雅迪嘉的眼中,班加羅爾卻是「世界的確不是平的」的具體證明──班加羅爾的印度人因為幫美國人做事,就自覺高人一等、有了明顯的傲氣。
班加羅爾的成功就像德里的不成功一樣,讓有感覺的印度人傷心,因為他們知道成功與不成功的理由都是一樣的:社會階級。無法撼動的社會階級加深了成功者與不成功者之間的鴻溝,財富並沒有給印度社會帶來普遍的改變,反而加深了也強化了強度社會本來的階級落差。雅迪嘉對這無法改變的印度傷心,強烈到他甚至不能責備,不能咒罵,只能諷刺──愛有多深,恨就有多強烈,恨太深,諷刺,就停不下來。在這些表面風趣內在顫抖的文字裡,讀者看到心如刀割的印度人,和「金磚四國」的樂觀光明完全不同;和充滿威脅動能的《世界是平的》也完全不同。
其實,從奈波爾到伊蘭達蒂‧洛伊(《微物之神》),關於印度,這些年讓人有愉悅之感的文學作品真的不多。因為,就像《白老虎》所描述的,這個世界有兩個完全不同的印度:光明的和黑暗的,清明的和混沌的,富有的,以及窮乏的。印度的真貌就是有讓人開心不起來的地方。
印度,古老的恆河,佛陀的國度,智慧的源頭,在雅迪嘉的筆下卻是無望的「雞籠」,印度「黑暗區」的廣大窮人像雞籠裡待宰的雞,明明看著一隻一隻左鄰右舍、親朋好友陸續被拉出去,卻還是安於現實和現狀,絲毫沒有想過要離開這個雞籠,甚至於,當其中某隻雞動心起念要脫離時,雞籠裡的其他雞還會聯手幫「主人」把這雙雞追回來。這樣認命、次第排列、牢不可破的社會階級秩序,才是真正讓人絕望的地方。
雅迪嘉在這本拿下曼布克獎的小說《白老虎》裡寫就是這樣一個絕望的故事。在印度貧民窟長大的孩子巴蘭,為了擺脫貧窮,一路努力向上、精心布局;然而,因為印度的種姓與階級制度根深柢固、滴水不漏,巴蘭最後選擇殺死他的雇主(留學美國的印度富豪之子),並帶著雇主的錢跑到班加羅爾,成為一名成功的外包企業家。
很顯然的,佛里曼看到的班加羅爾和雅迪嘉看到的班加羅爾並不相同。當佛里曼說「世界是平的」的時候,他掛心的是,班加羅爾會搶走多少美國人的飯碗?請注意,飯碗是從美國人手中「搶」過來的哦;雅迪嘉看班加羅爾卻充滿反諷冰涼,出身貧民區的巴蘭竟然必須用殺死雇主的決絕手段才能脫離貧窮、加入班加羅爾的外包行列,成為顛倒生活配合美國人作息的外包企業——在一個窮人的命運早成定局的社會裡,機會散發出的致命誘惑,為貧富不均的森然秩序舖排出人性善惡模糊的空間,這是小說動人的地方──可惡之人必有可憐之處。讀者認同的並不是巴蘭殺人的邏輯,讀者是為巴蘭不認命的決心怦然心動並且心疼。
殺人者,天理不容,那麼,巴蘭的心中是否有一絲一毫的悔意?殺人者會招致在鄉下家人滿門抄斬,那麼巴蘭的心中可曾有一絲愧咎?
表面上,巴蘭不懼不悔,雅迪嘉甚在結尾處讓巴蘭打算生孩子來暗示他在班加羅爾重新開始的生活已經豐裕美好到他想要延續下去,但骨子裡,巴蘭怎麼想呢?殺死有權有勢的主人後,他已不再看報紙、不看新聞,怕的就是會突然看到家鄉的消息,像什麼某某村落某一家族全數遭到滅口之類的新聞,雅迪嘉讓巴蘭不看的東西,正是他要讓讀者看到的東西。《白老虎》裡處處都是這種「留白」,透過「沒有敘述」,讀者感受到的是瀰漫的肅殺,以及與這種肅殺對抗的生命韌性,也才真正了解巴蘭為了改變命運,巴蘭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小說以寫給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七封信貫穿主角巴蘭從貧民區的生活一路到成為企業家的歷程。好了,為什麼這些信是寫給溫家寶呢?書裡面一再提到的、可能的理由是:印度的民主選舉。「中國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民主」,巴蘭真的想跟中國炫耀印度的民主嗎?當然不是的。小說裡,「印度式的民主」根本是一場悲劇式的鬧劇,完全不足取。這些信,從這個世界上人口第二大的國家寫給人口第一大的國家;從一個窮人基本上不可能翻身的黑暗國度, 寫給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的改革新天地;從一個世人賴以開悟重生的宗教原鄉,寫給金融海嘯過後新的世界救世主;從一個古老的國家寫給另一個同樣古老的國家……,這當中,有許多不言可喻的心心相印、惺惺相惜,以及,更可能的,一種「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心情練習。因此,信的收發兩端,構成了這部小說的內在人道暗示。
白老虎是保育類動物,雅迪嘉的《白老虎》既已寫成,或許就提醒了世人,印度的白老虎瀕臨絕跡,世人聯手保護 ,刻不容緩。這部小說在讓人發笑的同時也讓人落淚,在讓人落淚的同時,又催生了更深刻的諒解,以及,行動的力量。
(本文作者為記者、作家)
得獎紀錄:2008年曼布克獎名人推薦:〈專文推薦〉世界的確不是平的
彭蕙仙
站在「第一世界」觀看的湯瑪斯‧佛里曼,曾以「世界是平的」的角度,讓「第三世界」的印度在國際經濟價值鏈上成為新焦點,他眼中的外包聖地——印度班加羅爾正是平了的世界起點,但是在印度裔作家亞拉文.雅迪嘉的眼中,班加羅爾卻是「世界的確不是平的」的具體證明──班加羅爾的印度人因為幫美國人做事,就自覺高人一等、有了明顯的傲氣。
班加羅爾的成功就像德里的不成功一樣,讓有感覺的印度人傷心,因為他們知道成功與不成功的理由都是一樣的:社會...
章節試閱
謹致:
溫家寶閣下
寄件人:
白老虎
總理先生:
你我都不說英語,但有些事只能用英文講。
我的前雇主,已故的阿莎克先生的前妻粉紅夫人教會我其中一句這樣的英文;而在今晚十一點三十二分,大約十分鐘前,當全印廣播電台的女士宣布:「家寶總理將於下週前來班加羅爾訪問」,我嘴裡立刻吐出那句話。
事實上,每當像您這樣的大人物來到我國參訪時,我都會講一次。倒不是我對大人物反感,就我看來,我認為我跟您是同類。但每當我看到敝國首相與他那幫尊貴的徒眾們坐著黑頭車到機場,下了車在電視攝影機前向來賓行合十禮,告訴訪客印度是個多道德多神聖的國家,我就得用那句英文不吐不快。
現在,閣下您即將在本週來我國訪問了,不是嗎?全印廣播電台在這種事情上通常還挺可靠的。
剛才那句是個笑話,大人。
哈!
所以我才想親自問您,是否您真的要來班加羅爾。因為如果您真的要來,我有重要事情相告。電台的女士說:「家寶先生有任務在身,他想認識真正的班加羅爾。」
聽到這句話時,我的血液都凝結了。如果說有誰知道班加羅爾的真相,那個人就是我。
播報員女士接著說:「家寶先生想與印度企業家會面,聽他們親口說說自己的成功故事。」
她繼續解釋了一下。很顯然,大人,您們中國在各方面都比我們先進,唯獨沒有企業家。敝國雖然沒有飲用水、電力、下水道系統、大眾運輸工具、衛生觀念、紀律、禮貌或準時觀念,但我們確實有企業家,成千上萬個,在科技領域裡更比比皆是。而這些企業家,我該說我們這些企業家,設立的外包公司差不多掌控了全美國。
您希望學到如何才能培養出一些中國企業家,這是您來訪的目的,這讓我倍感窩心。但我又想到,為了符合國際禮節,敝國首相和外交部長會帶著花環、作為伴手禮的甘地小木雕、列滿關於印度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小冊子,在機場迎接您。
所以我必須用英文講那句話,大聲地講出來。
我不光是詛咒和罵髒話。我是個身體力行、力求改變的人。我當場決定要寫一封信給您。
在信的開頭,容我對您說明我對中國這古國的崇敬。
我在一本叫做《異國東方奇譚》的書裡讀到你們的歷史,書是我從人行道上撿來的,想當年我試著給自己一些啟蒙時,我會到舊德里的周日二手書市逛逛。書裡講的大多是香港海盜和黃金,但也有一些有用的背景資訊,書裡面提到你們中國人熱愛自由,相信個人自由。英國人曾經想要奴役你們,但你們不讓他們得逞。我很欽佩這點,總理先生。
您要知道,我曾經是個僕役。
世界上只有三個國家從來沒被外國人統治過:中國、阿富汗、阿比西尼亞。我只欽佩這三個國家。
由於我敬重中國人對自由的熱愛,同時也相信未來世界是掌握在黃皮膚和棕皮膚的人手裡,因為我們過去的白人主子把精力浪費在雞姦、講手機和嗑藥上,所以我想告訴您班加羅爾的真相,不收取任何費用。
就是告訴您,我一生的故事。
當您來到班加羅爾,在等紅燈時,會有個男孩候跑到座車旁敲您的車窗,拿著用玻璃紙精心包裝的盜版美國商業書籍,書名可能是:
經商成功的十個祕密!
或是
七天內輕鬆成為企業家!
請不要浪費您的錢在美國人的書上,那些都已經過氣了。
我才是明天。
若說正規教育,我或許有些欠缺,坦白說就是我學校沒畢業。又有誰在乎呢!我沒讀過很多書,但是該讀的都讀了。我是自修而成的企業家。
這種人才最優秀,相信我。
當您聽完我的故事,知道我是如何到班加羅爾,如何才成為最成功(雖然可能也最不為人知)的生意人,您就會完全瞭解到,在這人類光榮的二十一世紀,企業家精神是如何誕生、培養和發展出來的。
快接近午夜了,家寶先生。正是說話的好時機。
我感覺很輕鬆,大人,希望您也是。
我們開始吧。
在開始之前,大人,我從我的前雇主,已故的阿莎克先生的前妻粉紅夫人那裡學到的那句英文是:
What a fucking joke.(真是個他媽的笑話!)
失蹤人口協尋
民眾注意,明令通緝照片中之人,本名巴蘭.哈外,又名穆那,人力車伕維克蘭.哈外之子。年齡:介於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膚色:暗黑。臉形:橢圓。身高:約五英尺四英寸。身材:瘦小。
這個嘛,以上所說已經不算完全正確,大人。「膚色暗黑」依然沒錯,不過我有點想試試最近推出的美白乳霜,印度男人也可以像西方人那樣白,但其他的,唉,錯得離譜。班加羅爾的生活很不錯,有美食、啤酒、舞廳,我沒得抱怨。「瘦」跟「小」?哈!這陣子我的體態好多了!「胖」和「啤酒肚」或許比較正確。
但我們繼續吧,時間可不多。現在我最好解釋一下。
……來自迦耶區的拉斯滿加村。
這地區非常有名,全世界都知道。貴國的歷史是由我出身之地塑造出來的,家寶先生。您一定聽過菩提迦耶,佛陀在那裡的一棵樹下證悟,開創了佛教,然後佛教流傳到全世界,也包括了中國。菩提迦耶正好在我家鄉附近!距離拉斯滿加不過幾英里!
我不知道佛陀是否曾經步行經過拉斯滿加,有的人說有。我自己覺得祂是用跑步經過這裡,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村外,一次都沒有回頭!
閣下,我很榮幸向您報告,拉斯滿加就是典型印度村莊的天堂,有足夠的電、自來水和電話。我們村莊的孩子三餐都吃營養的肉、蛋、蔬菜和扁豆,如果用捲尺和磅秤來量他們的身高體重,都符合聯合國等機構設定的最低標準,我國首相都簽署了這些機構的協定,也經常高調出席眾多國際研討會。
哈!
電線桿──不能用。
水龍頭──壞了。
兒童──就他們的年齡來看過瘦也過矮,頭的尺寸過大,大眼睛閃亮亮,像印度政府內疚的良心。
對,典型印度村莊的天堂,家寶先生。改天我一定要去中國,去看看你們的村莊是否比較好一點。
大路中央有成群的豬隻聞遍整條污水溝,每隻上半身都很乾燥,長毛糾結成針狀,下半身則像泥炭一樣黑,身上的污水閃閃發光。路上還有鮮紅和棕色的羽毛飛掠而過,因為公雞就在房子屋頂飛上飛下。穿過豬群和雞群就是我家,如果它還在的話。
在我家門口,您會看見我們家裡最重要的成員。
那頭水牛。
嫌犯最後現身時身著藍格子聚酯襯衫,橘色聚酯長褲,褐紅色拖鞋……
褐紅色拖鞋?呸!這種細節只有警察才編得出來。我斷然否認。
藍格子聚酯襯衫,橘色聚酯長褲……呃,嗯,我也很想否認,但很不幸他們沒說錯。那種衣服,大人,是僕人喜歡的樣式。製作這張海報的那天早上,我還是個僕人。(但那天晚上我就自由了,而且還穿上不一樣的衣服!)
好,那張海報上有個句子實在讓我很不滿,讓我暫且回去修改一下:
……人力車伕維克蘭.哈外之子……
是人力車伕維克蘭.哈外先生之子,謝謝!我父親是個窮人,但他正直又有勇氣。如果沒有他的教誨,我現在不會坐在這個水晶燈下。
每到下午,我便從學校到茶館找他。茶館是村裡的中心,警察到村裡來騷擾村民時,也會把他們的吉普車停在這裡。太陽快下山前,會有人繞著茶館走三圈,大聲搖著手上的鈴,他的腳踏車後座綁有貼在厚紙板上的色情電影海報。一個傳統印度村莊怎能少了色情電影院呢,大人?河對面有一家戲院,每天晚上都在播這種電影,兩個半小時的奇情故事,都由金髮美國女人或寂寞的香港女士主演──這是我猜的,總理先生,我可從來沒有跟著其他年輕人跑去看那種電影!
人力車伕在茶館外把車停成一直線,等待巴士讓乘客下車。
嗯,我懷疑中國──或地球上其他文明國家──也有人力車伕,您要親眼看見才知那是什麼。骨瘦如柴的男人坐在腳踏車上,身體往前傾踩著踏板,後面車廂上載了小山丘似的中產階級皮肉──胖男人帶著胖老婆,以及他們的購物袋和食品雜貨。
當你看見這種骨瘦如柴的男人,請聯想我父親的模樣。
他是個人力車伕,或許該說是人的馱獸,但我父親是個有計畫的人。
我就是他的計畫。
謹致:
溫家寶閣下
寄件人:
白老虎
總理先生:
你我都不說英語,但有些事只能用英文講。
我的前雇主,已故的阿莎克先生的前妻粉紅夫人教會我其中一句這樣的英文;而在今晚十一點三十二分,大約十分鐘前,當全印廣播電台的女士宣布:「家寶總理將於下週前來班加羅爾訪問」,我嘴裡立刻吐出那句話。
事實上,每當像您這樣的大人物來到我國參訪時,我都會講一次。倒不是我對大人物反感,就我看來,我認為我跟您是同類。但每當我看到敝國首相與他那幫尊貴的徒眾們坐著黑頭車到機場,下了車在電視攝影機前向來賓行合十禮,告訴訪客印...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