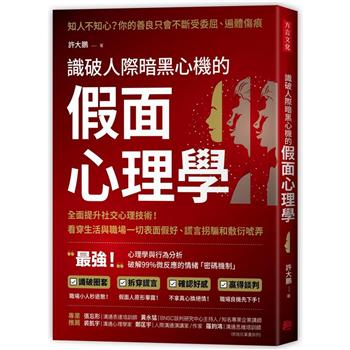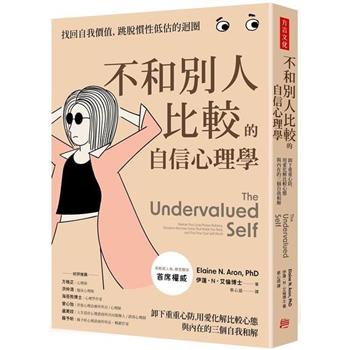十一月某天的落日餘暉下,我們在歐席古的其中一個鮭魚養殖籠旁,凍得渾身發抖。數千尾鮭魚浮在籠子頂端不停打轉,牠們搖頭擺尾、跳躍騰挪,爭搶懸在半空的塑膠管所噴出有如五彩紙屑的錠狀飼料。魚群似乎毫不受室外華氏零下五度(約攝氏零下二十度)的氣溫影響,牠們對於藏身魚群之中徐緩移動的新奇機械似乎也不知不覺:一台類似長橢圓形版R2-D2的機器人正朝四面八方發射綠色雷射光束。
這台暱稱「刺鰩」(Sting Ray)的設備是由深海鑽油產業的工程師為了消滅海蝨專門打造,是歐席古「軍火庫」裡正在進行測試的武器中,特別稀奇古怪的一件。「刺鰩」會透過即時傳輸影像「監看」魚群,並利用類似霍爾赫.艾勞德的「停看噴」機器人內建軟體的人工智慧程式,辨識魚鱗顏色和質地有無異常。就如「停看噴」機器人學會如何分辨雜草和作物,「刺鰩」也學會區分海蝨和鮭魚鱗片上的斑點。機器人一偵測到海蝨,就會在數毫秒內發射一道常用於眼科手術和除毛的二極體雷射,將海蝨消滅。鮭魚的魚鱗像鏡面一樣會反射光束,但呈凝膠狀有點像蛋白的海蝨在雷射照射下,會變得硬脆並漂離。
歐席古與兩名競爭對手萊瑞海產集團(Lerøy Seafood Group)和薩爾瑪集團(SalMar)合作,為機器人研發計畫投入一百五十萬美金的種子基金。三家企業最早於二○一四年開始進行測試,如今在挪威和蘇格蘭各地的鮭魚養殖場共已裝設約兩百台專門焚化海蝨的機器人。不過歐席古談起這項科技時只輕描淡寫。「這只是將消滅海蝨的古老方法加以機械化。」他告訴我。「刺鰩」機器人模仿的是大自然中所謂的「清潔魚」如隆頭魚(wrasse)和圓鰭魚(lumpsucker):這種清潔魚會將寄生在大魚鱗片上的海蝨一隻一隻吃掉。多年來,歐席古都會在鮭魚養殖籠裡放入好幾批清潔魚,作為減少海蝨感染的防疫措施,但是只靠清潔魚群還是無法應付大規模爆發的海蝨疫情。而飼養除蝨用的清潔魚群不但必須提供特殊食物,還要在養殖籠內為牠們打造講究的海藻棲地。
研發「刺鰩」機器人的公司總經理約翰.布列維克(John Breivik)表示,這台機器人是仿效圓鰭魚再加以改良。「每十萬尾鮭魚可能需要一萬尾清潔魚才能控制住海蝨數量,但換成雷射機器就只需要一到兩台。」他強調清潔魚和機器人在除蝨工作上可以相輔相成。清潔魚比較擅長解決魚鰓下面的海蝨,而機器人可以鎖定清潔魚看不見的無色海蝨幼蟲。「這是老方法與新方法的協同作業。」他如此分析。在使用「刺鰩」的養殖場,海蝨數量減少了百分之五十,而他們的人工智慧系統也透過累積鎖定海蝨的經驗,變得更聰明、更有效率。「就像是複
利效應。」布列維克說。至於歐席古則沒有布列維克那麼樂觀。「再看看。」他語氣平板,兩眼覷著養殖籠中不停有光束閃動的冰冷海水。
多年來測試過無數新方法皆徒勞無功,歐席古的憂慮其來有自。大約十年前,海蝨問題剛開始失控時,歐席古和其他業界領袖在飼料裡混入以「虫拜拜」(Slice)為商標的農藥「因滅汀」(emamectin benzoate)來除蟲,這種藥劑會經由鮭魚腸道內襯進入組織,海蝨在此吸收藥劑之後就會斃命。使用藥劑一開始有效,但後來海蝨身上出現抗藥性。歐席古和其他業者也試過藥浴法,在鮭魚成熟期間每隔數週以雙氧水沖洗。但海蝨再次適應了新環境。他們也試過用高壓水流清洗,把感染海蝨的鮭魚送進類似洗車場的設備裡沖洗。但這種方法所費不貲,甚至帶給鮭魚心理創傷造成發育不良。
現在歐席古在測試「刺鰩」機器人以外的其他機械技術,包括能夠容納十五萬尾魚的巨大活動式養殖籠。如果籠內有可能爆發海蝨疫情,就能將整個養殖籠降入更冰冷的海水層,讓海蝨無法存活。他也在研究於養殖籠外裝設孔目極為細小、可阻絕海蝨進入的網狀護板,再搭配水下攝影機和數位感測器,以及早偵測海蝨疫情。
若是所有措施都宣告無效,歐席古也已預作準備,打算將魚群全數隔離。他斥資數千萬美金,研發出外壁材質為固體聚合物的球形養殖籠,這種稱為「蛋籠」(Egg)的籠子深一百五十英尺、寬一百英尺,每籠可容納二十萬尾鮭魚。「蛋籠」與北歐海岸線的美學背道而馳,半浮半沉在峽灣中,儼然像白色幽浮,但是可以完全阻擋寄生蟲入侵。此外「蛋籠」也號稱具備其他環保層面的優點,包括減少排泄物排放、避免鮭魚生病或逃脫,「蛋籠」與其他研發中的「密閉式圍容系統」(closed containment system)皆獲得環保團體和沿海居民的支持。然而,這種技術非常複雜且成本高昂。「蛋籠」裡的水必須從較深的海水層打入,還需持續換水過濾,以除去微小的汙染物;籠內必須裝設扇葉,以製造出強度經過精密計算的水流供魚群逆流游動(鮭魚能夠游很長的距離,養在靜水裡無法鍛練出適合的肌肉量);需要裝設浮標系統以吸收籠外水流造成的衝擊(互衝的水流事實上可能會讓魚群暈眩不適);籠內產生的大量排泄物和廢物需要捕集和處理;必須進行徹底而全面的衛生清潔措施,以維持蛋籠清潔和籠內魚群的潔淨健康。歐席古也投入經費研發一種甜甜圈形的圍容系統(暱稱自然就是「甜甜圈」[the Donut]),它的運作原理和「蛋籠」很相似,但是設計成可產生控制得更精準的強勁水流讓鮭魚逆流而游,功用就在於養出「身材更好」的魚群。
某方面來說,這些圍容系統就是水中的垂直農場—皆是由高科技嚴密控制的生長環境。採用圍容系統的水產養殖場,理論上至少能夠抗衡海洋暖化的壓力:籠內的海水可自更深、溫度更低的水層抽取,酸鹼值則可加以處理調整。但這些措施都會導致成本節節攀升。「投入大筆金錢只為了矯正水產養殖業的錯誤,這種做法也許顯得很荒謬,」英格麗.羅梅德如此對我說,「要是全球對於海鮮的需求量沒有飆高,而捕撈的漁獲量也沒有這麼急速衰減就好了。」
中國的水產養殖始於西元前一千年左右,早在西周時期就有人養殖鯉魚。當時還沒有任何生態系統的科學論述,但是周朝人發展出現今所謂的「混養」(polyculture)機制,即結合了水產養殖、種植蔬菜和圈養牲畜的整體系統。牲畜和魚群的排泄物可以用作推動系統運行的燃料:利用鴨子和豬的糞肥在魚池裡培養藻類,而富含氮的微小藻類則可作為池中幼鯉的食物。鯉魚長成之後就可移往水稻田放養,魚群會吃掉可能傷害稻作的雜草、昆蟲和幼蟲,富有氮的排泄物可幫作物施肥;而田中的水稻不僅可幫魚群擋太陽,還能在鳥禽前來捕獵時供魚群藏匿。「這種稻魚共生系統中,隱含深刻的生態智慧。」南方水產的喬許.高德曼告訴我。「比起分別種稻和養魚所利用的土地面積還小,卻能產出更多的稻米和漁獲,還能節省肥料、殺蟲劑和勞力成本。」混養系統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至今在中國仍有數百萬英畝的水稻田採用此種農法。
然而到了現代,中國以及其他地區大多數的水產養殖業者採行的是農企業單一耕作模式,類似美威集團的鮭魚養殖,以極大規模生產單一產品。養殖場的單一魚種養殖方式導致嚴重的近親交配問題,持反對意見者認為這會有損魚群健康,長久下來甚至不利於水產養殖業的營運。有愈來愈多新創業的較小規模水產養殖業者如高德曼,則致力於復興古老的混養方法並應用於大規模魚類養殖。「概念是讓籠飼魚群產生的排泄物滲入周遭水域,為其他作物提供肥料養分。」如此一來既能有效處理汙染物,也能將生產力最大化。
早在一九八○年代初期,高德曼還是就讀採進步主義教育的漢普郡學院(HampshireCollege)的大學生時,就創辦了他的第一座水產養殖場,他親手打造出一個系統,可將魚群排泄物當作羽衣甘藍、萵苣、番茄和莓果的肥料。如今,南方水產的總部便設在麻薩諸塞州的特納瀑布(Turners Falls),距離漢普郡學院二十分鐘車程,高德曼將此處一座舊機棚改造成可養三十萬尾尖吻鱸的魚塭。他首先吸引新英格蘭的主廚來與他合作,將養殖鱸魚「當地捕撈」的特色用以招徠顧客,儘管這種鱸魚原本生長在澳洲和東南亞。連鎖超市和餐飲業者也受到吸引:全食超市、「藍圍裙」(Blue Apron)生鮮食材電商平台、時時樂連鎖美式餐廳(Sizzler),以及股東包括李奧納多.狄卡皮歐(Leonardo DiCaprio)、為全國超市供貨的「珍愛鮮味」(Love the Wild)冷凍養殖魚類加工產品製造商,皆將南方水產列為供應商。雖然市場對於養殖鱸魚的需求增加,高德曼卻開始重新省思讓公司獲得成功的經營模式。
與高德曼十四年前創業的時空相比,世界已經大為不同:「我們這個年代的首要環境議題是氣候變遷,以及如何以更精確的方法衡量氣候所造成的衝擊,而我的想法從此也不同以往。」高德曼近年慢慢將養殖事業重心移往越南。雖然自家產品無法再標榜「當地捕撈」,但高德曼表示:「在越南養殖的尖吻鱸更好,碳足跡也更少。將養殖場移往尖吻鱸的原生地,收穫後冷凍再運往市場販售,所消耗的資源事實上比先前在美國當地養殖的模式更少,與一般直覺所預期的情況剛好相反。」
拜訪他在特納瀑布的養殖場時,我明白了原因何在。鱸魚養殖場就像是水產版的珀杜食品公司(Perdue)養雞場,每個小小的養殖槽裡都擠了成千上萬尾魚。特納瀑布的養殖場需要巨大的水處理系統,每天必須能過濾超過五千萬加侖的水。系統本身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因為需要持續不斷抽取極大量的水加以淨化和充氧。「很像開了一間加護病房,」高德曼邊說,邊從養殖槽裡撈出一尾蒼白已死的尖吻鱸,「魚群生活福祉的所有層面都必須在掌控之中,否則整群陣亡不過是十分鐘內的事。只要有個幫浦或閥門故障,牠們就沒命了。」像「蛋籠」這樣設在海洋中的密閉圍容系統,在物流上的很多層面都與陸上的水產養殖系統一樣複雜,但是具備一項關鍵優勢:水資源容易取得且不虞匱乏。
在越南沿海開設養殖場後,高德曼得以取法中國古老的整合式水產養殖概念,養一些其他水產跟尖吻鱸當鄰居。他在養殖槽周圍種植呈長簾幕狀的蘆筍藻(Asparagopsis)以及其他可食用的藻類,這些古老的水生物種能夠儲存二氧化碳,並吸收魚群排泄物裡的硝酸鹽和磷酸鹽,再轉化為自身組織。高德曼說永續發展的關鍵在於學習吃位在食物鏈最起始端的食物,而海藻的位置幾乎就在最開端。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亞曼達.利特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 210 ~ 449 | 明天吃什麼:AI農地、3D列印食物、培養肉、無剩食運動……到全球食物生產最前線,看科學家、農人、環保人士在無可避免的氣候災難下,如何為人類找到糧食永續的出路
作者:亞曼達.利特 / 譯者:王翎 出版社:臉譜 出版日期:2021-07-08 語言:繁體書  1 則評論 1 則評論  共 1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明天吃什麼:AI農地、3D列印食物、培養肉、無剩食運動……到全球食物生產最前線,看科學家、農人、環保人士在無可避免的氣候災難下,如何為人類找到糧食永續的出路
歡迎收聽《讀冊過生活》節目,第079集 【 談《明天吃什麼》一書】
☆普立茲獎得主、《第六次大滅絕》作者伊麗莎白‧寇伯特(Elizabeth Kolbert)激賞之書☆
☆亞馬遜書店逾兩百則評價,讀者平均四點六顆星好評推薦☆
➢➢嚴峻的氣候與環境挑戰當前,全球糧食危機迫在眉睫,
想要繼續餵飽全世界,就得在傳統與創新間找出「第三條路」!
吳東傑(綠色陣線執行長)
余麗姿(農傳媒總編輯)
余宛如(桃園市政府資訊科技局局長)
金欣儀(直接跟農夫買社會企業創辦人)
童儀展(食力foodNEXT創辦人暨總編輯)
董時叡(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副院長)
蔡培慧(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執行長)
賴青松(青松米、穀東俱樂部發起人)
——齊聲推薦
➢➢日漸攀升的年均氣溫、不斷膨脹的全球人口、益發稀缺的天然資源,與節節下降的農地面積……
我們習以為常的餐桌風景,即將不復存在——人類的明天可否產出足夠的糧食?又能吃些什麼,以維繫文明存續?
全球的糧食生產現場向來深受氣候與環境的影響。
而近年異常的乾旱、高溫和洪澇發生頻仍,聯合國估計,
未來糧食產量可能會以每十年遞降百分之二至六的幅度,
威脅著人類賴以維生的重要命脈。這些損失會讓食物價格在二○五○年上升近兩倍;
在世界人口達到九十億之譜時,糧食引致的種種衝突與挑戰將更趨嚴重。
本書作者亞曼達.利特為了這重大且迫切的議題,
造訪了全球許多地方,如中國、肯亞、以色列、挪威以及美國許多州,
她親至科學家、農人、環保人士工作的各個領域,
一探他們分別拿出怎樣的應對之道,以回應全人類迫在眉睫的危機:糧食不足。
作者綜覽動植物科學、食品科學、糧食生產技術,
以及氣候與環境科學等面向,從全方位、多角度探討與食物相關的重要議題。
這是一本放眼全球、夠宏觀、可讀性也高的作品,
揭露了世界各地為了糧食供應而絞盡腦汁、尋找出路的狀況與進展。
在本書中,作者會帶我們看到——
❏挪威水產養殖業者巧妙利用人工智慧,訓練除蟲機器人在毫秒之間,以雷射光除去養殖鮭魚身上的海蝨。
此做法無須飼養除蝨用清潔魚,也能降低對海洋生態的破壞程度。
❏美國最大垂直農場運用先進的氣耕技術,利用布片取代土壤,讓作物根系穿過布料懸於半空,
並藉著噴灑富含養料的混合溶液霧滴,取代耗水、造成汙染的灌溉與施肥,同時又能產出味道不輸傳統農法種出的蔬菜。
❏出身印度的食品研發者努力開發「實驗室培養肉」,利用動物幹細胞製作出「活的」肌肉細胞,
口味與衛生均不遜於屠宰肉品,而溫室氣體排放量相較傳統畜牧業也少了四分之三。
❏材料科學界經由研究蔬果外皮構造,找出方法將釀酒剩餘的葡萄皮再製為天然「密封噴劑」:
噴在蔬果上即可拉長農產品保存期限,改善市場、餐飲業者與家戶中剩食浪費的問題。
❏農田中數位工具應用的潛力日漸受到重視:裝設紅外線感測器的無人機可在田地上方來回巡視,
以監測作物吸收和反射陽光的情況,供農人從遠端即時評估作物的生長和健康情形。
❏缺水的以色列數十年來推動具前瞻性的水利工程計畫,利用數學演算法偵測並預防供水管線破管、漏水,
更回收再利用廢水,以供灌溉、工業用水,與民生用水區隔開來。最終在國內淡水稀缺的條件下,依然做到了水資源自給自足。
透過作者第一手記錄的這些故事,讀者會對目前全球糧食產製的現況與燃眉之急,
以及未來可能的解方與技術突破,有更深刻的理解。
另外,也可能在看待食物生產、食品科技應用,乃至於政府相關政策等方面,獲得更多省思的角度。
▍口碑推薦
亞曼達‧利特用《明天吃什麼》一書帶領我們暢遊未來的世界,整段旅程令人悚然、刺激無比,而最終也相當振奮人心。
——伊麗莎白‧寇伯特(Elizabeth Kolbert)/《第六次大滅絕》作者
本書內容充實,結合了傳統、人道、文化、環保與科技。作者各種資料引用出處詳細,同時文字風趣,非常難得。
——余淑美/中央研究院院士、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全球正在遭受COVID-19病毒肆虐的同時,氣候變異、土壤鹽化、耕地面積減少、海洋污染……嚴苛的生態失衡,
威脅全球糧食生產的腳步沒有停歇,再不行動,我們將無法餵飽全世界。然而,自《寂靜的春天》問世以來,
對於農糧體系的論戰逐漸變成「去發明化」與「重新發明」兩個路線,兩者難以交集跟對話。
作者切入新興科技的快速發展,探究科技創新如何用AI、3D列印、大數據等在世界各地,
針對基改種子、除草劑、過度捕撈、食品加工……這些當代食農體系的問題指出一條新的道路:
例如一個信奉樸門農法的程式工程師,用科技來服務生態,減輕地球壓力的同時,又能餵飽全世界
。所幸,就我所知,台灣也在這「第三條路」上沒有缺席。
——余宛如/桃園市政府資訊科技局局長
這是個既有旱災,又頃刻淹大水的年代,同時也是個一年之內不斷創下高溫紀錄,又被寒流威逼的世紀,
這就是我們現在生存的地球。本書作者試圖探索能否以永續且公平的方式餵飽所有人的大哉問。
「要麼在大自然給你重擊時順勢而為,要麼轉行去做別的」,為了人類的未來,
作者選擇了第一條路去找出解決之道。然而,這類書籍往往很容易淪為說教式的論述,
但作者卻可以非常生動地將每種解決方式用故事性的文字,帶領讀者從一個個故事裡的人、事、物
去了解永續飲食所面臨到的問題與挑戰,也將該書的閱讀性提高到另一個層次。
——童儀展/食力foodNEXT創辦人暨總編輯
「結凍的蘋果花」故事發生在二〇一二年美國密西根州,當年的蘋果、櫻桃花全部罕見地在四月凍死、蘋果減產近九成。
美國佛羅里達州也因暖冬與低溫時數不足,造成桃子果實偏小形狀不佳,科學家推測,極端氣候所致農作物災損情況只會愈來愈頻繁……
俗話說:「呷飯皇帝大。」意思是三餐溫飽是人民最重要的事,面對極端氣候造成的天然災害農損,
產量減少背後的意義是,我們亟須正視糧食不足的危機。以台灣來說,二〇一八年相較二〇一九年,
農作物的總產量就減少百分之四.八九,這也呼應了今年缺水危機,許多農民辛苦栽種的農作物都死於乾旱的困境。
作者在書中提到,比起早期人類野外採集的游牧時代,從事農耕更是勞力密集的工作。
隨著非洲肯亞地區在過去二十五年的平均氣溫變化達到史上最高溫,蟲害、農作物疫情增加,
人類如何在更炎熱的氣候條件與全球人口不斷增加之下,餵飽所有人呢?
若想了解過去到未來農業發展的脈絡,以及現今其他國家的糧食產製現況(諸如冷凍乾燥正餐、人造肉),
這本書將會是最好的嚮導,帶我們一起用不同的觀點與角度,來了解全球從土地到餐桌的議題。
——蔡培慧/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執行長
在這個氣候暖化、旱澇交替、瘟疫橫行的年代,我們習以為常的小確幸還能維持多久?作者從一位關心自然保育/環境永續的消費者立場,
開始思索並面對人類可能的未來──就從每天的餐桌出發!從美國到中國,從基改作物到農業機器人,或許您未必同意作者的思考與論述,
但不得不佩服她世界走透透的超強行動力,以及以第一人稱提問與溝通的堅強意志力,明日餐桌的未來究竟何在?相信這本書會提供您許多寶貴的線索……
──賴青松/青松米、穀東俱樂部發起人
作者簡介:
亞曼達.利特Amanda Little
《能源之旅》(Power Trip;暫譯)和《平地而起》(From the Ground Up;暫譯)兩本書的作者。她的文章題材離不開環保、能源和科技等議題,作品可見於《浮華世界》、《滾石》、《連線》、《紐約》雜誌和《華盛頓郵報》等知名媒體刊物中。她也是Salon.com和Grist.org的聯合專欄作家,以及《紐約客》和《富比士》網路平台上的部落客。利特在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英文系教授調查報導和非虛構類創意寫作課程。
譯者簡介:
王翎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所畢業,現專事筆譯,新近出版譯作為《歐洲中世紀城堡》和《口感科學》。期盼繼續深入書中世界徜徉探索,享受揀字選詞和推敲琢磨的樂趣。
章節試閱
十一月某天的落日餘暉下,我們在歐席古的其中一個鮭魚養殖籠旁,凍得渾身發抖。數千尾鮭魚浮在籠子頂端不停打轉,牠們搖頭擺尾、跳躍騰挪,爭搶懸在半空的塑膠管所噴出有如五彩紙屑的錠狀飼料。魚群似乎毫不受室外華氏零下五度(約攝氏零下二十度)的氣溫影響,牠們對於藏身魚群之中徐緩移動的新奇機械似乎也不知不覺:一台類似長橢圓形版R2-D2的機器人正朝四面八方發射綠色雷射光束。
這台暱稱「刺鰩」(Sting Ray)的設備是由深海鑽油產業的工程師為了消滅海蝨專門打造,是歐席古「軍火庫」裡正在進行測試的武器中,特別稀奇古怪的一...
這台暱稱「刺鰩」(Sting Ray)的設備是由深海鑽油產業的工程師為了消滅海蝨專門打造,是歐席古「軍火庫」裡正在進行測試的武器中,特別稀奇古怪的一...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言
第一章:初嘗苦果
第二章:殺戮田園
第三章:抗旱種子
第四章:機器農夫
第五章:理性感測器
第六章:向上發展
第七章:逆流而游
第八章:嗜肉成癮
第九章:敗部復活
第十章:浩淼夢想
第十一章:緊急措施
第十二章:歷久彌新
第十三章:雖豐亦儉
後記:成長
第一章:初嘗苦果
第二章:殺戮田園
第三章:抗旱種子
第四章:機器農夫
第五章:理性感測器
第六章:向上發展
第七章:逆流而游
第八章:嗜肉成癮
第九章:敗部復活
第十章:浩淼夢想
第十一章:緊急措施
第十二章:歷久彌新
第十三章:雖豐亦儉
後記:成長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