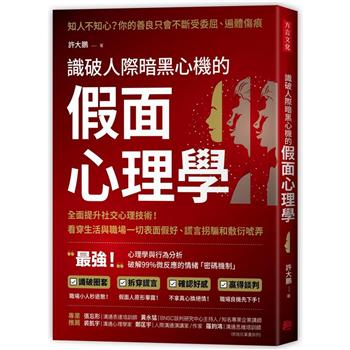文學導讀
普希金的小說藝術
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系副教授 鄢定嘉
在俄國,普希金是一個神話。
神話源起於一八八〇年莫斯科普希金雕像落成,當時屠格涅夫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發表演說,推崇普希金在俄國文化的地位。二十世紀俄國文學一分為二,無論意識形態遭到控管的蘇聯文壇,或者去國離鄉的流亡文學界,無不以普希金為凝聚他們的力量。二〇一〇年由聯合國宣布每年六月六日(編按:普希金的生日)為世界俄語日 ,隔年俄國政府將這一天訂為國定假日,只要有俄國人的地方,就必然有以普希金為名的各項活動。
儘管「製造普希金」的流程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但普希金的美好,你得讀過他的作品才知道。
「一切開端的開端」
俄國文學的許多傳統皆肇始於普希金。他以俄羅斯傳統童話故事元素為基石,寫出《魯斯蘭與柳蜜拉》、《漁夫與金魚的童話》、《金雞的童話》等敘事詩;他的情詩〈我曾愛過您⋯⋯〉、〈我銘記奇妙的瞬息⋯⋯〉等字字珠璣,情意深遠綿長;他研究俄國歷史,以悲劇《鮑里斯‧戈杜諾夫》思考人民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若非他的政論詩〈在沙漠撒播自由種子的人⋯⋯〉、〈在西伯利亞礦區的深處⋯⋯〉、〈阿利翁〉,就無法理解十二月黨人的悲慘命運;從敘事詩《青銅騎士》中,可以看到彼得一世所建立的俄羅斯帝國,是如何偉大,又何等可怕;透過中篇小說《上尉的女兒》,看得出詩人對於農民暴動首領普加喬夫的好感,以及對於百姓的同情;他在由〈莫札特與薩里耶利〉、〈石客〉、〈吝嗇騎士〉、〈瘟疫時的盛宴〉組成的《小悲劇》中,生動刻畫人性眾生相;耗時七年完成的詩體小說《葉夫根尼‧奧涅金》詳細描繪十九世紀初期貴族青年的生活,並塑造具時代特色的「無用人」典型。
瘟疫蔓延時期的創作
一八三〇年春天,普希金終於得到娜塔莉雅‧岡察羅娃母親的同意,歡天喜地準備婚事、迎接期待已久的家庭生活。由於女方家道中落,無法籌措嫁妝,所有婚禮開銷都落在俄國第一詩人身上。普希金的父親將位於尼日哥羅德省博爾金諾村的一小片莊園贈與他當結婚禮物,九月初詩人前去處理土地買賣事宜,預計停留三週後返回莫斯科。不料當地霍亂肆虐,對外交通遭到封鎖,普希金被迫留在當地,直至十二月五日才得以離開。
行動上的限制並未影響普希金的創造力,困在博爾金諾的三個月,被文學史學家稱為「博爾金諾之秋」,正是普希金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他完成一八二〇年代南放時期即著手寫作的詩體小說《葉夫根尼‧奧涅金》、由四篇「案頭劇」組成的《小悲劇》、三十多首詩歌,以及《貝爾金小說集》。
普希金前後僅花了四十天(九月九日至十月二十日)寫就的《貝爾金小說集》,是他在瘟疫蔓延時期創作中最具特色的一部,也是詩人寫作生涯中第一本真正完成的散文體作品 。小說集收錄五篇短篇小說〈射擊〉、〈暴風雪〉、〈棺材匠〉、〈驛站長〉、〈村姑大小姐〉及〈出版者言〉。該書原稱《已故的伊凡‧彼得羅維奇‧貝爾金小說集,由AP出版》,普希金假託貝爾金為作者,藉其故友來信說明這些故事都是貝爾金「從不同的人物那裡聽聞得來」的真人真事,只是改換了人名與地名,而他只是負責處理出版事宜的AP。到了一八三四年出版的《由普希金出版之小說集》正式標示作者為普希金,標題則簡化為《貝爾金小說集》。
尋找小說之道——《貝爾金小說集》的浪漫主義反諷
為什麼普希金採用故弄玄虛的面具手法?除了避開死對頭布爾加林的毒舌諷刺,也想進行一場創新的文學實驗。彼時,詩歌的黃金時代已近尾聲,小說蓄勢待發,即將接手文學主流大位。布爾加林的《伊凡‧維日金》(Иван Выжигин, 1829)是俄國第一本暢銷小說,他以曲折的歷險情節包裝枯燥無味的道德教化,獲得讀者大眾的激賞,並創下驚人銷售紀錄,除了主導大眾閱讀品味,也影響當時的寫作策略。
普希金中學時期以〈皇村回憶〉一詩受到前輩傑爾札文讚賞,敘事詩《魯斯蘭與柳蜜拉》則讓詩壇大老茹科夫斯基自稱「被打敗的老師」,因為普希金,俄國有了詩歌的黃金時期。一八三〇年以前,普希金尚未完成任何散文創作,歷時七年寫就的《葉夫根尼‧奧涅金》雖是小說,但以韻文寫成,在講述男主角奧涅金的故事時,他不時以抒情插敘中斷敘事,好與「柳蜜拉與魯斯蘭之友」直接對話。七年後在博爾金諾為這部作品劃下句點時,普希金或許感受到自己和讀者的距離,於是寫下:「不論你是何許人,諸位讀者,/不論是友是敵,如今我願意/與你朋友般,互道別離。」而同時展開的《貝爾金小說集》,可視為作家在與往日讀者道別時,重新定位小說創作的實驗場……
(本文摘自《黑桃皇后與貝爾金小說集:普希金經典小說新譯》之文學導讀)
跨界導讀
普希金與俄國歌劇傳統
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王寶祥
「一如普希金,葛令卡所稱頌,同是理性之光,智慧之澈;一如詩人,他明察若要取瑰寶,得深入人性找,唯除此之外,樂與詩亦將絕。」──作曲家學者亞薩菲夫《葛令卡傳》
Ⅰ 來不及寫歌劇的詩人
普希金經常被譽為「俄羅斯的莎士比亞」,若以作品改編成歌劇的數量而言,三十七歲便因決鬥而英年早逝的他,文學創作不及年過五十才辭世的莎翁多產,改編數因而也較少;然若以作品被改編成歌劇的比例,更重要的是,依改編的流傳度相較,普希金恐怕則更勝莎翁一籌。
莎翁的戲劇改編成歌劇,除了布列頓《仲夏夜之夢》外,更著名的反而是非英語的外語改編:托馬(Ambroise Thomas)的《哈姆雷特》(Hamlet)是法語,威爾第的《奧泰羅》(Otello)是義大利語;而改編普希金的歌劇,幾乎清一色是俄語。但兩相比較,普希金比莎翁還占個優勢:本地歌劇萌發,與文學興發正好接軌。而莎士比亞身處的伊莉莎白一世,與詹姆士一世時期,英倫尚未發展歌劇,因當時歌劇藝術正處義大利翡冷翠實驗階段;然而俄羅斯歌劇發軔期,則與普希金活躍期密合重疊。
俄國歌劇史,幾乎就可說是普希金作品改編史。從發展初期,就與普希金的作品緊密連結,鮮少人能不被影響;彷彿落地前就培育的臍帶,供給所需養分,一路伴隨其成長茁壯。普希金的戲劇創作,《鮑里斯‧戈杜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1825)以及四齣獨幕劇集合的《小悲劇》(Маленькие трагедии, 1830),全數都有歌劇改編,後者曾在一九九九年普希金誕辰二百年紀念,於俄國彼爾姆的柴可夫斯基歌劇院完整演出。非戲劇類型也照樣改編,包括長篇小說《上尉的女兒》(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1836),中篇小說《黑桃皇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敘事詩最多改編,連《青銅騎士》也由葛里葉(Рейнгольд Глиэр)改編成芭蕾舞劇(1949)。
俄國古典音樂的濫觴,亦同時於俄國歌劇的濫觴,咸認由葛令卡(Glinka)開端,他被尊為「俄羅斯民族音樂之父」,只寫了兩齣歌劇,卻奠基未來俄語歌劇的發展路徑:《為沙皇獻身》(Жизнь за царя , 1836),與《魯斯蘭與柳蜜拉》(Руслан и Людмила, 1842);前者改編歷史,開啟了俄國歷史歌劇,後者改編普希金,開拓了俄國童話歌劇。
號稱俄國歌劇之父的葛令卡,僅小普希金五歲,彼此相識。他曾說服出席他第一齣歌劇《為沙皇獻身》(1836)首演的普希金,為其下一齣《魯斯蘭與柳蜜拉》撰寫劇本(libretto)。只可惜不出三個月,詩人就不幸死於決鬥;俄羅斯音樂與文學雙巨擘合作的美談,因而擦身而過。
葛令卡改編普希金一八二○年的敘事詩《魯斯蘭與柳蜜拉》,一八四二年在聖彼得堡首演,歷史背景是中古的基輔羅斯,故事卻溢滿瑰麗想像,宛若童話。英雄救美的傳奇,邪不勝正的奇幻征戰,受歡迎程度歷久不衰。更成了莫斯科波修瓦劇院的招牌好戲,在國際舞台則最常以著名的序曲,為音樂會開幕的固定曲目……
(本文摘自《黑桃皇后與貝爾金小說集:普希金經典小說新譯》之跨界導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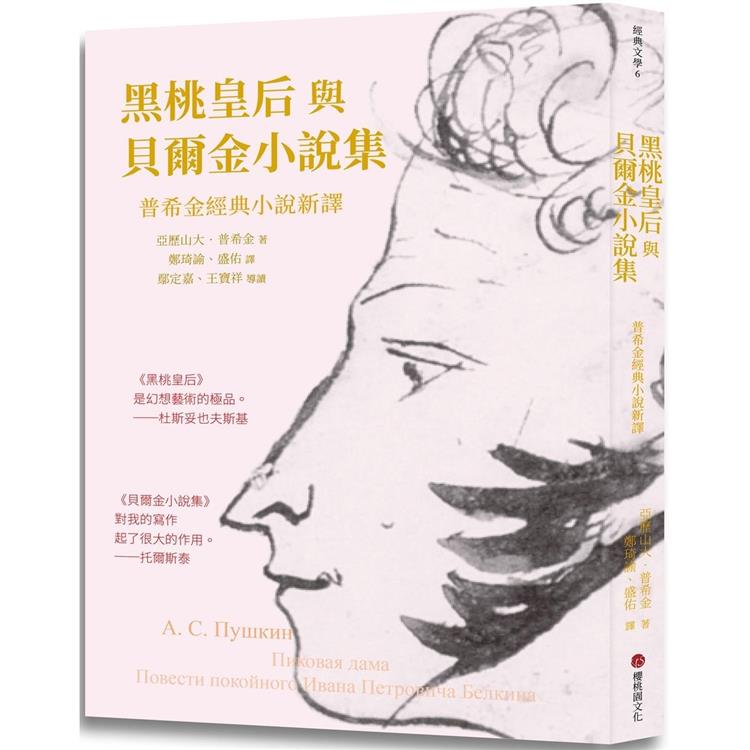
 共
共  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俄國詩人,劇作家,小說家,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歷史學家,政論家。俄國浪漫主義的傑出代表,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是十九世紀前期文學領域中最具聲望的人物之一,被尊稱為「俄國詩歌的太陽」、「俄國文學之父」,現代標準俄語的創始人。普希金的詩體小說《葉甫根尼·奧涅金》全景式地展示了當時俄國社會的全貌堪稱「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他不僅支持十二月黨人的某些觀點,更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那個時代的主要社會性的問題:專制制度與民眾的關係問題,貴族的生活道路問題、農民問題;塑造了有高度概括意義的典型形象:「多餘人」、「金錢騎士」、「小人物」、農民運動領袖。這些問題的提出和文學形象的產生,大大促進了俄國社會思想的前進,有利於喚醒人民,有利於俄國解放運動的發展。 普希金的優秀作品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他的抒情詩內容豐富、感情深摯、形式靈活、結構精巧、韻律優美。他的散文及小說情節集中、結構嚴整、描寫生動簡練。普希金的創作對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及世界文學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高爾基稱之為「一切開端的開端」。。代表作有詩歌《自由頌》、《致大海》、《致恰達耶夫》、《我記得那美妙的一瞬》、《魯斯蘭和柳德米拉》、《青銅騎士》等,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短篇小說《黑桃皇后》、中篇小說《上尉的女兒》等。
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俄國詩人,劇作家,小說家,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歷史學家,政論家。俄國浪漫主義的傑出代表,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是十九世紀前期文學領域中最具聲望的人物之一,被尊稱為「俄國詩歌的太陽」、「俄國文學之父」,現代標準俄語的創始人。普希金的詩體小說《葉甫根尼·奧涅金》全景式地展示了當時俄國社會的全貌堪稱「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他不僅支持十二月黨人的某些觀點,更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那個時代的主要社會性的問題:專制制度與民眾的關係問題,貴族的生活道路問題、農民問題;塑造了有高度概括意義的典型形象:「多餘人」、「金錢騎士」、「小人物」、農民運動領袖。這些問題的提出和文學形象的產生,大大促進了俄國社會思想的前進,有利於喚醒人民,有利於俄國解放運動的發展。 普希金的優秀作品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他的抒情詩內容豐富、感情深摯、形式靈活、結構精巧、韻律優美。他的散文及小說情節集中、結構嚴整、描寫生動簡練。普希金的創作對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及世界文學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高爾基稱之為「一切開端的開端」。。代表作有詩歌《自由頌》、《致大海》、《致恰達耶夫》、《我記得那美妙的一瞬》、《魯斯蘭和柳德米拉》、《青銅騎士》等,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短篇小說《黑桃皇后》、中篇小說《上尉的女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