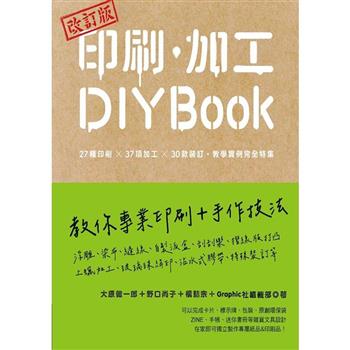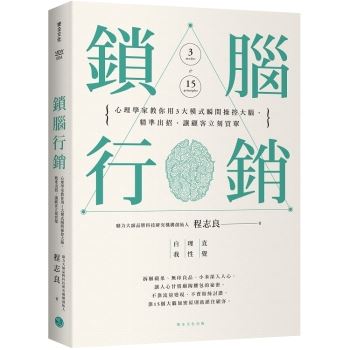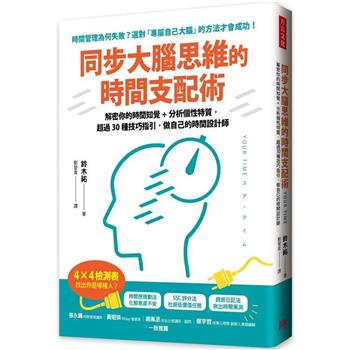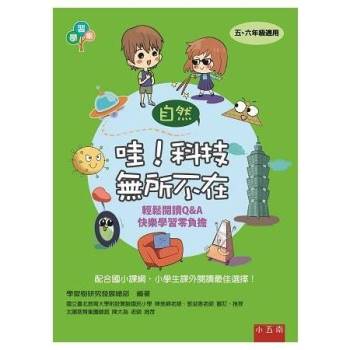序幕
這個十乘八的房間連扇窗戶都沒有,其中一面牆壁密密麻麻裝滿鐵條,從地板一直延續到天花板。鐵條之間滲進一絲絲微弱的光線。外面一個黑色架子上有一台小電視,轉到最大的音量持續著惱人的白色噪音。門邊的盤子上還殘留著煮得稀爛的晚餐,殘餚早已風乾。
堆放在右手牆邊的睡床倒是鋪設得十分整齊,床單的每個角落都俐落地收進薄墊底下,粗劣的綠色床單拉得平平整整,只有他坐的位置陷了下去。他弓著身子,神情專注。身上的藍色汗衫被汗水浸透,在皺褶處和腋下部位留下暗沉的汗漬。汗臭味混雜著殘羹的腐餿味瀰漫在屋內。
他睜開雙眼,找到身旁的檯燈,按下開關。亮晃晃的白色燈光照亮了他手上的模型。對於這三十二顆用石膏複製的人類牙齒,他早已熟稔到能用拇指找出它的輪廓:暴出的門牙,鋒利的犬齒,缺了一角的前臼齒。他見過這副不完美的牙齒露出笑容過,只有那麼一次:就是在剛開始的時候,在恐懼降臨之前,曾經閃過那麼一剎那的笑容。接下來的幾個鐘頭,這副牙齒就一直痛苦地咬合著,或是在無聲地嘶喊時,繃緊的唇間才不經意地露出牙齒來。
他彎下身子,拉出藏在床底下的一個盒子,擺放在自己的膝頭上。他轉身取出口袋裡的鑰匙,然後打開盒子。朝石膏模型投以臨別的一瞥,然後將之放進盒中,與其他的那些收在一起。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了。
看著第一位被害人死去的那一天,之前和之後並沒有多大的改變。你還是一樣地醒來,或許會漏過早餐,甚至省略午餐,不過你終究還是會吃飯……只是早晚的問題。你還是一樣要睡覺。而且逐漸回復作息。也許和之前的節奏不太一樣;也許會出現不搭調的時候,不過至少沒有人聽到。那是屬於你自己的拍子。
他再度把盒子推回床底下,連同其他的紀念品一併收藏在一處──那些被他奪取以及從他手中溜走的生命。他閉上眼睛,吸入這悶熱、禁錮人的空氣。
我的監獄只是一個工具,一個用來自我訓練的場地,一個中途站。我注視著身後的鐵條,以及在我周遭的這方圓之地,這個監所。一想到你遠在他方,而我竟在這個地方,這對你來說,是多麼悲慘的事!但是,就快了,我很快就會到你那兒。與你相聚。
我在入口與出口間愈來愈來去自如了。
他將檯燈關掉,鑰匙收進口袋,起身走到門口。推開門閂,踏出房間。伸手去關掉電視,看著屋內唯一的光源在螢光幕中央縮成一個小圓點,然後陷入一片漆黑。他穿過地板,拾級而上,在跨過門檻前稍稍暫停,然後就走進他開著冷氣、光線充足的家。
她二十九歲,嬌小而苗條,穿著白色細肩帶小可愛,淡粉色羊毛衫,配上牛仔褲,一個蜻蜓樣式的髮飾將她挽起的深色長髮固定在頸背處。她的膚色顯得病懨懨,藍色的雙眼更是陰鬱黯淡。在她身旁有一只洋娃娃,那是她按照說明一步步完成的女紅作品,不過早在縫上嘴巴前她就已經失去興致了,而用棕色毛線編製的頭髮也並未用蝴蝶結綁成一束。一旁還擺著一個用陶土捏製的煙灰缸,尚未完全上色,還有大拇指的力道在那上頭留下一個捏痕。
她想不起自己坐下來的原因。她拉開書桌抽屜,取出輕薄的代禱卡、以及聖修士庇佑神父芳香的紅色玫瑰經念珠。她將念珠纏繞在手指上,低下頭來,開始禱告。她告訴聖約瑟1,她不敢接近他,因為耶穌已經長駐在他心頭附近。
沒來由地她又感受到一種熟悉的壓力從腹部油然而生,這種感覺讓她不安。按照過去的經驗,這裡面混雜的恐懼會讓她產生前所未有的興奮,但是現在只有恐懼快將她淹沒。她甩出左手,打在記事簿上,把記事簿從桌子上掃到自己面前。她一邊試著利用眼前的遭遇,一邊卻感到腦袋彷彿要脫離自己的軀體。一捲深色的軟片在她眼底展開;經過編輯的黑白影像,一幕幕採光不良的畫面狂亂地加速放映著。她的右手在空中探索,纖纖手指想要找到那兩條直線,讓眼前的這一切停格,然後再找到反向箭頭,倒轉所有的畫面。但這顯然並非她所能控制。流竄在她體內的是想要留在當下的衝動,而非倒轉回到過去,看清隱沒在黑暗中另一部分的記憶。但是,就在她沒來得及拿筆記下前,她已經昏倒了,癱軟在地板上,連帶紙、筆、鉛筆都掉落在她身上。她看到的最後一幕就是她的朋友,站立在門口,縮回到小孩子的模樣。
喬.盧楚西警探的頭埋在兩膝之間,止不住的淚水縱橫兩頰,滴落在他下方的地毯上。他的臉色蒼白,額頭冒出斗大的汗水,而在劇痛發作前他讀報時留在指頭上的油墨也跟著輾轉捺印在自己的額頭上。半個鐘頭以前,他來到牙醫診所,要求急診治療──據他估計,當時的疼痛應已達到八級,至於現在則已經超越可以估計的規格,並且還在持續增加當中。極度的噁心在他體內肆虐,但他還是維持著彎腰的姿勢,連吼叫聲都哽在喉頭。
「喬?喬?」接待小姐從走廊衝進來,「跟我來。」
她瞄了候診室一眼。「有誰看到剛剛那是怎麼一回事?」
「他就坐在那邊看報紙,然後接了一通手機。當他再坐下時,他就開始不太對勁。」喬聽得出來,說話的人是他來這兒時坐在他對面的那位面目慈祥的長者。
接待小姐伸手搭在喬的肩頭上。「帕希瓦醫生一會兒就來了。在此同時,要不要我拿什麼給你?」
「也許可以給他一杯水?」又是那位男士的聲音。他已經站了起來──喬看到那個人棕色的麂皮帆船鞋就停在他面前的地毯上。喬掙扎著舉起顫抖的手,試著婉拒這兩位的好意。
「我覺得他甚至對來電的那位人士都無法開口。」那位老者說。
只有喬自己明白,他不是因為痛楚而無法開口。只是那個聲音攪亂他原本的生活,慢條斯理而又沉重的音調中盡是提到未完的往事,這樣的聲音讓他無從答起。
「是盧楚西警探嗎?每一次當你看著你妻子嬌小的美麗身軀,一直往下……直到那緊實的小腹,上面一道道的疤痕時。或是當你把她翻身過去──她很輕,你大可輕而易舉地把她翻過去,不是嗎?背面上也有好幾道疤痕──讓我覺得自己好像一直在送禮給你。呃,我想知道的是:當你看到那些疤痕的時候,你還會想要她嗎?」他停頓下來。「還是你比較想要我?」他大笑了好久。「告訴我。到頭來誰倒霉?是小可憐安娜.盧楚西還是大壞蛋杜克.羅林?」他的聲音不見了,留下一陣沉默。然後他的聲音再次響起,也是最後一次響起。「還有,警察先生,你解決不了我。是我──來──解決──你。」
第一章
喬.盧楚西和丹尼.馬凱兩位警探踏進電梯,正打算到六樓曼哈頓北區凶殺組的辦公室。再過三個鐘頭,他們從八點到四點的輪值工作就可以告一段落。一個瘦巴巴的矮個子跟在他們後面衝進電梯,一副神經兮兮、站不住腳的樣子。
「你知道嗎,我可以從你的雙手看出你的未來。」光滑的棕色皮膚,左眼下垂,他就站在喬胸前一吋的位置,臉上掛著微笑,抬頭看著喬。喬望了丹尼一眼,然後伸出一手手掌。
「不是你的手掌!」他大吼著。「不是你的手掌!是你的手背!我要從你的手背來瞭解你。」喬把手翻過來。
「另一隻手也要。你也是。」他看著丹尼說。「兩隻手。兩隻手。這麼多的手讓聰明人也會變笨2。」
喬和丹尼相視一笑,然後照他吩咐地乖乖伸出雙手。
「你們太早笑了,」那個傢伙說。「就我現在判斷,可能情況不怎麼樂觀。有可能鴨多踩壞叢木3。」
「我們並不想知道壞消息,」丹尼說。「對吧?」
「對。」喬附和著。
「對。」那個人說。「可是我在這兒並不只是個使者的身份。你們將來就會知道。我就是一切事情的起源。就這樣:砰地一聲,我啟動了這一切。而且我看到未來就是從這裡,從破的這九針4開始。」
喬緩緩地點了點頭。
那個人伸手去調整他頭上那頂紫色針織帽,拉出其中一只護耳蓋在臉上。他又轉了一下帽子,然後才回神去看他們的手。
「有了,」他說。「我看到了。我真的看到東西了,」那個人說著。「我看到一行我的名字,一行是案由,第五大道之王,一行是你們的產品,再一行是你們的牌子──」
「你是廣告文案的撰寫人?」喬問道。
「還有一行是你的將來,」那個人繼續說,愣愣地盯著眼前這雙手。
「好啦,」丹尼說。「那到底是怎樣?」
噹地一聲響起,電梯門打開,六樓已經到了。喬和丹尼走出電梯。在電梯門關上之前,那位滿口一行的先生把臉湊在門縫前。
「那一行是:你完蛋了,你們兩個都是。那是不是兩行?難道是兩行?」電梯門緊緊關上。
兩個人大笑起來。
「又是一個可以送到HDP的EDP,」丹尼說。EDP是指有情緒困擾的人(Emotionally Disturbed Person),HDP則是指住宅維護及保存部門(the Department for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該部門負責的工作就是核發第八條款的住宅津貼5。
「我們應該送他到外交部去,讓他告訴外交部的官員說他們麻煩大了,」丹尼接著說。
「我倒希望他真的能想出一整段鏗鏘有力的台詞來。」喬說。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亞麗珊.巴克蕾的圖書 |
 |
$ 238 ~ 359 | 奪命鈴聲
作者:亞麗珊.巴克蕾(Alex Barclay) / 譯者:張可婷 出版社:尖端 出版日期:2010-12-2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76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奪命鈴聲
我在入口與出口間愈來愈來去自如了。
凶手在被害人家裡行凶,屍體就棄置在玄關,留待心愛的人去發現。每位受害者生前都接到了電話;沒有任何強行入侵的跡象:被害人是自己開門迎接死亡的。
經過一年的請假,並且遭到一名精神異常者可怕的折磨,紐約警局的警探喬.盧楚西終於回到工作崗位上。現在他發現自己愈來愈抗拒介入備受媒體關注的案件。連續殺人事件不斷發生;被害人所有的傷害都集中在臉部,屍體死狀悽慘,數目一再攀升,也對他的工作以及私下生活帶來更大的壓力。喬全心投入調查工作。但是正當他覺得快要破案時,調查工作受到一場悲劇波及,而另一個被害人也命在旦夕。
作者簡介:
亞麗珊‧巴克蕾(Alex Barclay)
一九七四年生,家中有四個兄弟姊妹,青少年時期的她便熱愛閱讀犯罪小說,那也成了她長久以來的興趣與嗜好。目前居住在都柏林附近。
她以簡潔的白描文字,俐落的切片手法,爆炸性的節奏,跨時空的雙線劇情,嚴謹而紮實的結構,宣示犯罪書寫的明日之星到來。
已出版作品有:《暗室》、《奪命鈴人》。
章節試閱
序幕
這個十乘八的房間連扇窗戶都沒有,其中一面牆壁密密麻麻裝滿鐵條,從地板一直延續到天花板。鐵條之間滲進一絲絲微弱的光線。外面一個黑色架子上有一台小電視,轉到最大的音量持續著惱人的白色噪音。門邊的盤子上還殘留著煮得稀爛的晚餐,殘餚早已風乾。
堆放在右手牆邊的睡床倒是鋪設得十分整齊,床單的每個角落都俐落地收進薄墊底下,粗劣的綠色床單拉得平平整整,只有他坐的位置陷了下去。他弓著身子,神情專注。身上的藍色汗衫被汗水浸透,在皺褶處和腋下部位留下暗沉的汗漬。汗臭味混雜著殘羹的腐餿味瀰漫在屋內。
他睜開雙眼...
這個十乘八的房間連扇窗戶都沒有,其中一面牆壁密密麻麻裝滿鐵條,從地板一直延續到天花板。鐵條之間滲進一絲絲微弱的光線。外面一個黑色架子上有一台小電視,轉到最大的音量持續著惱人的白色噪音。門邊的盤子上還殘留著煮得稀爛的晚餐,殘餚早已風乾。
堆放在右手牆邊的睡床倒是鋪設得十分整齊,床單的每個角落都俐落地收進薄墊底下,粗劣的綠色床單拉得平平整整,只有他坐的位置陷了下去。他弓著身子,神情專注。身上的藍色汗衫被汗水浸透,在皺褶處和腋下部位留下暗沉的汗漬。汗臭味混雜著殘羹的腐餿味瀰漫在屋內。
他睜開雙眼...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亞麗珊‧巴克蕾 譯者: 張可婷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10-12-21 ISBN/ISSN:957104407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76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