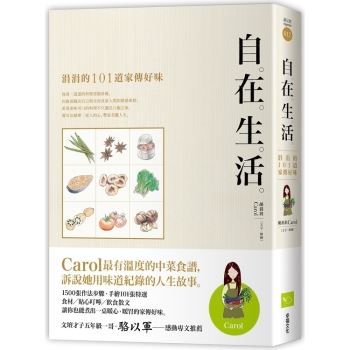懷念沈君山
管惟炎先生首先是位學者;忠於所學的學者,也是一位中國智識份子;忠於中國讀書人原則的智識份子,而且,我相信,他到最後還是一位原始的理想共產黨員;忠於原始理想(雖然他自己也知道那理想實踐起來終究只是幻想)的原始共產黨員。
我第一次見到管先生是在1990年美國加州的浩然營,一個聚兩岸精英於一堂的暑期研習營;1990年是第一屆,那時六四剛過一年,管先生因為支持方勵之和學生運動,從合肥的科技大學校長位上被拉下來,海外聲望很高,而且確實學有專精,是理想的講員,他正在朱經武實驗室訪問,我打電話和他連絡,他說很樂意來,不過不願意談民運的事,這我了解,但他的專業學員們一定聽不懂,商談之後,選定了講中國的科學和教育,這他當然是遊刃有餘,不過這不是一個刺激的題目,反應也就平平,但我看得出來,大陸的學員,無論國內海外,對他都很尊敬,私下我們也海闊天空的談了很多,短期內,他大陸肯定是回不去了,我問他是不是考慮到台灣,尤其是到清華來教一段時期書,他問了許多台灣的情形,但最後並未置可否。
回到台灣不久,就聽說管先生可能要來清華,國科會爭取他來台最是熱心,顯然也有政治動機,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他從德國打來的電話,說他考慮來台,不過不希望做「反共義士」,不要做「政治」教授。我向他保證,若來清華,學校絕對以物理教授相待,外界的活動,若他自己堅持不參加,想來也不會有人勉強他。
不久,管先生就來了清華,他的辦公室在一樓,我的辦公室在七樓,下班前後,只要他的房間燈亮,我又沒有事,就去敲門,他若不忙,就坐下來海闊天空的聊。管先生是位傳奇人物,十四歲做紅小兵,很早就入團入黨-黨齡比江澤民還早-從蘇北家鄉游擊到東北,解放後在東北「幹了一段活」(他自己的用語),調回北京,被選拔去蘇聯讀書,應該算是「黨」刻意培訓的尖端紅專人才,他在蘇聯追隨卡皮查(Kapitsa,1978年諾貝爾獎得主),紮紮實實的讀了幾年書,回到中國,留在科研專業,當然也當上專業中的領導,一度是北京中科院的院長人選,後來去擔任合肥科技大學的校長,那時合肥科大是並不亞於清華北大的頂尖學府,後來,前面也提起過,因為支持方勵之和學生運動,去職出國。89年秋,曾被海外民運人士推選為民運組織的領袖,但他並未接受,後來就來了台灣。
管先生確實首先是學者,也極喜歡教書,和年輕人溝通。這對他去國後十幾年的生活適應,有極大幫助。89年前後的大陸民運人士,流亡到海外,常常調適困難。他們言論生活是自由了,卻遠離了群眾故國,「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他們擁抱了民主,但終究是馬列極權教育下孕育出來,西方的民主並不是他們血液中的一部分。水土不服。很多人,極聰明優秀的,也要一段時間才轉型過來。管先生是少數的例外,他從來沒有完全脫離本業,因此也很快的就又回到乾淨明亮的科學殿堂,怡然自得的過他學者的生活,他並沒有自我放逐,遺世隔絕,關心大陸,也關心兩岸,偶而也寫寫文章,不過絕大部分時間,他是在做一個真正的「物理教授」。
春去秋來,十幾年過去了,管先生先退休,離開清華,到淡江教書,然後又回到清華做兼任教授。這期間有兩件大事,是他很得意的,一件發生在六七年前,有一天,我走過他的辦公室,那時因為擔任行政職務,忙來忙去的,很久沒見到他和他聊天了,看見燈亮,就敲敲門進去,才聊了幾句,他忽然又神秘又興奮的從皮包夾中拿出一樣東西,說要向校長報告。我一看,原來是身分證,中華民國的身分證,他終於拿到中華民國的身分證了。那瞬間,他獻寶似的天真喜悅之情,就像一個拿到畢業證書的中學生。
另一件就在一年多前,有一天我收到系裡的通知,說要辦茶會慶賀管先生得「傑出教學獎」,系裡過去也有教授得傑出教學獎,但多沒有由系出面辦茶會。可見系裡對這次管先生的得獎有多重視。這確是不容易,傑出教學獎由學生推選,全校競爭,是清華最受尊重的獎項,管先生已經七十多歲,退休了再回來教書,只是和學生自然相處,不多活動,忽然得了這麼個獎,系裡和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給他辦個慶賀茶會,是物理系的人情味和系主任的周到。那天我當然去了,好幾位已退休的老教授也到了,管先生喜氣洋洋,好像個新郎倌,到處打招呼,又拉著我和我照了好幾張相。
其實那一陣子,我們常見面,卻不是在辦公室,是在大操場。1999年我中風後常去操場散步復建,管先生也常去,兩人就常碰上,我一跛一跛的,他倒走得筆挺,但兩眼往前目不旁視,我不打招呼,他還看不見我,畢竟我們都老了。最後一次相見,也就在他出事前三四天,兩人一邊蹲躅著走,一邊閒聊,他說他現在又不能回大陸了。
89年之後幾年,六四的事漸漸淡下去,因此出亡的人士也陸陸續續的回去。管先生在北京的朋友,讓我傳話給他,歡迎他用開會或探親的名義申請回去,只要不公開不活動就可以。但管先生不願意,要回去就公開回去,他沒有錯,不說平反,也得光光彩彩來個歡迎會之流,我給管先生說,這不是對錯的問題,大搖大擺的回去,有人臉上就掛不住,人家在台上,你就讓著點兒,可管先生不同意,因此有一陣就熬著沒去,或許這就是中國讀書人的原則(或者彆扭)吧。後來,大概是一次超導會議,管先生以一個科學家的身分回去了,這是中性的,大家都可以接受,以後就常可以去,管夫人還在北京中科院工作呢。
但管先生畢竟是管先生,一年多前他去北京,不好好在家裡待著,卻四處的走,人家知道,也沒限制他,走著走著就到了合肥,和從前認識的學生教授見見面,人家也裝做不知道,可管先生或許覺得這樣還不夠光明正大,就去找學校的黨委書記,一個從前是他下屬,有些過節的人。還要求和學生開個座談會,其結果座談會當然是沒開成,那黨委書記想想,管惟炎來找他,很多人都知道,管還是名單上的人,並沒有正式拿下來,知情不報也不行,就給上報了。於是管先生就被勸著提前離開合肥,上火車後老覺得有人跟著,車到了徐州,果然露了面,是兩個人,很禮貌也很客氣,但說好說歹的要管先生趕快離開中國,不然他們不好交差。管先生和他們論理,可是他們只是苦著臉懇求,管先生倒同情起他們來,當晚請他們好好的吃了一頓,第二天第一班飛機就出來了。從此,再申請也拿不到「台胞證」,回不去了。
這個故事他不只講了一次,我也不只聽了一次,兩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嘛,可每次細節都多一些。那次在大操場上講了後,不過兩三天,忽然傳來一個消息,他在台中訪友,被摩托車撞著,昏迷過去,當晚就去世了。朋友同事知道,都十分震驚哀悼,想起操場踽踽獨行的身影,我當然懷念不已。但回首想想,人生一世,石火光中,須臾此生,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生老病死人之四苦,生死既不能免,只能求少些老病,管先生在老之方至,耳尚聰目尚明之際,忽然既無痛苦可能也不自知的走了,未必不是福氣。在這世界的大操場上,我看來還得多走幾圈,就將他講的故事先寫下來,他年有緣,在另一個世界的大操場,若偶然再逢,或者可再補充些細節吧。
管先生去世後三日,夫人自京趕來清理遺物,再攜骨灰返京,管先生終於光明自由的歸故鄉,再不要什麼入境簽證了。在京開了個儉樸的追悼會,生前故交學生堂堂皇皇的來致祭,至於他不屑和不喜歡的官場人物,聽說就在不受歡迎之列,這樣,管先生在天之靈,也可以安慰了吧!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