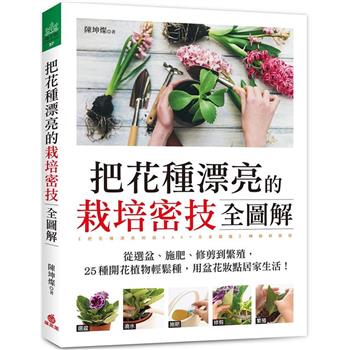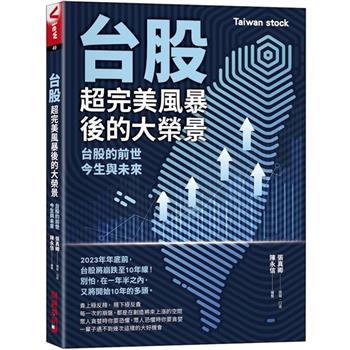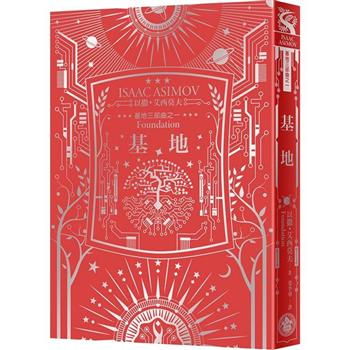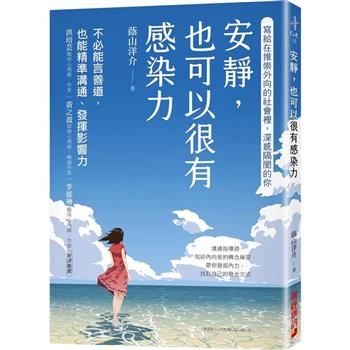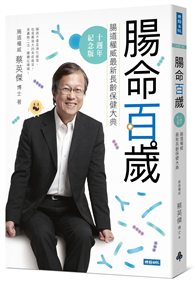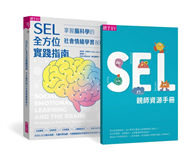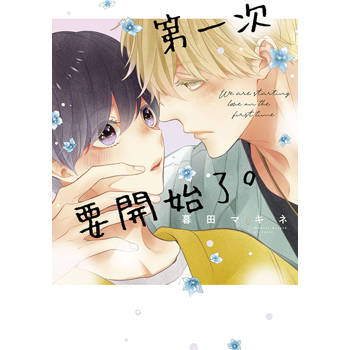余其芬,九○後新生代作家,因為求學而往返於台北與上海,關於兩座城市的美好,透過她的眼與筆以及位於台北郊區的小小廚房,亦如風景又如畫地篇篇展開。
在台北,儘管出現在她生活中的人只是萍水相逢,她卻真切體會世間溫暖有多珍貴;在上海,儘管許多事物都只存在遙遠的回憶裡,她卻保存了藏在深遠時光裡的情感。
台北和上海,異鄉與故鄉,城市、記憶與情感的時光膠囊。
◎國立政治大學道南文學獎 小說、新詩首獎得主
◎第五屆豆瓣閱讀徵文大賽 文藝小說組 優秀獎
名人推薦
作家 柯裕棻
歌手 鄭 興
──溫暖推薦
「其芬的文字是午後陽光正好時窗外飄過的雲,輕輕的,把我的思緒帶回她所編織的那幾座城市的記憶裡面。這些生活,大多是細碎的,真誠又體己,時而像是本日記,時而像是篇民族誌田野筆記,時而又像一個在耳邊絮叨家長裡短的朋友。我一邊點著頭說著『是啊』,一邊會心一笑,想著該不會又是她那念舊、敏感的小情緒來作怪了。可是說著說著,我怎麼竟也偷偷濕了眼眶了呢?」──鄭興(歌手)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余其芬的圖書 |
 |
$ 224 ~ 288 | 年年: 城市與記憶的時光膠囊
作者:余其芬 出版社: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12-27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年年:城市與記憶的時光膠囊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余其芬
1992年出生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編輯出版專業,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傳播碩士,曾獲道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新詩組首獎、第五屆豆瓣閱讀徵文大賽文藝小說組優秀獎等。
讀研究所時,輾轉於上海臺北,也終於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時間來寫散文和小說。人為什麼要寫作?可能因為每個人都是終極孤獨的個體,都不完美,都害怕離別,才需要文字引起的共鳴和帶來的溫度。希望我能一直寫一直寫,去記錄生活中的瑣碎片段,上海、臺北的雙城故事,和生命裡的悲歡聚散。
余其芬
1992年出生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編輯出版專業,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傳播碩士,曾獲道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新詩組首獎、第五屆豆瓣閱讀徵文大賽文藝小說組優秀獎等。
讀研究所時,輾轉於上海臺北,也終於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時間來寫散文和小說。人為什麼要寫作?可能因為每個人都是終極孤獨的個體,都不完美,都害怕離別,才需要文字引起的共鳴和帶來的溫度。希望我能一直寫一直寫,去記錄生活中的瑣碎片段,上海、臺北的雙城故事,和生命裡的悲歡聚散。
目錄
萍水相逢的善意
我們看海去
兩地書
西門:寫給臺北的情書
華西街記事
木新市場的日與夜
阿芬廚房
政大寫作坊
畢業快樂 祝你快樂
離別•時刻
回上海小記
一本書與一座城
《繁花》:海派市井的頹然感傷
鄭興: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臺北
臺北的春天 幾場花事
25歲的「中年」危機
我們的少女時代
消失的理髮店
再見 東方書報亭
你有多久沒有因為一盆28塊的沙拉而快樂?
不放暑假的夏天
上海的55個秋日
我記憶裡有關雪的種種
冬至:如何測量思念的距離
年年
無預期告別
在香港,偷得浮生半日閑
現代戀物癖
人與草木:願你像仙人掌有刺 卻能開出溫柔的花
我們看海去
兩地書
西門:寫給臺北的情書
華西街記事
木新市場的日與夜
阿芬廚房
政大寫作坊
畢業快樂 祝你快樂
離別•時刻
回上海小記
一本書與一座城
《繁花》:海派市井的頹然感傷
鄭興: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臺北
臺北的春天 幾場花事
25歲的「中年」危機
我們的少女時代
消失的理髮店
再見 東方書報亭
你有多久沒有因為一盆28塊的沙拉而快樂?
不放暑假的夏天
上海的55個秋日
我記憶裡有關雪的種種
冬至:如何測量思念的距離
年年
無預期告別
在香港,偷得浮生半日閑
現代戀物癖
人與草木:願你像仙人掌有刺 卻能開出溫柔的花
序
序
在開始寫這篇序言的時候,我還是不太敢相信這是我的第一本書。可能在23、24歲的時候,我突然萌生了一個想法,想在25歲時出一本書。現在儘管我已經過了25歲,卻在機緣巧合下有機會實現這個願望,這種感覺很奇妙。
這本書收錄了我這幾年零零散散的一些文字,最早的那篇應該是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寫的,距今也有了差不多五年了。前兩天無意中看到剛剛念研究所時拍的照片,照片裡的我有一種傻乎乎的天真神情,突然很明顯地感覺到時光的流逝和自己身分的轉變。
這本書中故事的發生地點,絕大多數是在上海和臺北,而這些故事似乎都和「告別」有關。從小我就是非常念舊的人,因而最害怕告別。朋友和我說,「有時候你過於多愁善感」,我想這可能和我的星座也有關係,摩羯,上升雙魚,悲觀敏感,天性使然。
記得從臺北畢業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看到自己離開臺北前發的朋友圈,是一張照片,我和一同畢業的北京室友還有臺灣的同學在機場的合影,照片旁顯示著大大的時間──「昨天」。
這是真正的「昨天」,意味著我從此脫離校園,不再是學生,也意味著註定要和許多同學、朋友、老師暫別,不得不走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而這本書中的「告別」,除了具象的、與他人的告別,也有許多是更加抽象的告別,比如許多關於上海的故事裡,我寫下許多童年的瑣碎小事,寫作的過程是在回憶、緬懷,也是在和這段舊時光告別。日新月異的城市,很多我們熟悉的場景、事物都將不復存在。那些舊的時間、空間、場景裡,我們曾投射了許多感情,儘管經常感到不捨,但卻無可避免,我們漸漸接受和很多人事物都終須一別。
這樣寫來未免有些悲觀,但這些陸陸續續寫下的文字,很多都記錄下當時的情感。我總認為情感是抽象的,難以百分百地通過文字去描述、傳達,但這些文字的符碼,變成了密碼和機關,日後我再讀到時,觸發了相關的回憶,就會想起某個特定時刻下的情緒,在這些文字中一部分當時的、更年輕的自己得以保留。
在臺北念研究所的兩年,我經常在臺北想念上海,或是放假回家時在上海想念臺北。我喜歡「後知後覺」這個詞,因為人都是在離開一座城市、一段特定時間後才會想念,身處其中時卻很難意識到當下有多美好和珍貴。
很小開始,我就對閱讀和寫作感興趣,但卻一直未能提筆寫下些什麼功課以外的文字。直到研究所,可自由支配的時間漸漸變多,我偶爾寫散文,也開始寫小說。與寫小說相比,寫散文的過程更加輕鬆自在,很多時候甚至不用思考,讓文字代替我去表達。我不願意把寫作當作一件過分嚴肅的事情,更多時候,寫作是為了讓情感有一個出口。那些你在現實生活難以表達的、或沒有對象可以傾訴的情感和情緒,文字都成為你的「救贖」,讓你放肆地去表述你的孤獨、怯懦、傷感和迷惘。
畢業兩年後,還是常想念在政大的生活,在傳院上過的課、看不懂的文獻、大勇樓的讀書會、文學院裡盛開的鳳凰花、後山的螢火蟲、午夜走過的恆光橋、河堤開過的櫻花、木新市場的煙火氣……也想念那時年輕的自己,和朋友在臺北街頭閒逛,去看電影或買東西,我們說著現在早已忘記的玩笑話,曾經笑得很放肆,也會為論文的進度苦惱。當然也想念政大傳院的各位老師,我的導師柯裕棻、方念瑄老師、蔡琰老師、孫秀蕙老師、郭力昕老師等等,每一位都讓我學到很多,也想念各位同學,我的室友宋淳、文悅,還有許許多多大陸和臺灣的朋友,感恩我們一起度過的兩年時光。
這兩年的時間很快過去,有笑有淚,也有一些誤會、爭執,有很多失望、孤獨和情緒低落的時刻,現在再回頭看,它們可能都是長大的過程中必經的階段,經歷以後,我們才能更勇敢和成熟一點,對自己瞭解得更多一些。
能有機會出這本書,要感謝的人很多。首先是我的父母、外婆、雙胞胎妹妹,我的妹妹余其芳也特別為這本書畫了非常精美的插圖,再現了很多我們一同經歷的場景,讓這本書更有意義。我也要特別感謝政大的盧非易老師和國立新加坡大學出版社的林少予老師。我與林老師素未謀面,他將我的小說〈小白龍〉推薦給東美出版社,才促成了之後的合作。當然也要感謝東美出版社各位編輯老師的辛勤工作,在這本書出版的過程中付出了很多心血,讓我感動。
對我而言,寫作不是一件需要「堅持」的事情,需要堅持的是那些有些痛苦的事情,比如減肥,寫作更像是一種陪伴。這本書中的故事基本上一兩個小時就能寫完,我很享受這個過程,像做了一場舒緩壓力的心靈瑜伽。而寫小說就比較費時費力,有時像在跑曠日持久的馬拉松,賽道裡也只有你一個人,更為艱辛一些。希望未來有一天,我也能出版一本小說,這也算是一個新的小心願吧。
在故事開始前寫的「閒話」就到這裡,歡迎你和我一起走進上海、臺北,走進我的故事裡。
我沒有很大的野心,無論是否還會有第二本書,我還是會繼續寫下去。
謝謝你翻開這本書!
在開始寫這篇序言的時候,我還是不太敢相信這是我的第一本書。可能在23、24歲的時候,我突然萌生了一個想法,想在25歲時出一本書。現在儘管我已經過了25歲,卻在機緣巧合下有機會實現這個願望,這種感覺很奇妙。
這本書收錄了我這幾年零零散散的一些文字,最早的那篇應該是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寫的,距今也有了差不多五年了。前兩天無意中看到剛剛念研究所時拍的照片,照片裡的我有一種傻乎乎的天真神情,突然很明顯地感覺到時光的流逝和自己身分的轉變。
這本書中故事的發生地點,絕大多數是在上海和臺北,而這些故事似乎都和「告別」有關。從小我就是非常念舊的人,因而最害怕告別。朋友和我說,「有時候你過於多愁善感」,我想這可能和我的星座也有關係,摩羯,上升雙魚,悲觀敏感,天性使然。
記得從臺北畢業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看到自己離開臺北前發的朋友圈,是一張照片,我和一同畢業的北京室友還有臺灣的同學在機場的合影,照片旁顯示著大大的時間──「昨天」。
這是真正的「昨天」,意味著我從此脫離校園,不再是學生,也意味著註定要和許多同學、朋友、老師暫別,不得不走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而這本書中的「告別」,除了具象的、與他人的告別,也有許多是更加抽象的告別,比如許多關於上海的故事裡,我寫下許多童年的瑣碎小事,寫作的過程是在回憶、緬懷,也是在和這段舊時光告別。日新月異的城市,很多我們熟悉的場景、事物都將不復存在。那些舊的時間、空間、場景裡,我們曾投射了許多感情,儘管經常感到不捨,但卻無可避免,我們漸漸接受和很多人事物都終須一別。
這樣寫來未免有些悲觀,但這些陸陸續續寫下的文字,很多都記錄下當時的情感。我總認為情感是抽象的,難以百分百地通過文字去描述、傳達,但這些文字的符碼,變成了密碼和機關,日後我再讀到時,觸發了相關的回憶,就會想起某個特定時刻下的情緒,在這些文字中一部分當時的、更年輕的自己得以保留。
在臺北念研究所的兩年,我經常在臺北想念上海,或是放假回家時在上海想念臺北。我喜歡「後知後覺」這個詞,因為人都是在離開一座城市、一段特定時間後才會想念,身處其中時卻很難意識到當下有多美好和珍貴。
很小開始,我就對閱讀和寫作感興趣,但卻一直未能提筆寫下些什麼功課以外的文字。直到研究所,可自由支配的時間漸漸變多,我偶爾寫散文,也開始寫小說。與寫小說相比,寫散文的過程更加輕鬆自在,很多時候甚至不用思考,讓文字代替我去表達。我不願意把寫作當作一件過分嚴肅的事情,更多時候,寫作是為了讓情感有一個出口。那些你在現實生活難以表達的、或沒有對象可以傾訴的情感和情緒,文字都成為你的「救贖」,讓你放肆地去表述你的孤獨、怯懦、傷感和迷惘。
畢業兩年後,還是常想念在政大的生活,在傳院上過的課、看不懂的文獻、大勇樓的讀書會、文學院裡盛開的鳳凰花、後山的螢火蟲、午夜走過的恆光橋、河堤開過的櫻花、木新市場的煙火氣……也想念那時年輕的自己,和朋友在臺北街頭閒逛,去看電影或買東西,我們說著現在早已忘記的玩笑話,曾經笑得很放肆,也會為論文的進度苦惱。當然也想念政大傳院的各位老師,我的導師柯裕棻、方念瑄老師、蔡琰老師、孫秀蕙老師、郭力昕老師等等,每一位都讓我學到很多,也想念各位同學,我的室友宋淳、文悅,還有許許多多大陸和臺灣的朋友,感恩我們一起度過的兩年時光。
這兩年的時間很快過去,有笑有淚,也有一些誤會、爭執,有很多失望、孤獨和情緒低落的時刻,現在再回頭看,它們可能都是長大的過程中必經的階段,經歷以後,我們才能更勇敢和成熟一點,對自己瞭解得更多一些。
能有機會出這本書,要感謝的人很多。首先是我的父母、外婆、雙胞胎妹妹,我的妹妹余其芳也特別為這本書畫了非常精美的插圖,再現了很多我們一同經歷的場景,讓這本書更有意義。我也要特別感謝政大的盧非易老師和國立新加坡大學出版社的林少予老師。我與林老師素未謀面,他將我的小說〈小白龍〉推薦給東美出版社,才促成了之後的合作。當然也要感謝東美出版社各位編輯老師的辛勤工作,在這本書出版的過程中付出了很多心血,讓我感動。
對我而言,寫作不是一件需要「堅持」的事情,需要堅持的是那些有些痛苦的事情,比如減肥,寫作更像是一種陪伴。這本書中的故事基本上一兩個小時就能寫完,我很享受這個過程,像做了一場舒緩壓力的心靈瑜伽。而寫小說就比較費時費力,有時像在跑曠日持久的馬拉松,賽道裡也只有你一個人,更為艱辛一些。希望未來有一天,我也能出版一本小說,這也算是一個新的小心願吧。
在故事開始前寫的「閒話」就到這裡,歡迎你和我一起走進上海、臺北,走進我的故事裡。
我沒有很大的野心,無論是否還會有第二本書,我還是會繼續寫下去。
謝謝你翻開這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