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人對於芬蘭的印象,是憤怒鳥、NOKIA、桑拿浴,以及聖誕老人和Linux作業系統之父的故鄉,其實,這個高度開發國家,除了工藝設計一把罩,還有極富特色的民族性格與文化,這裡甚至孕育了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閱讀本書,能讓您對芬蘭歷史有更深一層的體會,帶您認識芬蘭的不同面向。
《神聖的貧困》的影響力之於北歐,正如《阿Q正傳》之於中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西倫佩成名作〜
作者將本書題名為「神聖的貧困」,是為了永誌不忘在極端貧困下生活的絕大多數芬蘭農民──他自己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這些農民的命運完全仰仗地主施捨的一小塊土地。他把他們的「貧困」稱為「神聖」,是因為這貧困像「不可逃脫的命運」一般,被人們懷著「宗教般的順從」接受了下來。
貧窮是會遺傳的,這遺傳來自於心靈的匱乏;心靈的貧困,正是最大的貧困。
《神聖的貧困》是西倫佩〔弗蘭斯•埃米爾•西倫佩 ( F. E. SILLANPÄÄ )〕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作者在親眼目睹了芬蘭民族主義者與無產者之間的戰爭後寫下了這部小說。芬蘭是個長期落後的農業國,在佃農制的統治下,農民們在不足以糊口的土地上耕種,還要抽一部分時間到地主的農場服工役,他們不受契約的保護。西倫佩把他們的貧困稱為神聖的貧困,是因為這種貧困就像不可逃脫的命運一樣,被人們懷著宗教般的虔誠而接受下來。
小說的主人公尤哈生性淳樸而又愚鈍。他出身於破產的農場主家庭,一生的夢想都是發家致富。尤哈父母早逝,投奔舅舅,卻被舅舅趕出家門,為了生存,他先後當過伐木工和雇工,拼命幹活賺錢,終於當上了佃農,購買了自己的奶牛和馬,甚至娶妻生子,擁有一小塊田地和房屋。對自己充滿信心的尤哈原以為生活會從此蒸蒸日上,不料兒子忽然得了重病,田地又歉收,妻子在貧困中死去,心愛的長女去給貴族老爺做女傭的時候不明不白地墜湖而亡。痛苦的老尤哈被社會民主黨人的言論吸引,積極參加農民起義運動,懷著天真而盲目的熱情被捲進了革命的大流。然而新政權很快失敗,尤哈偷偷扔掉的來福槍被復仇者們發現,卻被錯當成殺死農莊主的兇手……
尤哈絕對不是自覺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形象。這個愚昧、善良、貧弱、麻木不仁的農民被時代推著走了一輩子,臨老才感受到了自由的光輝,卻在理想還未實現時就重新沉入黑暗。這個文學形象體現了作者對芬蘭底層民眾的悲憫,對他們一生遭受的種種壓迫和屈辱的同情。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余志遠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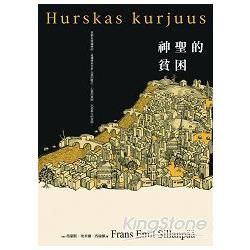 |
$ 80 ~ 246 | 神聖的貧困
作者:弗蘭斯.埃米爾.西倫佩(Frans Eemil Sillanpää) / 譯者:余志遠 出版社:九(音勻)文化(信實文化行銷有限) 出版日期:2013-10-1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88頁 / 14.8 x 20.8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1 則評論 1 則評論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弗蘭斯.埃米爾.西倫佩(Frans Eemil Sillanpää, 1888-1964)
芬蘭作家,193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1888 年 9 月 16 日出生于芬蘭坦佩雷市(Tampere),曾考入赫爾辛基大學念生物學,後因經濟困難,中途輟學,從事文學創作以謀生。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神聖的貧困》(Hurskas kurjuus, 1919)、《少女西麗亞》(Nuorena nukkunut, 1931)、《夏夜的人們》(Ihmiset suviyössä, 1934)等。《神聖的貧困》是其成名作。
1943 年任芬蘭筆會榮譽主席及芬蘭作家協會主席。
譯者簡介
余志遠
1935年生,浙江鄞(一ㄣˊ)縣人。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1958年獲選為第一批赴芬蘭留學的學生,在赫爾辛基大學研習芬蘭語與芬蘭文化。後任教於北京外國語大學,並從事芬蘭文學翻譯工作。
序
推薦序:
很高興看到芬蘭唯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弗蘭斯.埃米爾.西倫佩(Frans Eemil Sillanpään)名作:《神聖的貧困》在台灣出版。他擅長用抒情詩意的語言描繪芬蘭的自然風光,同時對小說人物的心理刻畫十分細膩。對悲劇主人翁一生場景的描繪,也讓人同時看見芬蘭從1860到1917年獨立之後的內戰年間,民生經濟、國民意識等各方面的改變。鄉村小人物的一生,其實也反映了一個大時代的變遷,而作者對人物細緻的心理描繪與轉折,讓人對於那個時代,多了一份同情與了解。
芬蘭近年來的各方面成就,從音樂、設計、教育、音樂、到建築,無不引起世界注目,然而,在現代化的外表背後,也許較不常為世人所看見的,是那曾經貧困並尋找建立民族認同的掙扎過去;而那所謂的過去,其實並不遙遠。小說主角被槍斃倒下的時代,離此時此刻甚至還不滿一百年。閱讀小說,最能讓人感受並想像過往年代的場景,並從另一個角度來回顧歷史。這本小說讓長居芬蘭的我,對芬蘭歷史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希望它也能帶給您,另一個認識芬蘭的面向。
定居芬蘭作家、部落客:凃翠珊(北歐四季)
譯 者 序
位於歐洲北部波羅的海之濱的芬蘭有其獨特之處。嚴峻的氣候條件、美麗的自然環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其他因素使芬蘭人形成了極有特色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在形成和發展民族文化過程中,芬蘭文學一直起著重要的作用,在不同時期,芬蘭先後出現了一批民族作家,如基維、康特、阿霍、西倫佩、瓦爾塔里、林納等。他們的作品代表了芬蘭文學的主流,反映了芬蘭人民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在世界文學寶庫中也佔有一席之地。民初魯迅曾把北歐文學介紹到中國,他翻譯的康特短篇小說《瘋姑娘》刊登在《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中。1949年後,我國文學界開始通過翻譯,較為系統地引進芬蘭文學,先後出版了芬蘭民族史詩《卡勒瓦拉》,芬蘭作家基維的代表作《七兄弟》,以及明娜.康特的《作品選》(包括戲劇和小說)和林納的長篇小說《北極星下》,以及部分芬蘭作家的短篇小說。西倫佩的長篇小說也有中譯本,但多數是根據英譯本翻譯而來的,直接根據芬蘭語原文翻譯過來的西倫佩長篇小說,《神聖的貧困》還是第一本。
弗蘭斯.埃米爾.西倫佩(Frans Eemil Sillanpää, 1888-1964),出生於芬蘭坦培雷市以西漢曼居洛(Hmeenkyr)教區的一個農民家庭,他的父母是從外地移居而來的,經受過該地移民世世代代通常經受過的種種磨難。西倫佩曾就讀於坦培雷中學,1908年考入赫爾辛基大學,攻讀數學和生物學,後因家庭經濟困難,中途輟學,從事文學創作以謀生。他從小瞭解農村生活,對勞苦大眾懷有深厚的同情心,但是他有宿命論的觀點,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重大的歷史事件,主人公幾乎都是命運的犧牲品。他的作品包括長篇小說《生命與陽光》(1916)、《兒童時代》(1917)、《神聖的貧困》(1919)、《海爾杜和蘭納爾》(1923)、《早逝╱少女西麗婭》(1931)、《男人的道路》(1932)、《夏夜的人們》(1934)、《八月》(1944)、《人世悲歡》(1945)等,短篇小說集《我親愛的祖國》(1919)、《天使保護的人》(1923)、《地平線上》(1924)等。1953年西倫佩發表他的生平自述《這樣生活過的孩子》;他的社會政治文章及遊記發表於1956年,名為《日在中天》。西倫佩擅長人物心理刻劃、描繪大自然,寓情於景,使人物和景物水乳交融,交相輝映。他成功地描寫了農民生活、農民與大自然的關係,並因此於193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神聖的貧困》是西倫佩成名之作,它是一次對人生大膽無畏又辛酸痛楚的描繪。小說發表於1919年這個悲慘的年頭,作者是在親眼目睹了民族主義者與無產者之間的國內戰爭,在風雲變幻的驅使下寫成這部小說的。他把這部小說題名為《神聖的貧困》,是為了緬懷在極端貧困的條件下生活的大多數芬蘭人民,為了銘記他出身的、他感到最親切的那個階級。芬蘭長期以來是個落後的農業國。在佃農制的統治下,農民們在不足以糊口的土地上耕種,有一部分時間還要到地主的農場服工役,他們不受契約的保護。西倫佩把他們的貧困稱為「神聖」,是因為這種貧困就像「不可逃脫的命運」一樣,被人們懷著「宗教般的虔誠」接受下來。小說的主人公尤哈.托依伏拉,除了忍受物質貧困之外,還得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婚姻家庭帶給他的也是災難。尤哈雖然最終捲進了革命洪流,但他仍然沒有逃脫悲慘的命運,這是他性格發展的必然結果。尤哈絕對不是自覺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形象。西倫佩可以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呼籲憐憫,卻不可能以高瞻遠矚的智慧審視人類社會的種種複雜現象。但他的藝術成就仍然是卓越的。在《神聖的貧困》中,他描繪了典型的芬蘭自然風光,展現了帶著地道芬蘭氣息的一幅幅風俗畫。尤其為人所稱道的是,西倫佩的作品具有一種單純樸素的風格。
對我們來說,閱讀西倫佩的作品是一種享受,但也是一種挑戰。西倫佩是芬蘭語言大師,其作品無論語言還是內容都是很細膩、深邃。在本書翻譯過程中,芬蘭專家 Risto Koivisto 自始至終與譯者保持密切聯繫,熱情地為譯者釋疑解難,譯者在此謹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們還要感謝中國青年出版社和芬蘭文學資訊中心(Finnish LiteratureIn formation Centre, 簡稱 FiLi),沒有他們的全力支持,這部譯本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余志遠
2012年4月10日於北京外國語大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