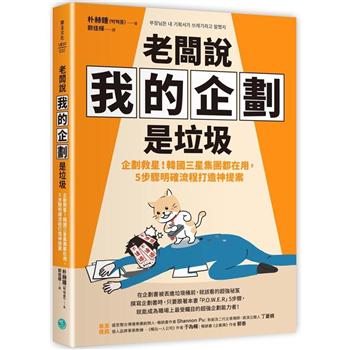令人驚豔之作!
媲美千萬暢銷書《閣樓裡的小花》與《少女死亡日記》
亞馬遜網路書店與Goodreads網站讀者5顆星推薦
從來沒有讀過像《畫星星的女孩》這般令人著迷和無法忘懷的故事。──艾蜜莉‧米漢,Hperion總編輯
我的家很完美,手足很友愛,母親從不多說話,
唯一要做的事是:聽父親的話。
身上有瘀青是正常的,我愛我的家……
即使是幽暗可怕的森林,星星的光芒依然會穿透樹葉,照亮黑暗,
於是,六歲那年我刻下第一顆星星,到我十六歲時,樹林裡已到處是星星。
對克瑞斯威一家來說,位於森林深處的破爛大宅就是他們可愛的家,
多年來他們遵循上帝的嚴格規定生活,而神的旨意由父親直接傳達:
他們是世上僅存純淨之人,必須互相嫁娶;
早上必須全家聚在一起朗讀父親寫的「聖書」。
父親不相信現代醫學、教育、水電,他們也必須不相信,
他們能取用的水來自室內地板上一桶桶發臭的自來水,
唯一的廁所只有在父親認可的緊急情況才能使用。
十六歲的凱絲蒂和她的手足們時時刻刻謹守規定,
因為若不合規矩觸怒了父親,就得被關進黑暗的「墓穴」,
她唯一的娛樂是:半夜在森林裡遊盪,在樹上刻劃一個又一個星星,從六歲開始。
這樣幾近與世隔絕的日子在母親摔斷腿,卻無法向警方清楚交待來龍去脈時發生變化,
他們在警方的介入下終於開始上學,擁有家庭以外的生活。
凱絲蒂的世界迅速擴大,曾經奉為唯一真理的信仰開始動搖,
她深刻地意識到:她身上不該有人為造成的瘀傷,她的家庭非常不正常。
正當她暗中醞釀脫逃計畫時,她父親卻語出驚人地宣布:
上帝不再提供我們活著所需的一切,回歸天國的時刻即將來到……
本書細膩描繪每位家庭成員的心境轉折,凱絲蒂如何發覺到家庭的異常、掙脫心理枷鎖,
在尋求幫助卻遭受現實殘酷打擊時仍不退回原點,為這個令人揪心的故事點亮溫暖的光。
作者簡介:
依萊莎‧瓦思Eliza Wass
自由作家、編輯、記者。她出生於南加州,完美的父母生下九個完美的孩子。她有成千上萬的朋友,大部分都包著書衣,不然就是推特重度上癮。依萊莎曾經和全世界最棒的男人一起住在倫敦七年──她的亡夫愛倫‧瓦思,「愛倫‧瓦思與止血帶樂團」的主唱,他啟發她追逐夢想,過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歡迎參觀她的網站:www.elizawass.com,也可以上推特關注她:Twitter@lovefaithmagic
:
譯者簡介:
康學慧
英國里茲大學應用翻譯研究所畢業,從事專職翻譯多年。現居於寶島後山的小鎮,沉醉於書香、稻香與米飯香。譯作包括《最好的妳》、《小謊言》(春光)、《謎蹤系列》(果樹)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各界好評推薦:
*今年我讀過數一數二的佳作。──露易絲‧歐南爾(Louise O’Neill),知名青少年小說作家
*黑暗、美妙,有時又令人膽寒,一如午夜在樹林深處遊蕩。新人作家瓦思才華驚人,不容錯過的處女作。──契兒斯頓‧懷特(Kiersten White),紐約時報暢銷作家
媒體推薦:
*令人屏息、膽戰心驚的成長冒險。讀者將被拉進克瑞斯威家族的封閉世界,即使燃燒殆盡依然為他們感到心疼……令人難以釋手,程度可比《閣樓裡的小花》。──《科克斯書評》
*作者描繪出以信仰力量為中心的家庭,令人戰慄。──《出版家週刊》
*引人入勝。──《童書中心月報》
*一次又一次帶來情緒上的衝擊……小說描述家庭歷經絕望變化的痛苦過程,但主角凱絲蒂敘述的語氣不曾動搖。──美國知名《號角雜誌》
*不容錯過的處女作……陰森卻豐富的世界令人著迷。──Bustle網站
名人推薦:各界好評推薦:
*今年我讀過數一數二的佳作。──露易絲‧歐南爾(Louise O’Neill),知名青少年小說作家
*黑暗、美妙,有時又令人膽寒,一如午夜在樹林深處遊蕩。新人作家瓦思才華驚人,不容錯過的處女作。──契兒斯頓‧懷特(Kiersten White),紐約時報暢銷作家
媒體推薦:*令人屏息、膽戰心驚的成長冒險。讀者將被拉進克瑞斯威家族的封閉世界,即使燃燒殆盡依然為他們感到心疼……令人難以釋手,程度可比《閣樓裡的小花》。──《科克斯書評》
*作者描繪出以信仰力量為中心的家庭,令人戰慄。──《出版家週刊》
*...
章節試閱
六歲那年我刻下第一顆星星,到我十六歲時,樹林裡已到處是星星。有些我甚至不記得曾經刻過,有時候我懷疑是不是別人刻的——漢南、黛兒薇、卡士柏、莫迪墨或耶路撒冷,但也可能是我的另一個哥哥,死掉的那個。不過,我知道,只有我會這麼做,我知道只有我會刻星星。
~1~
星期天凌晨三點,我站在史陀布里吉女士的屋脊上,小心地保持平衡,看著弟弟用木棍挖出一堆落葉。史陀布里吉女士住院了,所以沒有人會聽見我們清理排水管的聲音,但卡士柏盡量不發出聲音。我們得在晚上來清理才不會被看到,卡士柏說他想給老人家一個驚喜,但又不希望被我們的父親發現。
我仰頭瞇眼看星星。「我今天在學校發現一件討厭的事情,你想聽嗎?」我知道他不想聽,卡士柏不太喜歡討厭的事情,但他很願意聽人傾訴,於是他簡短地說:「講給我聽。」同時繼續忙個不停。
「你知道仙后座是我的星座吧?」父親給每個子女一個星座,彷彿星星是他個人的財產。卡士柏沒有點頭也沒有其他反應,因為他不喜歡這個話題的方向。「呃,基本上,在希臘神話中,仙后座源自於衣索比亞王后卡西歐佩雅,她因為虛榮而受到懲罰,被綁在天空的一張椅子上。她就這樣被綁在天上,我的星座竟然這麼慘。」
我的另一個弟弟莫迪墨在下面一陣亂叫,他負責把風,應該認真留意動靜。「衣索比亞王后並沒有真正被綁在天上,妳應該知道吧?」他高聲說:「那只是希臘人瞎編的鬼話,妳瞭吧?」
「我知道,但父親也用『仙后座』這個詞,代表他很清楚這段故事。」我說。
「沒錯——父親是怎麼說來著?字詞有多重意義。我相信他一定想告訴我們什麼,八成是要我們把妳綁在椅子上。」
「反正也沒差。」我低聲說,只讓卡士柏聽見。
他瞪大了眼。我一直覺得卡士柏這個毛病很怪,每次有人表達不滿,他總是一臉錯愕——真的很震驚,好像他完全不曾有過這種感受
「凱絲蒂,現在只是過渡階段,上天堂之後就會好了。」他輕柔地說。上帝一定是惡作劇才會給卡士柏這樣的聲音,因為卡士柏的容貌像天使,絕對是我們兄弟姊妹中最好看的一個,連女生也比不上,但他說話的聲音很粗嗄,活像一天抽兩包菸的建築工人,所有女生都為之瘋狂,不過他從來沒察覺。
「我不想等,我希望現在就變好。」
我聽見莫迪墨沿著水管爬上來找我們,活像個小老鼠。莫迪墨幾乎是白子,所以比起其他兄弟姊妹,鎮上的人更愛欺負他,他也比其他兄弟姊妹更會惹事,大致上是有來有往。
「我不懂,妳怎麼會以為別人過得比我們好?」莫迪墨爬上屋頂。「每個人的人生都一樣爛。」
「哦?我很樂意和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交換人生,得到『真理的福祐』簡直是種折磨。」
卡士柏忽然緊張起來,看來我說得太過分了,下一瞬,他猛然跪下,我們腳下的屋頂震動。
「卡士柏,怎麼了?」我以為他跪下是為了緊急禱告之類的。
「下面有人。」他用氣音說。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不相信,由此可見我被整過多少次,但一道燈光往屋頂照過來,劃過我們頭頂,莫迪墨急忙撲倒,壓低身體趴在屋頂上。沉重的腳步聲踩在乾枯草坪上,我遲疑了一下。
「凱絲蒂,快趴下!」莫迪墨說。他八成因為太急著趴下而感到丟臉。
光束照在煙囪上,形成一道微黃的光圈,光束晃動一下,然後延著屋脊照過來,就快照到我了。
我可能會被看見,我心裡想,雖然很蠢,但我想被看見,我太想被看見,以至於不在乎是怎樣被看見。我感覺我的手腕被握住,卡士柏把我往下拉到他身邊。
「有人在上面嗎?」下面的人大喊,是個男人,聲音老老的,我瞬間由呆滯狀態清醒過來。那個人不是來拯救我的,他不是正義武士也不是白馬王子,甚至不是英勇的少年。
我忽然害怕起來,於是偎靠著卡士柏,隔著他的二手衣感覺他急速的心跳。
「喂!上面有人嗎?」他問,好像我們故意吊他胃口。林野另一頭的遠處傳來狗的嚎叫,那個人說:「八成只是老鼠。」然後拖著腳步穿過草坪離去。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一動也不敢動,莫迪默大字形趴著,像放在屋頂上的娃娃,卡士柏則跪在我身邊望著天空。之後,莫迪默坐起身,掀起厚唇舔舔牙齒,稍微痛縮了一下。「凱絲蒂,幹得好,他差點看見妳。」
「真的被看見的人是你吧?」我放開卡士柏。「你也聽到了,他剛才說『只是一隻老鼠』。」
「他明明說的是『只是老鼠』,是複數。」
「你們還是先回家好了。」卡士柏突然說道。我們兩個一起轉身,目瞪口呆,彷彿無法相信他不要我們留下。我們兩個根本沒幫上忙,我們自告奮勇來把風,但就連這個也沒做到。
「卡士柏……」我開口喚。他拾起木棍通水管,濕答答的垃圾一團團落在地上。他們八成會以為是老鼠幹的,不然就是上帝賜予的奇蹟,我猜卡士柏八成希望他們這麼想。
「來吧,凱絲蒂,我們走。」莫迪墨往排水管的方向溜下屋頂。雖然他們兩兄弟個性迥異,但莫迪默對卡士柏有種莫名的敬重。
我看著卡士柏。假使我認真幫忙,說不定他會讓我留下,我可以自己找根棍子,不然也可以徒手挖出葉子。
卡士柏執意要為鎮上的人做好事,那些人討厭我們、嘲弄我們,常用難聽、噁心的話罵我們,但卡士柏最喜歡幫他們掃門廊、拔雜草、擦窗戶。我個人對他們沒什麼好感。「好吧,」我說,「我們走。」
我跟在莫迪墨後面爬下排水管。一道籬笆隔開史陀布里吉與希金斯兩家的農莊,我們悄悄沿著籬笆前進,一抵達樹林,我們兩個同時開口說話。
「妳不該那樣考驗卡士柏——」
「明天會不會熱到可以去游泳?你說呢?等一下——什麼意思?考驗他?」
「妳不該那樣抱他。」他用力推開一根樹枝。
「你在說什麼?我很害怕!」
「我只是為妳好,不要假裝聽不懂我的意思。」
我想說話卻沒有開口,我總是盡可能不說話,原因很簡單:因為不確定我的兄弟姊妹在想什麼。我不確定他們相信的程度有多深,我甚至不確定自己相信的程度有多深,因為父親相信很多瘋狂的事情。
父親教導我們,說我們是世上僅存的純淨之人、尊貴之人,因此我們必須互相嫁娶。當然不能舉行世俗的婚禮,因為法律禁止,但是我們將在天國的儀式中結合。我被安排嫁給卡士柏,黛兒薇與漢南配對,可憐又可愛的耶路撒冷只剩下莫迪墨。
小時候,我真心認為能和卡士柏配對是我賺到。真幸運,我分到最好看、最善良的弟弟!後來媽媽出意外,我們被迫去真正的學校念書,我這才發現嫁給親兄弟不但違法,而且噁心透頂。
克瑞斯威家的六個孩子相親相愛到永遠,完美至極,只是……我原本有個哥哥,他的名字也叫卡士柏,他比我們三胞胎(我、漢南、黛兒薇)早出生,但他過世了。而新的卡士柏──有一天我會嫁的那位,他其實是之前那個復活重生。
我冷得發抖。「明天要開學了。」我真的不知道還能說什麼。我早已學到教訓,不可以太期待上學。
「嗯。」莫迪墨舔舔牙齒。
「你的嘴巴怎麼了?」
莫迪墨慌了,急忙搶先穿過樹林。「沒事。」
「你一直碰它,一直用舌頭去頂牙齒中間,好像那裡有什麼。」
「親愛的老姊,我能在那裡藏什麼?行李箱?迷你雨傘?」
我忍不住大笑,加快腳步追上他。「天曉得,我以為你弄破嘴唇了。」他仔細觀察我的臉,想找出蛛絲馬跡。「你知道,你可以告訴我的,我不會說出去。」我最近才學會保密,小時候我很愛告狀,我們六個都一樣。我們之間的競爭很激烈,如果父親少愛其他兄弟姊妹一點,他就能多愛你一點。
莫迪墨噘起嘴,然後痛得一縮。
「我用媽媽的生命發誓,一個字都不會說。」這是個很嚴重的毒誓,因為媽媽雖然活著,但幾乎一輩子都懸在生死之間。
或許是因為這句話,莫迪墨停下腳步,身體靠在一棵樹上,我刻在樹幹上的星星懸在他肩膀上方。莫迪墨的唇很厚,那是他唯一好看的地方——豐厚、微翹,顏色像莓果。他捏住上唇往上拉,像掀窗簾一樣,裡面腫起一個紅色水泡,顏色很深,感覺很痛。
「上帝啊,怎麼回事?是不是父親——」
他的手鬆開唇。「不,不是父親弄的,大白癡。我很怕被他發現。」
「那是什麼——難道是疱疹?」我問。他一推樹幹站直,頭也不回大步穿過樹林。「噢,上帝啊,是別人傳染給你的嗎?」
他大聲咆哮,我則盡可能保持冷靜。在所有兄弟姊妹之中,我認為莫迪墨是最不可能和人接吻的一個,不只是因為他的外貌,而是因為他幾乎討厭所有人。「噢,上帝啊!你和誰接吻了?」
「不要隨便亂說那個詞!」這就是兄弟姊妹最令我不解的地方,他們嘲弄一些規定,同時又死命堅守另外那些。莫迪墨剛剛承認和人接吻,卻又責備我不該把上帝掛在嘴邊。
「哇,萬一父親發現,你會吃不完兜著走,我連想都不敢想會有多慘。」他快步在樹林間行走,快到家時,我追上去叫住他:「等一下!對不起。說不定我可以幫你。」
「怎麼幫?」他的語氣很衝,但他還是停下腳步,煩躁地把玩連帽外套。
「可以去買藥膏。搽了會比較不痛,也好得比較快。」父親不相信現代醫學——更何況莫迪墨犯下親吻外人的罪孽,他更不可能給他藥搽。我努力表現體貼,但我實在太想知道莫迪墨吻了誰,甚至連指尖都感覺到那份好奇的觸動。
「哦?妳要幫我去買?」
「不,但我可以幫你去偷。」
他的瞳孔放大,泥灰色的眼眸中央突出一抹黑。「凱絲蒂。」
「為什麼不行?我從來沒有被逮到過。我知道你被抓過,但我很聰明也很小心。我去幫你偷。今天就去。」
「今天是星期天,藥局沒開門。」
「『大美國』一定有,大美國什麼都有。」
他舔了舔水疱。「凱絲蒂,去大美國偷東西一定會被抓。他們知道我們是什麼人,鎮上所有店家都知道,大家認定我們是小偷。」
「還不是你害的。」
他冷笑。「我送妳巧克力的時候妳怎麼沒抱怨?還有我們在樹林烤牛排那次?」
「那塊牛排最棒了。」我微笑。「所以啦,我虧欠你很多,至少得去試試,反正我不怕他們。」
「我擔心的不是那些人。」
就在此時,房子出現在我們眼前,披著幢幢暗影,裹著腐朽木材。我討厭這棟房子,這是全世界我最討厭的地方。每道走廊、每個角落、每個小地方都藏著回憶,假使望著一個地方太久,我恐怕會陷落進去,沉溺於回憶,直到尖叫著回到現實。
我在森林邊緣徘徊,那些不時有的念頭竄過我的腦海:妳可以乾脆離開。妳可以乾脆離開,永遠不要回來。但另外又有無數想法瞬間湧出,有如剛掃過又冒出的灰塵:妳還太小,得要養得起自己才能和父母斷絕關係,況且妳也沒有親戚朋友。假使妳去兒福處求助,假使妳說出他的所作所為,所有家人都會變成妳的敵人。妳依然愛他。這些想法中最可怕的則是:萬一他說的都是真的呢?
我從不曾說出這些想法。我慎重提防、努力壓抑,每當快要浮出腦海便硬塞回去。
有些話永遠不能說,因為一旦說出口,將會改變一切。
我蹬起腳跟上下蹦跳。「幾點了?」
「呃,我不知道;五點?」
「我們現在就去好不好?在祈禱之前回來。」我們每天早上六點半要禱告。我覺得沒必要立刻回家,反正我們也睡不著。我們幾個都有失眠的問題,除了漢南,因為要練足球,所以他強迫自己入睡。我們其他人總是時睡時醒,整夜翻來覆去,我猜是因為我們很清楚自己錯過了多少,以致整夜睡不著,也可能是我們害怕錯過更多。
莫迪墨搖頭。「一定趕不及。」
「大美國離這裡才兩英里,頂多二十分鐘的路程。現在的時間正好,店裡不會有太多人。」
「人多才好,比較不會被看到。」
「大家都對我視而不見,我幾乎等於不存在。」
莫迪墨板起臉,但我轉身出發時他還是跟了過來。我加快腳步,集中精神不去想會發生什麼事,不去想該怎麼計畫,因為計畫只會帶來失望。硬是改變未來的方向,最後的結果絕不會如你所願,這是父親教我的道理,因為他凡事都要做計畫,我從中學到這個道理。
我希望有一天人生能豁然開朗,我希望人生不必照著地圖走。我希望所有東西消失,包括我腳下的道路,如此我便不需要知道自己正在往哪裡走。
我專注思考種種可能。我不害怕,當大美國出現在眼前,我自認已經準備好了。
「你在這裡等。」我對莫迪墨說。他沒有擺臭臉或咳聲嘆氣,只是縮起身體躲在一棵樹後面目送我離去。
~2~
大美國是一家加油站附設的便利商店,就在通往奧司川的高速公路旁。天色漸漸明亮,停車場空空如也,魯沛站在櫃台後面,頭稍微往後仰,呆呆望著遠處,彷彿在自我催眠。
我確切相信我可以直接走進去,他絕對看不到我,在這個鎮上我真的有這種感覺。我們過馬路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那些所謂的「好人」,都會轉頭看反方向。老師就算發現我的手腕上有瘀血也不會直視我的眼睛;學校的男生就算在走廊上撞到我,也只會瞪著我頭部上方的空氣,然後加速離開。黛兒薇和我一起修戲劇課,我敢發誓,即使我們上台表演,即使舞台上只有我們兩個,其他同學依然可以對我們視而不見。
因此,我以為能像隱形人一樣直接走進大美國。
我穿越停車場,踏上人行道時,我盡可能不看自己映在玻璃窗上的身影——慘白發灰的皮膚,毫無造型的棉質布袋洋裝,毛躁長髮編成繁複髮辮盤起。我心中的自我形象與現實相差太遠,有時看到自己會嚇一大跳。
我壓低下巴往門口走去,我推開門,迎客鈴叮咚作響(至少我好像聽到了),但魯沛頭也沒抬。我彎腰躲在貨架後面,經過雜誌架,走向小小的保健區,我蹲下,用裙子蓋住膝蓋。我的視線飛快掠過保險套、衛生棉條、熱力軟膏……
抗病毒藥膏。我一把抓起,這時迎客鈴再次發出叮咚聲響——一次、兩次,然後接連四次。我先看到那些人的腳,一整排五顏六色的雪靴,我立刻判斷應該是和我同齡的少女。當一個人討厭自己的生活時,最難忍受的,是過著你想要的那種生活的人,儘管如此,我還是忍不住想看。
我往後靠,謹慎又好奇,終於看到芮娃狐媚的笑容,她正穿著成人版兔裝。整群女生——芮娃、莉莎、達拉、愛蜜莉‧希金斯,還有一個我沒看過的黑人女生,她們每個都穿著色彩繽紛的瘋狂兔裝,上面印著逗趣圖案,彷彿為了搞笑而特地買這些衣服。她們的每個人的頭髮都挑染粉紅色,八成是一起染的。她們很可能一起過夜,早上出來買東西。
「魯沛!」芮娃尖聲喊。芮娃其實並非人氣女王,但人氣女王該做的事她一項也不放過,她似乎以為遲早有一天大家會聳肩接受,然後開始崇拜她。「我們要做煎餅!你有沒有賣做煎餅的材料?」她說的每句話都以驚嘆號結尾。
魯沛滿臉傻笑,跟著她們在店裡走來走去,似乎聽不膩她刺耳的尖細聲音。
「魯沛!那種好的在哪裡?這不是好的那種!我要上面印著馬的那種!記得嗎?我超愛那個牌子!魯沛,今天是我的生日喔!猜猜我幾歲!對你而言還是太小了啦!」其他女生也在嘰嘰喳喳,但因為芮娃嗓門太大,所以聽不見她們在說什麼。
我應該馬上衝出去,這是絕佳時機,卡士柏會說這是「福祐」,每次有好事發生他都會這麼說──不過發生壞事時他總是嘴巴閉緊緊。
我沒有衝出去,反而感覺到自己的畏縮。我感覺自己蹲低,整個身體包住那條藥膏,彷彿想趁機融化滲入商店地板,我甚至沒察覺那群女生來到身後。
「嘿!」莉莎匆忙後退,撞上她後面新來的女生。
那個女生的頭髮編成辮子繞在頭上,她的姿態不知為何讓我更加畏縮。
「我知道妳是誰。」她說,而我很確定這輩子沒見過她。
莉莎發現我手中的抗病毒藥膏,我感覺脖子、臉頰,連眼睫毛也全部漲紅。她蹙起眉。「我以為你們家的人不相信現代醫學。」她的語氣彷彿我是社會學實驗的觀察對象。
「嘿!莉莎!愛蜜莉!妳們在跟誰說話?」芮娃出現在走道盡頭(陷阱!),她的小型部隊緊跟在後。「噢!老天!真不敢相信!」
我的腦中一片空白,這就是所謂的極度驚恐。我得快點出去,但我不能拿著藥膏從芮娃旁邊衝出去,她絕對會一口咬定我有疱疹或其他噁心的髒病,更何況我不打算付錢。
我將藥膏拋回貨架,撞掉了保險套、衛生棉條與熱力軟膏,然後我拔腿狂奔,以跑百米的速度衝向門口。
芮娃罵了一句髒話,張開手臂想攔住我,但我及時衝了過去。我高速跑過停車場,經過芮娃家的Range Rover高級休旅車,她媽媽坐在車上等。我聽到她們整群人狂笑,我聽到芮娃的連篇驚嘆號逗得她們陣陣傻笑。
我跑過去時,莫迪墨伸手想抓住我。「有沒有成功?」我沒有停下腳步,我聽見身後傳來他重重的腳步聲。「凱絲蒂,有沒有拿到?妳被抓到了嗎?有人在追我們嗎?」他放慢腳步,但我繼續跑,甚至加快速度。「凱絲蒂!」他大喊,但最後還是放棄阻止我。我不停往前跑,直到終於只剩下我一個人。
六歲那年我刻下第一顆星星,到我十六歲時,樹林裡已到處是星星。有些我甚至不記得曾經刻過,有時候我懷疑是不是別人刻的——漢南、黛兒薇、卡士柏、莫迪墨或耶路撒冷,但也可能是我的另一個哥哥,死掉的那個。不過,我知道,只有我會這麼做,我知道只有我會刻星星。
~1~
星期天凌晨三點,我站在史陀布里吉女士的屋脊上,小心地保持平衡,看著弟弟用木棍挖出一堆落葉。史陀布里吉女士住院了,所以沒有人會聽見我們清理排水管的聲音,但卡士柏盡量不發出聲音。我們得在晚上來清理才不會被看到,卡士柏說他想給老人家一個驚喜,但又不希望被...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