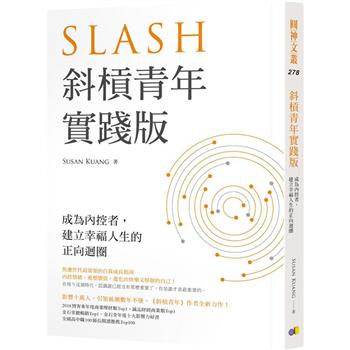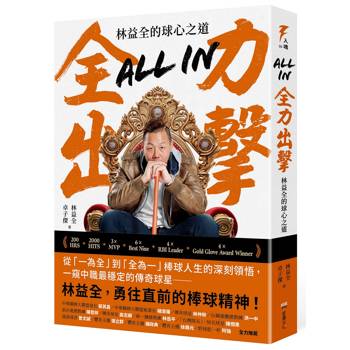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侯旭東等的圖書 |
 |
$ 210 ~ 350 | 東漢生死觀【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余英時 / 譯者:侯旭東等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6-23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216頁/21*14.7cm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東漢生死觀
本書是於英時先生對於東漢民間生死信仰的考察,尤其是以「魂升天,魄入地」為代表的靈魂觀念,並強調中國人並不是等到佛教傳入才產生地獄觀念的。
作者簡介
余英時
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年生,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2006年獲頒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