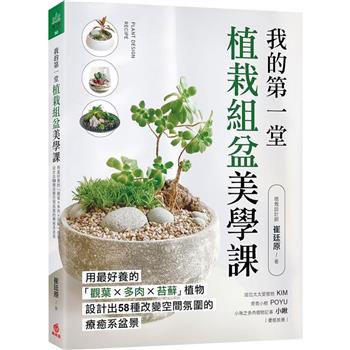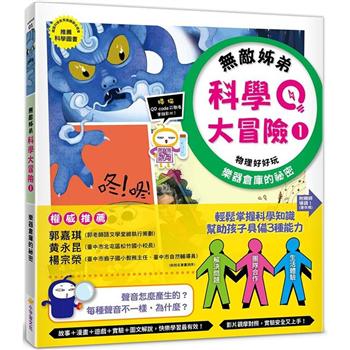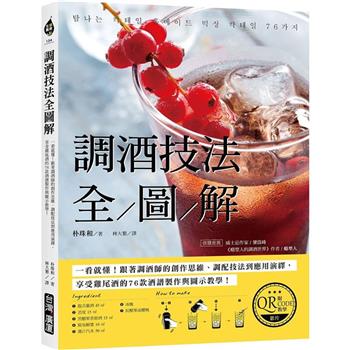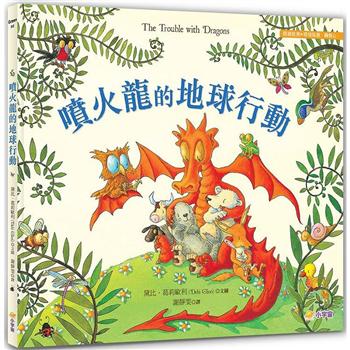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保羅.哈朋的圖書 |
 |
$ 309 ~ 458 | 愛因斯坦的骰子與薛丁格的貓:友誼、競逐與背叛,兩位偉大物理學家為統合自然的不懈努力,如何引領對萬有理論的終極追求 (電子書)
作者:保羅.哈朋(Paul Halpern) / 譯者:吳那 出版社:臉譜 出版日期:2025-04-2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364 電子書 | 愛因斯坦的骰子與薛丁格的貓:友誼、競逐與背叛,兩位偉大物理學家為統合自然的不懈努力,如何引領對萬有理論的終極追求
作者:保羅.哈朋,Paul Halpern 出版社:城邦出版集團 出版日期:2025-04-24 語言:中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