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身處困境、猶豫不決的時候,我就想到這句話,我總是對自己說,沒有什麼能讓我與建築的靈魂和其內在的本質背道而馳,這才是最重要的。——保羅‧安德魯
1999年,保羅‧安德魯以一個前衛非凡的蛋殼造型,獲選為北京國家大劇院的設計競圖案,當時引起一陣軒然大波,輿論指責他忽略中國傳統建築風格,破壞了天安門與紫禁城周遭環境歷史文化的和諧,不但開工儀式因此被迫取消,還有100多位國家級院士、建築學家與工程學家聯名抗議,要求停工15年。
但自2007年10月完工開放後,「北京國家大劇院」從之前被譏笑為「鴨蛋」,變成「水上明珠」,還被評選為中國10大新建築奇蹟之一,同時也被北京市民票選為北京十大新地標之一,保羅‧安德魯現在則是大陸最炙手可熱的外國建築師。
本書由保羅‧安德魯親自撰寫及拍攝,敘述他是如何構想出這座面積相當於二十座足球場、五座奧運標準泳池的巨蛋結構,以及他如何經歷競爭激烈的競標,承受被要求修改的壓力,克服各項施工過程面臨的挑戰,完成這座全世界最大型的複合式劇院。
保羅‧安德魯在書中以坦率直白的文字,記錄了他在長達6、7年建造期間的心情轉折,例如面臨困難的沮喪挫折、各方輿論指責和謠傳交相攻擊的憤慨、施工品質未按標準的無奈,以及與業主溝通出現障礙的焦慮等等。
這是關於一位建築師內在真實世界的告白,還有這座充滿未來感的玻璃鈦合金建築怎樣誕生的幕後故事。
作者簡介:
保羅‧安德魯(Paul Andreu),1938年生於法國波爾多近郊的小鎮,從小便對建築與藝術有興趣,法蘭西高等工科學校畢業後,進入巴黎道橋學院和國立美術學院,主修建築與工程學,30歲不到,便完成巴黎戴高樂機場第一航站的設計案,成為交通運輸建築設計中的經典之作。
接下來的三、四十年間,他前後設計了包括開羅、雅加達、杜拜、上海浦東等遍佈世界各地60多座機場航站,成為全球設計最多機場的建築大師。除了機場建築之外,安德魯也設計過許多大型公共建築,例如巴黎新凱旋門、日本關西機場海上建築、日本大阪海洋博物館、法國冬季奧運跳台滑雪場等。
安德魯之所以能夠跨越東西文化藩籬,受到東西方國家青睞,主要在其「用建築說故事」的獨特方式,善於將光線運用作為一種建築語言,讓他所設計的巨大建築空間顯得神奇多彩,變得更動感,更具有想像力、感染力,不但不會令人覺得遙不可及,反而還賦予了建築特殊的生命力。
現年七十歲的安德魯,為法蘭西藝術院及建築院院士,曾獲法國國家建築大獎、佛羅倫斯Gould大獎、法國營建與美術協會「達文西」大獎、日本Nekkei BP技術獎、日本建築協會獎、法國航空航太協會特別獎、Aga Khan建築獎、英國建築技術協會特別獎、國際建築學會「水晶球」獎等。而除了理性的建築設計之外,他還曾寫過《我蓋了許多機場航站》(1998)、小說《記憶的群島》(2004),展現他人文色彩濃厚的感性一面。
保羅‧安德魯代表作
1974~ 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第一航站(陸續包括2A、2B、2C、2D、2E、2F航站)
1987 巴黎新凱旋門
1988 法國阿爾貝維爾跳台滑雪場(1992年冬季奧運場地)
1993 大阪海洋博物館
1995 日本大阪關西國際機場(世界首座人工島機場)
1996 阿布達比國際機場第二航站
1997 北京國家大劇院
1997 印尼雅加達國際機場
1997 法國波爾多機場
1997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
2004 成都科技創業中心
2004 上海東方藝術中心
2005 新廣州圖書館
2005 澳門海神綜合中心
2005 成都法院大樓
譯者簡介:
唐柳,南京大學外語系學士,法國克萊蒙費朗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曾任500強公司(Alcatel,Cocacola)金融分析師,現就職於生物科學技術公司,兼職翻譯撰稿及文化交流活動。王恬,南京大學西語系法國語言文學學士,法國巴黎三大現代文學碩士,現就讀博士班,專攻電影史,曾任大學教師、翻譯,代表譯作有《電影手記「美女與野獸」拍攝日記》等。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我很少讀到如此富有教育意義的敍述,在這當中,在這段工程建造的期間,作者一點一滴傾訴自己所完成的成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文字不僅著眼於工程的進展,也透露建築師的感受和想法,其中還包含了苦惱和疑慮……——法蘭西院士程抱一透過保羅的文字,我彷彿也聽到工地的聲響,看到音樂廳的天花板以及穹頂的木材飾面。……我喜歡花園的規劃,喜歡那個水池……我喜歡這顆蛋,喜歡它出色的簡單外形,而這些想法都來自這個用筆和記事本工作的人。——法國藝文推廣協會執行長OlivierPoivred’Arvor北京國
得獎紀錄:我很少讀到如此富有教育意義的敍述,在這當中,在這段工程建造的期間,作者一點一滴傾訴自己所完成的成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文字不僅著眼於工程的進展,也透露建築師的感受和想法,其中還包含了苦惱和疑慮……——法蘭西院士程抱一透過保羅的文字,我彷彿也聽到工地的聲響,看到音樂廳的天花板以及穹頂的木材飾面。……我喜歡花園的規劃,喜歡那個水池……我喜歡這顆蛋,喜歡它出色的簡單外形,而這些想法都來自這個用筆和記事本工作的人。——法國藝文推廣協會執行長OlivierPoivred’Arvor北京國
章節試閱
一、2005年6月1日
白天的雨洗掉了沙塵,夜色一片明淨。
南面水池的石板基本上算是完工了。我等待這一刻已經很久了:池水平靜下來,第一次能夠看見穹頂在水池中的倒影。當我在設計柱子和穹頂時,就像以前在美術學院學的,我並沒有將穹頂限制在對稱的水平面上,而是將曲線往垂直面延伸了一小部分。我只知道早在古羅馬時期就有過這樣的設計。這座橢圓形建築物是否能如我們所期望的,給人拔地而起、卻不孤單薄弱的感覺呢?這是我第一次可以這麼具體地評論它。當然,我們之前繪製了很多設計圖,包括正面圖、剖面圖,以及透視圖,但這些設計圖只能勾勒想像中的建築物樣貌。
掛在穹頂上的燈使得整個弧面線條分明。夜幕降臨之時,我們將看到燈光的效果。效果會好嗎?現在由於水池的水位比將來完工後的高度略低,因此還無法斷定效果如何。但不管怎樣,我算是放下心中的大石頭,像這樣弧形稍稍帶有垂直的部份,其實是幾乎察覺不到,但卻製造出預期的效果。我們都知道,優雅的造型通常來自於幾何圖形的小小變形。報刊雜誌的排版人員對這點比建築師一定更瞭解。人類直立的姿勢,是重心使然,最後變成一種習慣。而由於這種習慣使然,那些我們從中想追求抽象與單純之美的幾何圖形,如果只是中規中矩,會讓人大失所望。為了符合我們心目中完美的標準,設計的圖形必須是有「瑕疵」的,更確切的說,是有待「修正」的,但這當然和建築上的錯誤是完全兩回事。
幾個世紀以來,一些傳承下來的建築學知識成了課本裡的內容。但是,特別是當設計新的和超大型建築時,我們所不瞭解的建築知識其實比已知的要更多。除了一些技術之外,我們其實還有一大片空白未知的領域。毫無疑問的,隨著認知科學的發展,尤其是在感知方面的研究發展,我們仍有很多地方需要學習。不過令人尷尬的是,我們會懷疑這些科學研究演繹出來的部分和暫時性的真理。它們看似過於簡單和概念化,而我們對它們幾乎完全不瞭解,但我們堅信,與其通過筆直和確定的道路來穿越森林,我們情願在森林中自己摸索。直覺最終會單獨地指引我們走下去,途中一定伴隨危險,會平淡、醜化一個設計,會讓看到的人覺得不忍卒睹,甚至渾身不舒服。
如同其他藝術家一樣,建築師會追尋直覺的想法。我們心知肚明,太多來自直覺的想法沒法向世人解釋。一般人總是將「直覺」與「靈感」連在一起,這並不正確。其實我們不是心血來潮。和自我鬥爭多少都會感到痛苦,但不會一直沉溺於自我。我們思索、推敲、躊躇、焦慮,直到確定每件作品都是心血的結晶。
我常想,如果最早我是選擇從事物理方面的研究,我的人生會是怎樣?創新,不論是在這方面或是那方面,永遠是無法滿足在已經架好的框架裡,在強烈渴望的推動和直覺的指引下,創新總是敢於打破常規。在思維的領域裡,科學和藝術來自於其中兩個對立的方向,各行其道。然而兩者相遇的次數比我們想像的要頻繁多了,而且,它們相遇並不是彼此模仿或刻意尋找對方的結果,而是一種意外的、驚喜的相遇。
無論如何,我選擇了建築業,並且從事這一行,因為當我逐漸了解這個行業,我發覺它是如此吸引人。這是個有難度並十分苛求的行業。會帶來短暫的歡愉,但有時難免也有許多失落。由於決策者和評判者對設計作品往往不瞭解或輕視,那隨之而來的痛苦簡直讓人難以忍受。更可怕的是,當建築師的目標無法進一步被探索和實現時,那些紛雜感受都只能隱藏在內心深處。至少,對於那些只是追求寧靜的生活,或者反之,對於爭權奪利和追趕潮流的人來說,建築這一行並不是一個值得羡慕的職業。
身為建築師,我們是服務者而非指揮者。但無論我們是否能贏業主的尊敬,都不是為主其事者服務,建築師服務的是設計案,是建築,是那些我們負責承擔的任務。
對於那些不確定要做什麼、只想以最快方式賺到最多錢的年輕人來說,建築師並不是一個理想的職業。這是一種佔據了——甚至可以說是霸佔了你整個生活的職業。但是,同樣,如果你願意完全投入其中,它也會給你的生命帶來一種意義。因為那時,你的生命會由焦躁恢復平靜,沮喪會漸被遺忘,不一定是欣喜若狂,但是會有建築與世界融為一體的時刻,會有感到幸福快樂的時刻。
對我而言,2005年6月1日夜幕降臨的這個時刻,就像照片所呈現的,也是讓我內心充滿幸福、信心和希望的一刻,是一個鼓舞人心的時刻。
二、整體剖析
在參加關於工作或建築研討的講座時,我不會準備書面資料。我會依據不同的聽眾和主題,以及我當時的心情,準備一系列不同的圖片。我利用畫面來闡述我的想法,儘量使我的表達生動而不呆板。有時我會依先後順序來解說這些畫面,有時會倒過來說明,更多時候我會隨機展示這些畫面。敍述一個故事往往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畫面也會左右我的心情和聽眾的想法。當然,我所說的內容都是一樣的。
然而,即使我想保持客觀,也不刻意避免主觀,但描述北京國家大劇院對我來說仍是一件困難的事。如果現在和將來,它真的如我所願成為建築上的里程碑,每次我對它的描述仍會不同。這對我或別人來說,都是一樣困難。現在這樣,將來也是這樣。好比面對一個有機體,大家很容易對各個部分有一致的認識,但永遠無法真正瞭解各部分的侷限,也不知如何區分各自的功能。
但既然一定要對這個建築描繪一番……
北京國家大劇院的穹頂下有一個歌劇院、一個音樂廳和一個戲劇場。每場演出或音樂會都是大眾與藝術家見面的機會。觀眾穿過花園,走過水下長廊,就會來到圍繞著所有表演廳的公共大廳。藝術家則在一個龐大的地下世界為演出做準備。那裡有包廂、彩排室、錄音室、商店、化妝間和服裝室供他們使用,接著他們走上劇場、歌劇院的舞台或交響樂池。地下世界中最神秘、同時也是最基本的,就屬這個演出準備區了。
大劇院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公共大廳。這是大家津津樂道的部分,至少它看起來色彩繽紛、明亮,又令人感到舒適。
構思大劇院的內部設計是最嚴肅、最令我緊張、更是最要求精確的部分。每次我待在後台看彩排時,我總是非常欽佩藝術家和機械師精準無比地控制時間與協調彼此的動作。每次我都和自己說,我必須同樣精確地規劃空間,而且這種規劃將會對演出有所助益。規劃是先源於一個主要的概念,但更多是來自於大眾永遠不會注意到的一連串微小細節。對於不知道一場演出是怎麼產生的人來說,這種說法可能聽起來很可笑而且荒謬。但每當我因為承接公共空間設計案而疲憊不堪時,都是想到建築中被人忽略的那份真實需求,才重新找回了力量。
但是該如何介紹這些為演出做準備的場所呢?它們多樣,功能各異,不可或缺,但要如何解釋它們的運作?一一解釋設施嗎?光用幾個字是沒法做到的。我也不知道該如何用所有必備的細節來介紹。其實與公共大廳相比,這些為演出做準備的場所更是整體團隊合作無間的地方,得集合各種不同專業技術,並互相銜接。總之,這些部份和表演的創作密切相關,也許不要說得太清楚比較好。不管怎麼說,演出常常是在黑暗中開場的。
另外,也許劇院建築師最重要的任務是幫助觀眾盡可能靠近這個黑暗的邊緣,等待一線光亮。我不確定「幫助」這兩個字是不是恰當,但是我找不到更合適的字眼。
我可以確定的是,建築師永遠不該試圖撩撥觀眾的情緒或消弭觀眾原有的情感;他也不該利用建築來傳遞某種訊息或觀點;他不該像我常聽到的是「觀眾的導演」,或者更籠統地說,他也不該是建築的使用者。其實除了功能之外,建築並不是中性的,或者說不應該是中性的。相反的,建築一直都和其他藝術一樣,是為世界增添一個生命,每個人都會看到,都會詢問,都會想去瞭解它是什麼,甚至它是誰。一個建築首先應該是有用的,具有保護功能的,然後才可能來啟發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力。
三、鴨蛋
建築一旦出了名,往往就會招來譭謗與讚譽。尤其是那些引人爭議的、讓人關切的重要建築,總少不了綽號。綽號能恰當地表達贊許或反對的情緒。有些綽號拙劣且不懷好意,有些則恰如其分又幽默。戴高樂機場的第一航站大樓被稱為卡曼貝爾乳酪 ,我就覺得很好笑。有段時間大家還稱龐畢度中心為「管道教堂」。當有人替建築物取幽默的稱呼時,也是一種對建築物本身優點和成功的贊許。
國家大劇院的綽號太多了,我知道其中一些:鴨蛋、水母、牛糞……
最後一個綽號「牛糞」,是一些優秀的知識份子創造出來的,但他們的出生地和職業都離牛屁股遠著呢。我不想自誇熟悉庇里牛斯山地區的鄉村。不過,因為家庭的緣故,在戰爭快結束時,我曾住在法國西南部的蘭德斯省(Landes)。雖然後來我也曾待過別的地方,但都沒住那麼久。到現在我都還能清楚記得牛糞的形狀、堅硬程度和氣味。在乾燥炎熱的夏天,牛糞由外往內變乾,並在不斷傾盆而下的大雨中被沖散。我雖不是牛糞專家,但至少相當瞭解牛糞。我敢說大劇院的樣子實在不至於令人聯想起牛糞。散播這個比喻的人,既缺乏常識,而且用字低俗。如果他們的目的只是要讓人聯想起糞便,那又為什麼不說得直接一點,讓同好者更熟悉,獲得共鳴?
「水母」這個綽號沒有造成轟動,甚是很可惜。水母在水中有著漂亮非凡的曲線,行動緩慢而優雅。不過取名的人是想強調這座建築的外形令人想到水母擱淺死去,然後被埋在沙灘的畫面。這是那些從未離開過海邊和海岸的人最熟悉的水母。
比起其他綽號,「蛋」這個稱呼,會更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而流傳下去。
不過,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強調是「鴨」的蛋。我很少看到鴨蛋。大約六十年前我吃過鴨蛋,只記得鴨蛋殼帶青綠色。
說到底,所有的綽號都只是在外形上大作文章。「它好像……」這是世人解讀事物的方式,我覺得很無聊,因為一點意義也沒有。我記得有一回在中國參觀一個岩洞,形狀各異的巨大鐘乳石和石筍附著在岩壁上或者突出來,導遊把它們比喻成各種稀鬆平常或著名的事物。這是象鼻,遠一點的是駱駝,那些是竹子,那是城牆等等。沒有驚喜,沒有新奇,完全失去獨立的美感以及令人驚訝的特質。把世界縮小成你知我知的小小天地實在太可怕了!若是我們能承認自己無知,也願意表達探索世界的意願而參考抽象的概念,那就好了!儘管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度過不少時光,但是我們知道就只一點皮毛而已!
不過時間越久,我越喜歡「蛋」這個綽號。
至少就兩點來看,這個綽號是合理的。
從力學上來說,穹頂是一個「蛋殼」,像蛋的殼,它的力量和抵抗力來自它的連續性和雙曲弧,表面壓力也被分散了。不論誰想壓破夾在雙掌之間的蛋,一定知道得花很大力氣才行,我當然也試過。相反的,想把蛋殼的任何一個碎片壓碎根本不費吹灰之力。
最初我們在設計這個建築時,並非沒有考慮到這個均勻的殼。在最後一輪或倒數第二輪的競標中出現的穹頂,是由三個部分組成:玻璃棚頂及兩側的蛋殼。整個穹頂由纜繩系統和兩側蛋殼的支撐杆加以穩固。來自建築上層重量的壓力會被兩側的蛋殼分散。可是在我們獲選後,當得知考核工程與完工的期限時,我們發現不可能在要求的期限內妥善建完這樣的建築。我們必須找到另一種設計樣式,既保留建築的特質,又可將計算和建築工程簡化。通常,有制限的條件與追求更經濟的效益──當這兩項是建築師一致
同意的美德,而非貪戀權力的無知者毫無道理的政治決策時──可以引導出更明智、更合乎實際的解決方式。新的解決方式是整個外殼結構,有的部分是單層玻璃外殼,有的部分是雙層外殼,外層為金屬面板,裡層是玻璃和木板。這種構想使得整個龐大的結構變得比較輕盈,幾乎只比艾菲爾鐵塔重一點,而且非常牢固,非常經濟。
我想「蛋」的比喻,如果從被穹頂包覆與圈住的角度來看,會讓人更覺得貼切。
複雜的生命,以越小的刻度來測量就顯得越大,蛋的簡單形狀所包含的也是這個道理。大劇院形狀的純淨、精密和準確也是如此。隨著生命的開展,它所能夠發展的比想像的還大。生命有其已設定的功能,也有其可塑性,可以隨著時間去適應環境的變動。生命是連續不斷的曲線,無窮無盡,令人暈眩,一旦捲入其中,就融入這個弧線裡,隨其擺動,唯一希望的就是打破保護最初成長的殼,然後自由成長,走向世界。這些年來,我抱持著這個願望生活和工作,大劇院也有這般的生命,就像所有的生命超越了我的想像和願望。
再回到形狀這個問題上來,既非牛糞也非水母,也不是鴨蛋。它有一個非常精確的數學公式,與其把這個公式看成是什麼了不起的發明,不如把它當成一種讓人好奇的東西。這是一個「超橢圓形」。它的公式是 (x/a)ⁿ + (y/b)ⁿ + (z/c)ⁿ = 1。
在競標的最後階段,有一天,我在建築工程簡報會議上,在黑板上寫下了這個公式。我這麼做並非為了增加說服力,而比較是為了自娛。在選定由我們承接標案之後,過了一段時間,有人通知我說,上層官員想要知道設計的定案內容。我希望當時已經正確寫下公式,但我不太確定係數n是多少。我的合作夥伴都知道我常常忘記係數的確切值:2.4。 這個數值沒有任何意義,而且會被那些不是專家的人忽略。在經過許多試驗後,我們找出這個數值,而這個數值會賦予這個建築物緊繃的曲線,不會因為距離近而看起來軟弱不振,不會像「一團靠近火的奶油」。
為什麼會選擇超橢圓形呢 ?因為多年前我在《美國科學人》雜誌上讀到一篇關於超橢圓形的文章。最先使用超橢圓形的人是丹麥的皮耶特•海姆(Pietr Heim),他曾經設計過一個位於斯德哥爾摩的廣場,我不知道這個廣場如今是否還在,只在雜誌上看過照片。超橢圓形出現在各種東西上,如煙灰缸等。我設計過一張藍色的超橢圓形桌子。僅此一張。它非常長。而大劇院將是我的第二個,或暫時是最後一個擁有超橢圓形嚴謹之美的作品。
希望大家不會以為我們僅僅滿足於從數學得來的簡單公式,甚於聽憑偶然獲得的靈感。每條路,不管是在空間的或思維的,都一樣艱難。之所以選擇某條路並非為了方便,而是為了美感,或對隱藏其間的簡單性深深著迷。因為重要的是路程,而非目的。
是蛋嗎?當然不是。它是一個簡單、經過設計的形狀,藉由水中的倒影形成一個完整密閉的形體,散發謎樣的氣息,吸引來此欣賞音樂的人,或被莫名慾望驅使前來、卻不所求而又執迷不悔的人。
算了,所有的綽號都是好綽號,有趣的綽號才會吸引大家想來親眼看看。
另外,多虧了電腦網路的存在,我最近發現超橢圓形也叫做「拉梅曲線」,這是由1818年研究超橢圓的法國工程師和數學家命名的。
一、2005年6月1日白天的雨洗掉了沙塵,夜色一片明淨。南面水池的石板基本上算是完工了。我等待這一刻已經很久了:池水平靜下來,第一次能夠看見穹頂在水池中的倒影。當我在設計柱子和穹頂時,就像以前在美術學院學的,我並沒有將穹頂限制在對稱的水平面上,而是將曲線往垂直面延伸了一小部分。我只知道早在古羅馬時期就有過這樣的設計。這座橢圓形建築物是否能如我們所期望的,給人拔地而起、卻不孤單薄弱的感覺呢?這是我第一次可以這麼具體地評論它。當然,我們之前繪製了很多設計圖,包括正面圖、剖面圖,以及透視圖,但這些設計圖只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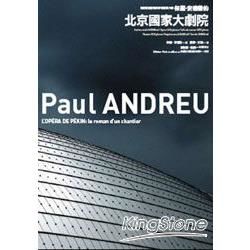
 共
共  安德魯,在希臘語中為安德烈,在日爾曼語中為安德斯,暱稱為安迪。
安德魯,在希臘語中為安德烈,在日爾曼語中為安德斯,暱稱為安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