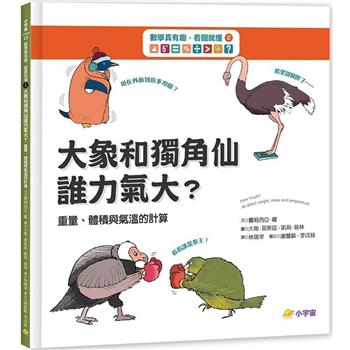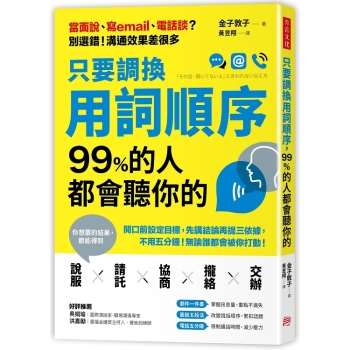宗教的動力心理學是一種臨床的、精神分析的心理學
普呂瑟結合心理學與宗教學的理論,包括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奧圖的現象學、自我心理學、英國的對象關係理論,再加上神學及社會/文化研究的基底,融合為他所稱的「宗教的動力心理學」。
普呂瑟不同於多數宗教學研究將焦點限於禱告、密契主義、崇拜、起信、宇宙意識等概念之發展,他則是使用規範式的資料或臨床觀察,配以適當的連貫性,將神學命題視為宗教概念形成的產品來評估,並把宗教生活中不明顯的或尋常的特色都放入解說的範圍。他以臨床的、精神分析的心理學,結合文化心理學、詮釋學,和深厚的宗教現象學知識。
在本書《宗教的動力心理學》中,普呂瑟引述的神學,除了對《聖經》的詮釋之外,還有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代諸多神學家的作品。而最重要的則是近當代新教神學──幾乎都是宗教現象學觀點的──包括士萊馬赫、齊克果、奧圖、田立克及海德格等。他把這些宗教現象學的觀念拿來和動力心理學互相比較,或作交叉詮釋,使得他的心理學與宗教哲學之間互相發生了相當平衡而帶有高度啟發性的意義。
作者簡介:
保羅‧普呂瑟(Paul W. Pruyser,1916-1987)
1916年誕生於荷蘭的阿姆斯特丹,1946年畢業於阿逢文理中學(Avon Gymnasium),之後進入阿姆斯特丹大學攻讀心理學。由於戰後歐洲社會情況殘敗,他們一家移民至美國。1953年他在波士頓大學拿到心理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在波士頓期間,他已經開始在波士頓州立醫院以及波士頓兒童醫院擔任臨床心理師的工作。1954年受聘到堪薩斯州的托皮卡州立醫院(Topeka State Hospital),兩年之後他成為梅寧哲基金會(Menninger Foundation)的成員,1962年前後則開始擔任該基金會教育部門的副主任,而主任就是卡爾‧梅寧哲(Karl Menninger)本人。後來他升任該基金會的「科際整合研究學程」主任,並獲頒「精神醫學研究與教育」的Henry March Pfeiffer講座教授榮銜,直到1987年他逝世為止。
除了臨床心理學的實務與教學訓練之外,他同時還在托皮卡市的第一長老教會擔任過幾年的長老,代表過該教會參加全國教會理事會的委員。也擔任過一屆「宗教的科學研究學會」會長,以及The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和Pastoral Psychology兩種專業期刊的編輯諮詢委員。他曾得到美國心理學協會(APA)第36分組的Bier Award和美國教牧諮商協會的傑出貢獻獎。
譯者簡介:
宋文里
天主教輔仁大學心理系專任教授。1985年取得美國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教育心理學系諮商心理學組(Division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博士,1993-1994年間於美國哈佛大學宗教研究學院(Divinity School)進行博士後進修。學術專長領域為文化心理學、藝術心理學、文化的精神分析、宗教研究、批判教育學。著有〈「迷信」與「空虛」:關於大學生超自然參與經驗之意義病理研究〉、〈以啟迪探究法重寫碟仙〉、〈負顯化:觀看借竅儀式的一種方法〉、〈物的意義:關於碟仙的符號學心理學初探〉、〈創真行動:閱讀史瑞伯的一種他者論意義〉及〈天佑美國:一則爆炸性的政治神話〉(合著)等論文。譯作包括Carl R. Rogers的《成為一個人》、Edward O. Wilson的《人類本性原論》及Jerome Bruner的《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學的觀點》等作品。
章節試閱
第二章 宗教中的感知歷程
現象學家們愛說:透過感知(perception) 人才能關聯於世界,而人和世界的雙方在感知活動中都是主動的參與者。世界對於感知者「會打開」或「給出其自身」;而感知者則「如實取得其所見、所聞、所觸」且由此而將世界變成他的世界。這個命題看來實在夠陳腔濫調,也太自然而自明,以致讓人忘了其中對於感知的態度帶有多麼積極的意謂。感知對於人和自然來說都是受到歡迎的機會,這雙方也因而得以知道彼此。
對於感知採取這樣歡愉的態度,可不是每個人都能享有的。極多的人所受的教育是要不信任自己的感覺(senses),以及感覺所揭示的世界。很多宗教運動都對感知有深深的偏見,並宣稱感知會帶人去接觸一個「錯誤的世界」,並且感覺就會把人引入肉欲橫流之中。這種消極的態度有很多樣的形式。這種調子可能像是《傳道書》作者那樣,認為感覺或感官化都是虛空。也可能像柏拉圖主義那樣,認為感知所得的世界帶有脆弱乃至容易蒸發的性質,在其中沒有任何事物是可以恆久的。另外還可能像斯多亞學派(Stoicism)那樣,強調感知世界的無益,而如這般的態度就使得巴特勒(Samuel Butler)宣稱:生命就只是一段漫長的疲倦歷程。有些信仰體系甚至主張:感知不只是淫佚、虛華、不穩、無用,還實際上是錯誤且善騙的。心靈要求的是真實的麵包,但感知所給的卻是不能消化的石頭。
對於感知的另外一種態度,有個例子是用三隻小猴子各自掩蓋住眼睛、耳朵和嘴吧,以表示牠們沒看見、沒聽見或沒講出邪惡。在這樣的評價中,不是所有的感知都應阻擋或禁止,而只是其中「邪惡」的部分,因此,只要能遵守一些道德的基本原則,選擇性還是有希望的。但關於「好感知」、「壞感知」的道德知識會投射回到人類的猿猴祖先身上,就暗示這種想法實係源自對於感知的古老禁忌。確實的,我們有很多證據可說:古代人和現代人實在不像現象學家那般樂觀地認為人和世界可以在感知的動作中和諧一致。打開你的眼睛,你就可能會看見恐怖的事物,讓人畏怯的景象,危險的存有,甚至看見神本身!人可能在風中聽到鬼魅和精靈的低訴;你的手可能摸到什麼一溜而過卻無法抓握的東西,因而認定那是來自某種陰幽棲息地的怪物;一陣氣味飄來,也可能暗示某種不可見的魂靈降臨身邊。甚至有些原本看來清晰穩定的東西,譬如天體,也會開始有詭異不祥的運動。自然是既可親又恐怖、既吸引人又令人排斥、既可以信賴又令人狐疑的。感知讓人接觸到奧秘之物,不論它是聖或非聖,是善或邪惡。正因為看乃是對於被看見的實在之參與,所以感知動作本身就可能會被人當作本來含有奧秘性,充滿巫術性質和有力的能量,還會帶來可怕的後果。採取這種觀點的話,感知歷程就必須要由禁忌和宗教儀式來加以節制。在西奈山上的摩西不准看到神;修女的帽套所造成的像是一種隧道視覺(tunnel vision),其功能比較多的是排除性而不是收納性;即令在今天,有些墨西哥印地安女人還是不能用眼睛瞄她身邊經過的男人。
在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感知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一書中,你可以看見對於感知的第四種態度。也許可以描述之為一種把感知提升到超過慣例辨認之上的企圖,譬如不只說「這是一間房子」、「那是一棵樹」,而是達到靈感充沛的、詩意的、對於本質有移情的肯認,譬如讓人能說出「世上沒有一個地方像家一樣好」,或像詩人里爾克(Rilke)那般說「真的,你就是那樹」。這種觀點所主張的是感知更新,而它的前提是:通常的感知實際上只是衰退的感知,以致變得功能不足。這種觀點背後也有很長的宗教史。在要求感知有最高限的澄澈性之時,也設定了澄澈性乃是「真正的真實」之標記,而這正是宗教人在團體中,或在獨處時,竭盡所能要達到的感知提升。透過身體的動作、節食的實驗以及呼吸、體態、舞蹈的調節,透過吸入迷醉物質、睡眠的剝奪、曝現在有毒刺激物之中,透過沉思默想、有節奏的叫喊和擊掌,這世界上許多虔誠獻身的人就這樣嘗試著要改變他們通常感知的敏銳度,想要臻至一種光明的狀態,並能在其中說:「看哪,我把一切事物都更新了。」
然而,這種光明澄澈的視覺還不是至美至善的境界。擴充心靈的澄明、加速時間感的流動,和伸展空間感知的座標,都是很能讓人著迷的演練,但這些對於對象的選擇都還是漠不關心的。假若澄澈性就是其目的,那麼,任何客體、對象或刺激都行:一朵玫瑰、一顆寶石、一瓶墨水、蜂蜜的香味、或雙簧管吹出的升F大調。可是,但丁要見的只是貝德麗采(Beatrice), 而偉大的密契者們要見的則是他們所欲求的神。在融入萬物創造或與萬化合一,以及和創造者面面相覷,這兩者是有區別的。前者的特徵乃是在感知者和他的世界的某部分之間有同儕關係,而後者則是權力不相稱者之間,一方仰賴著另一方的關係。在這樣的觀點下,你想要分享的乃是他者所具有的大自主性。在這種對於神靈的密契感知中,對象的價值才算是一切,而不是感知者的敏銳度,雖然後者是不可忽略的。不論想要的對象是什麼:貝德麗采、耶利米(Jeremiah)的上帝、童貞馬利亞(Virgin Mary)、或酒神戴奧尼索斯,密契的愛者至少有兩條敞開的路徑供他遵循。他可以朝向與對象的絕對統一,因而犧牲他自身和對象的種種認同;或者他可以努力追求最直接的面面相對,在其中的愛者與被愛者都維持著各自的認同,但形成一組雙人舞。那些尋求統一的人是單元論者,他們不耐於所有的差異,而那些尋求面對的人則是某種的二元論者,他們也許認為很多差異都是淺薄的,但最尊重的差異是在於終極者(the ultimate)與偶隨者(the contingent)之間。
很明確地說,感知在宗教的角色中有個值得注意的面向,就是說:感知這個動作本身就已被宗教作出評價。我們發現感知會受到鼓勵或不鼓勵,會被磨尖或搓鈍,會被昇揚或阻梗。它會被儀式化,或被歸入禁忌和限制。它會是承載崇拜的工具,也可能會因為它對於虔信有所威脅,而不准在崇拜中發生。它會被視為神聖,也會被視為妖魔。
因此之故,宗教心理學的要務之一,就是對於感知歷程如何進入宗教體驗之事,進行探索和描述。雖然我希望不要在潔癖的要求中誤入迷途,但我仍有個目的,要把林林總總貼近於宗教的感知體驗作個速寫。從簡單的感覺到複雜的感知歷程都值得我們的注意,因為就如我在第一章就已指明的,我們對於宗教的操作定義廣佈在一道長長的光譜上,由簡單到繁複,由可笑到可敬,毫不偏誤。
視覺
對於「視」這個字所指的感知歷程,及其宗教的意義何在,有個擲地有聲的論點是說:除了指視覺之外,它還用來描述一些根本不含視覺歷程的體驗。所謂「有識(視)之士」指的是一個很有想像力的人,有能力產生前此無人見及之事。在「璜‧迪亞哥以靈視見及瓜達魯佩的聖母」這句話中,所指的是一個鮮明映射的意象(image),但旁觀者卻無法看見。一位「先見者」其實是個預言家,或是個先知,他宣說了即將到來的事。聖徒在報告他的靈視之時,正是「看見了」眼睛所不能見的事。有些僧侶、薩滿(shamans)、國王和平民從古至今都曾把夢境描述為「所視」。類似於此的是在男男女女身上出現的各種顯靈都發生在沈睡或昏迷中——也就是視覺機制失去功能的時刻。
在這些關於「視覺」一詞的密集運用上,都帶有奧秘的性質,其中指涉的是在體驗中的偉大、有力、或不尋常。也都涉及了神聖物之被凡人瞥見,而有時瞥見者還是閉著眼睛的。這些靈視也許是至福之見,也許是恐怖之見,但總之就是不可名狀。有時它會被描述為啟示,很特別的啟示,其所啟示者確是睜眼難見的。不論是在感官之外或屬超感官的,其超越尋常所見和超越腳踏實地的現實考驗,而臻至形上真理的特殊視覺,都必須歸給宗教來作評審和鑑賞才行。這種靈視體驗之強度,不論其內容為何,對於所見者而言,其力量與其產生的情緒之深刻,對於幾乎任何文化、在任何時代,都具有宗教上的顯要意義。
但是,把這種體驗的強度或希罕和宗教對等起來,這樣的等式卻可能帶有欺矇的義涵,或是可憎的後果。它有可能使得凡夫俗子又是作為信徒的我們而言,在日常所見之上製造了蒙蔽之效。一個人但凡從街上走進任何崇拜的場所,都會注意到在環繞的光線之中好像有些什麼事情發生。室內環境通常比較幽暗,至少在入口之處是如此,當他再繼續往裡走近聖殿時,他會看見室內有些地方安排著特殊的照明效果:神龕、神像、講壇、或滿是裝飾的牆面,被精心安置的窗戶或投射燈光、彩色玻璃而來的特殊光線所照射。有時教堂內部不是比較幽暗,而是比起平常的光線更充滿五光十色的燦爛。在某些崇拜的禮儀中,照明效果會跟著禮儀的內容而變化:在禱告時光線稍弱些、在講道時光線投注於講道者、在聖餐禮時整個建築物都瀰漫著幽暗的色調。這些光影變化當然是無止無盡,有時也會遵循歷史的來龍去脈,譬如從古代的太陽神崇拜到條頓民族的林中空地儀式,從山頂的祀典到地下洞穴的祭拜儀式。既然神祇在傳統上都要安置在高地或地下,則光線本身就具有宗教的價值,也會被各個不同的信仰體系加以儀式化。於是隨著光的價值,睜眼、閉眼、瞇眼的動作,或凝視、敞視、仰視、俯視等等都會獲得宗教上的意義。
根據新教的老生常談,略帶貶義地說,天主教彌撒就是一場「養眼的盛宴」。作彌撒的風格形式在各教堂會因國家文化的差異而變化,但對於大多數新教徒來說,其色彩之豐富倒是真的可觀:在窗上、牆上、在雕像、在教士和典禮助手身上的衣袍,還有崇拜所用的種種物品上的紋飾,以及天花板、地板上的馬賽克,在在都是如此。衣袍上的色彩遊戲隨著典禮主事者的姿態而變化,教士在聖壇上經常轉動身子,創造出一種視覺印象的集合,很像在市集上看農民身著土著衣冠所做的舞蹈表演:色彩不斷跳動、變換、旋轉,讓眼睛也專注於這種恆常的運動狀態。真正讓人心醉神迷的視覺刺激就這樣連番轟炸著崇拜者,其中有很多人不但學會將各種物件連結起來,有些人甚至把色彩本身連上特殊的宗教意義。神聖禮儀的色彩有各個季節和各特定場合的不同:紫色、白色、綠色、紅色、黑色、粉紅、金黃,每一種都應使觀者激起某些可知的反應。在整個聖壇之中還有特殊的光出現:燭光在整體的光照中佔有一席特殊的地位,除了增加特殊的色澤之外,還為靜態的整體環境添上鮮明的運動感和刺戟感。
乍看之下,這個養眼的盛宴和古典的新教崇拜場所之中清靜、冷冽的色調構成十足的對比,特別是在美國和西歐的清教教會中。清教徒們拒斥了天主教崇拜中的色彩,並把一切的調子都用白色、灰色和黑色使之黯淡下來。水洗牆、橡木斑或漆白的座椅、穿著學院式黑袍的教士,頂多是書邊上染有摩洛哥紅的聖經,打開放在講桌上,而那是唯一能夠養眼之處。事實上,清教徒的眼睛被設定為不可停留在任何怡悅的顏色上。他的耳朵應該聆聽,為此之故,視覺印象必須受到嚴格的限制。甚至在衣著上,清教徒也必須降低其彩度到剩下黑白,因此前來參與教會聚會的人只能用衣著的材質和裁減工夫來勉強看出他們的地位差別。貴格會教徒(the Quakers)是拿清冷的環境來作為密契的、內在之光的訴求。
在西方世界兩種崇拜形式的基本感官歷程上就有這般驚人的差異,實在是因為對於感官的宗教價值及其功用作了不同的評價。當這些差異日益風格化並且在信徒之間一代又一代地重複實踐之後,就會跟進一步的宗教聯想和價值判斷產生了當然的連結。眼睛似乎特別受到天主教傳統的偏愛,而新教傳統則偏愛耳朵,雖然兩種傳統對於多種感官刺激的用法都還不少。視覺在天主教傳統中較常被人陳述,或至少比新教傳統更受到青睞。天主教禱告時較常睜著眼或眼睛盯著聖壇,新教的禱告則較常是閉著眼的。我記得以前有一次暑假在荷蘭一個老漁村的新教教會中禱告,你可以看見,那裡的人在禱告時是把帽子蓋在眼睛上,顯然是要在漫長的禱告過程中,把不意闖入的視覺場域給完全遮蔽。
我的要點是說,在一個既定的傳統中,你不但學會抬高自己的這個風俗習慣,也一定會把以負面的方式看待其他習慣。在新教的改革派主流中,天主教或安利甘宗(Anglican )對於感官的偏愛即是縱情、世俗、奢華、驕慢、乃至邪惡的。對於天主教徒和安利甘宗信徒而言,喀爾文教派(Calvinism)的偏好則是黯淡、苛薄、貧乏、重智、便宜行事。神學作品有很多是意圖要將私人立場予以理智化,而在已經言宣的思想和實際作為之間,會有些風格出現,在其中,這些看起來簡單而中立的心理歷程(譬如感覺、感知之類)也會沾上複雜的宗教意義。
在教堂的室內採用彩色玻璃窗來照明或遮光,在有組織的宗教之中,已經是個極其複雜的名堂。我不知它的起源何在,但我猜想這種沒有特殊形式的五光十色表面,其使用方式應該和人們欣賞寶石的方式很類似:就為了作為光本身的遊戲。但它終究變成一種富有教導性的物件,讓缺乏文化識能的信眾也能而明瞭他們應該知道的信仰內容:透過象徵或具體描繪的神、使徒和聖徒的畫像、耶穌生平的故事,等等。它們也可以描繪信眾本身的生命:他們的領袖、教會建立的故事、過去成員的回憶、慷慨捐贈者的紀念碑、再劃上家族的樹狀圖譜,還有各種有關社會地位的附件。有些母題具有高度的象徵性,有些則具體得不得了。有了這些輔助性的目的,就會使得一扇窗子不只用來聚光、散光,而是純然作為視覺聚焦之用了。有此之後,窗子也會變成一種沉思冥想的對象。在崇拜場所的光效之歷史就以此方式轉了一整圈:從開頭的工具性用途,經過再現的目的和高度象徵性,到末了甚至成為形上意義的中心。
當你能記得宗教語言中有多少光明和黑暗的喻示,則意義的這種演化或週期起伏現象就不特別奇異了。愛色尼人(The Essenes)就自稱為「光明之子」,並且期盼他們和「黑暗之子」之間會有一場啟示錄般的戰爭。神和光之間的連結非常古老,並且流傳很廣,其本身也超過日月崇拜的階段而維持下來。Sol Invictus(無敵太陽)的主題在某些基督教會中仍然使用;用燭火作光的奉獻也仍然保留。在神和聖徒的頭部用光環來裝飾,也是教會的教學輔具或再現藝術中所常見。文藝復興的繪畫每當涉及神這個不可見的造物主時,會在圖的邊緣用射出的光線來表示。
光之為神聖,是希伯來的創造神話中所描述的第一個動作,而它只要翻個身就會變成神聖的眼睛。神可被描繪為無所不見之眼,而人類的眼睛在浪漫文學中就用來證明人類的永恆尊嚴,或人類靈魂之具有神性的根源。然而人的眼睛所具有的奧秘性質也可使之取得負面的價值,譬如「邪惡之眼」。
但人眼不只是看見光譜上的顏色。它還是組織和辨認空間的器官。而空間也有極為繁多的宗教意義,可以安排或儀式化為崇拜空間、神聖場所、階層化的空間秩序,讓人能因此知道他在宇宙中「所在的位置」。一些空間的基本向度,譬如「高」和「低」,「右」和「左」,「在上」和「在下」都充滿宗教的價值,並且在教堂建築中以潛在的框設來表現,成為許多文化風俗的基礎。
比較宗教的研究者們總是反覆指出神聖空間在古代和當代宗教體系中的重要性。空間之為神聖,在各文化和各實際的環境中會有些變化,但無論如何,你總會發現在部落或村落附近有一塊封鎖起來的區域,當地群體的宗教生活就以此地為中心。這裡和「塔布」(taboo)一詞的基要意義連在一起:這是一塊禁地,不許任何逾越。這種場所,或在其中的物體,是帶有「魔那(或魔力)」(mana)的。這個地方是奧秘空間的中心,其中住有神,或每當神降臨時,就來到此地。神聖空間可以是某些山川、草原、林間空地、谿谷或洞窟;可以像一塊岩石的切口那麼具體而特殊,也可以像整片天空那麼廣闊而無垠。假若你特意觀看的是古代或原始宗教的話,空間的奧秘性質之基本形式是很容易辨認的;但你可能忽略了就在你我之間的當代宗教裡,也一樣有此。每一個崇拜的場所都可為神聖空間的存在作證:從都會區的街邊聚會所,到最華麗的哥德式大教堂,從國家公園裡保留的崇拜場所,到最現代的教會建築物。
對於空間的精心運用,且完全意識到空間所具有的奧秘性,其最佳範例是在明尼蘇達州的柯理治維(Collegeville)鎮上,由布洛以爾(Marcel Breuer)為聖本篤會所建的聖約翰大修道院(St. John’s Abbey)。從老遠之外,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巨大的水泥鐘塔,活像個凱旋門。你從它的底下往上走幾階,上了岩石的平台,打開教堂的門,走進一個狹窄、幽暗、天花板很低的空間,迎面碰上施洗約翰的雕像,他的姿態讓你覺得好像他在邀請你往下幾階,走進受洗池。在往下之時,不論你的視覺上或就字面意義來說,就是在走向另一排開向聖壇的門戶,然而在實際向前之時,你首先會通過一片低垂的大陽台,其遠端突然開向教堂的信眾席位,又高又寬,被大開的窗戶照得光耀無比。在這建築之內,空間的安排就是為了神聖禮儀的最大方便,你在穿越這裡之時的感覺,就是沉潛和奮起,收縮和舒張,忽暗又忽明。我的要點是說:像這樣的視覺空間體驗,其實在任何集體崇拜的安排上都屬內在的需要,不論在建築物下游的效果上是成功或不成功,是有意或只是將就。
為崇拜而做的安排大部分都是空間安排。而私人為禱告所做的安排也是如此。就宗教而言,空間有階序和層級。在人和神的交往中,層級可以清楚辨別,也有一定的樣式。教士可以比普通百姓站上較高階,這是指在神壇上工作時,或在各種典禮上的站立之處皆然。人民會留出某些空間給教士以及他們的神,留給自己的地方則比較狹窄些、低下些,這樣似乎比較適合芸芸眾生的位置。
崇拜用的屋宇,在建築設計上,會為動力的宗教行動所當發生之處創造出一個空間的焦點:神龕、講壇、洗禮盆、貴格會會議屋的中央空地等等。關於天主教儀式中聖壇的正確位置,已經產生無止無休的辯論:是要擺在正中央,好讓所有的人可以在四周面面俱到地看見它?還是應擺在教徒席的前端,讓會眾只見到它的正面?應該把它放在禮堂的講台上,讓它高高在上?還是應該放在與會眾的坐姿一般低的位置?類此的爭辯也被帶入新教的崇拜:聖餐禮桌的理想位置應在何處?甚至在佈道時,講壇的高度和場所應如何調整?高度本身在哥德式大教堂是極受頌揚的,而讓人向上仰視確是哥德式建築藝術裡最具支配性的空間主題。但凡參觀過墨西哥的條提華坎(Teotihuacán)廟宇遺跡的人,一定難忘阿茲鐵克(Aztec)儀式在空間區分上那種水平線條的絕對支配性,更遑論該金字塔的高度如何,它的石梯有多長,以及它的頂端安置有什麼圓錐體。在此一視界中,最具支配性的是邊線,最重要的線條是水平,最有掌控性的結構則是梯田般的平台。
在禱告中,人們受到的教導是把臉朝下,那麼誰敢昂首?在傳統中禱告者應該跪下,那麼誰敢站起?對於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當他在從事宗教動作之時,他的眼睛要向上看或向下看,是得聽從於儀式的。任何有違於常規的舉動乃表示了自由主義、自由思想、抗議,或甚至藐視。在晚餐桌前,所有的人都在「低頭」,除了趾高氣昂的年輕人之外,這在儀式化的空間向度和奧秘氣氛之中,總是帶有膽大妄為的調調。而終有一天,年輕人「也會屈膝下跪」的!
再說一次,宗教語言中充滿著空間喻示,用來描繪神與人的實在面貌。神高人低,或說,人本是卑微的。神聖智慧深不可測,人與之相比就是淺薄且不在同一平面上。神會讓一些聖徒在他的右邊,而那些受詛咒者則放在他的左邊,乃至丟入地獄。虔誠者會相互勸勉,以便揚昇他們的心靈,或者會仰望救贖所來之處。《新約》作者們的三層宇宙中,人、神和魔鬼是各據一層。在面對這種特異的語法之時,你儘可以辯稱:所有的生命都住在空間中,而宗教的生命也無所遁逃於這一基本的實在。但這種反對之論卻漏掉了核心要義:宗教觀點之下的空間本身是奧秘,而空間的諸向度則是儀式化的,因此,空間感知和空間中的運動會有些規則和價值超過了物理上的必然性。空間的奧秘性對信仰者而言,是心理上的真實(psychically real),且必具有行為上的後果。它能決定殯葬儀式,並能設定殯葬規則,如葬在地下、地上、在支架上、在土墳裡、在金字塔下、或在拱狀墓穴中。它也決定埋葬的姿勢是直立的、或躺著的,是手腳蜷曲的、或四肢大張的。它還決定人的遺骸是要放在聖地裡,或放在開放的墓園,或要散在大地或海洋中。它決定所謂教會財產的觀念,並依此而得以免稅或享有某些地帶的特權。它又決定家裡是否能設有供奉的祭壇、雕像專用的壁穴、或什麼地方可以放置神像、十字架、或神聖經文。它決定了聖經是否要和其他家用的書冊一起放在書架上,或要放在特別的地方。它創造了路邊的祭壇、放置聖書聖卷的神龕、以及為了作沉思冥想,那是要安排成自然或人為的環境。空間的奧秘性逼著人去站著、坐著、下跪、或匍匐,它甚至教人該戴帽或脫帽。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視覺體驗,原則上都屬正常的感知歷程。即令有些時候會包含著許多象徵作用和種種剩餘價值,它們總都是發生在適度的現實考驗和社會從眾性之內。那麼,非正常的視覺體驗又如何呢?而宗教的幻覺又怎麼說?在所謂的「靈視」上,不是充滿了宗教的非正常或邊緣的視覺現象嗎?我要把非正常的感知歷程先按下不表,到本章的後頭再說。我們應先談其他幾種感知樣式,譬如聽覺、味覺、嗅覺、觸覺等等,而這些也各有其正常與非正常的功能。
第二章 宗教中的感知歷程
現象學家們愛說:透過感知(perception) 人才能關聯於世界,而人和世界的雙方在感知活動中都是主動的參與者。世界對於感知者「會打開」或「給出其自身」;而感知者則「如實取得其所見、所聞、所觸」且由此而將世界變成他的世界。這個命題看來實在夠陳腔濫調,也太自然而自明,以致讓人忘了其中對於感知的態度帶有多麼積極的意謂。感知對於人和自然來說都是受到歡迎的機會,這雙方也因而得以知道彼此。
對於感知採取這樣歡愉的態度,可不是每個人都能享有的。極多的人所受的教育是要不信任自己的感覺(senses)...
作者序
「宗教的動力心理學」這門學問
普呂瑟把他自己的宗教心理學冠上個「動力(論的)」(dynamic)形容詞,他自己在序言中解釋說那是「一種理論導向的簡稱:即臨床的、精神分析的心理學,其中也包括了一些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的考量。」但是,讀完全書,你會發現他的說法對於自己的理路還說得不盡完整——它事實上還包括了精神分析在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之外的發展(譬如:英國的對象關係理論),再加上現象學的神學,以及社會/文化研究的基底。
我們可以把他的這套學問攤開來仔細瞧瞧,也許還可以進一步向我們的學界顯現一個事實——就是它到底可不可能融入我們的學院知識體系之中,變成可教可學的課程?
首先要談關於「精神分析」的問題。臨床/諮商心理學或更廣義的心理治療學(psychotherapy),其根本的濫觴之處本來就是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很多現有的心理治療理論和技法(technique)都是從佛洛依德那裡取得一些資源而後發展出來的。但在心理系的課程中,對於佛洛依德的討論實在太少——我們只要參看一種目前在網路上可以查閱的資料庫,叫做「精神分析電子出版物網頁」(Psychoanalytic Electronic Publishing, PEP Web),就會發現從佛洛依德之後一世紀以來,精神分析在世界各地的知識界有極為驚人的發展。但是包括美國和台灣的心理學教科書在內,我們的學科資訊和理解的落後程度簡直不是筆墨能夠形容。
美國曾經在二○年代開始歡迎佛洛依德,但是到了五、六○年代,受到各種保守主義(甚至包括「人本主義」)的影響而極力排斥精神分析。然而由於英文《佛洛依德心理學著作全集標準版》(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以下中文簡稱《全集》,英文簡稱S. E.)在七○年代完全出齊,有些人開始認真閱讀,到了七○年代末終於讀出很多心得,發展出幾種不同的「後佛洛依德」精神分析,譬如較早在英國發展的「對象關係理論」(object relations theory)、美國的「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和「自體心理學」(self psychology)、乃至更接近當代的「關係論精神分析」(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等等。這些人士在開始時曾公開呼籲要展開「重讀佛洛依德運動」。意思是要掃除五、六○年代各種保守主義的誤讀、誤解。這個運動發生時,美國已經建立了許多在大學以外的精神分析研究機構(譬如普呂瑟加入的梅寧哲基金會就是其一)遍布於美國各地,還向南北美洲,乃至向歐洲倒傳回去──當然在歐洲是以英國為基地向歐陸傳佈的。在這一波運動中,大學的心理系基本上是缺席了。
除了佛洛依德傳統之外,還有榮格(Carl G. Jung)的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 psychology),也因為英文版的《榮格全集》之發行,一樣產生了世界性的傳佈。再加上法國還產生了一種特別的「回到佛洛依德」運動,就是由拉岡(Jacque Lacan)為首的另一種精神分析,其發展態勢在知識界稱之為「如火如荼」毫不為過。這些學問在心理學系過去的課程中都只有蜻蜓點水般地略略提及,卻幾乎毫無迎頭趕上之力。
普呂瑟所使用的精神分析理論,從本書以及1974的那本Between Belief and Unbelief看來,除了仰賴古典的佛洛依德之外,他引用了其他幾位屬於佛洛依德傳統的作者,如普菲斯特(O. Pfister)、鍾斯(E. Jones)、賴克(T. Reik)等。他也很看重榮格和艾瑞克森(Erik Erikson),在此之外還不得不借用了一點自我心理學,因為當時美國的自我心理學在哈特曼(Heinz Hartmann)和拉帕波(David Rapaport)的領導之下幾乎構成了一種對於精神分析的壟斷態勢。然後他表現了對於英國對象關係理論更高度的興趣。如果我們以普呂瑟作為一個標竿,那麼要養成一個像他所具有的精神分析知識,在心理治療學的課程中其實並不困難。從譯者本人近年來的教學經驗來說,把古典的佛洛依德串接到自我心理學、對象關係理論(Object Relations Theory),乃至再接到1990至2000年間逐漸醞釀成形的關係論精神分析,在心理系的研究所課程中嘗試過幾次,都可以引發學生高度的興趣,所以,關於精神分析的問題,心理系的缺席確實不應再繼續了。
其次要談現象學的神學理論,或是宗教現象學的問題。在普呂瑟的傳記中,我們只知道他在基礎教育中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文,因此他曾經自行翻譯過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作者以拉司穆斯(Erasmus)的拉丁文作品,並且會讀希臘文的聖經。但除此之外看不出他曾經特別受過神學教育或專業訓練。也許就是博雅教育的基礎使他能夠自行作哲學思考,並且加上他作為基督徒的經驗,使他也會主動閱讀新教的神學思想。這可從他在年輕時寫過的幾篇哲學性的文章中看出,譬如:〈命運的觀念〉“The Idea of Destiny”(1959);〈現象學、存在主義心理學與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學〉“Phenomenology, Existential Psychology, and Psychoanalytical Ego Psychology”(1961);〈道德、價值與心理健康〉“Morals, Values and Mental Health”(1963);〈意志與意願的問題:選擇性的歷史概覽〉“Problems of Will and Willing: A Selective Historical Survey”(1967)等等。
在本書中,他引述的神學,除了對《聖經》的詮釋之外,還有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代諸多神學家的作品。而最重要的則是近當代新教神學——幾乎都是宗教現象學觀點的——有士萊馬赫、齊克果(Kierkegaard)、魯道夫‧奧圖(Rudolf Otto)、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等,還包括海德格(Heidegger)在內。他把這些宗教現象學的觀念拿來和動力心理學互相比較,或作交叉詮釋,使得他的心理學和宗教哲學之間互相發生了相當平衡而帶有高度啟發性的意義。
以上這樣的說明,目的是要讓讀者明白他的「宗教的動力心理學」並不只是和精神分析有關的心理學,而是摻有相當深厚的宗教現象學知識在內。然後,這就把我們帶回到宗教心理學如何可能在我們的學術界或教育機構中發生的問題。
心理學人文化與心理學的「學科承諾」
宗教心理學是人文心理學的一個例子。「心理學」這個詞彙放在任何知識脈絡中都會讓人聯想起它和各種人文/社會學科的關係,譬如和哲學、藝術、人類學、社會學、教育學等等。這是「心理學」本該有的內涵,但是,我們的心理學裡為什麼找不到這些東西?
2007年11月,我到河南大學參加「中國心理學會」之中的「理論心理學組」的討論,第一次在會上聽到好幾位報告者用到「學科承諾」這個字眼。他(她)們是在問道:「心理學的學科承諾到底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在台灣竟從來沒有人提過。「心理學」被定義為「科學心理學」,並且還是科學之中狹隘的實證主義把心理學知識完全綁架住,這就是我們的心理學在絕大多數的大學心理系中不證自明的前提。但是,這種綁住的狀態是知識界的共識嗎?我們的知識界,也就是知識份子們的活動場域裡,到底有沒有心理學家的參與?從前在楊國樞先生意氣風發的年代,他曾被視為某種的「青年導師」,只不過,奇怪的是,在作為公共知識人的時候,他所發表的言論基本上是以政治的意見為多,心理學則很少——或者說,不知道要如何拿心理學到知識場域來發揮。
我們把問題拉回到宗教心理學。台灣的宗教現象一直是生機躍動、潛力無窮的,但這個生命場域當然也就是難題叢生的知識領域。只是,在我們的知識界,能用心理學來談宗教議題的人實在少得不成比例(就是我在上文提到的五、六位而已)。我們確實需要以學科承諾的態度來回應整個社會對於心理學知識的需求。宗教心理學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我們需要發展這種迫切的知識,除了心理學本身之外,在宗教學、人類學、社會學以及在文史哲的相關學問中也都是如此,因為我們必須以適當的知識學問來連接上自己所身處的社會脈動——我們每一個人和我們所置身的社會事實上就其「脈動」來說,只要我們是活著的,焉有不「共振」的道理?Karl Jaspers曾說:宗教是每一個文化所擁有的固定想像。我們從小就應該接受它,到長大才會真正意識到,它是歷史的基礎。而在這當頭上,接受宗教知識,譬如閱讀某種的宗教心理學經典,就是必要條件之一了。我們現在談的是一本「宗教的動力心理學」。讓我們來為這本書是否能列在「經典」的位置上,作個仔細的評價,以便知道我們是不是需要「重讀」它。
普呂瑟的《宗教的動力心理學》在宗教心理學上所佔的地位
宗教研究在西方世界是人文學裡傳統最古老的一部份,所以在一般著名的綜合大學,特別是在歐洲,它都是不可或缺的學術部門。但是談到宗教心理學,以英語世界來說,卻發生了一次特殊的事件,那就是詹姆斯在1901年從美國被請到英國去發表他的《宗教經驗之種種》。這是因為學院心理學的發展,美國領先了歐洲,因為它是宗教研究裡最後發展出來的新領域。
我們從詹姆斯的《種種》當中首先學到的就是宗教心理學要排開宗教史、教義研究、宗教組織等問題而要專注於宗教在個人身上發生的體驗。所謂的「神聖」(the divine)可以完全不假手於外在的條件而在內心發生。這個重要的前提所引發的下一步當然是關於這種體驗如何得以被描述的問題。詹姆斯先把人分類成兩種類型,就是「健康人」和「病態人」,而他所鍾愛的宗教體驗事實上都是發生在後者。宗教是如何開始(這即是關於起信、改宗、皈依的問題),以及它發展到最高境界——也就是在聖徒以及密契者(mystics)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則是詹姆斯所關切的問題高峰。這本經典以一種高昂的姿態完成了開路的第一步工作。
接下來,有些人要接續這個問題,但稍稍降低姿態,談談普通人的宗教經驗,普呂瑟提到的有J. H. Leuba (1912)和G. A. Coe (1916),而普呂瑟沒提到另一個也算是早期的接續者E. D. Starbuck (1899), 這些作者由於觀點比較狹窄,所以都不算很成功,無法接續扛住經典的地位。詹姆斯仍是唯一的經典。一直到了1950年,奧波特(Gordon Allport)以一本小書《個人及其宗教》(The Individual and His Religion), 寫出了一個人一生的宗教經驗如何發展演變,並且在那之後也把這種生涯和社會現象結合起來,作了有關宗教人與社會偏見之間的關係研究。他所提出的「宗教人比非宗教人帶有更多社會偏見」這一命題震憾了“In God We Trust”(唯神是信)的美國人社會。後來奧波特把他對宗教人的定義精緻化,而產生了一種「內因—外因」(intrinsic-extrinsic)信仰的區分概念,把偏見歸給外因信仰者,從而拯救了內因信仰者的宗教。所以,在這次的思想波動之中,奧波特這位心理學家也成了英雄,而他的那本書也就因此變成了一本小小的經典了。
在此同時,也就是從詹姆斯以來的半世紀,在歐洲剛好也是精神分析學術迅速茁長的時候。佛洛依德的宗教研究引起了波瀾壯闊的迴響,不過,我們在上文已經提過,這是在學院心理學以外的發展。它出現了很多經典好書,但就是不屬於學院心理學的貢獻。所以,到了六○年代,一位從歐洲移民到美國的學者,以一個宗教人和臨床心理學專家的身份,重新接手詹姆斯到奧波特的宗教心理學發展大業,但是,他把精神分析帶了進來,只是仍以非常「心理學」的方式——用心理學所有解釋個人經驗的每一個重要範疇都拿來分別寫成一個章節:感知、智性、思維、情緒、運動以及人和世界可能發生的所有關係,包括和自己的關係,這樣寫下來,完成了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把宗教體驗和臨床心理學完全結合起來,把健康的宗教人到病態的宗教人全部都作了一次完整的解釋。
光從這種寫作的企圖來看,就知道這是要作為一個整全理解的知識大業,而當它作出來之後,我們可以說,他把詹姆斯到奧波特的傳承已經很準確、很完備地接上手了。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這本書寫的都是宗教人,而眼光尖銳的評論者告訴他:不信者的年代早已經降臨,你必須把眼界打得更開,讓宗教心理學能把所有的「非宗教人」也包括進來。於是,他旋即接納了評論者的意見,再接再厲地完成另一本書,就是在六年後(1974)出版的Between Belief and Unbelief(《在信仰與不信之間》)。
說到這裡,我們就可以把經典評價的問題拉回來,作一個結論:普呂瑟對宗教心理學的貢獻,如果是用兩本書,而不是一本,來作評價的話,他確實讓宗教心理學發展到了一個高峰。他自己曾謙虛地說,未來宗教心理學真正的思想核心,應該仍是佛洛依德的動力理論和奧圖的現象學,他也預言這一趨勢即令是再加五十年也不會被打破。但我們用比較具體一點的方式來回顧的話,就是能把佛洛依德和奧圖結合起來並具體呈現的宗教心理學,到六、七○年代為止,在英語世界中,仍只是普呂瑟一人。至於從他往後的五十年到底會有什麼發展,我們一方面可以相信他所說的那兩種「思想核心」具有顛撲不破的道理,但我們更可能看見的是,它將會以某種跨學科的形式而發展,譬如以「文化心理學」的方式,甚至以「文化研究」的方式,而我們目前所見的學術趨勢確實是如此的。譬如晚近的發展,有一波結合著文化心理學和詮釋學、動力心理學的宗教心理學新潮流正在發生中,主要的作者大抵是以歐洲學者為主,美國學者會加入的也比較不是心理系的人。這個潮流反應在J. A. Belzen所編的Hermeneutical Approaches in Psychology of Religion(《宗教心理學的詮釋學取徑》)一書中。而在這些作者中也開始產生了很具有經典架勢的作品,譬如比利時魯汶大學的Antoine Vergote就是一例。我們大家還應睜大眼睛來觀察、或動手來加入這個運動。
從傳記的描述看來,普呂瑟確實是個謙恭為懷的人。他沒有自誇的習慣,反而在晚年時都還在為別人打抱不平。他認為有位和他同時代的人文學者古迪那夫 (Erwin R. Goodenough)寫的一本宗教心理學 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實在是個遺憾。他說古迪那夫所具有的世界宗教那種深廣視野,是他自己所不及的。雖然古迪那夫不是個心理學家,但他提出的解釋範疇可能是心理學有待學習的下一步。這個具體的預言,我們也應該配合著上述的發展趨勢來一併傾聽才是。
「宗教的動力心理學」這門學問
普呂瑟把他自己的宗教心理學冠上個「動力(論的)」(dynamic)形容詞,他自己在序言中解釋說那是「一種理論導向的簡稱:即臨床的、精神分析的心理學,其中也包括了一些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的考量。」但是,讀完全書,你會發現他的說法對於自己的理路還說得不盡完整——它事實上還包括了精神分析在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之外的發展(譬如:英國的對象關係理論),再加上現象學的神學,以及社會/文化研究的基底。
我們可以把他的這套學問攤開來仔細瞧瞧,也許還可以進一步向我們的學界顯現...
目錄
譯者導讀
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宗教中的感知歷程
第三章 宗教中的智性歷程
第四章 宗教中的思維組織
第五章 宗教中的語言功能
第六章 宗教中的情緒歷程
第七章 宗教與動作系統
第八章 和人的關係
第九章 和事物與觀念的關係
第十章 和我自己的關係
第十一章 一些不斷重現的難題
中英譯名對照表
譯者導讀
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宗教中的感知歷程
第三章 宗教中的智性歷程
第四章 宗教中的思維組織
第五章 宗教中的語言功能
第六章 宗教中的情緒歷程
第七章 宗教與動作系統
第八章 和人的關係
第九章 和事物與觀念的關係
第十章 和我自己的關係
第十一章 一些不斷重現的難題
中英譯名對照表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