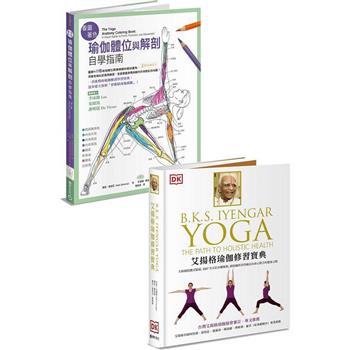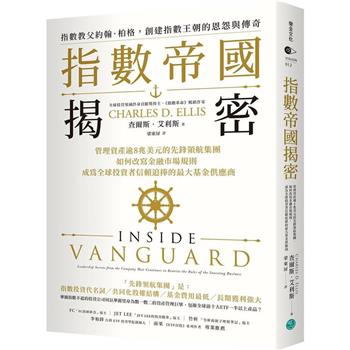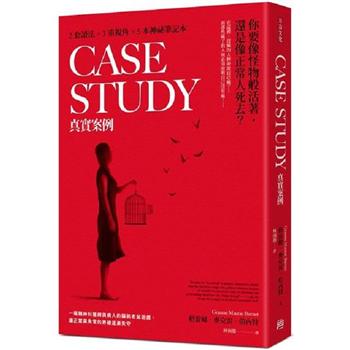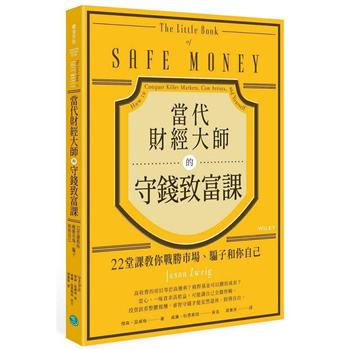對於藝術的觀察而言,「美」的概念是否還是一個充分可運用的概念?
我們在這裡看見了一種從客體到主體的或者從指涉到標示的轉換:
因為為了查明什麼東西可以被視為『美』的,即使如此長時間地觀看事物,直到我們可以從它們的存有中梳理出美的事物。
『對我來說,美學的任務似乎首先是在於觀賞者的進程描述。』
本書特色
長期以來的傳統藝術理論,其焦點多半仍只侷限在藝術本質的鑽研與探討上,而沒辦法將視野擴展到藝術作為一個社會系統本身的自主性運作觀察上,以及更重要的是,延伸至藝術的觀看者對於藝術的觀察與溝通上。當代社會學系統理論大師尼可拉斯.魯曼於1974年德國卡爾斯魯爾(Karlsruhe)的一場跨學科研討會中,率先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對於藝術的觀察而言,「美」的概念是否還是一個充分可運用的概念?
過諸如「美/醜」等特殊的符碼化過程,來成功地引導出藝術的溝通的問題。
此一深刻的提問以及極具創造力的系統論式理論觀點,很快地滲透到了許多跨學科的討論中,並且在文學、文化、藝術的研究領域中迅速開花結果。
作者簡介:
尼可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 1927~1998)
是當代極有成就的社會學家。他的一生共留下約60本專書和300多篇論文。他提出的社會系統理論,對歐洲社會科學界的影響很深遠,但他在英語系國家的接受度,卻遠不如他的筆戰對手──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
魯曼後來定居於比勒費爾德附近的歐林豪森(Oelinghausen),直到1998年辭世。魯曼過世兩年後,當地市立歐林豪森文理中學,更名為「尼可拉斯.魯曼文理中學」。為紀念魯曼,比勒費爾德儲蓄銀行(Sparkasse),每兩年頒發一次「比勒費爾德科學獎(Bielefelder Wissenschaftspreis)」。而魯曼的出生地——呂訥堡市,在他過世後,也將城西新地的一條街,命名為「尼可拉斯.魯曼路」。
獲獎:
1988年,魯曼獲得──斯圖加特市的黑格爾獎(Hegel-Preis)。
1997年,魯曼獲得──歐洲阿馬爾菲社會學社會科學獎(European Amalfi Prize for Soc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
譯者簡介:
張錦惠
現職:德國Tubingen大學現代英國文學暨語言學系博士候選人
學歷:德國Bielefeld大學英國文學/德國文學/社會學碩士、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學士
專長:文學理論,文學與情感,英國與德國文學從浪漫主義至現代,美學研究
章節試閱
學習閱讀
S.9現代社會生產出諸多不同的文本類型,這些文本類型要求人們以不同的方式來閱讀它們。某種程度上來說,根據某一文本類型所專殊化而成的閱讀習慣,會妨礙讀者模塑出另一種不同的文本閱讀方式;而且,因為這裡所關乎的,乃是在很大程度上來說無意識進行的、人們早已習以為常的例行程序,這類的專殊化過程因此是很難改正過來的。
我想我們最好是區分一下「詩的文本」、「敘事性的文本」、以及「科學性的文本」這三種文本類型。在接下來的部分裡,我們首先要處理的是科學性的文本;不過,要想清楚闡述科學性文本的特性,我們無論如何還是得先說明科學性文本並不能使用詩或小說的方式來閱讀,以及它們為何不能使用這樣的方式來閱讀的原因。
虛構性文本得以自成一個特殊的文本類型,這要歸功於一個漫長的、歷史性的習慣化過程,這樣的過程從十七世紀開始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其條件就在於克服了在「真實的實在」與「虛構的實在」兩者之間做出區分的難題。一開始,小說經常讓自己展現為一些彷彿偶然被拾獲的信件,或者是一些偶然被發現的筆記,目的在於說服讀者相信它們所告知之訊息的真確性。在敘事性的文本中,文本的脈絡關聯則是來自於張力(Spannung),也就是說,來自於那牽引讀者前進的未來本身的不可知;然而,從相反的角度看來,若想解消這股張力的話 — 如同尚‧保羅(Jean Paul)已經紀錄下來的一般 — ,人們勢必得回溯到那些已經被閱讀過的文本部分上。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讀者將會遭遇到一個弔詭,亦即「他已經知道什麼東西是他還不知道的」弔詭。敘述(Erzählung)不僅在其情節的時間中開展出來,它本身也是藉由時間之助,亦即藉由「已經閱讀的/尚未閱讀的」這組區分之助,被結構成一個文本。
詩的閱讀則提出了一些完全不同的要求。它們絕對不是以韻文的形式來呈現敘述,而且也不能夠以線性的方式從頭到尾一行一行地閱讀。詩主要取決在聲音的元素、不尋常的字詞選擇(即使是在一般字詞的選擇上也是如此)、反義與對比的辨識與斷定上,以及尤其是取決在韻律學(Rhythmik)上,後者確保了一種以非深思熟慮的方式(untersinnig)所同時完成的統一。這樣的閱讀要求讀者必須具備專注的短暫記憶以及多層次的遞迴 — 然而,所有這些都不是光靠將心中所想的事物說出來便能生成。
S.10同樣地,科學性文本的閱讀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要求。這裡,我想到的是以語言的形式表述出來的文本,也就是說,我想到的並不是以數學計算或者邏輯計算等秘文撰寫而成的文本。即使是科學家也一樣,如果他們想要出版的話,他們就必須造出句子來。然而,就針對出版目的而言必要的字詞選擇來說,它們事實上乃是受到一種對於多數讀者而言無可想像的偶然性規範所支配。即使是科學家自己本身,也甚少會去釐清這樣一件事實。文本中絕大部分的內容,其實是可以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來予以表述的,而且假使隔了一天再來寫它的話,它或許就會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表述方式出現。
造句時所需要用到的字詞填充內容,會避開任何一種概念性的調控規制。例如說,在前面這個句子中所使用的「避開」這個詞。這乃是無可避免的,即使是我們用最謹慎小心的態度,來處理那些被負載上概念性意涵的字詞本身的可區辨性以及可重新辨識性,情況也是如此。它們所構成的,始終只是這個文本整體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讀者應該要如何找出這些關鍵性的字詞來呢?
這樣一個問題對於下述的兩種人,亦即翻譯者與初學者而言,可以說是相當嚴重的。我至少在這兩種讀者的族群中,發現到我自身的書寫是如何受到偶然性所支配 — 儘管我已經盡可能小心翼翼地去處理理論脈絡關聯的連貫性和精緻化的問題。
對於一篇文本的理論脈絡不夠熟悉的翻譯者,經常會花費同樣多的力氣在翻譯所有他們看見出現在文本中的字詞上。這並非意味著他們依循著這些字詞的排列順序 — 這多半而言都是根本不可能達成的 — ,並且在這樣的意義上『逐字逐句地』翻譯。但是,他們不認為自己有權可以隨意操弄這些句子的填充內容。他們從既有的詞彙對等項中選出一些替代選項來,它們顯然是最合乎這篇文本中的字詞所要表達的意義;而且,我不知道翻譯者應該怎麼做,才不至於在翻譯時彷彿是用另一種語言寫出了一些全新的、和本文截然不同的文本。我們因此只能建議那些對科學有興趣的讀者,盡可能地學習多種不同的語言,如此一來,我們至少還能被動地掌握(也就是說,閱讀與理解)這些文本。
初學者(尤其是大學新鮮人)發現他們一開始就面臨到了大量以句子的形式所編列而成的字詞,他們可以逐字逐句地閱讀這些字詞,並且根據這些句子的意義來理解這些字詞。但是S.11,關鍵的地方在哪裡?什麼是我們應該『學習』的東西?什麼是重要的,什麼只是旁枝末節而已?在讀了幾頁之後,我們或許便已經記不得我們剛剛讀了些什麼。對此,我們又可以提出什麼樣的建議?
其中一種可能性是去記住那些名字 — 馬克斯(Marx)、佛洛伊德(Freud)、紀登斯(Giddens)、布迪厄(Bourdieu)等等。很明顯地,大多數的知識都是被歸結整理在不同的名字底下,有時候也或許會被統整在諸如社會現象學、文學的接受理論等等不同的理論名稱底下。大學的初級課程或者導論性文章,便經常是以這樣的方式來做編排。然而,我們在這樣的課程或文本中,卻甚少或者幾乎沒有學習到諸概念之間的關聯,以及尤其是這些文本所嘗試要予以解答的諸問題。而畢業考的考生們,便在他們畢業考的前夕來到教授的辦公室,說他們想要考關於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考題,或者太多的話,就考關於胡貝托‧馬圖拉納(Humberto Maturana)的考題,接著他們便準備好去告訴考官,關於這些作者們他們究竟瞭解了些什麼。
另一種可能性是針對一些特定的論題領域 — 例如民法的瑕疵責任問題、社會化理論、風險研究等等 — ,同時間去進行大量的文本閱讀。如此一來,我們便可以慢慢發展出一種對於已知事物的感覺,並且對『研究的現狀』有一定的熟悉度。接著,新的事物會因此變得明顯而突出。但是,我們在此學習到的,卻是某種多半會非常迅速被超越、接著又會被再度荒廢掉的東西。此外,這也同時指出了學習古典語言的好處。因為我們從來就不需要去荒廢古典語言,反而只需要去遺忘它們而已。
科學性文本的閱讀問題,顯然就在於當我們閱讀的時候,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一種短程性的記憶,反而是一種長程性的記憶,來藉此獲得一些參照點,幫助自己在本質性的事物與非本質性的事物、新的事物與純粹反覆出現的事物之間做出區分。然而,人根本沒辦法記住所有的事物。這時,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記憶式的學習法(Auswendiglernen)。換句話說,我們在閱讀時必須是高度選擇性的,並且能夠組織出大規模的網絡化指涉。我們必須要能夠理解「遞迴」(Rekursion)是什麼。然而,假使沒有人可以事先提供我們任何的說明或指示的話,我們要如何學習到這些呢?或者我們充其量也不過只是注意到一些比較引人注目的地方罷了(例如在前一個句子中,我們注意到的是『遞迴』,而不是『必須』)?
對此,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或許在於自己勤作筆記 — 並不是作摘錄,而是將已經讀過的東西濃縮且有組織地予以重構。將已經被描述過的事物再重新描述一次,這會訓練我們幾乎是自然而然地將注意力集中在『架構』(frame)上,集中在觀察的圖示上,或者也會S.12集中在那些導致這篇文本只提供了某些特定的描述,而沒有提供其他描述的條件上。就此而言,假使我們始終也可以一併考慮到:「當某種特定的事物被拿出來作宣稱之時,沒被提到的事物是哪些?被排除掉的事物又是哪些?」的話,這或許是更有意義的。倘若我們提到的是『人權』,那麼問題或許是:這位作者的陳述是要與什麼東西做出區分?是要與非人權做出區分?還是要與人的義務做出區分?或者它們是以比較文化的或歷史的方式,來與不知人權為何物卻依然可以過著美好生活的民族做出區分?就這樣一種探討文本陳述的另一面的問題,文本通常不會給予任何相關或者明確的答案。但是,我們便因此需要藉助自己的想像力,來幫助這篇文本解決這樣的難題。對於詮釋的合理性或者甚至是真理的疑慮,在這裡都是不適宜的。這裡所關乎的首先只是一個固有的摹寫系統(Aufschreibsystem),只是對於某種值得注意之事物的探索,以及學習如何閱讀的問題罷了。
這接著便導出了一個問題:我們要用這些被摹寫下來的東西做什麼?無疑地,我們首先會製造出大量的垃圾來。然而,我們卻是如此被教導的:從這些活動中,我們預期會生產出某些有用的東西,否則我們很快便會失去繼續做下去的勇氣。我們因此應該考慮到,我們是否要整理這些筆記,以及如何整理這些筆記,如此它們才可以在後來的時間裡隨時供我們所用,或者最起碼作為一種具安慰效果的幻象,縈迴在某人的腦海裡。這就需要一台電腦,或者是一個裝了許多編號卡片及一張導字索引目錄的卡片盒。持續不斷地『安插』這些筆記,因此是另一個耗費時間的工作流程;但是,它同時也可以是一個幫助我們擺脫閱讀的單調無趣,且似乎可以順便訓練我們記憶力的活動。
但是,上述這些考量的確都是針對這樣一個提問而提出的:我們應該如何學習科學性文本的閱讀方式?這個問題的解答很簡單,我們只需要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斷回溯到已知的事物上,換句話說,我們只需要長期性的記憶即可。所有這些都不是自行延伸發展出來的。對此,改述式的書寫法或許是非常合適的;而且,即使我們多少還是必須推遲自己對於科學生產力所抱持的期望,這樣的書寫法也依然是適用的。
這或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提醒我們想起,我們在這裡的所有考量所賴以出發的問題點,亦即文本種類的分化,乃是於十八世紀時才首次出現。這其中不僅包含了現代小說,以及更為講究的(我們幾乎可以說是:多媒體的)抒情詩,另外也包含了科學性的時事、政治評論等。這樣一種在上述所有這些領域中進行的文本分化,S.13明顯很容易受到印刷術所魅惑。或許,我們現在應該重新回過頭來,對書寫的固有成效提出更多的說明,尤其是鑑於電腦所能提供的各類可能性。
學習閱讀
S.9現代社會生產出諸多不同的文本類型,這些文本類型要求人們以不同的方式來閱讀它們。某種程度上來說,根據某一文本類型所專殊化而成的閱讀習慣,會妨礙讀者模塑出另一種不同的文本閱讀方式;而且,因為這裡所關乎的,乃是在很大程度上來說無意識進行的、人們早已習以為常的例行程序,這類的專殊化過程因此是很難改正過來的。
我想我們最好是區分一下「詩的文本」、「敘事性的文本」、以及「科學性的文本」這三種文本類型。在接下來的部分裡,我們首先要處理的是科學性的文本;不過,要想清楚闡述科學性文本的特性,我們無論...
作者序
譯序
長期以來的傳統藝術理論,其焦點多半仍只侷限在藝術本質的鑽研與探討上,而沒辦法將視野擴展到藝術作為一個社會系統本身的自主性運作觀察上,以及更重要的是,延伸至藝術的觀看者對於藝術的觀察與溝通上。當代社會學系統理論大師尼可拉斯.魯曼於1974年德國卡爾斯魯爾(Karlsruhe)的一場跨學科研討會中,率先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對於藝術的觀察而言,「美」的概念是否還是一個充分可運用的概念?魯曼接著於1976年發表了一篇名為《藝術可否符碼化?》的文章,探討藝術系統作為一個自主的社會領域 — 有別於經濟、政治、科學系統的運作 — ,如何透過諸如「美/醜」等特殊的符碼化過程,來成功地引導出藝術的溝通的問題。此一深刻的提問以及極具創造力的系統論式理論觀點,很快地滲透到了許多跨學科的討論中,並且在文學、文化、藝術的研究領域中迅速開花結果。爾後,魯曼又陸續在不同的期刊中,發表了許多透過系統論的觀點來探討文學與藝術的極具創見之文章。這些文章由新一代系統論學者倪爾斯.韋伯(Niels Werber)統編彙整,連同魯曼生前未發表的一些文章一同集結成冊,收錄在2008年出版的「文學藝術書簡」一書中。如同韋伯在本書後記中所提到的,諸多的藝術觀察者可以在相同的意義下觀察一件藝術作品,而且他們所意指的乃是在出現在他們面前的同一件物品,這樣的情況根據魯曼的觀點來看,事實上乃是一件極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這類的藝術溝通 — 就如同發生在社會中的所有成功的溝通一般 — 究竟是如何成功出現的,它們需要有著什麼樣的預設條件,這般的演化過程究竟是如何有可能出現的,這些問題因此都是本書的關注焦點所在。
一如在所有魯曼的譯作中都會提及的,魯曼在論述中所使用的語彙,基本上都具有相當高的抽象程度,而且比起很多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而言,社會系統理論的術語與日常生活用語之間也有著相當明顯的差距,再加上中德文之間轉換與落差的問題,都使得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面臨到重重的煎熬與困境。因此,要如何以盡可能精確無誤的文字,不偏離作者的原意,又能讓讀者理解本書之論述,對於譯者而言著實為一項艱辛的挑戰。譯者在此也只能盡力做到讓譯文正確無誤而已,至於雅的部分,則要請讀者多多海涵。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為了使譯文能夠更為明確清晰,譯者在文中使用了一些本文中沒有的符號。例如,文中出現的「」這個符號皆為譯者所加,為本文中所沒有之符號,用以突顯一個概念或者德文中的一個子句。再者,譯者在:(冒號)與—(破折號)兩個符號的使用上,也不全然遵照原文的用法。譯者盡可能是以原文的用法為準,唯有在句子過長或過於複雜之時,才會變更這些符號的使用。再者,在此書的原文中,魯曼經常直接引用拉丁文、希臘文、英文、法文、義大利文及西班牙文的文句;除了德文與英文譯者直接譯出之外,其他語言皆在譯文中保留原文,並以括號中譯按的方式,譯出中文的意思,希望藉此保留作者在原文中使用這些外來語文的原意。至於文中譯名的部分,譯者原則上盡量選擇目前慣用的譯名為準。人名的部分基本上皆翻譯成中文,並在括號內附上原名,希望可以藉此避免讀者混淆。譯文中照錄了德文的註釋。為了避免繁瑣,譯者並未將原註中使用的德文通用縮寫譯出。但是為了幫助理解,在此列出文中各縮寫的意思,以供讀者參考使用:「Hrsg.」:編輯,「a. a. O.」:出處同前,「S. 123」:頁123,「S. 123f.」:頁123及124,「S. 123ff.」:頁123及之後,「insb.」:尤其是,「ders(或dies)」:同一作者,「Diss.」:博士論文,「Bd.」:冊,「bzw.」:以及,「Aufl.」:版,「in」:收於,「z.B.」:例如,「et al.」:及其他作者,「Neudrck」:(老的作品)新印,「Nachdruck」:再印。
最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得到多位老師與友人的協助,在此特別提出,以為致謝。目前任教於輔仁大學社會系的魯貴顯教授,在本譯文的校訂與潤飾上花費了許多時間與精力,並且耐心為譯者解釋理論中艱澀抽象的部分,在此致上最誠摯的感謝。在外國語文的翻譯方面,法文的部分要特別感謝就讀於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院社會學博士班的陳逸淳,而拉丁文與希臘文的部分,則要衷心感激目前於德國蒂賓根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的松沢裕樹等友人所給予的諸多協助。另外,還要感謝的是譯者的丈夫熊坂元大,他分別在原文的深度分析及外國語文的翻譯上,提供了譯者相當多的建議與協助,並且在譯者必須同時面對懷孕的不適與翻譯的困境時,給予最大的支持與鼓勵,在此謹致上最衷心的感謝。最後要感謝的是譯者肚子裡即將出世的小孩,感謝妳陪伴我度過這一年間不能算是輕鬆的趕稿歲月,希望妳的出生可以和這本書的出版一樣,平平安安,順順利利。
張錦惠
2012年12月 於 台灣高雄
後記(倪爾斯.韋伯)
I. 一場關於銜接能力的測試
S.438西元1974年,畢勒佛(Bielefeld)文學研究家齊格飛.施密特(Siegfried J. Schmidt)邀請一些專家來到卡爾斯魯爾(Karlshruhe)的一場跨學科學術研討會,共同來研討這個問題:『今日是否還有一種使用「美」的概念的有意義方式?』。受他的邀請而來的藝術家有好比說約翰.葛茲(Jochen Gerz)與堤姆.烏里希斯(Timm Ulrichs)、哲學家有好比說君特.葛伯爾(Gunter Gebauer)與恩斯特.歐德麥雅(Ernst Oldemeyer)、語言學家彼得.哈特曼(Peter Hartmann)、心理學家漢斯.賀爾曼(Hans Hormann)、藝術史家馬克斯.英達爾(Max Imdahl)以及化學工程師漢斯.魯普夫(Hans Rumpf)。 這位年僅34歲的教授為『文學理論』所列出的邀請名單以及針對性的邀請函,揭露出一種渴望重新組織關於藝術的言論以及藝術在社會中所扮演角色的願望。這一切都在醞釀之中。哈洛德.史澤曼(Harald Szeemann)那一再備受藝術家矚目的第五屆文件展(documenta 5),已經藉由事件、展演、觀念藝術、社會造型藝術、以及行動藝術等,撼動了人們對於應該如何談論『藝術』的理所當然的想法。最新的藝術或許是『有趣的』,或許也可能是『精神錯亂的』或者『激擾人心的』 — 但是,是『美』的嗎?
施密特對參與者所提出的問題是:有鑑於最新藝術中的這樣一種發展,我們難道不需要刪去『美的』這個概念,或者徹底重新賦予它新的定義嗎? 由於這些報告人也只是想以一種暫時性的且相對化的方式,來回答什麼是美以及什麼是藝術的問題而已,他們因此還可以應付施密特所提出的問題 — 鑑於不同的美學理論,鑑於社會族群的社會化過程,鑑於風格指標、規範、語言遊戲、制度等等。即使其中一位或者兩位報告人依然非常樂於從人類的心理-物理配置S.439、從人類學的基本配備或者跨歷史的搜尋模式出發,來為那以科學性的方式來觀察美在經過數千年之後所產生之變質的做法,賦予一個固定的支撐點,但整體而言佔優勢的還是下述這樣的一致意見:即使是意料之外的常數,也有可能毫無錯誤地被嵌入變化多端的『脈絡』之中。找尋美的理由,並不是在那作為一種美的事物的美的事物之中,好比說在一座古代的阿波羅(Apilli)雕像中,或者在一首里爾克(Rilke)的詩中,或者在一幅勞倫(Lorrain)的畫中,反而是在周遭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我們在這裡看見了一種從客體到主體的或者從指涉到標示的轉換:因為為了查明什麼東西可以被視為『美』的,即使如此長時間地觀看事物,直到我們可以從它們的存有中梳理出美的事物,這樣的做法乃是不夠的,我們反而必須連同他們的期望以及那些在某些特定社會情況及歷史情境中被使用來為『美』提出解釋的準則,一起研究這些觀賞者。這場研討會在結束前有一句話是:『對我來說,美學的任務似乎首先是在於觀賞者的進程描述。』 美從作品的實質內容中,游移到了主體的審美體驗上。
這樣一種將『事物本身』轉換成一種經由觀賞者所產生之『事物相關物』的接受優先性,並不是那樣顯而易見且不言而喻的。自古代以來,哲學家、神學家以及其他的教義學者便已經給出了一些具約束力的答覆,來回答關於什麼時候可以將一件作品稱為美的問題,也就是說,當『X是美的』的陳述是真的,或者當人們說它是美的而且它實際上的確也是美的物件,確實對應於語言關係以及事物的實質內容時,人們便可以將一件作品稱為美的。不過,今日的我們已經知道,即使在這裡,真理同樣也是仰賴於每每不同的一整套規則與準則,這些規則與準則使關於美的陳述變得可能,並且同時也對其做出了限制 — 完美的黃金切割,因此是美的;高貴的王室英雄以悲劇性和英雄式的方式死去,貧窮可憐的平凡人被嘲笑,因此是美的;王子所熱烈追求的牧羊女原來是一位公主,因此是美的;以合乎規則的方式來描摹某個典範的比例與透視觀點,因此是美的;以有益且有趣的方式來策劃一堂道德教育課,因此是美的等等,諸如此類。相反的:不成比例的、沒有道德的、非英雄的、沒有展望的、S.440醜陋的等等,因此並不是藝術。美的規範性規定,以及甚至還有對於他性(Alteritat)、複數性、否定性以及無功能性等的『批評式』規定 — 就如同阿多諾於1970年出版的《美學理論》(Asthetische Theorie)中將這些都指定為成功的藝術,並且用相同的姿態來駁斥庸俗作品、文化工業和宣傳廣告一般 — 於1974年的卡爾斯魯爾失去了它們的效力。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對於庸俗作品的重新評價,取代了阿多諾被引以為據。 什麼東西是『美的』(或者是『扭捏作態的』) — 這似乎是一種新的常識(common sense) — 的問題,會根據每每不同的情況且『基於它所代表的理論』,而為它自己以及那被觀賞的藝術作品被固定下來。 就如同施密特用一種激進的、在今日幾乎是不言而喻的表述方式所提出的一般,藝術所關乎的乃是一種美的『建構』(Konstruktion),而不是對於美的事物的真實描述。
尼可拉斯.魯曼也參與了卡爾斯魯爾的學術研討會,我們可以在這本書中讀到他所提出的諸多討論。 但是,就如同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的情況一樣, 他並不是這場研討會的焦點人物,反而完全處於邊緣的地位。他那關於『藝術的可符碼化』問題的報告以及他的對話文章,看起來似乎既不符合卡爾斯魯爾研討會的倡議計畫,也不符合人們在那裡企圖留存下來的東西。魯曼對那已經變得有問題的『美的取向』討論乃是如此堅持。 他雖然並沒有提倡一種藝術S.441的本體論, 但卻一反所有關乎藝術在一種『高度合理化的、去神話化的勞動與消費世界』 的條件下高度仰賴市場、階級、教育及社會的命題,斷然地宣稱藝術的自主性,這在1974年就彷彿是一種以老套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式的(即便不是反動的)方式,來將藝術從社會影響力中隔離開來的舉動一般。魯曼接著甚至將茅頭顛倒過來,而且偏偏用了馬庫色(Marcuse)來將所有那些『拒絕藝術的美』的人都解釋成反動的,這樣的做法讓人絲毫無法理解。 而且,正當這些語言學家、文學研究者、藝術史家以及哲學家們,在所有這些相對化的過程背後,發現到接受者乃是一個阿基米德式的支點,據此人們可以做出『美』是什麼的決定時,魯曼卻在接受美學那迎面而來的波濤巨浪 中逆向而行,宣稱藝術家與觀賞者之間差異的統一。當藝術成功出現為溝通之時,我們不能在接受者那裡『預設一些完全不同於生產者的準則』,反而必須『假定一系列將所有事物合法化的觀點』。 他不想『在評價的準則中將生產與描述兩個層面劃分開來』;魯曼在討論中反對將那被認為是以天才的、無意識的、無規則的或者特異的方式來進行創作的作品『生產者』,與他那為數眾多的 — 亦即,『科學性的』、『意識型態的』或者『天真的』 — 『描述者』劃分開來。因為作品而變得可能的藝術溝通,將這兩種角色聚合在一起。不管是藝術家、科學家、批評家、政治家、還是戀愛者 — 只要是始終想對藝術作為藝術表達意見,或者甚至是為其他人創造出可被感知為藝術的藝術S.442的人們 — ,都必須正確地判斷出『事物』的『選擇準則』與『運作規則』。
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事物?這樣的事物難道不會作為一種構成物被暴露出來嗎?光是這樣還不夠,魯曼也將藝術家剛剛才幸運闔上的黑盒子(black box)整個打開,一窺藝術家在勞動的當下所做出的決策, 而且他『將所有事物合法化的觀點』,令人不禁懷疑地想起他們過去在『以反教條主義的方式來重新建構』論述的過程中,曾經採用過的規範與規則。 即使是藝術家所強調的個體主義 — 『這裡有著這麼多藝術的確定性,就如同有著這麼多的藝術家一般』 — ,他也同樣讓它失敗觸礁。就此而言,至關重要的並非在於那依然是如此令人振奮的創造力或天才,反而是『造成溝通減少衰退的條件』,這些條件不僅出現在『金錢、經濟、法律』的情況下,並且同時也要求藝術達成一種『共識』; 一種當然是與自由主體透過辯論的方式所達成之協議毫無關係的共識,它反而是源自於引導機制的演化 — 好比說金錢或者權力等『媒介』。這聽起來必然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去保護藝術免於受到市場及權力的損害,魯曼反而想要明確地『藉由功能性的抽象概念之助』,以類比『金錢符碼』及『權力符碼』的方式來理解藝術。 他建議就像政治、法律或者科學一樣,將藝術理解為以一種特地為此分化出來的象徵性一般化媒介所形成的一種二元符碼化了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溝通S.443,這樣的建議在1974年引發了不只一次的反對意見,不論是他的命題還是他所使用的語彙,都是令人感到如此陌生、不熟悉。藝術可否符碼化?魯曼的構思證實自己乃是無可調停的,這正好清楚地指明了那些人們嘗試在其中與他搭上線的對話片段。
我們或許會期待一位社會學家 — 尤其是期待一所『改革的大學』 — 去談論一些關於角色特有的或者階層特有的通往藝術的途徑,批評藝術的評價在學校、學院、博物館以及類似場所被制度化的現象等等,但魯曼就像是模控學家一樣談論到符碼與綱要,像是生物學家一樣談論到演化成就的條件,像是技術專家一樣談論到圖示化、時間節約、簡化或者效率等,而且偏偏想要 — 彷彿所有這一切在阿多諾過世的五年後還顯得不夠糟似的 — 將美回溯成一種『選擇的傳遞』(Selektionsubertragung),它很明確地應該可以和私有財產、金錢與權力的『成功演化生涯』相比較。 這樣一種不尋常的比較學,並沒有將藝術(包括文本藝術與音樂…)貶低至政治工具化或者經濟適銷性的等級上,反而相反地允許人們認真地將藝術視為現代社會的一個獨立且同等級的領域,這樣的作法在早期的魯曼接受中經常被錯估與誤判。正是系統論的能力 — 雖然憑藉著它諸如系統與環境或者符碼與綱要等抽象概念,還無法讓所有事物彼此之間相互比較,但至少已經可以讓諸如政治、經濟、教育、科學、宗教與藝術等如此不同的功能領域之間彼此相互比較 — 在這期間受到高度的讚揚,而且諸如『複雜性的化約』、『分化』或者『銜接能力』等表述,早就已經是大眾媒體的慣用語彙來源。數以千計的課堂報告、數以百計的論文、以及數十本的專書著作,每年都會讓人聯想到魯曼的這些命題,並且嘗試去測試和改變它們,這些著作證實了魯曼關於藝術之思考的銜接能力。魯曼在《社會系統》(Soziale Systeme)的〈前言〉中強調說明,『古典學家是古典學家,因為他們是古典學家』。光是如此,便已經足以擁有一個『偉大的稱號』,這樣一個偉大的稱號將會因此一直不斷被重複 — 而人們S.444並不需要思考古典學家在煩惱些什麼的問題。在三十年前,魯曼絲毫沒有蒙受這樣一種成為古典學家的風險。成為一位『論述的奠基者』 ,亦即,成為一位諸研究者可以在他的『名號』基礎上繼續專殊化的論述創立者, 這樣一種成就史證實了系統論在卡爾斯魯爾的研討會中所發出的『噪音』。 魯曼本身一直要到十年之後才又開始針對藝術發表意見。
II. 從一種『一般性理論』的觀點來看藝術
魯曼在他的《社會系統:一般性理論的概要》第一頁上坦承,以書本的形式所呈現出來的系統論,對於讀者而言乃是一種難以忍受的『無理要求』。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它的『抽象性』,因為系統論藉由它的工具建構出它所描述的社會實在,而且倘若它不想讓自己『被現實欺騙愚弄』的話,所有這些建構與描述就必須要夠複雜。當理論『飛行在雲層上』的時候,它本身必須仰賴它的『起降工具』,如此才不會如同一架裝設了不具功能的雷達的飛機一樣,在第一次的實在測試中便失敗觸礁。不管是『死火山』,還是一個諸如藝術領域等如此崇高的領域,我們都必須予以保護。 另一個魯曼雖然沒有明白指出的嚴格要求,在於系統論式的社會學必須能夠在它的盲目飛行中去描述這整個社會 — 這個社會也包含了藝術在內,因為藝術的確展現出了這個社會實在的一部份。 我們究竟為什麼S.445要參與在這樣一種因為『相當封閉的雲層』而與事物分隔開來的超然理論中,而不是反過來在事實的基礎上繼續培育關於自己學科之專業領域的專業知識?比起一個從系統論的飛機上『偶然往下看』的人,肯定更熟知他們研究領域的藝術研究者、文學研究者、媒介研究者和文化研究者,尤其可以對自己提出『為什麼是系統論?』的問題。 為了至少能夠概略地闡述這樣一個問題的解答,《文學藝術書簡》的導論必須同時提出一個計畫來,說明那些引導魯曼的飛行器飛行的工具。
魯曼恰巧不是以系統論小商品的推銷員身份在卡爾斯魯爾現身。他在報告的一開始便清楚說明,他想要在『一種一般性理論的基礎上』來處理藝術,而且更確切地說,一種希望與藝術之間(就如同與好比說政治或經濟之間一般)保持不多不少的關係的理論。二十年後,他向他的公眾解釋他 — 『既不是一個藝術社會學家』,而且就專業而言也根本不是『往藝術史的方向』專攻『美學』或者對於『藝術場景』的反思 — 究竟為何會談論『關於藝術』的原因。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推動一種『全社會理論』,但是『社會學到目前為止太過於片面地不是從經濟就是從政治出發』來理解社會,而且過於倉促且草率地將其『交付給各種專家,例如說宗教、家庭或者還有藝術』。 但是,從魯曼的觀點看來,社會作為社會學的對象所包含的並非好比說特別是經濟或政治,反而是所有社會性的事物,包括從簡單的『社會接觸』到『社會作為考慮到所有社會接觸的整體』: 這其中包含了國家、政黨、行政機關、法庭,但是也包含了教派、托兒所、藝術空間和迪斯可舞廳。相對地,所有將這些領域本身的相對應的自我描述,都納入自己的理論勞動中的人,卻理所當然地假定,S.446權力的行使、資本的建立或者勞動是比較重要的,而且它們因此展現出了全社會理論的真正研究客體。政治因此被認為是比所有其他事物更重要且根本的,因為它本身也這麼做,但是,這樣的觀點對於這個社會的理論基礎而言,卻是不夠充分的。對於自身的卓越所抱持的信念,本來就是全社會的所有功能系統的典型特徵,而且同樣也是其特有特徵的,是從這些自我描述所派生出來的自我高估(好比說:政治可以創造工作機會、整合外國人、或者『賦予』有天賦的孩子大學文憑)。 不只是政治或者經濟,還有宗教、法律、科學、教育、愛情、藝術或者大眾媒體,都會生產出全社會的描述,這些描述很明顯地高估了它們自己的意含。不依循這些宗教性的、經濟性的、政治性的或者情慾性的世界藍圖其中之一,而且也不是相對應地以等級制度的方式,從一種被解釋為『規定形式的』或者『支配性的』『功能系統特徵』出發,來描述這個社會,以及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推動一種連字符號-社會的『連字符號-社會學』, 魯曼的功能分化理論從一個由不同的、等值的、自主的、無法彼此化約的社會系統所組成的全社會出發,而且我們依然可以根據一些『相對統一的準則』來分析這些社會系統。這個全社會理論因此『很難不去注意到諸如藝術等如此重要的領域』。 不將藝術描述為一個次級的現象,這樣一種承諾或許可以補償某些功能抽象化的無理要求。
魯曼所表述的這種對於一個『包含了社會學整體對象領域』 的『普世』理論的要求,為他也能夠談論『關於藝術』的事實提出了理據。而他探討全社會功能分化的命題,則解釋了他是如何做到這些的S.447:現代社會將諸如有限資源的分配、具有集體約束力之決策的完成、認識能力的生產、或者對期望所抱有之確定性的建構等問題,都委任給『諸次系統』(經濟、政治、科學、法律),而不能『允許自己在整個系統的層面上享有諸功能當中的決策優先權』。不管個別的功能系統嘗試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完成它們的任務,或許是透過民主的或者獨裁專制的方式,或許是透過資本主義的或者計畫經濟的方式,也或許是藉由國家的研究補助經費或者私立大學之助,它們都無法經由中央來予以協調,反而只能以演化的方式來取得協調一致。假使政治或經濟根本已經在社會上佔有一個優先的位置的話,這意味著其他的領域可能會被『政治化』或『經濟化』 — 而且執政黨或許會對法院訴訟的結果、藝術的美、或者研究結果的真實性進行干預,或者使得判決、品味、或者真理變成可買賣的。魯曼知道在有些區域中,這類藉以施加影響力的作法乃是司空見慣的,而且『網絡』(Netzwerke)承接且顛覆了這些功能系統的任務。 但是,他不只是注意到了這些,並且也警告人們提防不同功能符碼之間差異的解消。『倘若一個溝通實踐無法觀察到、注意到這樣一種區別的話,那麼它就只能造成混亂和混淆而已。』 我們的溝通實踐是否早已陷入這樣一種『混亂』的狀態中, 這個問題並沒有在魯曼那裡被提出來。功能系統的『自主性』以及『全社會的整體系統轉變成為一種功能分化的優先性』這個雙重的命題, 讓我們見識到了一種規範性的風格手法(Touch)。相對地,在最早期的系統社會學中,所討論的乃是這樣一個假設命題:到目前為止被視為典型特徵的全社會的功能分化S.448,是否已經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和影響範圍? 我們可以參考例如說反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的Fathwa【譯按:諭令】,參考『諷刺漫畫之爭』,或者由樞機主教邁斯納(Kardinal Meisner)所發起的、關於宗教崇拜與藝術之間關聯的辯論,來說明藝術系統的自主性已經是無可爭議的。相對地,魯曼從功能分化模式的『全球化』出發。 假使藝術是一個系統的話,那麼它的『獨立性』無論如何都是毫無疑問可言的;而且假使它是一個系統的話,那麼所有可以『在任何一個功能系統分化的例子中』被區分開來的事物,也都可以在藝術中被觀察到:功能、成效與反思、媒介、符碼與綱要 、成效的角色與委託人的角色等等。
因這樣一種圖示而產生的一個任務,乃在於規定出藝術為全社會這個整體系統所執行的功能。 魯曼在所有他探討藝術的文本中,都始終堅持「藝術是全社會的一個功能系統」S.449這樣一個研究命題。
換句話說,不同於一般而言常見的,從全社會的其他某些『實體性』層面上推導出藝術來(好比說,作為某種經濟『基礎』的文化『上部結構』,或者作為『統治』霸權的批判-顛覆性的相對物),藝術系統被與其他系統一同置入相同的理論比較架構中。諸如『階級』、『統治』、『世俗化』或者『勞動分工』等社會學的傳統基礎概念幾乎無法適用於此,因為它們的描述潛力對於全社會的次領域而言,依然是相當有限的。相對地,魯曼在他畢生的作品中所制訂的社會學研究工具,並沒有為某個特定的系統賦予一種理論內部的優先性。就這方面而言,社會的基礎要素 — 溝通 — 乃是全然非特定的。這裡的問題只在於:它是如何做到的?是什麼東西將藝術溝通和企業溝通或者廣告溝通區分開來的?一個可能的解答是:它的符碼化!諸如「美/醜」、「法/不法」、「擁有/不擁有」或者「好/壞」等二元符碼,引導著藝術、法律、經濟或者道德的溝通,並且同時留意特殊性與差異。符碼會製造出區別。這些都是很容易檢測的,我們可能會嘗試用美好的話語或者良好的品德,而不是用金錢來保存一種有限的資源,或者透過指出企業生產流程的合法性問題,來為悲慘的收支平衡表提出辯護。諸如金錢、道德與法律等媒介以及它們的符碼值,是不能彼此相互轉換的。 擁有金錢的人,長時間以來依舊無法獲得權力;擁有權力的人,因此不必然是一個良善的、富有的、或者美麗的人。自從三個世紀以前,藝術也開始用這樣的分化形式來做實驗,並且創造出一些為對抗哲學的美的學說及古典規則集所引發之阻力,而將美好的、真實的、強力的、神聖的或者明智的事物,策劃成醜陋的或者無聊的,並且將惡的、虛假的、S.450無能的、惡魔的或者愚蠢的事物,策劃成美的或者有趣的。 並不是美的事物本身,而是一連串從美的或醜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此或彼之間的決策,進展到下一個決策的(生產或者接受的)運作,才使藝術得以成為藝術。當其他的溝通決策 — 真的或假的、擁有或不擁有、及格或者不及格 — 佔據了優勢地位之時,人們才不會在全社會的藝術系統中進行溝通。
III. 溝通
根據魯曼的說法,探討可符碼化的問題會在不同的『文化領域』中被提出,不僅是在藝術中,同樣也在經濟中;這其中有它們的好處 — 這些『功能抽象概念』允許我們『比較』不同的文化領域 — ,同時也有它們的問題 — 這些理論抽象概念陷入了一種『與客體之間的危險距離』。 每一個第一次閱讀他的藝術著作的人,都可以察覺到這些好處與問題。關於藝術符碼化的諸考量,也是以相當抽象且反直觀的方式,從這樣一個宣稱開始:溝通要能夠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在每一個溝通的情況下 — 讓我們借魯曼迷萊納爾德.戈茨(Rainald Goetz)的戲劇性表述一用 — ,兩個『井然有序地分離的大腦』面對面站在一起,它們的感受、意圖、意識過程,對於彼此而言都是不透明的。 所有不是天使或者有精神感應能力的人 — 而且此乃是數十億的個體 — ,倘若想要告知其他人某些事物的話,他們便需要嘗試進行溝通。魯曼的社會學因此觀察溝通 — 而不是數十億的大腦、靈魂、意識。此所關乎的不是別的:『凡是要實際搞清楚這可能意味什麼的人,都會想要查明某些(許多、所有)個體在某一個時間點上S.451的具體意識狀態,但是馬上會明白這樣一種冒險行為是不可能的』。人們因此很快就會得出這樣一個洞見,『當他們在經驗上認真地將個體視為擁有身體與意識、記憶與瞬間感受性的個人時。』 我們可以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來理解魯曼那以駭人聽聞的方式被誤解的陳述:社會不是由人所組成的,而是由諸溝通所組成的。一個由人所組成的社會,是根本無法透過社會學來予以描述的。
社會藉由其生產與聯結,來以「自我再製」的方式進行自我再生產的基本要素,乃是溝通。它當然預設了人類以及其他更多的存在,但是,心靈、肢體、機器、空氣、食物、重力等等,都是屬於社會系統的環境。唯有溝通可以進行溝通。『物理性的、化學性的、生物性的過程,並不能直接干預溝通 — 除非是在破壞的意義上所言。噪音或者空氣的抽離或者空間的距離,可以將口語溝通排除出去。書籍可以燒毀或者被燒毀。但是,沒有哪一種火是可以撰寫一本書的』。 環境中所進行的諸過程,可以例如說破壞技術性的基礎設施,並且藉此來阻止溝通 — 閃電擊中了天線,而且螢幕變成了黑白的,但是環境並沒有因此規定這個家庭將會收不到哪一個頻道。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那著名的、在甲醛中游泳的鯊魚(《死亡在活人心中的物理不可能性》(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1991)所必須忍受的腐敗過程,是否展現出了這件作品的一個部分,這個問題為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與藝術家之間提供了一個爭論的機會,前者花了六百五十萬英鎊收購了這件作品。是否可以在不改變原作的情況下,替換掉這隻鯊魚?或者,赫斯特是否可以貫徹這項命題:他根本不是想用甲醛來保存什麼東西,反而是想用一種媒介『來溝通一個理念』?一如往常般,這樣一場爭論也是有可能出現的 — 並不是那條鯊魚作為一個物理的實體來進行溝通,而是藝術家、藝術貿易商、顧客、藝術批評家與藝術史家根據觀察來進行溝通,而那『腐敗的鯊魚』則代表了這些觀察的S.452必要性條件。 就如同火不會撰寫一本書一般,腐敗也不會生產出藝術來。倘若在數年之間,一隻在牠那泥濘般的浸液中完全腐敗的鯊魚,被認為應該可以作為一種藝術作品的話,那麼可以解釋這樣一種過程的,並不是生物化學家,反而是藝術系統的觀察者。
聳肩或者挑眉算不算是一種溝通?有些時候當然是,但很多時候也或許只是身體不自覺地做出來的動作而已。社會並非僅僅仰賴於這些歸因的不確定性。在社會演化的過程中,語言已經證實自己是一種有用的溝通媒介。之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它將大腦、靈魂或意識一起帶入談話之中,而且也不是因為當相同的事物被說出之時,每個人都會理解到相同的事物,反而是因為語言溝通享有這樣的好處:相較於擬態和表情手勢,語言溝通的形式乃是相當引人注目的,而且可以如此明顯與所有其他自然的噪音來源區分開來,因此人們可以很容易從這裡出發,來假定某個說話的人也想要參與溝通。我們假設某人說:『這扇窗子是開著的。』我知道什麼是窗子 — 這可能是認識論理論家始終抱持的想法 — ,並且也知道它是可以打開的。換句話說,這扇窗子是打開的,而不是關上的。換句話說,假使語言彌補了『分離的大腦』之間的距離的話,我便可以理解他人,他的陳述對我而言就會是有意義的嗎?不,因為我不知道哪些訊息被告知出來。訊息是一個做出區別的區分。 不過,我自己已經看見了窗子是開著的,為什麼這樣一件事需要特地作為一個訊息告知予我?換句話說,此所關乎的是否反而比較是一種指出天氣有點冷,而且我應該把窗子關上的指示?他者冷得發抖,自我關上窗子,他者點頭表示感激,我們理解了這一切。或者,這是一個S.453因為擔心沒有新鮮空氣,而請人務必靜靜地抽煙的要求?或者是一個對於我不管蚊子在晚上會不會飛進燈火通明的住家裡,又再把窗子打開的批評?或者是一個暗示著從後面的房子傳來的肆無顧忌的高分貝且可惜總是很難聽的音樂的影射?對於脈絡的掌握以及關於類似情境的回憶,在這裡一併湧入 — 或許在一個以書寫文字的方式或者是以印刷的方式來告知『這扇窗子是開著的』這個句子的情況下,這一切會有所不同,因為這個句子可能在很久之前,便已經在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被表述出來。讀者無法一下子就知道,這扇窗子現在究竟還存在不存在。文本必須一併提供對於理解而言必要的脈絡,並且在魏德金(Wedekind)的《春醒》(Fruhlungs Erwachen)(第二幕的第一個場景) — 我們在這裡逐字地找到這一句話 — 中作為一種供人參考的指示,指出這個訊息乃是與前面的場景和接下來的場景息息相關的。在一個在場者彼此互動的情況下,充斥著大量的將訊息和告知區分開來且延續溝通的可能性。我走近窗子,並且為自己點燃一支香菸 — 為了最後從那同樣也在抽煙的對話者口中說出的、關於發生在鄰居家裡的一樁竊案的評論中,注意到開著的窗子必然冒有遭人破門而入的犯罪風險,並且想像自己現在已經理解了這個被告知的訊息。『銜接的溝通』在這裡被使用來測試『先前的溝通是否已經被理解』。並不是對於開著的窗子的充分感知,反而是他者以及自我將『告知行為』與『它所告知的事物』區分開來的區分 — 而且更確切地說,自己以及他人的區分 — ,才使得溝通得以實現。 並不是當我知道『窗子』這個字所指涉的乃是這個世界中的一扇窗子,而是當我突然想起 — 並且在溝通中測試自己的這個想法 — 我希望談論關於如何保護自己的房子免於竊盜破門而入時,我才理解到這一切。溝通銜接上溝通,這樣的事態甚至也不是仰賴他者與自我的良善意圖,雖然語言理論家及超驗哲學家都認為,此乃成功的語言行動所不可或缺的,因為即使是關於人們現在是否真的需要在寒冷的冬天裡,走到開著的窗子旁吸煙的爭論,也會再生產S.454出在場者彼此之間的互動,並且將一個溝通銜接上下一個溝通。而且正是這樣一場爭論才得以明確地指出,自我已經完全理解了他者:此所關乎的乃是「冬天裡開著的窗子是人們所不樂見的」訊息之告知,而且人們因此不該在住家裡吸煙,如此便根本不會產生需要開窗『通風』(Power-Luften)的必要性。他者當然也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告知這樣一個訊息,例如說,將其表述為一種友善的請求,或者以擔心健康問題的藉口為由,但是,不管是在哪一種情況下,始終都是自我在不斷地將訊息與告知區分開來,讓它們彼此相涉,並且 — 魯曼是這麼說 — 理解它們。那些從『這扇窗子是開著的』這句話所開始進行的溝通,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選擇的提供,它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來予以答覆。首先,互動的過程限制了銜接可能性的範圍。在一段關於竊盜和開著的窗子的五分鐘長的對話之後,突然開始責罵起吸煙者的麻木不仁,這樣的舉動乃是相當怪異且可疑的;在這樣一段對話之後,比較有可能出現的或許是一場關於安全鎖或者行動檢測器之好處與價格的討論。
現在有一個論題,它始終可以透過更複雜的方式來進行討論 — 以犧牲諸如吸煙有害健康或者暖氣費等所有其他問題為代價。他者與自我也可以在後來和在別處再返回到這樣一個論題來,並且可以一直不斷提供進一步的觀點。假使他們成立一家保安公司的話,他們或許也會期待在此一論題上經驗到某種完全未知的事物。現在,在這裡反而非常有可能是專業人士在辦公期間溝通關於竊盜破門而入的風險問題,而並不是與偶然的遭遇相關,因為這裡的溝通是以一種公司的形式被組織起來的。組織以可預期的方式將成效的角色與委託人的角色聚集在一起。博物館、美術館、大學或者拍賣行等,也是屬於這類的組織,它們使得人們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時間裡,與某些特定的人,在某個特定的地點,協商探討某些特定的事物複合體。但是,它們的基本要素也是溝通,別無其他,而且假使此一在這裡被組織起來的溝通形式沒有再被延續下去的話,這個組織系統便會崩解。每一個溝通都可以在它的時間面向、事物面向、社會面向和空間面向上對自己提出諮詢,並且S.455區分出各自處理它們自己在這一方面問題的諸機制。傳播媒介或者交通工具克服了空間的問題,儲存媒介、儀式或者傳統彌補了時間的問題。相對地,溝通的符碼化將所有的文章都指向了某些特定的事物問題,並且絲毫不關心撰寫人的社會狀態,即使它對於參加一家俱樂部、一場開幕派對或者一個協會的門路而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更為複雜的形式始終是與專殊化的過程雙雙對對出現,而且,一旦某個特定的複雜性形式,除了在一個相對應被專殊化的脈絡之外,便根本再也不能予以協商討論的話,我們便可以提到一個社會系統的分化。當人們在這樣一種特定的脈絡中,使用了特定的工具手法來處理的這個問題,乃是具有整體社會的重大意義,並且因此是涉及到每個人的時候,此所關乎的便是一個功能系統。不管我們是否和在場者彼此之間的互動,與諸如公司、政府機關、博物館或者藝術協會,或者和功能系統有關 — 這個問題在所有這些情況下都會被拿來溝通,而且區別主要在於人們分別如何處理溝通的極不可能性以及它的複雜性的方式。
魯曼的理論工具顯然忽略了我們常見的宏觀社會學與微觀社會學的區分。因為一扇開著的窗子所產生的一個暫時性的互動系統,可以藉由相同的概念來予以描述,就如同卡爾斯魯爾那場具有高度預設的、探討關於今日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被稱為『美』的討論一般,我們只能在一個特定為此分化出來的科學系統組織的脈絡中,來想像這樣一場討論。同樣地,這樣一場對話 — 如同窗邊的那場對話一般 — 也是從第一篇文章開始,不過這個開頭和接下來可以延續下去的東西,無論如何都不是恣意的,因為這裡有一個論題(藝術),一個符碼(人們因此爭論道:科學的符碼指出了各式各樣常見的位置,而且本身是以研究的位階為取向等等),而且感謝這個在某段特定的時間內,將所有參與者集中在某個特定的地點中的研討會組織,人們因此有可能可以在繼續往下進行之前,回歸到那已經被說出的事物上,將諸論點聯結在一起,標記出一致性或者不一致性等等。所有這些都在互動的過程中將某些特定的銜接排除出去,並且同時提高那些或許在學術研討會的一開始S.456並沒有引起反響的文章的機會。倘若人們採用一種同時也備受他人讚揚的方法論、理論信念或者飽含學識的慣用法,來處理某個特定的問題的話,那麼讓其他人銜接上自己的文章的可能性便會提高。倘若他們根本就無視於這一切的話,這樣的可能性便會降低。正如藝術系統熟知各類不同的、在歷史上變動更迭的風格、禮節與流行時尚 — 在這些風格、禮節與流行時尚的架構之外,一件作品只有非常渺茫的機會,可以被接受為具有重要性的藝術 — 一般,科學系統中,規定什麼東西必須以什麼樣的方式被表述為什麼樣的論題,如此它才會被視為具有可信度的諸條件,也是無時無刻不斷變動更迭 — 自從數年前,『系統論』被納入媒介研究、文化研究、社會研究與文學研究的基礎課程規範之後,一個探討藝術符碼的命題本身所具有之銜接能力,在今日乃是完全不同於在1974年時的。倘若沒有這些科學的制度的話:大學、學術著作出版社、研討會、博士生獎學金、特殊研究領域等等,魯曼的報告 — 它本身理所當然已經預設了這樣一個系統 — 就會如同一塊漂石一般,漂流在這一片學院的景致之中。假使沒有藝術系統的相對應設施的話,那麼關於鯊魚的腐敗是否屬於藝術作品或者根本是毀了它的辯論,也將會同樣是難以理解的。這樣一種類型的溝通引發共鳴的不可能性,就如同藝術溝通的符碼之一以及為其目的所設置的諸制度、出版機構與功能角色一般,會因為全社會的『演化成就』而一轉成為高度的可能性。
IV. 藝術的諸區分
不管上帝是否將光亮和黑暗或者陸地和海洋劃分開來,或者某人也只是開立了一個帳戶或者預訂了一班飛機:一開始始終會出現一個隱含著決策意義的區分。為什麼是搭飛機,而不是坐火車,或者是自己開車?為什麼是這樣一個航線,而不是另一條?價格或者舒適度,究竟哪一個比較重要?一連串的決策,最遲得在網路上開始實際進行那五個步驟的預訂過程時做出來(或者由一名觀察者將這些決策強加在旅行者身上)。藝術作品同樣S.457也是從第一個的運作開始,這個運作同時做出一個區分並且做出一個決策, 好比說,在不同的媒介、格式、技術、藝術類型之間做出區分,並且做出使用某個特定的媒介,而不是所有其他媒介的決策。即使是上帝這位造物主也不再能夠躲在他自己的分化背後,反而必須在第一個區分的基礎上建構出所有進一步的事物,並且將鯨魚擺在水中,將人類擺在陸地上。一個一旦開始啟動的差異序列 — 這些差異全都做出了一個「此而非彼」的決策 — 將它自身結合起來,並且藉此獲得了形式。新的運作在作品之中的銜接能力界域,將會愈來愈狹隘。藝術家作為一個信心十足地掌握其自身創作的天才的『第二上帝』,如今已經被廢黜,但魯曼對於藝術作品的運作性理解,可以為這些藝術家的自我描述做出正確的評價 — 這些藝術家們傾向於將自身視為他們作品的媒介,並且打算讓自己沈浸在一個由差異所組成的級聯所自我生產出來的漩渦之中。
但是,『即使自由度是有限的,人們依然可以在其中做出決策』。 藝術作品可以被描述為諸區分的序列,這些區分在它們的鍵結過程中創造出進一步的銜接可能性,並且撤除了其他的可能性。一本小說可以在持續了一百頁之後,用許多不同的方式來繼續計數,但卻不太可能轉換成另一種語言,或者將小說裡的角色整個撤換掉,或者放棄掉原有的敘事角度或情節,而且也絲毫不可能以十四行詩的方式來為文本作終結。
從《社會的藝術》(Kunst der Gesellschaft, S. 316)擷取出來的這個魯曼的圖表,將藝術作品想像成一個濃縮的運作序列。每一個從運作到運作(Op)的步驟都會做出一個決策,這個決策乃是以「適合或不適合」、「成功或不成功」、「一致的或不一致的」、「美的或醜的」、「有趣的或無聊的」、「零或一」(0/1)為導向。每一個被執行的運作(從Op□到OpΩ)都是偶連的,因為它始終無視於其他的可能性,並且將這樣一些(而不是其他的)回溯或預測的條件實在化。而且,在持續增長的複雜性條件下,每一個運作也都應該是『合適的』 — 不管是否作為一種斷裂的策劃與展演,它也都必須作為綱要的『前後一致的』部分而變成可見的,否則這件作品就會被視為失敗的。
這樣一種序列模式可以同時適用在藝術的製作以及藝術的觀賞上。現在發生的這一切,對於之前所聽到的、所看到的、所閱讀到的事物而言,究竟適不適合?我在括弧中加上了「媒介的選擇」 — 我們或許可以將它標示為第一個決策 — 以及「最後一個運作(OpΩ)」 — 這個運作被賦予了一個透過運作的方式來封閉作品的艱難任務,也就是說,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來驅動這樣的事實:這幅畫已經完成了,這本小說已經到了尾聲,這個事件已經過去了,或者這個雕塑藝術已經是完成的。我們也可以藉助於相同的遊戲理論圖表,來展現出投資的綱要、一段打情罵俏、或者一段為了開著的窗子所展開的對話;當然,符碼化已經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將一件藝術作品指認為一件藝術作品,這並非意味著人們喜歡它。此外,自我認識到一些選擇的提供,區分出訊息與告知,並且在這樣一個意義上理解他者,這同樣並非意味著,自我也對他者表示贊同。我們無法從溝通的成功與否 — 即使是藝術的溝通 — 中推導出『接受或者拒絕被溝通的意義』的優先性。 自我也可以理解他者,即使他大叫出聲:「這扇窗對我來說怎樣都無所謂」。他者藉由他的告知達成了某種全然特定的事物 — 好比說,關上窗子 — ,這樣的情況雖然是有可能發生的,但是從所有其他同樣可想像的互動延續觀點看來,這看起來似乎是極不可能發生的。理解絕對不是暗示著共識。魯曼徹頭徹尾地提出了所有論述倫理學家都抱持的這樣一個希望,當他 — 而且他在卡爾斯魯爾的所有對話者當中,S.459也沒有一個人會同意這樣的說法 — 在討論中插入這樣的意見時:溝通『根本只會在那兒發生,而且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且當有差異存在之時。在完全相同的旨趣位階上,溝通就會成為多餘的。』 共識導致了沈默,導致了所有溝通都急凍而死。即使是指涉理論或者對應理論的擁護者 — 他們將語言固定在這個世界上,並且為真實的陳述表述出規則(諸如『這扇窗子是開著的』等『斷言的』或者『表願望的』語言行動) — 也被魯曼當眾羞辱了一頓,因為甚至連我們這個簡單的例子,也無法透過這樣的模式來予以描述。什麼樣的訊息會被告知,這非常明顯地並非取決在「有一扇窗子開著」的說法是否切合實際,反而是取決在溝通過程中諸選擇的相互聯結:『溝通既不是主要透過訊息的正確性(真理),也不是主觀地或者行動論式地透過告知的動機,而且最終更不是透過使得理解變得可能的語言與文化(傳統),與這個世界關連在一起。』 溝通無法被化約成它的任何一種構成要素,它也無法和外部世界、意圖、或者論述與性情結合在一起。換句話說,溝通如何在一個具體的情境中銜接上溝通,這個問題因此既不是現實主義者,也不是詮釋學家或者論述分析家所能預知的。那麼好比說系統理論家可以嗎?答案是不,但魯曼從這個想像的困境中,創造出一種『方法論式的』德行。他很明確地在探索追尋那些『可以成功將一般正常的事物解釋為極不可能發生的』理論。
溝通的成功、符碼與諸功能系統的形成、諸結構的存續、諸過程的進程等,魯曼的確將所有社會秩序全都視為極不可能發生的。此一理論架構引發了這樣一個臆測,亦即,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藝術溝通上,而且事實的確如此。即使其所關乎的並不是腐敗中的鯊魚,反而是木板畫或者華格納的歌劇時,藝術溝通依然有著非常高度的預設條件要求。它因此無法如同一段關於開著的窗子的對話一般,以如此機會論式的、非特定的、開放結果式的方式被執行與運用。藝術作品作為一個運作的序列,它要求S.460那引導著從藝術類型或者媒介的第一個選擇,到最後一個句子、最後一筆畫、或者最後一招的選擇過程的決策綱要,必須被一併注意到。在一個具體作品的層面上,此所關乎的乃是一種觀察,觀察某個特定的運作如何『在具體的一致性準則下,並且注意到那還因此必須出現在其他位置上的事物』讓自己關連上前一個運作。 這樣的情況可以說與對話的過程或者法庭的訴訟程序是一模一樣的。一個將藝術作品理解為藝術的溝通,它的特殊性就在於它的符碼化:某種事物是否是前後一致的,這並非取決於窗邊的對話情境以及他者的心情,或者取決於檢察官的起訴、目擊證人或者已經改變了的法律形勢,反而是取決在每一個對於此一作品之諸運作的觀察最終圍繞著的『美或醜』的問題上。我們是否要以這樣一種或者另一種方式來為符碼命名 — 一個已經被多次討論過的問題 — ,這對於魯曼而言並不是決定性的問題,重要的反而是與其他諸如好比說「真的/假的」或者「好的/壞的」等符碼形式之間的差異。符碼是『不可或缺的,當此所關乎的乃是藝術或科學如何將自身與全社會的其他功能系統區分開來之時』。 在一篇科學評論的脈絡下所提到的一致性,其所代表的意思乃是不同於在避險基金的投資計畫、結婚喜慶或者俳句的脈絡下所提到的一致性。
這裡涉及到了現代社會的一個依然相對新近的、『首先是極不可能的』演化成就: 亦即,人們在觀賞美的事物之時,他們心裡想到的並非主要是它們的真理、它們的超驗、它們的道德利益、或者它們在展現統治權上的可應用性,他們反而S.461是在生產以及接受的過程中,以「美/醜」的區分為其取向。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來,藝術家和藝術接受者從頭到尾只有根據這樣的事實才能夠被辨識出來:亦即,他們讓他們的溝通以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受到藝術的符碼所指引。這將他們與其他的觀察者區分開來,對於後者而言,藝術作品所關乎的乃是價格、使用權、意識型態的內容、哲學命題的闡述、可中介給學生的能力、情色刺激、或者精神性的啟發等等。藝術的符碼化標記出『一種特殊演化的起飛』, 在這樣一個起飛的過程中,各式各樣的形式被建構出來 — 例如說,新的音樂、展演、哈利波特小說、漫畫、或者導演劇等 — ,這些形式絕對不能被描述為對於那些也是如此存在於藝術的社會環境或者甚至是自然中的事物的重複或者再現。 『這種在全社會之中分隔出一個藝術特有演化領域的趨勢,出現在當藝術作品本身在不具任何外部支撐點的情況下,自行決定什麼是一致的(美的)以及什麼是不一致的(醜的)之時。』 正如在經濟系統中,只有以一個有限資源的市場為取向的價格存在,在法律系統中,只有其合法性主要取決在有效的法律以及嚴格遵守的程序規則的判決存在,而且在政治系統中,只有做出一些也可以約束牽制那些根本沒有參與在決策過程中的個人的決策一般,藝術作品 — 其功能僅僅在於『對一個並非自發地出現的形式安排中的秩序進行溝通』 — 也只有在藝術系統中才會被製作出來且被論題化。 在現代社會中,不管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還是一位悲傷的母親,都不是天生便具有藝術價值的。這裡只有溝通才能算數,而不是那或許根本就不是『在藝術系統中』被製造出來的事物。在文學研究中,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的詩《1968年1月27日紐倫堡第一足球會的創立》(Die Aufstellung des 1. FC Nurnberg vom 21. 1. 1968)便因作為此一代表例子而聞名 — 一篇在報紙的體育欄中發出關於一個足球協會成立球隊訊息的應用文本,S.462也可以變成一部文學作品:『瓦伯拉、李歐普、波普、路德維奇、米勒、維諾爾、布蘭肯堡、史達瑞克、史垂爾、布倫格斯、漢茲.米勒、沃克特 — 比賽始於:下午三時』。 人們在這裡根據杜象(Duchamp)的作品提到了『文學的現成品(ready-mades)』。 許多已經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聲稱自己是作品;重點只是在於透過「人們察覺到這個將球隊的成立轉換成文學,或者將某些腳踏車零件轉換成一種現成品」的方式來引導溝通。對於這些起決定性作用的區分而言,它們在社會環境中並沒有 — 馬克斯.英達爾也已經在卡爾斯魯爾指出 — 任何的對應物。 在分析漢德克的詩或者杜象的《腳踏車輪》(Bicycle Wheel)時,以溝通的方式被一併考慮進來的諸差異,乃是藝術的特殊符碼化以及其媒介與類型的內部演化所產生的產品。相反的,藝術作品可以被忽視或者誤解,因為它的單純存在並沒有將它揭示為一種對於藝術的貢獻,反而是相對應的觀察才會這麼做。無數個關於最終落在垃圾桶中的肥胖角落(Fettecke)的奇聞軼事,或者訪客掛上他們大衣的設備,都嘗試要證明藝術作品無法強迫人們遵照藝術的方式來注意它們。相對地,根據魯曼的說法,就『觀察藝術作品本身』而言,決定性的部分就在於察覺到,藝術作品做出了一個『獨立的且無法用另一種媒介來予以解譯的對藝術的貢獻』。 此所關乎的,並不是嘗試要在一幅畫上去告知「馬兒有四條腿,這位或是那位足球員代表紐倫堡在足球場上奔跑,某人悶不吭聲,或者坎貝兒(Cambell)的蕃茄湯罐頭有著紅色的標籤」等訊息。所有這一切的確有可能是如此,但重要的並非在於溝通的異己指涉這個方面,反而是在於它的自我指涉、它的形式、它的方式等等。『訊息在作品中被外部化,它的告知S.463則是源自於它那讓人得以辨識出它是被製作出來的人工性。』 而且這樣一種被製作出來的(換句話說,也可能是以不一樣的方式被製造出來的)客體,將人們的目光集中在它的形式上 — 至少當觀察者參與在這樣一種藝術溝通的供應中之時是如此。引人注目的,並不是「可以在這幅畫上看見一匹馬」,反而是這幅畫究竟是如何被畫出來的。湯姆.吳爾夫(Tom Wolfe)引述《笨拙畫報》(Punch)的話:人們並不是去畫出『關於某種事物,我親愛的姑媽』,而是『單純地作畫而已』。 某種事物必然只向這位親愛的姑媽指出了,鑑於此一被畫出來的事物,其所關乎的乃是一幅畫,而不是一片胡亂的塗鴉。魯曼為《探討藝術之文本》(Texten zur Kunst)所給出的答覆是:『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是藝術』,系統是以一種完全『不受對象影響』的方式來發揮功能,然而,它必須『可以被辨識為屬於藝術的』,否則『它便不是藝術』。
『唯有當藝術作品的觀賞者解譯出作品所使用的區分結構,並且據此辨識出,某種事物並不是可以自發性地產生之時,觀賞藝術作品的行動 — 將藝術作品視為藝術作品,而不是某種屬於世界的客體 — 才會成功』。作品的形式選擇,並不是僅僅在一種重新辨識出被再現出來的諸形式的意義上,來吸引感知,反而是引導觀賞者去『感知感知的行動』。 但是,某人確實將某種事物辨識為藝術作品,並且讓他的感知以及關於其感知的溝通受到某些特定的符碼與綱要所引導,這樣的事態乃是一種首先使得藝術作為藝術得以和其他不同事物區分開來,並且允許社會學將藝術描述為一個自主的溝通系統的成效。這種不僅使得這樣一種藝術特有的溝通變成可能,同時也賦予和鼓動了一些可能性的社會建制,乃是藝術的符碼。一旦這樣一種符碼的建構使得溝通變成可預期的 — 這種溝通並不是以政治、經濟、或者科學的準則,反而是以作品本身之中可以感知到的「美/醜」或者「一致的/不一致的」區分為取向 — 時,那麼S.464諸如一堆罐子或者洗滌劑、一車子的家具、一張『在空中』進行拍攝的照片、或者一張藉由『線條安排』來予以描繪的『黑色污漬』群等這類值得注意的選擇提供,確實作為藝術而引起重視的可能性便會提升。
符碼並不會事先規定什麼東西分別可以被具體地視為美的或醜的。這一切都取決在藝術每每所使用的綱要上 — 諸如一個具體的判決主要取決在那將法律符碼綱要化的法律形勢上一般。藝術作品也可以透過和自我所提出的要求相比較,和時代分期的風格指標相比較,也就是說,透過關注藝術符碼每每所使用的綱要,而被視為失敗的、醜陋的、或者無聊的 — 但是,至少在現代世界中,僅僅因為藝術作品在褻瀆神衹或者商業上是成功的,因為它並沒有正確地展現出階級立場,或者沒有對應於某種特定的哲學教義,而將它標示為失敗的,或許是不適當的,而且長久下來可能是徒勞無功的。即使是阿多諾也無法成功地貶低爵士或者好萊塢電影的價值,而且那過去基於政治的理由而受到高度讚賞的『社會現實主義』大師們,在今日幾乎已經全都被遺忘。藝術符碼化的社會制度化將這類的視野觀點全都過濾掉,並且將這樣一種『藝術』的論題化任務指派給其他的系統,後者並非將『藝術』符碼化為藝術,反而是符碼化為商品、廣告、理念、意識型態或者上帝的啟示的媒介,並且每每根據綱要來做出推薦或者提出譴責。
雖然藝術符碼的分化提高了對於一種希望作為藝術溝通被進一步延續下去的溝通的要求,但是,當它被S.465相對應地符碼化之時,它同時也提升了這樣一種溝通成功的可能性。我們已經觀察到的「複雜性的提升」與「專殊化」之間的關連,在這裡又再度發揮了作用:這種以一個特殊符碼為取向的趨勢,一方面使得始終愈來愈不可能的溝通形式得以產生 — 不過這些溝通形式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境中才會具有銜接能力 — ,另一方面,藝術系統透過它自己的固有建制,諸如博物館、劇場、朗誦會、歌劇院、交響樂團、慶典、藝術雜誌、以及文化節目等,來注意到這類的情境並不必然是偶然發生的,它們反而是可以被期待的。即使是一齣極端前衛派的戲劇的生產,也會因為這樣的遠景而受到鼓舞:它可以在揀選出來的圈子中被感知為藝術,而且即使是在『失敗』的情況下,它也依然是藝術系統的一部份。從魯曼的觀點看來,失敗的藝術也是一種藝術,而不是非藝術,不然還可以是什麼?正如一位經濟學家可以對不景氣或者破產倒閉感興趣一般,對於藝術的科學觀察者而言,下述的這樣一種觀點具有一個好處:我們也可以留意『失敗觸礁的』作品,將其視為新的嘗試的可能資源。不只是美麗的或者一致的作品,還包括醜陋的或者不一致的作品,都可以激發出各種銜接、評論、承接、變異的可能性。
V. 魯曼的風格
這裡所收集的魯曼的所有關於藝術與文學的重要文本中,魯曼嘗試用一些他所潛心研究的理論創新,來做出各式各樣的實驗。他在他討論『藝術的自我再生產』的評論文章中,測試了胡貝托.馬圖拉納(Humberto Maturana)和法蘭西斯可.法瑞拉(Francisco Varela)的『自我再製』理論,而且在他重新發現弗里茲.海德(Fritz Heide)於1926年所撰寫之探討關於『事物與媒介』的文章時所得到的收穫,激發了他關於《藝術的媒介》的思考,在重新發現喬治.史賓塞.布朗(George Spencer Brown)的《形式法則》(Laws of Form)時,創造出《世界藝術》這篇論文的運作性觀察概念來。假使我們不去追尋魯曼的理論發展痕跡,或者不去熟悉馬圖拉納、海德或者布朗的著作的話,那麼我們便很難進入魯曼的這些文本中,因為我們始終會一再面臨到必須去處理新的概念或者舊概念之新意含的困境。誰要是好比說在符碼化的問題意識架構中,參與在討論象徵性S.466一般化溝通媒介的理論中的話, 他便會問自己,這樣一個媒介概念跟演化理論脈絡中傳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跟大眾媒體的實在,或者跟「媒介/形式」的差異之間,可能有著什麼樣的關係。而且假使他認為下述這些命題非常具有說服力:『每一次揮毫的筆觸、每一個文字的選擇,都需要做出一個決定』,有鑑於『隨後的決定』,此一決定必須切合『整體結果』並且符合『美與醜的符碼差異』, 而且我們稍後還會讀到,『然而,對於藝術的自我再製而言,藝術作品既是一種條件,也是一種障礙』; 對於藝術作品而言,『媒介與形式的差異乃是作為一種差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或者藝術作品會『透過預先為觀察者規定出當他〔原文!〕想要參與在藝術之中時所必須遵循的諸區分,來要求對於觀察的觀察必須遵守紀律』。 我們可以很容易再繼續列舉出其他的例子。
魯曼將自己描述為一個當他『專心致志於一個諸如〔…〕「藝術」的題目』時,他應該『努力不再為此一事態情況增添任何新的東西』的『社會學家』,而當我們始終必須一再注意到,他對於藝術的『再描述』是多麼地仰賴於每每被使用的『系統論式描述工具』,以及這些工具是多麼地容易產生改變之時,這樣的自我描述便帶有一種反諷的色彩。因為魯曼在他的『系統論工具』上,始終會一再作出『重要的變更與修正』,例如說,透過補充『運作封閉性的原理』以及與此相關的還有『自我再製系統的理論』。
倘若我們使用這些從1974年到1977年的文本,來在進行觀察的同時觀察觀察者的話,那麼我們當然可以提出一個魯曼在致力於S.467藝術研究的方向上普遍依循的基礎問題。「某個事物為什麼是如此,而不是另外那般」,這乃是魯曼的核心問題。這樣一個問題是如此地簡單且成果豐碩。它將所有現在如其所是般無可或缺的事物帶到某個距離之外,並且讓它回歸到一個偶連性與極不可能性的地帶中。這樣一種創造出魯曼作品之思維風格的理論形態,會被應用在所有的層面與領域上。 在我們的脈絡關連中,這樣一個問題的內容是:為什麼會有藝術,藝術是如何可能的?這樣一個問題導向了一個整體性的考量:藝術是不是一個功能系統,它是如何在時間中保持不變的狀態,它是如何型塑出個人的角色以及組織,它是如何將自己與其他的系統做出區分,而且這樣一個系統的特有問題可能會是什麼? 相同的理論形態在具體藝術作品的運作層面上解消成一個序列,為了在每一個步驟、每一個組件、每一筆畫、每一個字或者每一個音調上去提問:為什麼是如此,而不是另外那般?針對這樣一個問題,那將諸決策都取向於一個特定的藝術符碼綱要的趨勢,給出了第一個解答。不過,魯曼始終還是一再不斷提出這個問題。不管是藝術家、藝術作品、風格的時代分期、還是藝術的類型,只要他/它是以這樣的方式被觀察的話,便會喪失他/它的不證自明性,並且作為從一個可能性的界域中所做出的一種具有高度預設且極不可能發生的選擇,而變成可辨識的。 每一個運作都開啟且封閉了一條通往後續運作的道路;每一個運作都是偶連的,換句話說,既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必然的。唯有作為一個具體的、可觀察的且可描述的『諸區分的秩序』,藝術作品才能夠將自身建構成一個在世界中的形式,但是,僅僅因為其他的決策本來也是有可能的,藝術作品因此可以被描述為一致的、美的或者成功的。 對於魯曼而言,藝術作品的成效正好就在於:它將它的形式展示為必然的,並且同時讓人可以辨識出這樣一個形式的偶連性;而藝術系統的成效,則在於準備好提供溝通的諸形式,這些形式使得人們有可能以這樣的方式來觀察和描述作品。在我們的S.468對話例子中,不管他者是否說出這扇窗子是『開著的』或者是『打開的』,對我們來說可能怎樣都無所謂;相對地,當這樣一些字詞被應用在一首詩的作品上時,重點就在於 — 我們想要的究竟是兩個音節還是一個音節,一個男性的聲音還是一個女性的聲音,或者也許是一個韻腳?針對「為什麼是如此(『打開的』)而不是另外那般(『開著的』)的問題,這首詩勢必要給出一個答案。藝術作品的形式決策因此出現為必然的,因為它『以一種自我限制的方式佔據了所有以不同的方式出現的可能性』。 同樣的情況當然也會出現在所有『偶然』作為一種程序而被置入其中的勞動上,因為這樣一種偶然的置入本身並不能以偶然的方式來產生作用,反而必須被驅動為一個專為此而精挑細選出來的程序。現代的(也就是說,自主的)藝術有義務要『規範自我生產的可能性過剩』。 換句話說,在系統論的典範中,恣意性或許是一件作品可能面臨到的最嚴重指控。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任何一個引導選擇序列的綱要可以被辨識出來。相對地,一個沒有替代方案的形式 — 這樣的情況應該是可想像的 — 既不是美的也不是醜的,因為它沒有任何選擇,可以讓自己如其所是般地存在。相對地,魯曼將諸形式 — 它們的運作並不是以『藝術特有的方式』被結合起來,反而是例如說依循『政治事務』的指標 — 視為『一種陪襯、一種裝飾、一種臨時性的豪華手段』。 魯曼建議,我們不應該讓這樣一種也可能出現在宗教或者經濟面上的『濫用』, 『回過頭去擊潰原本固有的準則意識』, 而且他以相當令人信服的方式指出,『光是在時間的推移過程中便可以注意到,這種以政治或市場為目的的意圖,將會逐漸喪失其意含』,因為最終會提出的只有這樣一個問題:『這件作品在藝術上究竟是不是成功的?』
VI. 意義與選擇性
S.469魯曼在一次訪談中表示:『我對「人」不感興趣』。 這類以及類似的陳述已經嚇壞了許多人。但是,魯曼所說的意思只是:在他的全社會理論中,『人』只是出現作為一種論題,或者作為一個歷史語意的參照點罷了,但並不是作為一種元素。因為社會系統進行溝通,它們是由溝通所組成的,而不是由人所組成的,而且即使是藝術系統也不是由藝術作品所組成的,也不是由美的事物或者易感的接受者,反而是由溝通所組成的。不過,溝通預設了心理系統對於藝術的感知。這些心理系統以感知的或者意識的媒介,而不是以溝通的媒介,來進行自我再生產。溝通不會感知自身,它充其量只能將感知論題化。意識也不會溝通,它充其量只能觀察溝通。雖然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乃是彼此的環境,但它們相互預設彼此,並且擁有某種共同性:它們雙方都處理『意義』。 這裡所關乎的乃是一種前語言的意義概念,它取決在一個簡單的差異上:『當下的事物與可能性界域之間的差異』。 不管是透過溝通的媒介,還是透過意識的媒介:意義都會設定一個區分,這個區分的其中一面會在運作上被使用,而另一面則保持為未被限定的。所有這些都會被感知 — 而且不是所有其他的事物;所有這些都會被告知 — 而且所有其他的變體都不會被實在化。每一個『特定的意義都會藉由引發某些特定的銜接可能性,並且使得其他的可能性變成極不可能的或者困難重重的或者瑣碎冗長的,或者(暫時)排除掉其他的可能性,來認定自己的資格』。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感知上:唯有當人聚焦,並且將其他事物推擠到視野的邊緣之時,他才會看見某種事物。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意識上:人們只能集中注意力在某種事物上,沈浸在某個特定的想法裡,追尋一個聯想,回憶起一個特殊的體驗,而所有其他可能性則在這一次中保持為潛在的。而且同樣的道理S.470也適用在溝通上,因為每一個銜接的運作不僅將一個變體實在化,並且始終也將其他的變體從溝通的當下延續中排除出去。每一個在偶連性替代方案的背景下所進行的現實化過程,都可以根據魯曼為藝術所寫入(圖表二)的運作圖示被展現出來。而且,如同在藝術的例子中一般,魯曼也在意義的例子中提出了這個問題:為什麼掌握住這樣一個現實化的可能性(而不是另一個)的情況,會是更有可能發生的呢?這個表面上看起來如此簡單的運作的事實 — 人們正好感知到他們正好在感知的東西;人們正好思考到他們剛剛在思考的東西;溝通就正好如同它剛剛進行的方式進行 — ,被標示為一種選擇的結果,這樣一個選擇必須在許多同樣是可想像的諸選擇的界域之前,被視為偶連的且極不可能的。換句話說,每一個具體的秩序都絕對不是必然的,反而是一個具有高度預設的選擇序列的結果。這整個社會系統的理論計畫,乃是靠著指出它們的觀察對象的偶連性與極不可能性為生,如此才可以為諸機制提出一些建議,讓一個具體的運作出現為可期待的,並且藉此來驅動某一個特定的選擇。換句話說,即使是藝術,也只有以一種『選擇』的形式出現才會有意義,而且這裡的問題是:什麼東西為什麼會被排除出去? 是一個正在流行的、以形式決策為取向的時代風格嗎?還是藝術類型的規則,或者是所使用之媒介的限制?將藝術作品觀察為偶連的形式或者被現實化的意義的行動,都需要提出這類的問題。這樣一種思維形態也支撐著這篇極富影響力的、關於藝術的媒介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媒介與形式的區分被引入,並且也對魯曼的觀察理論產生重大的影響,這個理論在1990年代探討藝術的文本中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不管我們是否用一隻柺杖在沙子上畫出一些人物形象,或者將漆石射在房子的牆壁上,不管我們是否在將塑膠袋加工處理成服飾,將車子駛過一條畫布,或者開闢一座庭園:在上述所有這些例子中,經過系統論的解消之後我們看到,形式不過就是從可能性的界域中所挑選出來的一個選擇的具體結果罷了 — 有一大堆的運作S.471和可能性可隨時供它使用,有不同的顏色、音調、或者還有文字,但是,始終只有某一個特定的顏色、音調、或文字,可以從中被選取出來。換句話說,形式始終暗示著:捨棄各種可能性、決策、選擇。同樣的道理也可以應用在觀察的運作上,魯曼借用史賓塞.布朗的說法來將其稱為形式。一個觀察始終會做出一個區分。這個差異的內部面會被列入考慮,而同時間產生的外部面則被忽略。每一個觀察始終都是在觀察某種特定的事物,而且唯有當對於這樣一個特定事物的觀察與所有其他事物劃分開來之時,這一切才是有可能的。進一步的區分可以在形式的內部面上建立出複雜性,然而,對於觀察者而言,形式的外部面卻保持在不確定的狀態中。這種不確定的事物保持在觀察序列的『架構』之外 — 保持這麼久,直到觀察者轉向形式的外部面,並且也在這裡再度同時進行觀察和區分為止。觀察的計算也是藉由偶連性的魔杖來改變這個世界 — 那一再被觀察的事物,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來予以觀察,也就是說,藉由其他將其他的事物帶入形式之中,並且排除掉其他事物的區分,來予以觀察。倘若其他的運作是可能的話,那麼每一個具體的運作都可以被理解為選擇。經由選擇性所營造出來的感覺。誰要是以這般反身的方式來觀察諸觀察的偶連性和選擇性,他便可以在任何一個必須注意到不同的事實、資料、事物的地方,看見偶連的觀察過程及區分過程的結果;而且這些事實、資料、或者事物都可以證實是形式。魯曼因此宣稱,『客體和生產過程指的是同樣一件事情〔…〕,因為兩者都是由於執行了「做出一個區分」的指示而出現,而且兩者同時出現。』 即使是觀察的形式,也可以被回溯到現實化與可能性界域之間的差異上。這樣一個差異雖然可以被忽略,但只是要付出這樣的代價:我們無法理解一個他人在其中以不同的方式來進行觀察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現代的社會中,這才是規則, 而且愈來愈多的觀察者都朝向同一個方向進行觀察,並且S.472打算擁有相同的客體,這樣的事態才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解釋的奇觀。
走經過一個房間,並且興奮地驚嘆所有一切都是如此現代的兩個人,被認出是某種裝置的一部份,這樣的事實預設了一種彷彿是由藝術溝通所賦予的感知,它可以辨識出這樣一種形式的媒介(好比說,『這是如此現代的!』這句話的影射界域、威尼斯的德國展示館中的白色立方體、兩個監督勢力的團體與意見等等)。相對地,誰要是將他的感知集中在一個主人翁的形象上,他便不是在觀察藝術作品,反而是例如說在區分出吸引人的和不吸引人的肢體,或者區分出男人和女人,或者年輕的和老的。不過,這樣一種觀察者也可以受那些有意義的差異所引導,因為它們選出了某個特定的事物,並且排除掉其他的事物,或者因為觀察設定了一個區分,這個區分的其中一面(往例如說「不吸引人/吸引人」、「年輕的/老的」、「男人/女人」的方向)被繼續分化出來,而所有其他的事物則被忽略。不管是形式、觀察、或者意義 — 此所關乎的始終是進行選擇與排除的選擇。被挑選出來的將會被繼續加工處理,人們會觀察細節,辨識它的細膩之處,發現比例、和諧、對比、或者斷裂;與此同時,被排除出去的則保持在『暫時未被實現的狀態』。 這其中也包含了這樣一個可能性:觀察者從一位表演者的吸引力或者迷人的醜陋中掙脫開來,並且注意到那引導堤諾.塞格爾(Tino Seghal)為2005年雙年會做出貢獻之諸形式決策的綱要。為了以這樣的方式進行感知,人們必須進行溝通,而且下述這些事實是非常值得瞭解的:塞格爾曾經攻讀過舞蹈編舞法,並且在2004年柏林冬季舞蹈大賽(Berliner Tanzwinter)的脈絡下,毫不掩飾地重新建構出二十世紀最不一樣的舞蹈風格。不管人們現在是否想要探究這樣一種展演的意義,希望描述這件作品的形式,或者觀察它的綱要 — 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此所關乎的都是:系統論式的架構一開始最先解除了所有的確定性,並且將其重新建構為偶連的且選擇性的運作。儘管有著各式各樣不斷變換的首要概念(符碼/綱要、觀察、意義、媒介/形式),S.473我們都可以在魯曼的所有文章中,發覺到這樣一種特殊的理論風格。
VII. 媒介與形式的觀察
媒介與形式的差異,區分出了不是以鬆散耦合的方式,就是以緊密耦合的方式出現的諸元素。魯曼借用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的說法,將鬆散的耦合標示為媒介,將緊密的耦合標示為形式。許多事物都很適合作為建構形式的媒介:時間、空間、語言、色彩、肢體、所有有意義的事物、所有可以被區分且被觀察的事物。好比說,語言使得諸元素得以供人使用,還有例如說以句子的形式,來使得緊密耦合變成可能的字詞及連結規則等。但是,肢體同樣也可以在一種使各式各樣的運動、姿態或者表情變得可能,如此人們可以從中做出選擇的意義上,被理解為一種媒介:某個特定的姿勢、腳跨出的一步、一個具體的動作,都可以被理解為這樣一種媒介的形式,因為一些基礎的運作將會被挑選出來,並且被予以組合。形式將一個媒介被挑選出來的諸元素彼此結合,因此唯有在這樣一種耦合中,形式與媒介才會同樣變成可見的。因為我們既不是觀察不成形式的媒介,也不是觀察單純的形式;我們感知為藝術作品的東西,始終是已成形式的,我們從未感知過脈絡、影射、類型、色彩、音調、聲音、空間自身,反而是形式率先且只讓我們注意到它的媒介,因為這個已成形式的媒介首先會讓人注意到,它也可以容許其他的形式出現。塞格爾作品中的監督者-表演者是否可以呼叫著說出某種不同於『這是如此現代的!』的話語,或者他們應該會吸引某種不同的東西?他們是否以不同的方式來做出動作,他們是否應該以不同的方式來提出強調?還有另外一個房間可以被設想成一個架構嗎?假使我們准許更多觀賞者進來觀賞的話,情況會是如何?魯曼的理論語言,允許我們將藝術作品理解為一個擁有複數的「媒介-形式-耦合」的大型形式,它使得人們可以非常精確地描述出一件具體作品的選擇界域。
魯曼的全社會理論的大型論題「分化」,論及了將系統與環境的差異應用在自己身上的應用方式。媒介與形式的差異也是S.474以反身的方式來產生功能。形式可以用來作為媒介,媒介可以在形式中被解消。這些說法裡頭還沒有什麼是藝術特有的。肢體這個媒介的形式,也就是說,某些特定的姿勢、一些跨步的動作或者運動,都可以被描述為鬆散耦合的媒介元素,它們的緊密耦合則可能會得出一種舞蹈的形式(或者一種訓練的規定)。句子的形式建構出一種敘事文本的(或者一種訓練規定)的媒介。書籍代表了圖書館的媒介。或者我們將目光轉向另一個方向,句子被解消成字詞,這些字詞又可以再一次被描述為字母或音節的緊密耦合。如同音樂一般,聲音使用空氣這個傳遞媒介,字母預設了視覺的傳遞媒介 — 人們可以將它們寫在沙地上,刻在石頭上,讓它們作為霓虹燈閃閃發亮,或者將它們書寫在紙上。紙張又再將纖維素、布塊或紙草耦合成緊密的形式。如同弗里茨.海德所示範給大家看的,人們藉由這樣一種區分實現了任何一個大規模的秩序。他們可以將星星標示為星座的媒介,並且可以將這樣一個在筆記型電腦上輸入的句子,解消直到成為記憶體的超小型負載狀態(0/1),也就是說,直到成為直流媒介的緊密耦合。媒介與形式的差異超越了系統論自我設定的界限,並且開拓了超然於溝通之外的空間。預設前提當然是:某人藉由這樣一個區分進行運作:一個將鬆散耦合的元素和緊密耦合的元素區分開來的觀察者。形式計算與觀察計算互為彼此的條件,並且可以彼此轉換。 當某種平庸乏味的事物(諸如一堆沙子)要成為一種媒介時,這就預設了一個觀察形式的觀察者。沙灘上的細沙可以作為鬆散耦合元素的媒介,它的緊密耦合(諸如沙堡、文字、象徵符號或者腳印等)給出一個形式,直到下一波潮水將這些形式解消,並且讓媒介得以供新的耦合使用為止。但是,在這之前,為了可以在別處且在後來將其投影在布幕上,沙堡可以被拍攝下來,文字可以被摹寫下來,象徵符號可以被記憶下來,如此一來,形式將會變成一種新形式的媒介,這個新形式已經跟沙粒沒有太大的關係,反而是S.475跟塗鴉標籤上的詞彙比較有關係。不過,所有這些運作都不僅是在一種『物理事實』的意義上預設了沙子,同時也預設了一個區分出沙子的不同耦合狀態,並且基於這樣一個區分而注意到了腳印的形式的觀察者。
每一個形式都可以再度成為另一個形式的媒介。馬歇.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已於1964年在他的命題中清楚表達了這樣一個洞見:『一個媒介的「內容」始終是另一個媒介。書寫文字的內容是語言,正如被書寫下來的字詞是活版印刷的內容一樣,而且印刷物又再是電報的內容。』 麥克盧漢不僅在這裡已經注意到諸如印刷術等媒介技術,同時也注意到了諸如小說的溝通形式,而且魯曼的「媒介-形式-區分」也開啟了他的諸如書籍、無線電廣播、或者電腦等儲存媒介、傳播媒介、和處理媒介的理論,這些統統可以作用為藝術的媒介,亦即,當它們模塑出可以根據藝術的符碼以及藝術的綱要來予以觀察的形式時,它們便可以作用為藝術的媒介。我們同樣也在「媒介-形式-區分」中注意到了魯曼的風格。每一個具體的媒介耦合,都可以被視為偶連的且極不可能的。而且這又再度涉及到一種一開始跟藝術根本毫無關係的理論,這個理論反而可以或好或壞地將投資描述為金錢媒介的形式,將位置描述為事業的媒介,或者將發送位置描述為電視節目的媒介。如今,是什麼東西讓一個媒介變成了藝術的媒介?這個問題的解答跟卡爾斯魯爾的報告所給出的解答沒有太大的區別:它的形式 — 這個形式嘗試以這樣的方式來耦合一個媒介的諸元素,亦即,它理解到自己對於觀察者而言,乃是出現為強制性的、一致的、美的、迷人的,雖然還有無數個媒介的耦合可以被想像出來。美的形式乃是被抑制下來的偶連性。作品必須透過它所擁有的這個形式來說服我們,這也就是說:它必須跟所有其他沒有被實現的媒介形式相競爭。假使它失敗的話,人們便會將它視為醜陋的形式。有一些參與在這樣一種觀察美的形式或者醜陋的形式的觀察活動中,並且也就其部分而言溝通關於這些形式的觀察者存在,社會要將這樣一個事態的產生歸功於一個S.476藝術系統的分化。在這樣一個系統中,甚至是引述、改變、或者評論魯曼文章,但卻並沒有因此推動社會學發展的作品,也是有可能出現的,因為它們對於科學的觀察(或者媒介的形式)並不必然是符合真實的或者是偽造的,反而是適合一件作品的形式構造的。系統論本身因此也變成了藝術的媒介, 而且負責做出關於此之品味判斷的並不是社會學,而是藝術溝通。
魯曼探討關於觀察概念、形式概念、與媒介概念的文本,尤其是在文學研究、藝術研究和媒介研究中,被證實是格外具有銜接能力的。其中的一個原因可能在於,這些概念構思似乎也能在系統社會學的理論脈絡之外產生功能。這種藉由觀察者計算或者形式計算所進行的分析工作,還無法讓人馬上成為一位系統論者。相對地,魯曼在他探討藝術或文學的文章中始終一再闡明,藝術的特殊觀察(不管是主體的屬格(genitivus subiectivus)還是對象的屬格(genitivus obiectivus))跟全社會的分化形式是多麼地息息相關。現代藝術、它的形式可能性、以及它的觀察模式,全都預設了全社會的功能分化。魯曼採用扼要重述的方式來為《無標題 — 為什麼?》這篇探討弗雷德里克.本生作品的短文作結尾:『總的來說,這也就是:現代藝術。現在的確是如此,不然還會是什麼呢?』魯曼探討藝術的文章的缺點在於,每一篇文章都可以以這樣的方式作結尾。而它們的最大強項則在於,對於那實際上應該是「現代藝術」的東西,它們提供了一種非常複雜且精確的理解。
編者筆記
S.477魯曼的秘書處曾經是一個寶庫。誰要是在九0年代驅車前往畢勒佛(Bielefeld),假使他夠好運的話,便可以在起身回家時滿載一車尚未出版的原稿。魯曼讓他的原稿不斷流通,他的秘書則隨時準備好一份副本或者一份磁碟。
這解釋了為什麼有些在現有文集中第一次發表的文章,在十年前卻已經被引用過,以及為什麼有些文本會出現在一些相當冷僻、簡直是不可能的地方的原因。因為實際上魯曼有些探討藝術與文學的文章,並沒有發表在學術界的文集與期刊中,反而是出現在藝術協會的目錄、讀本、或者教區和文化啤酒廠的系列著作中。
這些文本本身 — 就如同它們的刊載地點一般 — 是如此地風格迥異,而且除了探討一種全社會理論的精緻社會學文章之外,還有一些即興作品和演講紀錄。有鑑於魯曼的藝術社會學,後者的存在幾乎不會令人感到驚訝,但它們卻指出了魯曼如何能夠讓自己去迎合一個對他的全社會理論的預設條件全然陌生的公眾。尤其是他嘗試以富有想像力的方式來一併介紹這些預設條件的努力,使得這些通俗的文章變得具有閱讀價值。這些出版物之中,有一些是學術性的圖書館從未購置過的,其他還有一些則是已經不再供應的。這本集合了所有這些分散各地的、探討藝術與文學的著作的文集,將所有權威性的文本一次蒐集起來,並且讓它們變成可供使用的。
在檢閱這些文章時,我們只修改了一些明顯的印刷錯誤而已。魯曼將逗號使用成頓號的獨特標點法,就如他以希臘文或者拉丁文語幹為取向的拼字法一樣,在這裡被完完整整地保留下來。我們另外補充的,則是那些指出了在當時仍尚未發表、但在這期間卻已經出版了的文章草稿的所有註腳。
這個始於九年前、在法律上並不能說是毫不費力的、將魯曼探討藝術的文章(不管是未出版的還是已出版的)收集起來一併出版的計畫,從一開始便獲得了安德烈.基瑟霖(Andre Kieserling)的諸多支持,S.478對此我感到由衷的感謝。感謝伯恩.史蒂克勒(Bernd Stiegler)與安德烈亞斯.葛哈德(Andreas Gelhard)(Suhrkamp出版社)的耐心、朝目標邁進的決心、以及說服人的本領,並且感謝魯曼-施洛德(Luhmann-Schroder)女士友善地認同了我們的計畫,因為獲得了這些人的幫助,這一本書現在才得以順利完成,在這裡與世人見面。
感謝克勞斯.達姆曼(Klaus Dammann)提供我們許多關於偏遠地區以及尤其是魯曼那一幅畫(第7頁的插圖)的提示 — 在這一幅畫上,魯曼以一種圖解的方式來勾勒出他自己觀察觀察者的模式,並且將他自己標記為『NL』加進畫裡頭去。『被觀察的觀察者』(Beobachte Beobachter)這句題詞乃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這個進行觀察的系統論者的圖像部分中,他是否可以被觀察成一個蝌蚪、火箭駕駛員、海蜇、微生物、或者甚至是眾多要素的其中之一,則還有待進一步的解釋。這幅畫於1990年11月出版於一本巴西的期刊Entao. Jornal de Porte Alegre, Anno I., No. 4中。
我要感謝漢克.德.別格(Henk de Berg)為我們提供一長串的圖書目錄表,薩賓娜.坎博曼(Sabine Kampmann)為我們提供她的批評意見,以及堤摩.卡斯伯(Timo Kasper)為編輯目錄索引所花費的心血。另外,還要感謝所有協助此一出版計畫得以順利進行的出版商與編輯,尤其是弗雷德里克.本生(Frederik Bunsen)、齊格飛.施密特(Siegfried J. Schmidt)、彼得.富赫士(Peter Fuchs)、萊瑪.榮斯(Reimar Zons)、科多拉.郝克斯(Cordula Haux)以及盧德格.克勞森(Ludger ClaBen)。系統論的研究工作為我帶來了莫大的樂趣,能有這樣一種極不可能的且幸運的經驗,我要感謝那既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的益友的葛哈德.普朗波(Gerhard Plumpe)。
倪爾斯.韋伯,2008年3月2日於柏林
譯序
長期以來的傳統藝術理論,其焦點多半仍只侷限在藝術本質的鑽研與探討上,而沒辦法將視野擴展到藝術作為一個社會系統本身的自主性運作觀察上,以及更重要的是,延伸至藝術的觀看者對於藝術的觀察與溝通上。當代社會學系統理論大師尼可拉斯.魯曼於1974年德國卡爾斯魯爾(Karlsruhe)的一場跨學科研討會中,率先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對於藝術的觀察而言,「美」的概念是否還是一個充分可運用的概念?魯曼接著於1976年發表了一篇名為《藝術可否符碼化?》的文章,探討藝術系統作為一個自主的社會領域 — 有別於經濟、政治、科學系...
目錄
第一章 學習閱讀 1
第二章 藝術可否符碼化? 9
第三章 藝術可否符碼化?—節錄自討論中的片段 59
第四章 時代分期的建構問題與演化理論 141
第五章 藝術的媒介 173
第六章 藝術作品與藝術的自我再生產 197
第七章 世界藝術 275
第八章 基於藝術作品所進行的感知與溝通 361
第九章 藝術系統的演化 379
第十章 文學作為虛構的實在 405
第十一章 黑洞、黑色污漬 429
第十二章 『無標題』—為什麼? 435
第十三章 藝術的世界 441
第十四章 藝術系統的分化 465
第十五章 『浪漫主義藝術』的再描述 523
第十六章 文學作為溝通 553
第十七章 藝術的意義與市場的意義兩個自主的系統 579
第十八章 藝術的分化 595
第十九章 藝術的自主性 615
第二十章 社會的藝術 631
後記(倪爾斯.韋伯) 645
編者筆記 705
文章出處證明 709
第一章 學習閱讀 1
第二章 藝術可否符碼化? 9
第三章 藝術可否符碼化?—節錄自討論中的片段 59
第四章 時代分期的建構問題與演化理論 141
第五章 藝術的媒介 173
第六章 藝術作品與藝術的自我再生產 197
第七章 世界藝術 275
第八章 基於藝術作品所進行的感知與溝通 361
第九章 藝術系統的演化 379
第十章 文學作為虛構的實在 405
第十一章 黑洞、黑色污漬 429
第十二章 『無標題』—為什麼? 435
第十三章 藝術的世界 441
第十四章 藝術系統的分化 465
第十五章 『浪漫主義藝術...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