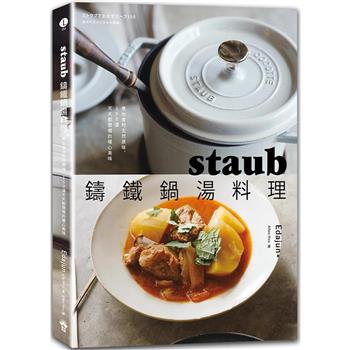尋找徐悲鴻
你知不知道徐悲鴻啊?
21世紀的某一天,我向身邊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問起這樣一個問題,人們都是不假思索地扔給我一個自己的答案。
徐悲鴻誰不知道,不就是畫馬的嗎?
哦,就是那個很早把西洋畫引入中國的人吧!
似乎不難回答,似乎又說不完全。
於是,尋找徐悲鴻就變得很有點意思了。
翻開最權威的辭典找吧。一代巨匠,靜靜地躺在《辭海》2247頁:「徐悲鴻(1895-1953)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畫家、美術教育家。江蘇宜興人。少時刻苦學畫,後赴法國留學。曾攜中國近代繪畫作品赴法、德、比、義及蘇聯展覽……」
理性,簡約,凝重,冷靜的事實陳述。能在《辭海》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是一種人生輝煌,儘管無法概括這位藝術大師的一生。
它們卻如同指示牌,引導人們靠近他。
今天,人們對徐悲鴻的名字,確實並不陌生。
上個世紀50、60年代,中國許多日常用品,類似搪瓷盆、暖水瓶、餅乾筒和各種器皿等,時常繪有徐悲鴻那超然出塵獨具風采的馬與鷹。
我記得那時家裡牆上掛著的月份牌:一天撕一張的日曆本,釘於一塊長方形的硬紙板,上面就是一匹墨筆酣暢的「悲鴻馬」。
我還記得搪瓷臉盆裡的圖案。天冷時我把手伸進熱水裡,撫摸著凹凸不平的馬的「肌理」:為啥靠近看是幾條黑墨塊,離遠點兒看卻是奔跑如風的駿馬?
沒有版權意識的時代,孕育了一個時代的奇觀。從這個意義上說,徐悲鴻早已是家喻戶曉的大眾畫家。
一位熟悉中國畫壇的加拿大畫家說,在中國,徐悲鴻畫的馬使無數招貼畫、明信片、郵票、刺繡工藝品、壁毯等受到啟發,並且時常得到未成熟的青年畫家的摹仿。與徐悲鴻的馬一起出現的唯一的問題是,人們如此經常地看到它們,以至於人們忘記了徐悲鴻除了畫馬以外,還同樣能畫其他的很多題材。
去徐悲鴻紀念館吧。
在北京我坐上計程車,司機聽我說的這個目的地,一臉惘然。我成了個引路人,把計程車引到紀念館門前。司機恍然大悟,說長了見識。
其實,專門珍藏徐悲鴻畫作以及藏品的紀念館,並不在小街小巷,就坐落在北京新街口一條主幹道上,鬧中取靜。
初來徐悲鴻紀念館的人,會驚奇地看到,在徐悲鴻塑像的背後,也就是紀念館庫房的前面,站著武警哨兵。若干年前,時任國防部長的張愛萍將軍專程來此參觀。將軍也是位著名書法家,他仔細觀看了這些豐富而罕見的藏品,連連讚歎。當他詢問紀念館的館藏狀況時,擔心地說,這麼多的國寶,沒有人守衛怎麼行!隨後,一個排的武警官兵奉命進駐,直到今天。春夏秋冬,日出日落,他們與徐悲鴻朝夕相伴。
這是大陸第一個軍人站崗的藝術家個人紀念館。
據說,至今這裡還是大陸的「唯一」。
活在孩子們稚嫩的聲音中的徐悲鴻是幸運的。
2005年5月,我在北京東較場小學三(1)班的語文課上,看到粉筆在黑板上寫出的題目「畫馬」,聽到學生齊聲朗讀這篇課文:
「四十《畫馬》:徐悲鴻是我國著名畫家、美術教育家。他一生都酷愛畫馬,以擅長畫馬而聞名,徐悲鴻喜歡畫馬,是因為他愛馬……」
2005年新版的全國小學三年級統編教材,將中國畫壇上這位無法忘卻的巨匠編入必讀課本,使這段不應斷裂的文化歷史重新得到連接。經歷了太多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人們彷彿重新意識到文化傳承對於一個民族本身的意義。
徐悲鴻一生浩瀚而博大,似乎很難讓三年級的學生完全明白。然而,將徐悲鴻編入教材的意義不僅在於訴說一段往事,更是在講述一種品格,一種風範。在種植無數夢想的少年時代,讓他們認識中國的一位文化巨人。
真實的徐悲鴻是怎樣的一個人?
似乎不成問題的問題,仍然令無數人心嚮往之。
他的妻子廖靜文寫過《徐悲鴻一生》,在大陸引起轟動。
他的前妻蔣碧微寫過《我與徐悲鴻》,在臺灣風靡一時。
她們寫出的,是屬於她們自己的徐悲鴻。
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該如何重新認識上世紀成名的徐悲鴻?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懷念徐悲鴻,他的魅力究竟在哪裡?為什麼徐悲鴻在新中國誕生時已是一代大師,以往卻總是回避徐悲鴻生存與成長的時代,以及與之交往的民國人物?
2004年,在徐悲鴻先生誕辰110周年的前夕,我終於踏上採訪之路,基本沿著這位藝術大師的生命足跡,苦苦地尋覓。
當初的想法很簡單,一個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民族的文化復興,而要復興民族文化,就不能不去找尋我們文化歷史上的那些先賢們。
很快我發現,這是一本太大的書。徐悲鴻的生命包含了如此寬廣、如此豐富的內容,幾乎勾連著一部中國近代史和當代史。比如,在先生最初的人生旅途上,他的身邊就已經站滿了歷史巨人、薈萃著一代大師。而先生早年生活在太湖之濱的江南宜興,一個鄉村僻靜之地,他何德何能,竟可以走入這樣的境界?
至於徐悲鴻與藝術、徐悲鴻與女人、徐悲鴻與這個紛紛攘攘的塵世,有著太多話題。一個已為人所知的徐悲鴻,一個仍鮮為人知的徐悲鴻,急需從光環或泥淖中抖落出來。無論徐悲鴻走得多遠,成就多大,似乎他總是擺脫不了貧寒的出身、私塾的薰陶和早年經歷所鑄就的執拗個性,這又告訴我們一些什麼?
徐悲鴻站在今人的視野裡,他還是那麼神采飄逸,魅力十足。一個被這麼多人關注乃至議論的人,本身就有著未被遺忘的榮耀。
又一次拜訪北京徐悲鴻紀念館,從這裡出發。
泱泱大國之都,名人紀念館甚多,但鮮有如此炫麗璀璨的。徐悲鴻猝然離世之時,妻子廖靜文把留在徐悲鴻身邊的1200餘件嘔心瀝血之作和1200餘件唐宋以來的名人書畫,以及徐悲鴻生前從國外收集的1萬餘幅畫冊與繪畫資料,全部無償地捐獻給國家,才使人們得以目睹這些罕世之寶的驚人風采。
這些以一位藝術巨匠特有的眼力和其畢生積蓄,苦苦收集到的藝術珍藏,是無法用金錢計算的。它們中間的很多身價,早已達到天文數字。
當你仔細觀賞面前這些藏品的時候,會有一個發現,在一些徐悲鴻格外珍視的藏畫上,蓋著一方專門的印章,題有四個字:「悲鴻生命」。
何為「悲鴻生命」?
也許在徐悲鴻的眼裡,生命即為藝術。
上帝並沒有特別眷顧徐悲鴻,依然讓他飽受磨難和憂患。
與常人不同的是,當這位偉大智者以藝術眼光,看待自己走過的人生之路的時候,痛苦變成了收穫,坎坷轉化為資本,給一個普通的生命注入了活力,苦苦掙扎的平凡生活,也就變成了一條追求與理想的康莊大道。
「悲鴻生命」,一把開啟大師心靈的鑰匙。
於是,我注定無法去說一個關於文人雅士的孱弱經歷。
我想說的,其實就是一個在上海灘餓得想要自殺的貧困小子,一個在人生與藝術的海洋中不斷尋覓的美術青年,鐵著心去打拚天下的生命故事。
一個外國友人把徐悲鴻叫做「中國鴻」,是他想像中的一隻大鳥。「中國鴻」是怎樣起飛的,又是怎麼越過千山萬水,飛向一片理想的天空?
讓我們一起,跟著徐悲鴻上路吧。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