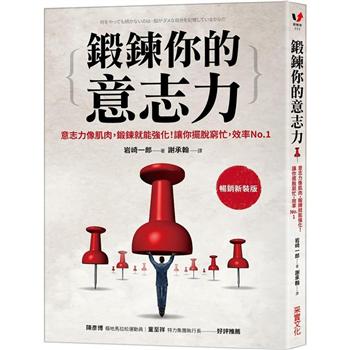「史上最精采的追獵故事。」─《時代雜誌》
逃亡的狂徒、地底的藏身處,
以及與大地之間的神秘聯繫。
★本書被無數媒體譽為英國經典驚悚小說(The Classic British Thriller),《故道:以足為度的旅程》英國作家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為其撰述深入評析。
★本書於一九四一年即由德國名導演佛列茲.朗(Fritz Lang)改編為電影【追捕】(Man Hunt),其後多次改編為電視,包括一九七七年BBC電視電影版本,由【阿拉伯的勞倫斯】主角彼得.奧圖(Peter O'Toole)主演;新版電影預計由班奈狄克.康柏拜區(Benedict Cumberbatch)製作與主演。
二十世紀經典驚悚小說之一
「一部刺激又深入刻畫的作品,原因在於其描寫心理層面之細膩,以及緊張情節中那些雋永的語言刻劃。」─《時代雜誌》(The Times)
「作者將一則懸疑故事帶入了藝術的境地。」─《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一個經典的懸疑故事。」─《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緊張懸疑,大膽鋪陳……戰後小說的高潮,絕對的經典之作。」─《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本書絕對足以成為一部經典。」─《週日郵報》(Mail on Sunday)
故事背景發生於一九三○年代,歐洲政局詭譎,戰爭一觸即發。一名英國獵人密謀暗殺歐洲某國獨裁領袖,卻在最後一刻事跡敗露而落入敵軍手中,慘遭刑求審訊,終在敵人的策劃失誤中生還,展開跨國界脫險行動。獵人無從獲得政府援護,被迫離開社會,在環境嚴峻的鄉間繼續逃亡,他必須擺脫身份與文明的束縛,以生存本能支撐自己—獵人已然成為被追獵的野獸,在他為自己挖掘的洞穴裡重生。
本書為具有哲學性的懸疑故事,當獵人面對土地、萬物之互動牽引,彷彿生命與自然的融鑄與辯證,為跌宕起伏的情節,增添了雋永的詩意。特別在追緝與逃亡、光與暗、搜索與隱藏等等各種二元對立的情節下,無論動作、認知與記憶,皆能巧妙將正反方做出對位情緒轉換。作者以精準篇幅描述了一場懸念充滿的獵逃,更處處顯見文本核心—偽裝與掩護之堆砌,從角色動機到身份與去向,藉由節制的文字,營造高度張力,除了絕佳的驚悚橋段,對於暴力的誘惑、生存心理與野性意識的探索,亦是成為不朽經典之因。
作者簡介:
傑佛瑞.豪斯霍德 GEOFFREY HOUSEHOLD(1900-1988)
生於英國布里斯托(Bristol),在牛津大學默德林學院(Magdalen College)接受教育。曾遊歷東歐、美國、中東與南美等地工作,主要任職於銀行。豪斯霍德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於英國情報單位服役,另有作品《A Rough Shoot》、《Watchers in the Shadows》、《Rogue Justice》與自傳《Against the Wind》。
譯者簡介:
李昕彥
荷蘭鹿特丹大學文化經濟碩士,現旅居德國,從事中英德口筆譯。
章節試閱
其實,我也不能怪他們。畢竟,誰會一邊拿著望遠鏡,一邊獵殺野豬或熊呢?因此當他們發現我隔著五百五十碼的距離窺視那座露臺時,當機立斷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至於他們的作為,就我個人的看法來說,其實相當謹慎了。我並不是那種囂張的叛亂或狂熱分子,而且看起來也不像是熱衷政治的人。或許我曾參與過南英格蘭農業選區的一些活動,不過那實在也說不上是什麼政治活動。我本身持有英國護照,假如我今天是在光明正大走向那間宅第時被發現而非在窺視行動中被活逮,那麼我還可能受邀一起共進午餐。
這些人肯定懷疑我背後的動機——或許是官方指使的任務?不過我認為他們排除了這個可能性。沒有任何政府會鼓勵刺殺行動——至少我們這些國家不會如此。那我會不會是個傭兵呢?看起來也絕對不像,任何人都看得出來,我不是那種訓練有素的殺手。那麼,是不是所有犯罪動機都已經排除了呢?正如同我的口供一樣——我就是個面對千載難逢的機會,而無法克制自己的獵人?
經過約莫兩到三小時的訊問之後,我發現他們已經動搖了。他們不相信我的說詞,儘管他們已經漸漸理解,一位閒來無事又富裕的英國人,他在獵過所有平民水準的獵物之後,確實會對這世上最大的獵物產生一種偏差的熱情。然而,縱使我的陳述不假,而那不過就是一般的打獵活動,這樣也無法改變他們的看法。他們不能放我一條生路。
當然,我在這個時候已經遭受相當程度的凌虐了。儘管指甲已經長回來了,但是左眼仍猶如塵垢秕糠。我這樁並不是什麼可以道歉了事的案子,而他們或許早就幫我舉辦過一場別具一格的葬禮了,獵人成隊對空鳴槍並高吹號角,所有名流都盛裝出席我的葬禮,最後再立座石碑紀念這位親愛的獵人同志。他們很清楚該怎麼安排這些事情的。
結果呢,他們卻辦事不利。他們帶我上懸崖邊,讓我雙手掛在峭壁上——動機非常狡猾,因為岩石上的抓痕幾乎可以說明一切——當人們發現我的屍體時,只要看到我的手指就知道答案了。當然,我撐不了多久,至於實際上撐了多久我也不記得了。我不懂當時自己為什麼這麼不想死,眼看自己求生不得,那麼不如早死早解脫——不過我就是不想死。畢竟願望常在——如果求生的執著也算是種願望。由於我個人過於文雅之故,那種野兔因為野鼬在後而拔腿逃亡的動力,實在對我也無法造成影響。野兔的心中沒有願望,我是這麼認為的。野兔沒有未來的概念,但是牠會逃跑,而我也想堅持到最後一刻。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生是死?我向來相信人的意識在肉體死亡之後仍會延續下去(儘管我對於會持續多久並沒有特別的看法),因此我以為自己應該是死了。經歷了那樣一段時間的墜落,我絕對不可能還有辦法活著,而且當時那瞬間的痛楚是如此地劇烈。我覺得大腿後側與臀部已皮肉分離,不管是挫傷、撕裂傷或刮傷都不重要了。顯然大部分的身體組織已不由我,也無法挽回。
我腦中閃過的念頭是但求一死,因為我沒有辦法想像自己如爛泥一般地苟延殘喘下去。我的周圍盡是軟爛的物質,我就這樣帶著荒謬的意識躺在裡面。我本以為這灘沼澤正是我殘破的肉體,挾帶著血腥的滋味,然後我才意識到身旁這軟泥般的部分可能真的是一灘沼澤,而我不管摔進那兒都會帶著血腥的滋味。
果真是摔進一灘爛泥之中,範圍不大,卻很深。好了,我想自己應該還活著——目前還活著,也就是說,我不確定自己還能夠這樣活多久——因為我看不到,也感受不到自己究竟傷得有多重。當時天色昏暗,而我早已全身麻痺了。我抓著一叢雜草將身體拉出爛泥沼中,猶如一具泥做的生物,束縛在泥巴之中。泥灘旁是一堆突起的碎岩,顯然我與其擦身而過。我已經感受不到任何痛楚了。我說服自己受傷的程度並沒有比當時掛在懸崖上更嚴重,因此決心要在他們下來搜尋我的屍體前離開。
儘管當時不是很清楚,不過我確實有充分的時間可以進行這些事情,因為在我的屍體僵硬並出現證人之前,他們並不會下來尋找我的屍體。這位不幸的獵人同志會在意外的情況下被人發現,屍骨健在,而一切全然是命運的捉弄——懸崖上的意外失足事件。
懸崖腳下是一片林地,除了那些稀疏或濃密的錯落影子之外,我也沒有其他印象了。腦海中的印象相當模糊,那也許是樹林或雲朵,也或許是海上的波浪。我大概徒步走了一英里路,最後選在一片濃密的樹蔭下昏厥了過去。夜裡數度恢復意識,但是又立刻昏了過去。當這險巇世界再次出現在我眼前時,太陽也即將升起。
天色破曉時,我試著想要站起來,結果只是徒然,而我也不再嘗試了。任何運用肌肉的動作都會與我身上那爛泥包覆的肉體相牴觸。每當一塊泥巴落下,我就會開始淌血。不了,我當然不想跟這些泥巴作對。
我知道水源在哪裡。我從未看過那條溪,而心中對於方位的堅持也許是來自地圖在潛意識中留下的印象。我知道水源在哪裡,因此就朝著那個方向過去。我趴著移動身體,雙肘代替雙腿——彷彿是一隻受傷的鱷魚,泥濘與血跡是我遺留下的蹤跡。我並不打算下到溪流中——我絕對不會洗掉身上的泥巴,因為我很清楚,那些泥巴正包覆著我的腸胃——但是我得爬到溪邊才行。
這是野獸在遭受追殺時的思考邏輯,不過,也許這一點邏輯也沒有。我不知道那些平常久坐不動的鎮民們是否也會這樣想?如果他們受到相當程度的傷害時,我認為他們也會這麼想。人必須要被傷害到幾乎從人間蒸發的程度,才會停止思考自己該做什麼——反正做就對了。
我讓自己留下的痕跡看起來像是爬進溪裡一樣,其實我只是爬到溪邊喝水,然後翻身躺進一灘大概兩吋高的淺灘中,我在泥中打滾也不會留下任何痕跡。他們會從我昨夜的棲身地一路追查到溪畔,而離開水面之後的行動就不得而知了。
我心中則是相當篤定自己的去向,而且這個決定完全要歸功於我務實的祖先們。野鹿會溯溪而上或下,離開水面時的痕跡都逃不過獵捕者的視覺或嗅覺;猴子就不會出現類似的行為,反而會模糊自己留下的蹤跡,然後消失在第三度空間。
我翻身躺進那片淺灘後,然後又蠕動回來——沿著蜿蜒的路徑來回蠕動著。要追蹤其實很容易,那看起來確實就像是一條鄉間小徑,我的臉不過離地六吋高而已。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他們在追蹤我到溪邊時並沒有發現,路上某些雜草倒塌的方向不太對勁——那代表我肯定又回到同一條路上了。誰又會想到這件事情呢?人在爬行時所留下的痕跡根本沒有任何規則可言——而誰又會在這荒郊野地的路徑留意這些細節呢?
我離開時的爬到了落葉松下,地質相當柔軟,而且完全沒有矮樹叢。我接著翻過其中一棵樹的樹幹,我的意思是自己攀了上去。最低的枝葉離地大概兩呎高,其上一層又一層,散發香氣的煤黑枝葉就像階梯一樣向上堆疊。我的雙手都還能使力,至於外觀已經不是我可以擔心的事情了。
當我爬過一個人的高度之後,我還不敢將靴子踩上枝葉,因為這樣會留下明顯的泥巴痕跡。我一口氣爬了十呎高——我心裡知道自己在分枝上停留越久,就越沒有力氣爬到下一個高度。那僅是強制左右手交替工作的三十秒時間——天曉得是什麼樣的潛在動力在推進這兩個活塞交互運作。我的朋友們總愛說我恣意濫用自己的體力,他們一點也沒錯。只是我萬萬也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有辦法說服自己發揮這樣的爆發力並爬上這棵樹。
接下來就容易多了,我現在可以用雙腳支撐身體的重量,每次抬起腳之前也可以隨心所欲,想停就停。我的雙腳並不是沒有力氣,只是沒有辦法移動。沒有任何殘缺,我不可能掉下去的,因為我身處在一棵多葉樹木的枝葉之中。當我繼續往樹頂上攀爬時,樹枝就變得更密、更細又更綠,然後我就卡住了。這樣對我再好也不過了,所以我又昏厥了過去。這樣實在是太奢侈了,幾乎是種罪孽。
當我恢復意識時,那棵樹正在輕風中搖曳著,空氣中竟是一陣平和。我覺得非常安心,因為我當時根本沒有這樣的期待。我彷彿就像是樹上的寄生蟲,在此紮根了。我既不覺得痛,也不會餓,也不會渴,我覺得好安定。眼前流逝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會對我造成傷害,我只與當下打交道。倘若心中有所期待,那麼我就會感到絕望,但是對於一隻被追殺又正在休憩的哺乳動物而言,感受到的就不會是絕望,而是希望了。
當我聽見搜索隊的聲音時,時間應該剛過中午不久。我在樹上看見他們從北邊的斜坡上走下來,當時的陽光刺眼,因此他們不可能發現我正推開柔軟的樹葉俯看著他們。我知道自己的雙腿並沒有在流血,否則落在下方枝葉的血滴就會是暴露我隱身於此的線索。雙手留下的淡淡血漬,只要有人仔細觀察就會曝光,不過那個位置是在樹中間不明顯的黑色枝幹上,不是什麼顯而易見的景象。
三位身著制服的警察正在山坡上踩著沉重的腳步走著——這些魁武又嚴肅的傢伙正頂著陽光行動,身後則跟著一位看似輕鬆並身穿便服的男人——他像條狗似地探查我所留下的路徑。我認得這個人,他是在那宅第中第一個訊問我的探員。他採用非常卑劣的手段逼我招供,而且早在其他同僚提出異議之前就已經動手了。他們反對的並不是他的手法,而是想到必須保我全屍才行,而且絕對不能出現任何不合理的殘缺截肢。
他們走近時,我可以聽到他們片段的對話內容。那些警察相當急著想要找到我的下落。他們對於實情毫無所知,甚至不清楚我究竟是男或是女,也不知道眼前是樁自殺或謀殺案。訊息拼湊之下,我發現他們被告知有人在夜裡聽到慘叫或是墜落的聲響,然後,他們就在那位探員的帶領下找到我的背包與在那灘泥濘中留下的混亂痕跡。我自然無法掌握當時的情況,只能透過那些印象拼湊眼前的情勢。我已經與那棵樹合而為一並感受到大自然的宏偉,然後一邊聆聽這些人的對話內容。當我理解他們對話中的含意時,已經是後來的事情了。
那位探員看見我留下的爬蟲類蹤跡消失在落葉松樹林下,他開始興奮地發號司令。他似乎相當確定我就在那片樹林之中,高喊要另外三個同僚繞到另一邊,以免讓我逃走,而他自己則是爬進低矮的枝葉。他大張旗鼓地展開行動,因為我可能正在迫切地等待救援,而他想要親自找到我。假如我還活著,那他就得巧妙地結束我的生命。
他快速穿過我所在的樹下,然後走進空曠的草地上。然後我聽到他的咒罵聲,因為他發現我並沒有在那片林地裡停留。其實這樣的判斷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畢竟我以為溯溪才是晨間出發的途徑。
然後追捕活動就停止了。幾個小時後,我聽到溪邊傳來一陣匆忙踏水的騷動。他們肯定是在水塘裡打撈我的屍體,雖說這只是條淺淺的山澗小溪,但是激流的力道足以滾動一個成年男人,直到撞上岩石或捲入漩渦之中。
夜裡,我聽見狗吠聲,我真的很害怕,於是開始發抖——痛楚再度襲來,痠痛、刺痛與抽痛,疼痛集合成樂章,全身上下的各個部位都隨著心臟跳動在消磨時光,音調時準、時不準,或是落了半個小節。我終究是活了下來,感謝那棵樹的療癒。那些狗或許已經發現我了,只是牠們的主人,且不論是誰,完全沒有理會牠們。他並沒有浪費時間讓這些狗去追蹤那些他自己就可以完成的路線,他在那條溪的上游與下游間不停地來回溯著。
夜幕低垂後,我從樹上爬了下來。我可以站起來了,藉著兩根樹枝的輔助得以緩慢地向前移動——拖著無法擺動的雙腳與僵硬的雙腿。我也可以思考了,過去那二十四小時的心理活動都稱不上是思考。我放手讓身體作主,說起逃亡與療癒,身體知道的比大腦還多。
其實,我也不能怪他們。畢竟,誰會一邊拿著望遠鏡,一邊獵殺野豬或熊呢?因此當他們發現我隔著五百五十碼的距離窺視那座露臺時,當機立斷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至於他們的作為,就我個人的看法來說,其實相當謹慎了。我並不是那種囂張的叛亂或狂熱分子,而且看起來也不像是熱衷政治的人。或許我曾參與過南英格蘭農業選區的一些活動,不過那實在也說不上是什麼政治活動。我本身持有英國護照,假如我今天是在光明正大走向那間宅第時被發現而非在窺視行動中被活逮,那麼我還可能受邀一起共進午餐。
這些人肯定懷疑我背後的動機——或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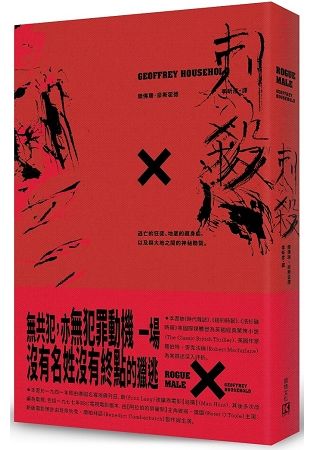

 共
共  2018/02/07
2018/02/07